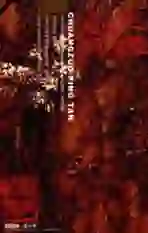在新疆再识朱向前
2004-03-23朱寒汛
朱寒汛
朱向前是我的父亲,没有什么人比我观察他的距离更近,我们曾共同生活多年,想不仔细观察他都困难。他似乎在一篇随笔中曾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我虽然乐于接受,但这毕竟可以说是朱向前的一厢情愿,因为这不是事实。当然我们的父子关系还挺好,这一点我下面说。
朱向前的作品我没怎么读过,就不说他在文学评论上的造诣了,要我说我也说不清。我的目的就是描绘一个血肉淋漓的他,反映他的一些特质或秉异。在别人眼中,提到朱向前大概可能是这样一组词汇:乐观、正直、自信、幽默、敏锐、思维缜密、健谈、善辩、有激情、富有感染力。这都是他的公众形象,在家里时不可能完全相同,他似乎能从语言的一种琐碎中找到别人难以理解的隐秘和快乐,即使在家也很健谈,天马行空,出语惊人。另外,他喝一点用乱七八糟的药材泡的小酒,自斟自饮,心满意足;也常在酒后练书法,原来是兰亭序,现在是苏东坡,一纸书成,左顾右盼,踌躇满志;养点花草,修枝剪叶,用一个喷水珠的塑料壶湿一湿叶子,情深意长。现在,他常常打乒乓球打到深夜,据说是为了减肥,但实际上“已从一个专业文学批评家堕落成了一个业余乒乓球运动员”(朱向前语),总的说来,我感觉他的确有点像他心仪的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固执、多嘴、口无遮拦、妙语连珠,看到不顺眼的事一定“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好奇、有深度、单纯真挚、讨厌装腔作势。
朱向前热爱旅游,喜欢自然。他讨厌束缚和现代化,不爱人造的安逸舒适,要回归自然,要到野地里走走。他的思路我基本理解,他时常抱怨现代工业对自然资源的摧残和滥用,电视上报道的省时的、高效的技术常赢得他的诅咒。他拒绝学电脑,拒绝学会使用任何操作稍微复杂的电器。他的观点有点极端,简直恨不得倒退500年,骑着青驴四处行走,做一个贾岛式的行吟诗人,我基本赞同他,但有时听他说得太偏激了,也嘲笑他:没有现代化,你得个盲肠炎弄不好就会死掉。他鄙夷地看着我:胡扯,漫山遍野都是草药!显得很不以为然、,而他的确有老来归隐山林的愿望。
我有幸几次陪同他去旅游,其中动作最大的两次是去西藏和新疆。西藏之行是在1996年,我屁大一点,记不清楚什么了,新疆是去年夏天去的,记得比较清楚。新疆是个好地方,空气清新,温差巨大,爱憎分明,风情万种。我们最初是从乌鲁木齐到那拉提草场,新疆真是大,经常是车开了几个小时还看不见人,只有灰头土脸的大货车拉着不知什么货物从我们对面呼啸而过,而我们乘坐的桑塔纳2000实际并不适应某些地段颠簸的路面。下午七八点钟的太阳还把车内营造成了一只蒸笼,龟裂的荒山、荒芜的野草,干燥的龟裂好像延伸到我的大脑里,心烦。一天下来,我们终于鸠头鹄面地来到那拉提,神销气索,四肢酸痛,下车我才发现原来站起来是那么舒服,理应长时间承担重量的是双脚而不是屁股。那拉提草场位于天山南麓,群山山脉下绵延一系碧草,近景远景错落有致,狂野的风从四面吹来,撩得人心惶惶。下车经行一处吊桥,通过一条寒气袭人的急流,进入一丛密林,有古木森森,树皮斑驳,跟惨白的河滩一个颜色,气象森严。走到这里时,我们的疲惫和焦灼早就没了,都变得很兴奋,诗人黄毅叔叔摆出专业摄影家架势,频频拍照,朱向前到此一游。
骑马。一路上,我们幻想了无数策马狂奔的景象。傍晚时分,一人一骑,一黄一黑一白,出现在幽暗的山道上。马的健硕优雅的优态使我浮想联翩,白马饰金羁,翩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哥舒夜带刀,矜夸紫骝好,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等等一些个名句乱七八糟地蹦出来。几个游侠在徘徊,寻找一个苍老的仇恨、一种高尚的感情使我激动得浑身乱颤。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若明若暗,豁然开朗,我们大声喊叫,静听着嘶哑的回音。他用鞭子轻拍坐骑的后臀,显示出一种没有必要的温柔,左右摇摆,像是困了。在摇摆中我的脑海浮现一个经历过的场景。那是在我的幼年,四岁小一点,那时的记忆模糊一片,没有什么条理。平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朱向前在北京工作,寒暑假回来住上一段。有一回他送我去幼儿园,时值南方阴雨季节,空气里湿得能捏出水来,即使不下雨,耳边也好像总是由远及近地传来滴滴答答的水声,水泥路两边的宿舍都是低矮的砖瓦房,整个环境都罩在一片青苔里,好像所有的事物都是从青苔里长出来的,一簇簇青苔水分充足,结构精美。我们在乎整的路面上行走,周围没有人,速度很慢,慢得我的记忆在那个地域定格,甚至只有周围的环境而不存在我们两个人,我们很高兴,我们都喜欢那种天气。他那时年轻,瘦得像匹狼,穿一件肥大的黑色风衣,领口竖起,裤子的裤线笔直,他的穿着总是这样,喜欢整洁到了洁癖的程度,胡子也刮得很干净,总很认真地洗脸。脸色阴沉,大概和长期的熬夜和抽很多烟有直接关系。但他的眼睛很亮,我至今很少看见这样的眼睛,尤其是他抽烟的时候,好像是远眺,又好像是凝视近处的某个东西。他不经意地看了一下四周,确定没有人,就突然捧起我举过头顶让我骑在他的脖颈上,并且呵呵笑了起来,脚步夸张而凌乱地行走,几步一退。我当时是个胖子,体型臃肿,行动缓慢,他的举动迅速打破了我习惯的动作频率,让我惊慌失措,好像胯下不是一个人的脖颈而是一匹癫狂的野马,头晕眼花但很刺激,过一会就笑了起来,他是极端爱整洁的一个人,小时候我总是胸前鼻涕浑身灰土从正面或侧面冲向他,以期他把我抱起来,哪怕能抱住他的大腿。可是他的态度冷淡,极少抱我,就连让我抱他的腿也是很困难的,他较我高大得多;就身体前倾双臂伸直按住我两肩保持我们之间的距离使我就范。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对骑在他脖颈上的事记得那么清楚,因为他和我的亲昵动作实在太少,绝对屈指可数……人项马背,江南西北,恍如隔世,幸甚至哉,好一阵胡思乱想。
晚饭是在一哈萨克兄弟家吃的,羊肉的膻腥味我已经记不住了,天涯海角,哪里没有羊肉呢。但有一个我记忆深刻的细节值得一提。大概是傍晚九点钟,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穿过几团暮云很匀称地洒在草原上,天山来风,一个轮廓浑圆的世界近在眼前,没有废气,没有塑料和噪音。我想这片草场和几千年几万年以前都没有太大差别。惟一不同的是牧民们拉响了柴油发电机,桔红色的灯光从帐篷上“田”字型的窗口里散开。眼前一个面色红润、身体健壮的三岁左右的哈族小女孩用一个几乎是她身体一般大小的铜壶洗手,打上肥皂,神情专注地搓,搓了足有七八分钟。我注意到他专注地看着那孩子,一边看一边笑,好像没什么更让他高兴的事情了,把烟从鼻孔里嗤出来,后背像咳嗽一样震动。他笑得真开心,没有心机、没有忧愁和苦恼,像一个孩子一样没心没肺地笑,像傻子一样,和人们想像的大有出入,在私下场合朱向前其实挺爱笑,他的脸上常常挂着笑的,不管失意或得意,以至于我不能相信有什么事能彻底击倒他,让他笑不出来。同时他又爱哭,真极端。我们一家在看电视的时候,每次看到较为感人的节目,譬如介绍命运悲惨而自强不息的人,学习成绩优异而不得不辍学的农村孩子,某个地区或少数民族的偏远和落后……他打哈欠,伸懒腰擤鼻涕点烟和被尘土迷眼睛的机率特别高,其实那都是偷偷地抹眼泪,但动作笨拙,眼圈通红,长吁短叹,好像很不耐烦。我和我妈也都很感动,但决不盛产泪水,当然他哭我们心照不宣——掩饰得太拙劣了,欲盖弥彰。一家只默然,难道我还趁机嘲笑他多愁善感?这些时候,我感到他天真烂漫,最能引发我亲近他的愿望,就像亲近一个被人痛打了一顿的小孩。一哭一笑,收放自如,那拉提的夜晚,天山明月,繁星满天,我睡得很实。
回到乌鲁木齐市那天晚上,韩子勇叔叔来为他送行,朱向前告诉我来作陪的是一位大人物。谁?周涛。我一听很激动,周涛先生当然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大人物,巨笔如椽,我年纪轻轻十八九岁就见到他并有幸认识了他,真是没有白活。韩子勇叔叔的评论我也看过,文字漂亮,也是我一辈子难以达到的水平。当天来的还有散文家刘亮程、北野、黄毅、周军成等几位叔叔,都是人物。那大概是我参与过的最“牛逼”的饭局(没别的形容词可用了)。周涛先生跟我握手,还送我两本书,激动得我不行。他红光满面,两眼炯炯,真是人中俊杰。周涛、韩子勇、黄毅、北野、周军成诸君都很能喝,基本上是喝不醉的,黄毅叔叔全程陪同我们,天天晚上小酌,他都是二比一轻取了朱向前。朱向前有什么量,至多也就是三两半,再加上一周来日均800公里行程的劳顿,他大约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就醉了。
我当时没想到他早已做好大醉一场的准备,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义无反顾、慷慨赴死的貌似豪爽。他醉得不但快而且很突然——刚开始的时候他的音量最大,谈笑风生,妙语连珠酒到杯干,既不推托,也不敷衍,扎扎实实地喝,而且喝得很痛快很受用的样子,还不时哈哈大笑,好似刚干了一票的梁山好汉,大家不停地拍手称快。然而很快他就开始舌头发硬,措辞也单调而匮乏,聪明、机智和幽默感都醉没了,他只能一边拍着周涛先生的大腿,一边反复说两进新疆是受到周涛美文的影响云云。周涛当时说是一点也没事也未尽然,但是绝对没醉,脑子清楚得很,他对向前的话起先是回应,还谦虚,然后返回来赞扬向前,然后就面带微笑,表情专一,什么头衔都默默接受——他发现朱向前已经醉了,什么话都进不了耳朵,也就没有说的必要了。
最后,朱向前不说话了,别人的声音大起来,他沉默了,脸色灰白,把玩着酒杯发呆片刻,突然把杯子一推,就势趴在酒桌上。事实证明他喝得太醉了,我认为那是他有史以来醉得最迅速最严重的一次。他被黄毅周军成提前架回了房间。我坚持到了结束,当时我也醉了,周涛先生说我是京都少年,有乃父之风,我就以为自己是咸阳游侠,能不喝吗?等我回到房间,他成一个“大”字形趴在床上,哼哼唧唧,气喘如牛,不久又吐了一次,真疯狂。后来我躺下,他吐后稍稍清醒了一点,我们就胡乱地说话,感觉自己的声音大,别人的声音小,可见全是大喊大叫。但大意我记得:他说能受到新疆众多文友的隆重接待和尊重,深受感动,也有一种成就感。我呼应说这帮人是我见过的最够意思的人。他又说要我努力,要看到做人的艰辛,为自己的人生而奋斗,他对我还抱有希望,说:“你现在条件太优越了,我那时候哪有那么好的条件,要是让我好好读书,我早念到出国留学,回来做学问,弄不好就是当代陈寅恪、胡适之。”我说没关系,上阵父子兵,自有后来人,其实我当时很惭愧,就哭了,真的,在学业方面,我伤了他的心。我没有认真学习过什么东西。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胡说八道的场景我必将终身不忘,至少现在想起来还像昨天的事。那天的交流也是我们之间最酣畅淋漓的一次,至少对我来说是,也是惟一的一次公平较量,甚至在语言的交锋上我占了上风。根据我的回忆,他的嘴里总能跃出一些锋利的物质,极能刺伤我,不光是我。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细节,就是他在文学系当老师的时候,有他的学生来家做客,有时是女学生,本来是喝水、讨教,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她们就稀里糊涂地哭,很伤心很内疚的样子,然后狼狈地走路,而且这种情况还不时发生。我当时深深地地同情那些阿姨,她们提着水果来,受了一肚子委屈回去,满腔热忱来,垂头丧气走,真是倒霉蛋。现在分析,朱向前肯定是批评他们的作品了,他批得投入,毫不留情地揭了人家比较致命的弱点,措辞尖刻,而且穷追猛打,恨不能致人于死地,女人的心房比较柔软,会搞文字的女人又习惯生活在赞扬中,能不哭么。但他还总是很不识趣地说下去,实在是一种愚蠢了,简直不可理喻。她们是不习惯,我皮糙肉厚,感官迟钝,他说得激奋,我听得恹恹。不过人们称他“酷评”由此可见一斑了,但他以工作态度来教育儿子的做法值得商榷。不过在此时此地的互发酒疯中,我浑沌中感觉到了一个真实的他以及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他作为父亲对我的感情。他对待真心的朋友,好像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辞穷,一定要喝酒,一定要喝醉,喝到吐为止,甚至吐完再喝。这当然须要酒量,但更需要真诚激情和胆量,醉后狼狈不堪的模样他也清楚,但他毅然地喝,畏畏缩缩,逡巡不前不是对待朋友的态度。第二天他醒来还是脸色铁青,目光黯然,中午周涛先生正式作东为他饯行,没喝两杯即罢。我看不喝是对,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大约都明白酒肉争逐是一种无聊,同样是一种虚情假意。
回京以后的一些日子里,我有时不由自主地回忆和朱向前一起的一些事情,感觉似乎开始真正对他有所认识。在生活的旅途中,他蒙着个冷峻的外壳一脸严肃苛刻,也许是他害怕暴露敏感多情的自我受到无端的伤害。他似乎用一双儿童的眼睛来观察世界,以儿童的直觉和判断力来对周遭的一切进行褒贬,他努力追求生命里的一些冲动,不知是在捍卫还是在挽留,就是这样一些零碎的小事常常打动作为儿子的麻木的我。童年的经历大概是他的精神家园,和他业已丢失的敝帚自珍的儿时作文、在抄家中流失了的几枚珍贵的毛主席像章、了条黄狗和一只八哥的野冢一起埋藏在赣西一隅某处墙角的红色泥土里。我也有相似的经历和童年的记忆,但相比之下他的要深沉艰辛得多,而他始终不曾背弃。所以我越发地喜爱他,不停地发现一个反常的他,被他搞得神经兮兮。
以上的话,我是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写下的,措辞也一反我的作文风格,但是请相信,遣词造句的手法可以改变,我的真心却不会变。表达三点真心的感谢吧:第一,感谢他把我带到这个人世,没有他就没有我,在别的世界里我不可能咀嚼到人世间的种种快乐和痛楚;第二,感谢他养育了我,使我在一个优良的环境下好吃好喝地长大,十几年精心呵护一朝成人,这其中的辛苦和普天下的父母没有二致;第三,感谢他深深的影响了我,使我接受并爱上了文学,成为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文学痴迷者,并帮我弄到了莫言、周涛、阿来等一些一流作家从四面八方邮来的指名道姓的亲笔签名书,使我成为了全中国最幸福的文学青年……
好了,打住。谨以此文献给朱向前人生的第五十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