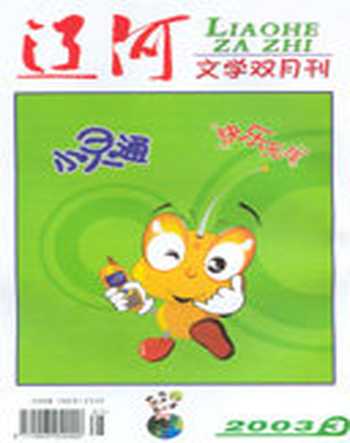访谈——访青年作家闵凡利
2003-04-29
本刊:近年来你在文学创作上收获颇丰,特别在小说创作上可谓是硕果累累。对“新禅悟小说”的构筑和开拓,你可是费了一番心血。有人曾把你说成是“新禅悟小说”的掌门人。对此你怎样看?
闵凡利:(笑)这个话曾有文友给我说过。当时我觉得很可笑,乍一听,我跟江湖侠客似的。首先我得声明,我不是掌门人。
本刊:你能就“新禅悟小说”谈一谈吗?
闵凡利:所谓“新禅悟小说”就是以佛道中人的故事为背景,通过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的追溯,展示生命的禅机和玄妙。佛道中人,虽然他们遁入空门,自称是出世之人,其实他们更入世。身在红尘中的我们,由于受权、色、贪等各种业障的侵扰,浮躁轻佻,急功近利,一点也不能静下来思考自己今后的家园和归途。因为这是一个拼命旋转的时代,人人都如飞驶的螺旋,只有旋转才会站得更牢。佛门中人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特殊一类人,他们是被尘世抛弃或者是厌恶尘世的,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但有的是漫漫的时间和长长的岁月。他们能用这大块的时间来静静地思考人自身的来去归还问题。他们的思考能让我们焦灼的心田得到滋润,能让我们凄冷的心间得到温暖。他们能给我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能让我们好好地反刍自己,思索自己。
本刊:你所说的佛门中人,实际上是更入世的啊!
闵凡利:对。每一个远离红尘的人,他们之所以放弃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其实都有着一段刻心铭骨的凄惨故事。他们无疑是这个尘世的逃避者,无论是为情、为欲、为爱,最终他们选择了离开。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无奈。在清灯伴佛的日子里,他们在不停地拷问自己:自己为什么错了?究竟错在哪儿呢?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本刊:就是这些拷问,其实是给我们现实中的人们提供一种信息,提供一种答案。就是尽量的少走弯路。
闵凡利:人的生命本就很短暂,也就三万多天的光景。人们活不过一株草。一棵树。人是不能走弯路的,人生是不容走弯路的,更别说犯错误了。
本刊:你对这些的思考就体现在你的小说《神匠》(《天涯》1996年第六期)、《魔人》(《莽原》1997年第三期)、《三个和尚》(《大家》2000年第六期)、《行路的和尚》(《岁月》1999年第四期)、《木鱼里的天空》(《大家》2002年第三期)、《杀手时代》(《红岩》2002年第三期)、《拣石记》(《青年文摘》2002年第一期)等小说上。对吗?
闵凡利:还有《寻剑》(《西南军事文学》2002年第二期)、《葱儿》(《当代人》2000年第六期)、《小呀小姐姐》(《飞天》1997年第六期)、《东张西望》(《时代文学》2000年第四期)、还有你们《辽河》上刊发的《一只走出屋子的猫》。
本刊:问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什么叫小说?
闵凡利: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先说一下什么叫大说。因为小说和大说是相对的,知道大说是什么,小说也就迎刃而解了。我认为,大说是统治者或权威者的说话。他们是当政者,说的话自然管用,人们爱听。当然,不听也得听,没办法不听。这些话就是大说。因为他们的这些话能成为指导和规范人们意识和行为的一种准则,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法律和法规,成为我们所必须维护和遵守的条例、命令和文件。
相对大说而言,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人微言轻,所说的不光不能指导人民的生活,而且也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老百姓很明白,他们叫小人物,所说之语自然就是小说了。他们的说话的作用只有自娱自乐,以博一笑。说到底,小说就是小人物说话。说一些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幻所忧,小人物不求什么,只求能说出来,能倾诉出来,这也就够了。后来,小说就成了一种文学体裁。《现代汉语小词典》(1983年修订本)上对小说是这样解释的:“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的矛盾。”小说就成了叙事的艺术,就成了语言的艺术。其实,这是小说的悲哀,因为任何一门学科始于哲学而终于艺术。比如京剧。比如书法。
书法就是写字。以前人们没有比较先进、方便的书写工具,毛笔这一简便的工具就承载了事情、语言等的记述工作。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逐步提高,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人们的书写工具得到了更新换代,现在已进入到了无纸化办公时代。只要有一台电脑,你就什么都有了。书法已越来越被人们所忽视,只能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下来。
本刊:你的潜台词是否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述方式。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已进入网络时代,网络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层面上的思考。特别现今这个阶段,对享受精神生活的人们来说,影视的速食性和直接性对懒于思考而喜欢享受快餐文化的人们来说已成了一种必然。
闵凡利:影视作为一个时代的表述方式,比起书面的小说受众面要广阔得多。最明显的一点,读小说得有文化,而看电影、电视根本什么都不需要。但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影视的所需要的母体大部分还是来自小说。她只是小说的另一种展现方式。而毛笔和电脑它们是一种工具的进步,只是电脑比毛笔在使用上更方便、更快捷、更先进、更能跟得上时代行进的步伐。
本刊:照你来说,文学不会消亡,小说不会消失。
闵凡利:最起码来说,在现阶段,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商品是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的。因为人们已意识到文化的商业价值,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正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经济价值。作为精神层面,文学就是一种食粮,只要嘴巴存在,粮食就有市场。人是一个双重体,只要人还需要精神,需要思考,需要滋润,文学就会存在。因为文学是水,她会浇灌我们已被风化的心灵,她能让我们日渐疲惫的心灵焕发生机。
本刊:看你的作品,我们发现一种现象,那就是你前期的作品多是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如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的《死帖》,还有给你带来声誉的《三个和尚》、《杀手时代》、《寻剑》等。可近期我却发现你的写实作品多了起来,如写乡党委书记的《解冻》、《地瓜啊地瓜》、《油钩子、油撇子》,还有你近期创作的《天下大事》、《张三讨债记》等,你能谈一下你的作品吗?
闵凡利:我是一个用想象力写作的作者。前期的作品的背景多是现实之外的故事。也就是我在现实之外重新给人们塑造了一个可能存在的空间,那是梦幻中的景象,但人们相信那是存在的,是活在他们精神层面上的。因为这些人物很纯洁,很美好。她们有着胎儿般的无瑕和洁净,她们一个个没有被污染。在她们身上,人本来的真诚和善良,纯净和质朴,自然与美好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我对自己的创作在题材上进行了扩展。我觉得一个作家是活在现实中的,他是现实生活中最有良知和责任的人,他不能回避现实,他应当关注现实、融入现实,与现实中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并及时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及心路历程。
本刊:你的作品经常出现“善州”这一特定的区域。据我所知,你的家乡滕州古时因滕文公善政,被孟子称为“善国”,“善州”是不是滕州市呢?
闵凡利:善州是我想象中的城市,她是虚构的。是我大部分小说中人物集中活动的场所,内里有滕州的影子,但不是滕州。在我眼里,滕州不是城市,它只是乡村的一个扩展,是个大乡村。最多是个大乡镇。而善州,她比滕州要大,她是鲁南风俗、民情及各大城市的总和。
本刊:说起善州,我就想起了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比如老舍与北京,冯骥才与天津卫,贾平凹与商州。作为作家,你是怎样理解这个问题的?
闵凡利:一个作家,他一生都在构筑着他心中的城市,他不光是这座城市的缔造者,更主要的,他是这座城市的魂。他是这座城市的代言人,他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喜怒哀乐,经历着这座城市的沧桑沉浮,他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维护着这座城市的尊严。
我与滕州的关系就是我因滕州而荣,滕州因我而更具内涵、更具魅力。
本刊:对于创作,请你谈一下天赋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好吗?
闵凡利:我一直认为,天赋与作家非常重要。天赋是与生俱有的。有一个残疾人叫什么的我忘了,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常到国外去演出,是一个很出色的指挥家。据说他出生时,对什么都迟钝,可一听到音乐,他就会随着节奏手舞足蹈。他就是专门为音乐而生的那一类人。天赋是深藏人体内的一种过敏源,它能使人对某一方面的认知的扩展达到一种极致的潜能。是能使作家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一定程度的酵母。创作本身是一种倾诉,是一种发现,是一种创造。有很多的东西还是潜意识的,所以说,第一个需要天赋的职业就是作家。
本刊:现在很多作家都“触电”了,你对这事是怎样理解的?
闵凡利:作家“触电”是一种能力的展示。作家为什么就不能去创作影视剧呢?我认识的很多作家,现在都在从事着影视剧的写作。影视剧的写作和小说的创作虽然都是创作,但本质上是有很大区别的,正是所谓的隔行如隔山。一个好小说家不一定是个好剧作家,但一个好剧作家也不一定是个好小说家。如果既是一个好小说家又是一个好剧作家,那相应的此人在小说及剧本的创作上的造诣将会提升到一个新层次。
如今是个以经济为尺码来衡量人能力的年代。作家处境的尴尬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出力不挣钱这个考虑。一个中篇,按三万字计算,能拿到两千元就是好收入了。如若你写个影视剧,三万字左右一部作品,最少也得拿个两万元。况且还是税后的。就说我的小说《解冻》吧,在《红岩》刊发后,《中篇小说选刊》、《小说精选》又先后相继转载,三个刊物我拿到的稿酬不到五千元。而卖这个小说版权,我是卖给曾拍过《新星》、《一代廉吏于成龙》的太原电视台,他们一张口就是一万元,并且是税后。说实在的,很多作家“触电”,有很大一部分是利益驱动。同是出力,为什么不抱西瓜而拣芝麻呢?
大部分作家还都处在一穷二白阶段,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拒绝平庸,拒绝媚俗,但我们不拒绝人民币。作家毕四海曾说过,“有钱能让我们尊严地活着。”有钱能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和办公设备得到改善,能使我们更加从容地面对浮躁,面对千变万化的风云变幻。小平同志说得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要说,贫穷也不是作家。
本刊:说到这儿,我们就必须说一下市场。你能否谈一下小说怎样更好地和市场衔接?
闵凡利:小说是作家创造出的产品,一种文化商品。因为一篇小说从创作到有人阅读,这本身就是在按市场规则运行了。就是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我国的作家由于受计划经济和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把这些东西游离于商品外,这是很可笑的。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作家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文坛上出现了炒作,出现了畅销书,这是好事,这起码说明作家们已经走向市场了。
作家怎样更好地和市场衔接,我记得在2000年《大家》第六期杂志上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是由兴安、李敬泽和陆涛在一起讨论的,是《关于类型小说的对话》。类型小说就是针对某一特定的读者群而去创作的某一类作品。如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还有童恩正的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恐怖小说等。最明显的例子是郑州《百花园》、《小小说选刊》所倡导的小小说,现在已蔚然成观。作家是思想最活跃的一类人,所以,现在很多作家都在瞄准市场,寻找卖点,主动出击。以求把自己的市场做得更大更广。
本刊:作家这一称谓,以前是很神圣的,是很受尊重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谁能发表一首小诗或者散文,转非、安排工作、提干等都不是难题,可如今,骂人都用“作家”这个词。我曾听一作家朋友说一笑话,说的是两个小孩打架,一个小孩骂了另一个小孩一句,另一个小孩想了半天,想出了一句厉害的,就说你再骂我,就让你长大了当作家!那个小孩一听,立即跳起来还击:你才长大当作家呢!你一家人都是作家呢!
闵凡利:“作家”和“农民”、“工人”一样,是一个称谓,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作家的宠爱不正常,而如今对作家的慢待和无视也是不正常,是走了两个极端,这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作家说到底是一种职业。就像“清洁工”“建筑工”一样,都是需要付出劳动的。它不像从政者,虽然从政者也是一种职业,可他们腐败也是工作,吃饭喝酒也是工作。还有一样,作家是用脑力来劳动的。况且,作家是在创造!
在现在这个年代里,作家贬值很正常。英镑、美元都贬值了,何况“作家”呢?你以为你是谁?只要你别以为作家了不起,作家有什么了不起呢?也吃饭喝酒打嗝放屁,除了会组合个文字编个故事,剩下的就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说,千万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心态一放平了,别人再怎么说作家怎么着,作家们也会一笑了之了。
本刊:你认为在一部作品里什么最重要?
闵凡利:智慧。就是作家的聪明才智。包括作家的叙事技巧、语言力度、人物内涵的扩延、主题思想的拓掘等。这些也就是海明威“冰山理论”的十分之七。透过这些,我们能预知这部作品的寿命和作家的生命力。
本刊:你认为一个作家最应该保持的是什么?
闵凡利:清醒。因为这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年代,如果一个作家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很可能会走失了自己。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比如我写一些应景的文字时我很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是为了偿还稿债,二是为了多挣些银子养家糊口。虽然有很多人说这些作品怎么怎么的感人,怎样怎样的高明,我明白,他们那是在恭维我、抬举我,一个傻子都有人恭维,一个哈巴狗都有人说乖,何况一个作家呢?
本刊:你认为自己的代表作是哪篇?
闵凡利:我还没有代表作。我总是认为我的所有作品都还没有达到想法和表诉的完美统一。
我总是认为我最满意的作品是正写的这一篇,可写出了又不是。从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我自认为说得过去的作品也就那么几篇。如《神匠》、《三个和尚》等。
本刊:看你的简历,我们才知道,你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今年才32岁。但你的生活经历坎坷多折,况且你的文凭只是初中毕业,又是身居底层的农民,你要在文学上有点成就,所受的痛苦和折磨一定要多于别人,就你的磨难说说好吗?
闵凡利:说我的磨难就是撕开我的伤口给人看。我一直认为,磨难是一个人的试金石。我初中毕业后便上不起学了。我兄妹五个,我排行第四。当时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靠我父母——两个老实巴交、但非常有志气的农民在土里刨出的粮食。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学会了平和地面对苦难,消解苦难。面对苦难最好是把自己融入苦难,在苦难中发现快乐和感动。
我感到最大的欣慰是磨难培养了我不屈的斗志。教会了我默默忍受和无声地抗争。教会了我流泪了就擦掉把目光投向光明的前路。磨难于我是一笔资源,一笔财富,它让我理解了生活的含义和做人的根本。
我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这近二十年来,我每一刻都不敢倦怠,我几乎在夜里十二点之前没有睡过,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我知道自己底子差,惟有不停地学习才能弥补我学识上的不足。也许是习惯使然,也许是我的生物钟被打乱,我一般的休息时间都是在夜里一点左右。
本刊:你能说一下你最近的创作状况和下一步的打算吗?
闵凡利:我最近正在给南方的一家电视台写个剧本。这个剧本杀青之后,我下一步要写的中篇是《穷局》、《奔小康》、《张三的面子》,这几个都是现实题材的。我今年的创作计划是:4个中篇,8个短篇。如今时间已将过半,任务完成还没过半,看来我只有快马加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