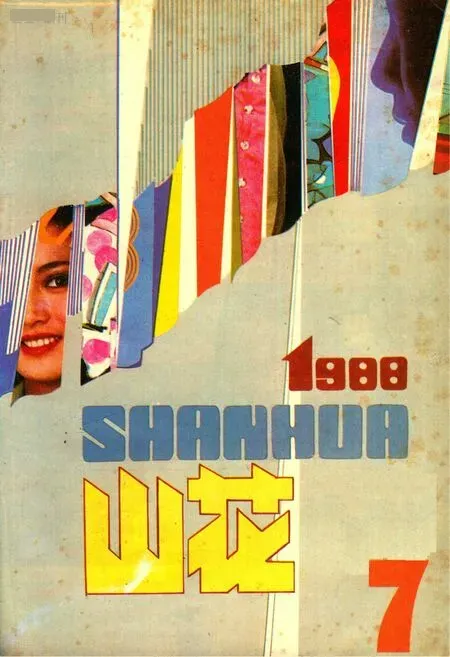女巫与夏葡萄
2003-04-29周晓枫
周晓枫
打牌打到半夜,又失眠,加起来睡了不到三个小时。还做个了怪梦,夏葡萄边刷牙边想,梦见自己的太阳穴如同橡胶树那样溢出胶质,一个看不清模样的人蹲在半空,不怀好意地提着空罐头盒,等待收割。夏葡萄侧过脸,太阳穴上方,隐约看见分叉的蓝血管。矫情又蹩脚的与会诗人怎么形容?智慧闪电?得了,她满脑子想着昨天的黑桃对Q,如果留到最后就好了,双扣,升三级。
九点。话筒里一阵刺耳噪声,然后电流低响。“同志们,开会了。”主持人仰起他的双下巴颏,手指头像谢茶那样磕着,夏葡萄路过时瞟了一眼他食指上的灰指甲。“马教授,杜老师……哎,魏青山你怎么也坐到后面去了?”主持人招呼着,使得前排座位不至空旷。推拖着最终还是位移的人物达到目的,这是惯例——开会之前,他们愿意主持人以大嗓门念到名字,在公众面前,自己的名声和重要性都是需要提醒和一再强调的。
夏葡萄困,准备熬到被介绍后就开溜。想到一上午的陈词滥调,满屋烟雾缭绕,而她,拉上厚厚的遮光窗帘,钻进被窝,在深黑和安静中入眠,夏葡萄的脸上浮升秘而不宣的享乐表情。
无所事事,夏葡萄沿途打量着那些脸。长的、短的、扁的、方的。傻的、机灵的、非常狡猾的、比蛇还毒的。贫乏的、胆怯的、纵欲的、健康又天真的、功成名就的。偷着放屁的、说话帮腔的、整人出汗的、恨自己牙痒的、爱自己乃至见面就得让对方捧场的,还有以后保证会自杀的。总而言之,都是和她夏葡萄无关的。
这种研讨会,名义上文学,实则旅游。总要抽出一两天做做样子吧,可会议内容实在莫名其妙。与会者中,大多数人漫漫一生中从未和真正的文学发生过一次性关系,却作出子孙满堂的样儿,大讲特讲霉烂的观点,以布道语气,还以为自己成了启蒙者,其实他们自己才需要被启蒙呢。仅是一种观点倒也罢了,见仁见智,不必趋同,但几位中年男子无比愤怒地讨伐散文虚构时反复质问作者的人格,学术争辩而已,有什么权力非法地引入道德批判?散文不能虚构?我看,我们连生活和荣誉都是虚构的。
不易察觉地,他在人群中窃笑,小小地,邪恶地。夏葡萄意外发现了一个同盟者。
涂了松油的火把燃烧,夜宴刚刚开始。笨手笨脚的飞蛾,还有蝙蝠,还是那身磨掉光亮的皮斗篷,围着光焰和脸色阴沉的主人飞……主人们用餐刀切开煎得脆脆的婴儿心,喝处女泪,晚餐的背景音乐是父亲们的哀嚎。树根朽烂,而野菇快速生长,加重着它们鲜艳的菌帽和毒素。
狂欢将持续到危险的黎明。
她有紫头发、铁锈色的血和变黑的心。为了掩饰灵魂的霉气,常常以香水媚惑。她穿着水做的裙袍,梅雨季节不合体,不得不拖着臃肿肥大的后裾;但干旱时期,她性感露骨。她渴慕虚荣,满纸谎言。她有丰富的想象力、配制秘方的天份。她熟知咒语,擅于用毒。
童话里,巫婆的形象都被描述为古怪龌龊:热衷熬制咕嘟冒泡的、令人恶心的汤,贪婪,孤僻,骑行在一把长柄扫帚上,从落地黑袍底端露出枯瘦的脚踝,但现在,她的荒凉远未到来,作为一个年轻女巫,她尽可享受,萤火虫般摇动诱人的臀部,她将翩翩少年劫掠。这个圈子,只有欲望,没有爱情——爱情是最大的笑柄。
提前离开宴乐,夜空中她独自飞行。月亮上的坑斑格外醒目,像摔烂的水果,黑暗中散发衰败中的甜。
女巫如愿找到了新猎物。他与众不同,最重要的,他有一种撩人的寂寞。
一座杂乱无章的县城。会址选在这儿,因为隔着不远,有个意欲开发的风景区,它的湖光山色需要被歌颂,并且县委提供全部食宿、旅游和礼品费用。作家们的到来似乎是件大事,到处张贴条幅,欢迎欢迎再欢迎,桌子上堆满家畜做成的菜肴,来,喝酒,再干一杯。接待人员的热情,改变不了这座小城的无趣,它远离古朴,又和现代无关。夏葡萄觉得八天的会期太长了。
早晨,许多勤劳的小店主“哗啦哗啦”掀开铝合金的卷帘门,出售水果、服装、低劣电器、配件和音像带。孩子跑进跑出,不知怎么就哭了,脸上青一块黑一块的。店铺楼上,穿着松松垮垮棉质睡衣的女人,用力拢着头发,开始千篇一律的一天。
本来清静的散步,被嘀嘀作响的摩托和横空直撞的自行车搅扰。和昨天一样,浏览街景得不到什么情趣和收获,穿高跟鞋的杜女士建议大家坐三轮车回去。
三三两两地上了车,夏葡萄和他恰好分在一辆车上。
她挨着他,闻到烟草气息。他抽烟时特别有享乐感,微眯眼睛,延长喷出烟雾的时间,他的肺叶全部为它打开。空气中,混合着县城特有的机油味和他缭绕的烟香,夏葡萄体验到一种缓慢发生作用的恍惚的幸福感。
一只蚱蜢落在夏葡萄的膝盖上。经过油漆的躯干,通体闪着化学绿光,它爆发力饱满的大腿随时保持着起跳姿态。这只莽撞的蚱蜢,用飞行员般装饰着保护罩的眼睛,洞察世事地,盯着夏葡萄。
女巫月夜到来,少年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香水弥散危险的气息,她的赤足有若梨花白。来吧孩子,在抚触中你将被麻醉,或者变得更加敏感,你将哭泣着,继续要求被征服。看花团锦簇,人丁兴旺,淫乱才是让世界繁荣的首要条件。
仲夏夜的后花园,交缠在广玉兰树下,白肉黑心的情侣,彼此是红人。“我要一醉方休!”她低语,“我们需要春天的酒精,需要燃烧,堕落需要进行得更加彻底。”
发酵的情欲让人烂醉如泥,她体验着身体在腐烂里的柔软,就像告别里的怀恋。
少年垂下眼睫,女巫在他甜美的睡容里犹豫了一分钟,没有像平常那样迅速离开。她发现,少年在做梦。
低暗光线下,埋藏人间一张张被磨蚀的脸。他们不知道关乎自己的秘密。梦是黑夜的宝石。人在做梦的时候,会分泌含有暗香的物质,如同树分泌松脂最后成为琥珀一样。神白天休息,以便黑暗里监视,及时采摘梦的宝石。人就是一种由神饲养的产宝石的家畜。人无法享有宝石,如同奶牛不能喝到自己乳房里的汁液。梦宝石泡在新月表面凝结的露水里,可以饮用,用以医治神的抑郁症。有时候,神采摘梦宝石会触碰到一些警醒者,他们就会在恍惚中,记得自己做过什么梦。而梦宝石也被魔鬼偷窃,因为要提前动作,魔鬼往往在果实尚未成熟的时候下手,所以梦宝石的色泽和味道都很怪;并且,魔鬼多毛的手不像神那样灵巧,易于把做梦人惊醒……这就是恶梦的成因。魔鬼偷窃梦宝石的目的不详,但肯定并非出自药用,可能仅仅出于对神意的违抗和蓄意破坏。
少年梦到无限而完美的爱情。女巫得到一块慑人心魄的梦宝石……光线烁动,在它深海蓝的核心。
这是小县城的特点。即使像火车站这么分秒必争、以时间为重的地方,悬挂的巨型钟,指针也是错误的——它们或许已经停了一年半载。逝若流水,与此地方何干?这里的人劳碌着,抱怨或者隐忍。爱与生死,疾病与疲倦,他们代代相传,生活秩序仿佛那段城墙,风剥雨蚀,依然不能被撼动。不走运的是,这里的日子,旧得没有味道。
那个指针,大得像把铡刀,夏葡萄看它危险地悬在高空。它停了,像刻舟求剑留下的剑痕,难道还有什么重大的记忆要被打捞吗?这不过是一次潦草的会议,一群凡庸过客,一座她再也不会来访的小城。夏葡萄将重归紧张的都市节奏,以及因习惯而舒适的孤独之中。
他个子高,坐在下铺有点儿窝,他就去了过道侧面的座位。不知是他光线移动中明暗交替的脸,还是因为自己坐了倒座,夏葡萄有点儿晕。杯子里的绿茶浮起,又降落。他不说话,看窗外的田。过了一会儿,下雨了,窗玻璃湿蒙蒙的。再后来,刚刚落下的水滴被风斜吹,像蝌蚪,从窗户左上方向下游动。那些淘气的小尾巴。想不起哪位后现代诗人说过,下雨就是老天爷在射精。夏葡萄想,这就是文人的限制和精神洁癖,他们只愿意承认玻璃上的雨水像蝌蚪,断然不会提到精子。他的脸映在显微镜下的精子活跃图里,夏葡萄偷偷地笑……小小地,邪恶地。
直到下车匆忙的分别中,他才说:“我给你留个电话吧。”没有纸,写哪儿?那组碳素墨水写就的号码印在手心,夏葡萄躺在她的单人床上,发觉它们并没有被她有意的汗水磨蚀掉。
雷雨之夜,他们等着闪电。那些天下掉下的树枝,难以在大地上生根。但假如巫师把它们栽插成活,这种剑戟般的院落植物,就可以抵御所有前来复仇的偏执者。
女巫倦懒地靠在羽毛床上,往日的澎湃活力如潮水退却……来自淫乱和恶毒的力量。她凝视宝石深处的闪电,那少年爱情梦释放出的灿烂,她知道它难以在魔界生长。什么是爱,就是额外柄授他人践踏自己的特权。花儿用蜜浆报答入侵得到果实,但巫婆的毒汁减少,就意味她的法力减少,尊严减少。女巫抗拒那种危险的向往,尽管,她夜夜临近少年的枕席。
黄昏,人间女子只需抬头,就看到晚霞:硕大而虚妄的玫瑰,那是微服出访的大神献给情人的礼物。他不能再度回访,因为,他忘记了她们的姓名,她们的地址,忘记了她们迷乱的呻吟,忘记她们雏菊般在瞳孔深处绽开的光芒——最根本的,他忘记了她们的区别。所以大神把玫瑰铺陈天际,以使遍布各地的情人无论身置何处都可看到,并在孤单入睡时开始缅怀或彻底失眠。这些床秘密地联结起来,最后,整个大地都成了压在大神身子底下的一张床。
神和魔之所以非凡,乃是因为他们避免了那些消耗自己的牵挂。浪子回头是乏味的,甚至比凡人成为圣徒还要乏味。随心所欲的女巫,何必仅止因为一个爱情梦而修改自己,像普通的女人那样愚蠢,那样可笑?!
聚会。灯红酒绿,低嗓音的伴歌,偶尔频闪之下的热舞。夏葡萄抽了半盒烟,该聊的也聊完了,就这么七七八八地坐,耗着。情人节之夜,大家聚在一起,相互证明,自己清白无辜,素得厉害。休闲花裤衩和露肩,宽手镯,闪烁的眼影,半醉的傻话和黄段子……估计再待二十分钟,就该散伙了。听这首歌,是夏葡萄最喜欢的爱尔兰乐队TheCranberries,她对主唱Dolores的敬意难以言表。但情人节听到它多少有些感伤:
Theres no need to argue anymore,
I gave all I could,
but it left me so sore,
And the thing that makes me mad,
is the one thing that I had.
I knew,I knew,Id lose you
Youll always be special to me.
多单调啊,日子贫瘠,缺少生动变化,今天的作家素材匮乏,又相互重复,除了男女恩怨,似乎没有别的情感发展空间了。撒了娇,偷个情,都算小调剂,谁又舍得花那么大气力,伤神而徒劳无益地,真的投入一场血泪斑斑的生死恋?说来说去,大家都是赢不起也输不起的人,喝口爱情汤,尝尝味儿得了,多吃怕上瘾,也怕中毒。所以,尽管他们平时也沾些小荤小腥,可真到给个情人名分的地步,谁都要犹豫,这帮人里,夏葡萄更坚决,干脆连对婚姻的兴趣都没了。她的单身宿舍经常会被半夜拍响,门外,站着苦大仇深、要求收留的秦香莲。夏葡萄觉得还是这样好,虽然自己过了三十五还像二百五,但一个人,清静。
她的手机响,“这么晚,谁啊?还是今天?”有了新话题,嗜睡的眼睛们亮了一下。夏葡萄也是意外的。见面已是深夜一点,夏葡萄不知他为什么非要约在此刻,尤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答应,而且,答应得那么痛快,早有期待似的。
他突然吻了她的左颊。
起风了。那是野花,屈下微小的膝。
脏的毛,被踩扁的身体,头部旁边是一摊烂掉的红色……那是带血块的内脏从死老鼠的嘴里被呕吐出来。女巫小心地把第三条老鼠尾巴放进钳锅。
这个世界充满败笔和抄袭。混血的儿子找不到双亲,秘密失贞的女孩酝酿未来和灾祸……几片乌云,就使整个天堂变得阴暗,那么,为什么,女巫不应该施展她的才华,捞取泥浊中一朵怒放的艳异之花?人间女子采用原始的蛊惑办法:把男人的头发或衣物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据说就可以得到他永不离弃的心——这些傻丫头,什么头发,衣服啊,指甲啊,这些对男人并不重要、剪去丝毫没有疼感的东西,怎么能够信赖?要他的血,要他在爱欲中流的血。
海蓝的梦宝石,泪水一样凉,荡漾在女巫胸口;海蓝的溶液,泪水一样凉,荡漾在窄口瓶里。女巫春花灿烂,迎向她的少年新郎。她知道必须是在今夜,必须在那个秘密时刻。她知道鲜艳的血流到蓝溶液中,会变成安静的深紫色。她知道少年将从此再也走不出她的长发缠绕。
金色面具,铁石心肠,蛇蝎美人吻上他的脖颈。
最后一瞬,女巫停止,她柔软的嘴唇离开那条轻轻跳动的血管,落在少年额角。她改变了主意,就算和自己打个赌。放弃技巧和蛊毒,女巫要和无数平凡女子一样,仅凭最简单的咒语。
她说“我爱”。
掉闸了,空调停了不到几分钟,要命的热就包围上来。电话铃响,他拿起听筒,语气里有双重的谨慎。夏葡萄知趣地离开,小心挪动,不发出声响。
她光着脚退到厨房,打开冰箱拿李子吃。红而圆满的果实,表皮蒙着水汽。她跪在沙发上吃。冰冷的李子,一个又一个,进入她的胃——网袋里掉进了台球,她觉得满了,够了,再多再狠的击打,也盛不进去了。尽管隔着房间,她也负责任地,咀嚼时不发出声音。
她在他身边的一个条件:必须保证毫无噪音。是的,无声,像宴会上的面条,小偷捏在手心的钥匙,夜半翻过寡妇墙头的偷情汉。一个李子滚落,除了落地时极小的闷响,它基本上是无声地,带着受伤的肉体,连滚带爬地躲进角落和灰尘里。夏葡萄想,无声,是一个有美德的形容词,因为无论是那些平常的事物,诸如泪水或死亡,还是好些非凡的诸如智慧,都是在无声中被触及的。
夏葡萄回忆起那个无声地落在左颊的蝴蝶吻,轻,短暂。蝴蝶停下后不扇动翅膀,它关闭绚丽的图案;只有它飞走,你才知道什么样的美停留过。夏葡萄曾被点化,不飞……她就那么停下来,并且闭合自己的美色。
巫术是一项需要魔鬼帮助和参与的游戏。长久和魔鬼打交道的人,容易以为自己不惧风雨,百毒不侵。然而,魔鬼不过是输了的神,巫婆只是坏掉的人——她有时会忘记自己人的身份。巫婆和儿童思维相近,都拒绝逻辑,过分相信奇迹。就是说,她们指望着几乎不可能的好运过活。是的,不管多么毒辣,在有的方面,她们就是孩子。
女巫日渐一日,沦陷在梦宝石深处——她的瞳孔反射着爱情的璀璨之光。新孩子的玩具,脏孩子的幸福花园,不可名状的幽蓝闪电将女巫彻底征服。女巫远离欢宴,远离她的魔鬼朋友们,千山飞渡,穿越黑暗去看望她的少年。空旷夜空,半轮月……那是深蓝的海面,鲸浮出它的脊背。
少年的名字越来越重,妨碍她飞行。她必须有所舍弃。她甚至放弃香水以减轻气味的重量。后来,女巫不得不断臂求生……她只有残疾了,才能带着她的爱情一起飞。
而少年,陷入怀疑。他向往女神,这是任何一个凡间女子难以承担的角色。他最初被吸引,因为她,有一种瑰丽的冶艳……他将她误认仙女。她日渐依恋,她屈从,不断吻他的小腿和脚趾,她深情得像个平庸的妻子。少年失望,然后渐生愤怒,他分不清这愤怒是针对她的还是针对自己的。莫如说,他的爱情,存在于由想象诱导的误解和骗局造就的完美期待里。曾经,邪恶有张引诱中焕发光彩的脸,让他舍不得摧毁;现在她躯壳都是破损的,深身笼罩不祥的霉气。一旦少年不再猜测,他就已决定。
女巫爱的那个少年给她最不易得到的礼物。他给她伤痕。
晚上吃什么?你提个建议。我没主意。我也无所谓。那出去再说。
两个人下了楼,边走边找饭馆。哪家都不顺眼,不是门脸低俗,就是装修浮夸。所以走了很远,还饿着。坐下来,又都没胃口。服务员送上来检验的鱼说是刚死的,仔细看,眼珠子都塌了。点的菜不合口味,咸的咸,淡的淡,怨对方没听从自己的建议。彼此都明白,不是找的饭馆不对,他们本来,就是找茬。
爱情如鲠在喉,你是把它吐出来还是咽下去??
为想念所支付的体力,使夏葡萄渐生恨意。她非常清楚自己陷入困境,爱的钝刀子开始威胁。如果可以,她选择那种爱恨不惊、风雨无忧的生活;而他,年轻的时候就准备建设被歌颂的晚年。夏葡萄厌恶婚庆日,只有两个人注册的小型企业犒劳员工而已,有什么必要搞得像盛典;他呢,未来稳定,幸福可见,太太的肚皮明显隆起,预示即将的丰收……夏葡萄仿佛看见他们的儿子,屁股通红得像印章,使他们的婚姻变得更加庄严、神圣、就像结婚证书所许诺的一样。夏葡萄和他之间,聪明得谁都不会犯错。
为什么别人能拿爱情当补药,夏葡萄只能把它当毒药呢?她如此警惕、怀疑、患得患失。文学作品里,或许活着爱情的女英雄,夏葡萄听见她对她的王说:“从我撕开的身体,让你尝到血中的咸味,仅仅因为,你说生活有点儿淡。”但夏葡萄自己,恐惧这种戏剧的真实发生。
他们注定告别。谁要对谁负责?笑话,又不是强暴。他是夏葡萄的一个疏忽。谁能给出一张完美地图,告诉你曾在哪里走错。
夏葡萄自嘲,其实没有什么是误入歧途——那种认为存在着一张由神设计的完美地图的想法,是对自己重要性的过分估计。
两个逗号可以分享一个句子,但苦痛永远不能均摊,像王冠,濒死者的食粮,女巫怨毒的爱情。她以为是自己操纵咒语,其实她被咒语控制,起先听命于魔鬼,继而听命于爱神,叛徒生涯让她付出累累代价。殉难的女巫永劫,她无法重获少年最初的眼神。这就是时间的谜底,就是最后报答。
女巫把自己埋在往事的泥沙。她老了,什么药汁也不能挽救她的皱纹……像一枚倔强的贝,贝壳上嵌着坚硬花纹,她不再开口。
夏葡萄曾经梦到自己老了。韶华已逝,手背上的皱纹坚硬得像贝壳。醒了以后,她并不惆怅,年轻女人的寂寞香,终会变成孤单的朽味。她还有短暂的几十年。
最近,她热衷参观一间不大的宠物店。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鹦鹉,乌龟,兔子,最多的还是猫狗。一脸苦相的贵妇狗爱上了一只香猪,舔它粗壮的脖子。一对吉娃娃永远像被虐待的双胞胎,忧伤莫名。还有那只博美,老打喷嚏。
每个周末,夏葡萄来这里认领一个狗儿子。认领仅限于心理活动,店主和宠物都不知道。她临时给她的宝贝起名字,有时叫“杜十娘”,有时叫“泡泡”,有时叫“小偷”。每个星期,她换个新的。上星期那只,常常被卖掉,携带着她不为人知的母爱,前往福祸未知的地址。这样好,她希望每周都更新,牵挂那么稀薄,伤感那么淡,新的很快替补上来,谁能记挂着谁?
大地上,是粮食和惊雷。天堂上,谁在醉酒高歌,击打月亮的人皮鼓。
女巫骑上她的扫帚,最后一次,追逐彗尾。迎面的尘沙和大雪让她闭上眼睛,索性盲目下去。在不为人知的身体部位,她有诡异的纹章。穿过夜晚潮湿发胀的丛林,她兀自飞去,笑声像兽。
时间的弓绳搭上肩胛,像自刎之剑。给想喝水的人饮下她自己的血,她不会再渴了,也有助于忘记比喝更多的欲念。
夏葡萄梦见一个身体残损的心碎女巫,女巫说,如果谁获得了她的一滴黑血,就可以让世上任何男人致命地爱自己。夏葡萄说:他爱不爱,我不关心;我要的,是我的不爱。
一滴黏的沥青般的稠血流了下来。烧灼的。
夏葡萄发现她在梦中咬伤了自己的舌尖,血珠带着陌生的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