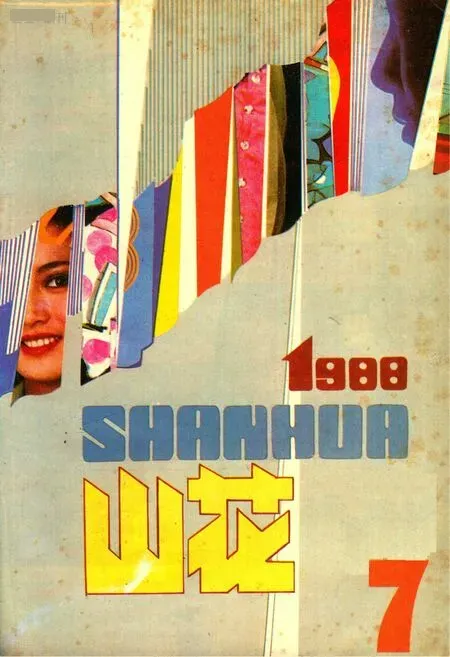现代性炎症与宏大叙事药引
2003-04-29詹勇
詹 勇
SARS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激荡了大半个中国,并向东南亚、北美等地进行全球性扩散,所到之处,莫不风声鹤唳。人类在一场疾病面前竟然如此惊慌失措以至于孱弱无力,这对现代性高度发展(尤其是科技神话的一再张扬)的文明世界来说,不啻是一个绝妙的反讽。但不管是在目前还是未来的情境中,玩味这种意义毫无任何理论价值,因为事态的进展,早已经突破了想象界和象征界的保护性屏障,我们不得不在实在界直面SARS。因此,针对SARS本身进行一些现代性病理学的分析和诊断,进而思考疗救的方案,是更为理智和负责的。
不管人们将SARS比作是新的鼠疫还是切尔诺贝利,仅仅只能作为一种深刻而普遍的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ies)之心理表征,而决不能说明SARS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中的特殊性质。虽然SARS具有某种后现代性色彩,如对权威的冲击,平面化和狂欢化的扩散趋向,对整体世界政治地图的区域性割裂,与个体化生命和琐碎化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等等。但是从总体上说,我还是将SARS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炎症(inflammation of modernity),即它是现代性问题及其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的一次集中而猛烈的爆发状态,远远超出了医学上的病症指认意义,对当下的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极其现实、深远的启悟作用。从SARS所造成的整体内在性影响--既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构成广泛的威胁,也直接冲击了现代性社会的每一层面--来看,我们有必要以一个整体性的视阈来考察SARS症候背后的病理机制。我认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一)现代行政体制(modern administrative system)在全球信息化时代面临的问题与挑战。SARS在各地以撒旦面孔惊现的时候,人们在惶恐之余,纷纷将不满发泄到对某些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迟钝,隐瞒,无能,低效,漠视等等)的抨击上,这些实际问题固然值得警惕,但更要看到它背后所触及的深层政治体制问题。大而观之,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之变革,其实正处于两个时代的交叉和叠合之中,一是由传统的计划时代向广义的市场时代的转化远未完成,二是由地域化市场向全球市场的转化方兴未艾,呈现出很浓厚的建构性特征。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探及问题背后的多样化症结。我认为包含这样几个要点:长期程式化运作所带来的隔绝性和相对滞后性,政府的社会化服务功能单薄,缺乏稳定而理性的应急机制,信息化运作程度较低。就SARS危机来看,它集中地体现在行政体制的功能性缺失(functional lost)上。我所指认的功能性缺失,既有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所谓的现代性设计问题的成分,前现代的心智结构和行为惯例魅影重重,计划时代的制度性制肘依然没有彻底消除,尤其是对于正处于不断建构中的中国现代性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且诡异,似乎在相当时期内是难以避免的;但事实更加表明,其中的操作问题是更为现实性的因素。 [1]
在SARS危机爆发的初期,信息的开放与透明是一个焦点性问题。正如杰姆逊(Jameson)所指出的,资讯的控制甚至于拥有,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无比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 [2]那些隐瞒疫情的官员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问题在于他们仅仅基于权力本身的下意识反应来作出应对,企图沿用《鼠疫》和《卡桑德拉大桥》所提供的传统信息封锁方式来控制疫情,进而以某种"关门打狗"的方案来度过SARS难关。从主观因由上说,这反映了对全球化时代信息属性的误读。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呈现出空前的全球流动的特质,加上以电视网络为核心的媒体手段的技术支持,我们发现信息的能指和所指发生了彻底分离,信息所指仍然具有地域化和此在性质,而信息能指则凭借传媒介质实现了脱域化的全球扩散,进行其闪电般的全球奥德赛之旅。尽管SARS病人只在少数地点和区域真实存在,但是关于SARS的信息能指却具有极其强大的爆发力和扩张力,某个社区新增了几个病人和疑似病例的消息,可以在十分钟内传遍全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隐瞒SARS疫情的无效和失败,是由全球信息化的新语境决定的。这又同时给我们提供了一面观照的镜子,误读导致误用,以4月20日为一分水岭,之前疫情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合理和充分的运用,或者说还未能作为抗击炎症的正面资源来加以使用。这一方面造成了对政府应有功能的抑制和损害,如应急机制和全面隔离措施启动的相对迟缓;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由于对信息资源的误用,造成了对信任机制的极大冲击,不少人在短期内甚至对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表示怀疑,反而相信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这又反过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由于信任机制的受损,政府的信息权力的合法性认同被削弱,这就加剧了行政体制的功能性缺失的趋势。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还将看到,信任危机也是与体制化的科学专家系统的运作失灵紧密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医学领域内的信任问题可以视作是功能性缺失的一种延伸和拓展的表现形式。然而在4月20日以后,形势发生了让许多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这固然是疫情严峻和恶化所迫,但从政府的雷霆手段和更张魄力来看,我们隐隐可以见及现代行政体制内在的强劲更新活力,最为炫目的是信息的全面开放,不仅向全国公众公布每日的即时疫情,而且利用全球信息化的资源环境,寻求国际理解、支持和合作,促进和改善了行政体制各项职能的开展,极大地恢复和巩固了民众的信任及信心,同时也为中国抗炎事业争取到了全球声援的有利语境。其次,以《公共卫生应急条例》出台为标志,表明政府已经超越了临时性、应急性的运作思维,转而寻求能够应对全球化时代信息风险的体制性建构。这一良性进程的端倪初现,再次证明了现代性的制度创新是在问题与解决、挑战与机遇的辨证戏剧中不断推进的。
(二)科学神话(scientific myth)及其信任的重挫。几乎可以说,20世纪以来诸乌托邦神话中,只有关于科学的神话是一直长盛不衰的。尤其在祛除人类固有的生理疾病苦难方面,"科学一直表明是人类的救星","科学自有它自己的种种奇迹和解答"。 [3]科学神话一再以不断推陈出新的叙述方式(蒸汽时代,工业时代,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得以讲述,作为现代性展开的一项重要议题,它已经内化为社会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科学本身也不断地被吸纳到社会体系之中,逐渐成为一种体制化的文明设施,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以专业区分为基础的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的形成。专家系统以科学理念的抽象体系为其内在支撑,以形形色色的交汇口(医院、机场、车站、港口、咨询机构等等)作为联系非专业个人或团体的交流孔道。各种专家则作为科学抽象体系的代理人居中进行运作,进而建立起一个信任的链条。这一信任链条有两大特点。一是日常性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态度通常是与日常行动的延续性相关联,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日常生活自身的环境所强化"。二是交汇口是其中的薄弱环节,"交汇口成为非专业人士的怀疑主义态度与职业化的专门知识之间产生紧张的地带这一事实本身,使它们被公认是抽象体系之所以脆弱的根源"。 [4]这次SARS导致的信任危机,也是由交汇口这一信任机制上最薄弱的链条进行突破的,医务人员也会被感染而且同样可能致死,医院成为最主要的传染场所和病毒引爆地,暂时还没有针对SARS的有效疫苗和特效药物,SARS的感染机率充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所有空间,这些事实不得不使人们猛然惊醒,原来科学这时侯也是这般无能为力。由这一突破口撕开,人们对专家系统乃至科学抽象体系产生了怀疑情绪,对科学神话的信任遭受了空前的挫击,这也是恐慌心理一个源头。
但也要看到,事情还远远没有陷入绝望的境地,正如鲁迅所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5]毕竟科学也是人类在此时唯一可以凭借的救赎之道,而且科学力量几乎在同时发起了反攻:"非典"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的完成,中国抗"非典"药物的突破性进展,美国也在研究治疗药物,各国医学家协商治疗对策。我们当然有信心看到在完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通过科学武器战胜SARS,科学神话也会继续其乐观的叙述。但是SARS至少为我们提示一个再次审视科学本身的节点。耐人寻味的是,今年也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一百周年,一个世纪以来,人类似乎通过掌握科学魔法而获得了生命的极大飞扬与自由,而SARS所给出的答案却是人类重新向其沉重的肉身进行坠落的可怖现实,(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也有类似的警示)这不由得使我想起穆旦的一句诗:"污泥里的猪梦见生了翅膀,从天降生的渴望着飞扬,当他醒来时悲痛地呼喊。" [6]从奥斯维辛、广岛、博帕尔到切尔诺贝利,现代性科学永远都不能摆脱这样一个基本的命题:科学的人本主义维度。不管未来的科学神话以怎样的姿态继续其高歌猛进的进程,我们在振奋之时,也要冷眼旁观,甚至要勇于不怀好意地提出一个无厘头式的诘问:"神仙?妖怪?"对于现代性方案中的科学神话,我们永远都需要一种重写的自觉,而"首先是对建立以科学技术解放全人类计划企图的合法性的重写。" [7]
(三)消费主义幻象(illusion of consumerism)的破灭。在全球资本主义洪流裹挟之下,消费主义的浪潮相应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在中国,以《上海宝贝》的风行一时为文本标度,消费主义在近年内以暴风骤雨之势横扫并浸润中国。与之相呼应,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出笼为代表,久为民族国家的历史话语抑制的日常性话语被彻底解除了封咒, [8]中国现代性叙事的两大主题--民族国家和个人欲望--展开了竞逐,而后者日益占据上风,这就为消费主义的扩张进一步推波助澜。当然,中国的现象也是全球消费主义趋势的一股浪流。在消费主义情境下,形象成为商品的新本体,幻象的营造及其消费成为核心的环节,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成为幻像世界的种种物像生产和再生产的主导场所,消费主义幻像除了带来感官及身体欲望的极大想象性满足之外,也"消除了消费者意识中社会现实原则本身",它通过抽取现实世界的"激情和事件的寓意符号",以戏剧性的方式重新组合现实,其结果是现实本身丧失了本体性,沦为符号的符号,而一个完全以符号建构起来的幻象世界取代了真相世界。 [9]这个世界满足了人们对安全感的欲求,因为符号及对符号的消费得到了真像担保的证明,而这正是幻像的最大魅惑力所在。
波德里亚(Baudrillard)指出,在消费主义的重重围困之中,"我们是以一种必需的幻觉方式、一种不在场的方式、一种非现实的和一种与事物非直接的方式生活"。 [10]借助于科技力量(如人工智能)的克隆和复制,人们似乎完全可以摆脱所谓的真实世界,进入一个具有高清晰幻像的仿真摹拟世界(simulacrum)。这一世界是如此的完美无缺,以致于我们只能通过反证的方式来冲破其无所不在的网络。这就是死亡的方式。死亡是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唯一边界和互通孔道,只有当死亡降临的时候,一切幻像才会遭受根本性的破灭。在电影《骇客帝国》(The Matrix)中,黑客们对"Matrix"虚拟世界不断进入、穿行和退出,维持着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应该绝对避免死亡,不管这种死亡是意念上的、程序上的还是肉体上的。而只要任何意义的死亡(尤其是肉体意义的)一旦发生,那就会被游戏完全剔除出去。应该看到,死亡不是外在切入的,而是虚拟世界内部游戏规则的本能变异,生命终结也是幻像游戏的一个部分,其实当一个声音冷冷的说"Game is over"的时候,还有一个声音在回应:"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从这个意义上说,SARS可以理解为这样几个词的简写:奇异(strange)、绝对(absolute) 、真实(real)、分离(separate)。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消费伊拉克战争,而不能消费SARS病,因为"人命关天"。死亡这一最简单、最野蛮、最冷酷、最直接的事实,在心理体验上,我们不能获得惯常的对现实的眩晕之快感,而是惊骇、焦虑乃至绝望。这就从根源上实现了对消费主义幻像的解构,把我们从虚拟世界中分离出来,重新拉回到沉重的真实世界,这正是现代性现实主义的底线所在。
(四)全球资本的去国族性利益(de-nationism interest)之魔障。这个问题可以与第一个问题联系起来,部分官员及地方政府对SARS疫情的隐瞒,根源于这样一个最大的恐惧:资本逃逸或是资本拒斥,从而造成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恶化,资本在这里被视为地方利益的最高象征。所以他们力图以信息封闭和垄断的方式来营造一个幻像性安全环境,以期留驻并吸引资本。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可疑的。从安全的意义上看,资本需要的是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而不是假定性安全(supposed security),它是彻底真实的安全,以至于任何潜在的威胁都是需要清除的,硝烟渐熄伊拉克战争就是向着全球资本的本体性安全的一次政治军事实践,所以营造安全幻像从根本上说是徒劳的;从资本本身来看,在全球化时代中,资本早已经剔除干净了任何附载的国族性意义,"它们拒不效忠于任何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 [11]简言之,全球资本完全以其自身为利益旨归,任何非资本力量企图将之塑造为自己的价值根基,只能是镜花水月式的空洞想象。这一判断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就在中国大力进行抗击SARS的同时,西方某些媒体肆意歪曲甚至妖魔化中国的现实,看似人道,其实是一点血性全无的无情和恶毒。这其中固然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成分,但从深层看,这是全球资本进行利益自为和调整策略所引发的表象。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阈来看,资本的前世今生,一直就烙着一个林冲脸上那样的金印,上面写着"非人"两个字,这里的人,应该是指整个人类。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资本是唯一极致化地摆脱人道主义的文明后果。而在全球化现代性的具体时期,我们尤应警醒被这一工具理性力量所吞噬,而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突破全球资本的利益魔障:民族国家的利益本体不能从资本机制上生发出来,全球资本只关注全球资本的利益,这是一个绝对封闭和保守的利益自足系统。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分析并不能构成对资本的意识形态性抗拒,因为这不是由我们的主观认知所决定的,而是由资本利益自体所决定的。资本是最没有面皮、最没有血性、最不会记仇、最不怕死的,中国市场的现实和潜在利益魅力,使SARS危机中的资本动向出现吊诡性的表现:退避和回流同时进行,互为表里地进行运作。
与SARS大行其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以更生后的新面貌大规模登场。这首先醒目地体现在媒体的叙述方式上,CCTV、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提出了"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刻","我们民族的新的考验","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民族寓言在SARS情境中得到了重新的叙述与书写。凤凰卫视更以全球化的眼光,标举"全球华人宣战SARS"的理念。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下我们看到了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诸关键词的引用和表述,不仅保留了经典宏大叙事模式的痕迹,更突出了新现实情境之下的重写性质。处于危急之中的中华民族这一现实性命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冷静而沉痛的对SARS所造成的民众生命毁灭之体认,对于国家正在面临或者将要面临的危机的焦虑,使我们在新型苦难叙事基础之上,仿佛听到了"救亡"这一沉睡多年的宏大叙事主题的呼吸之声,不过当下的叙事更接近关注民族现实状况和前景这一实质性问题。殉职的医务人员被褒扬为民族脊梁,使民族寓言中的英雄谱系得到续写,中央政府每日发布全国疫情通报,将区域性的数据整合为全国性状况的表述,让国人不仅知晓本地区的疫情态势,更对全国总体形势予以关注。这实际上了提供了一个集体性想象的共时文本,其主旨是不断强化关于"中国"的概念和信念,从而通过SARS这一焦点问题促进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的形成, [12]这些新的叙事表征都在很大程度上使久已淡漠的国族认同被再次发掘和高扬。
以防治SARS为实施途径,对广大人民进行的卫生和科学知识普及,同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心理恐慌的缓解措施(其典型的代表是爱国卫生运动),使我们看到了"启蒙"和"科学"主题的叙事在新的现实环境中得到了开展;国家领导人亲临抗击SARS的第一线,对基层民众的生命健康予以关注和保护,尤其是长期处于社会最边缘化地位的民工人群,也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一方面固然是防治疾病本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关于"人民""民众"的宏大叙事正以新的面目浮出水面。作为一个初步总结,我认为目前宏大叙事的新崛起根源于中国现代性的未完成性质(unaccomplishment),以及作为这种性质体现的独特而诡异的运行方式,它既像鲁迅所想象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 [13]以潜流状态持续开展,又像马克思所称许的那只老鼹鼠那样一待时机成熟就一跃而出, [14]即是一种延续性和突发性的双重变奏。
在各种宏大叙事新的崛起的背后,我们察觉到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境遇里的新的定位和权力转化。从隔离有接触史的健康人群的举措来看,我们隐隐看到了一种复合型权力的雏形,它集管理、观察、医疗、教导、服务、心理抚慰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形成一个有机的权力运作方式。权力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乃至个人生活的多个层面,初步显示了从内部控制和规范的作用方式。这一则可以看成是福柯(Foucault)所谓的控制的社会(society of control)的强化和普遍化,隐约出现了向生态权力(biopower)的新权力范式的演进趋势; [15]二则是现代性叙事主题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实现了新的整合。在国家指令之下,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景像:关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宏大叙事,与关于个人日常生活的琐碎叙事实现了共谋和对话,现代性的两大主题(民族国家和个人欲望)以非暴力的合作方式实行了新的重组。如果进一步扩展到全球化体系之中,我们发现民族国家充当着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存在着"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全球传染的时代"的逻辑预设, [16]另一方面民族国家还是具有相当坚固的边界隔离,SARS没有造成事实上的全球蔓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具有了脱逸出全球体系的可能,而恰恰说明民族国家这种地位的派定,正是其作为适应全球资本和人力流动设施的功能性运作方式,全球流通还是需要一定的边界划定的。
应该看到,宏大叙事只是疗救SARS所表征的现代性炎症的一副药引,作为体系化的症治方子,既存在于我们对现代性方案的重新反思之中,也存在于现代性方案的继续建构之中,这是一种不断反思中的践行性叙事,我将之理解为一种现实主义乌托邦(realism utopia)的想象与生成。这当然不可避免地导向信仰主义的问题。在当下,信仰主义具像为面对SARS危机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民族精神高昂的民族,也必然是免疫力顽强的民族。SARS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重新考验民族格性的契机,六十多年前贺麟先生所呼唤的"道德战斗、人格战斗"以新的面目提上了民族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日程。 [17]《老残游记》中那条很大然而吃载很重的船,及其航行在凶涛骇浪之中的形象, [18]早已经脱离了晚清中国命运隐语的限定涵义,更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性历程的寓言性叙事。李大钊则表述得更为明晰:"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注到很宽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千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迭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曲折回环,极其险峻。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 [19]这当然是一种宏大叙事的诗意书写方式,但却能穿透时空的阻隔,传达出这样一个永恒的声音:越是艰难的国运,就越需要雄健的国民。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之曲折、反复、震撼、坚忍,无不令人惊心动魄而荡气回肠。立在SARS肆虐的中国大地上,我们需要刚毅坚卓的民族意志力,也需要高瞻远瞩的理性洞察力,此时的危机终会表明这么一个现代性轮回:风险最大之地,正是命运重现之时。
注释: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33, 134页
[2]见杰姆逊为利奥塔所著《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的序言,(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3][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 ·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 1995年第281页,该节的标题是“科学—— 世界的希望?"
[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78,79页
[5]鲁迅:《野草·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第17页
[6]穆旦:《还原作用》《穆旦诗集》(1939——1945)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7][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重写现代性》《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37页
[8]参阅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 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1年,在话语建构上,尤其以第二部分“现代文学的想象:作家和文本"为关键。
[9][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 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至 13页
[10] [法]让·波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 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1页
[11]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资本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收入《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三联书店1998年第497页
[12]参阅Benedict Anderson的专著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83)
[13]鲁迅:《野草·题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14]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7
[15]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24
[16]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136
[17]参阅贺麟:《经济与道德》《文化与人生》商务 印书馆1988年第31页
[18]刘鹗:《老残游记》第一回“土不制水历年成患风能鼓浪到处可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
[19]李大钊:《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李大钊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355页。此文最初发表于1923年12月20日《新国民》第一卷第二号,已经编入中学语文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