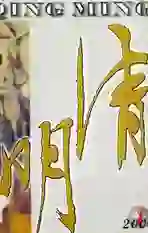我们
2000-03-31章渡
章 渡
我们一共有四个人,天天绑在一起玩。每天的早上或者中午,我们吃完饭就聚在我家的那间小屋里。我们歪在床上,说一会儿话,发一会儿呆,然后出门去逛。我们把手插在屁股口袋里,缩着脖子,冷着脸,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如果有一辆自行车,我们就三个人骑在上面,一个人在地上走。累了的时候,我们找个墙角,围成一圈蹲下来,认认真真地吸一根烟。
我们包括这样的四个人:我、孟千、林志引和何娇娇。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我们有了各自的绰号。我的绰号叫一碗好菜,简称好菜,这表明我的肌肉发达;林志引的绰号叫林志颍,因为他有一点点帅;何娇娇的绰号叫非洲柴鱼,因为她不但黑,而且身体像一块搓衣板,缺少女人高高低低的曲线;最后我们说到孟千,他叫名牌贩子,他一年到头都穿着名牌,在这座城市算得上鹤立鸡群。他的名牌服装不是很多,只有两套,冬春天一套彪马,夏秋天一套梦特娇。冬春天倒也罢了,夏秋天他就比较苦恼——他要忙着洗衣服。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脱下来,嚯嚯嚯地洗,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则是看衣服有没有干。所以夏秋天的晚上如果去他家玩,我们就能看见他光着膀子穿着裤衩的模样。
也许您已经知道,我们是一群无业游民。我们没有钱,没有学历,没有当干部的父母,有的只是大堆大堆的时间和薄得能削苹果的脸。像这座城市一成不变的灰漾漾的天空一样,我们的心情是平静的。我们既不高兴也不痛苦,既不想杀人也不想自杀。我们就是逛来逛去地过一些日子。
但是今天——五月一号,我们却有一点失落,因为我们的朋友何娇娇要去温州当坐台小姐去了。
何娇娇昨天晚上找到我们说,她要请我们吃饭,花子给了她一笔贷款。
我们咧开嘴笑。我们知道花子是她的父亲,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酒鬼,从他手上要钱比老虎嘴里拔牙还难。我们还知道,何娇娇即使买一卷卫生纸,他也要在本子上记一笔,记在何娇娇未来的婆家头上,并且要人家付十倍的利息。我们相信这样的人会给何娇娇吃擀面杖,却不会让她去吃馆子。
但这一次却似乎是真的,因为何娇娇把钱从口袋里露出来了。何娇娇说,这是去温州的路费。我穷怕了,我要出去搂几耙子。我的同学回来说,外面遍地都是黄金。
我们说,恭喜你呀,富婆。我们又嘻嘻哈哈勾肩搭背地说,那么走吧。
我们来到胡一刀大排档,找个偏僻的角落坐下,要了几个菜,上了八瓶啤酒,每个人都喝得晕头转向。昏黄的灯光下,我们看见何娇娇的脸通红,胸脯一起一伏,眼里夹着两粒叫做眼泪的东西。我们发现何娇娇原来并不是一个丑人,她甚至很有一些漂亮。我们心里顿时酸溜溜的不是滋味。
孟千说,柴鱼,你去温州当坐台小姐,不就是去做鸡么?
何娇娇说,做鸡有什么不好,投资少,见效快,永不磨损。
林志引说,那我们就太亏了。我们陪了你四年,连毛都没摸一根,却给别人留下个处女。你难道没听说过,肥水不流外人田——
何娇娇嘎嘎地笑起来,笑得东倒西歪,像一只钟摆。几分钟后,她才把自己停下来,她指着我们的鼻子说,你们想要吗?头一开的嫩豆腐,谁想要?
我们争先恐后地喊,我想要,我想要。相持不下。
何娇娇说,你们划拳吧。
我们捉对划拳,五局三胜。结果我输给了孟千,孟千输给了林志引,林志引输给了我。我们还是相持不下。
我们对何娇娇说,算了吧,把你的处女之身给我们看看,留作纪念吧。
我们回到我家的那间小屋,把门关上,围在床边,像一群手术大夫。何娇娇非常大方地脱光了衣服,我们直着眼睛把她从头看到脚,然后非常失望。
我们嘘声四起。我说,噢,我阳痿了。孟千说,你是一只白虎!林志引说,这简直是在搞同性恋。何娇娇爬起来,一句话不说,给了每人一个嘴巴,气鼓鼓地走了。
我们这座城市的老鼠不少,我们这条瘦狗巷的老鼠更多。这给了我们许多乐趣。现在,我们又抓到了一只,我们很兴奋。
我们玩老鼠是有经验的。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总结出了十八种玩法:我们把老鼠的尾巴压在板凳下,看老鼠咬断尾巴逃走;我们把老鼠身上浇上柴油,点一把火,看它烧得满街疯跑;我们把老鼠的腿捆起来,一人拉一头,四马分尸,让它疼得摆头;我们撮合老鼠交配;在公鼠的生殖器上插一根针,我们用打气筒往老鼠肚子里打气,看它嘭地一声爆炸……等等等等。今天我们准备玩第十九种玩法,我们要在老鼠屁眼里塞一粒黄豆,用胶布封起来,看它怎么节食,再怎么胀死。我们找来黄豆胶布,正凑在一堆使劲时,手里的老鼠却被人啪地打掉了。
一群不要脸的货!有人骂。
我们抬头,看见一位咬牙切齿的黑衣女郎——正是我们的朋友何娇娇。我们的脸红了红,涌上一股羞愧,随即又涌上一股奇怪。
我们说,你不是去温州当坐台小姐了吗?
何娇娇说,当了坐台小姐又怎么样?
我们说,你会有可观的一笔钱呀。
何娇娇说,那以后呢?
我们说,你用这笔钱开一家店,省吃俭用,赚更多的钱。你还了你父亲的贷款,开更多的店。你的钱越来越多,你盖楼买车,雇一大帮人帮你干活。
羽毛何娇娇说,那以后呢?
我们笑起来,那以后你就快活了。别人忙得屁滚尿流,你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逛大街。
何娇娇说,那么,你们看现在呢?我不就是舒舒服服地睡觉,然后爬起来逛大街吗?
我们面面相觑,掉进了她的圈套。我们感觉她一夜之间变得聪明了。后来偶而翻看地摊杂志,才知道这是人家早就玩过的把戏。
何娇娇说,你们有本事呵,该出手时就出手呵。拿酒把我灌醉,把我不该看的地方看了。你们打算怎么赔?
孟千说,怎么赔?大不了我们也脱光衣服给你看回去。
何娇娇啐一口:放屁!
我说,那我们请你看电影吧——《克林顿的爱情故事》,周华健主演。
林志引说不好,不符合中国国情。还是看好莱坞版的《金瓶梅》吧。出场的都是大腕,施瓦辛格演武松,莎朗·斯通演潘金莲,汤姆·克鲁斯演西门庆。据说武大郎一角让导演大伤脑筋,最后请了马拉多纳来客串。
何娇娇说,我不想看《金瓶梅》,也不想看《爱情故事》,我想去听崔健的演唱会。
崔健的演唱会?我们瞪大眼睛,表现得比较吃惊,在什么地方?在隋朝往事。我们知道隋朝往事是一家高档的夜总会,凡是阔人们想得出来的服务项目,里面都可以提供,因此收费比较高,现在加上崔健的演唱,收费就更加恐怖。我们赶紧翻口袋,把口袋翻得底朝天,也只凑齐十元钱。我们这时突然有点厌恶《义务献血法》,如果不是取消血源市场,我们每人去卖个200cc血,相信就能向何娇娇小姐表示一点歉意。而这座城市如此的落后,竟没有一家精子库,让我们去卖几管精子,就更让我们恨得牙痒痒了。
我们举着十元钱,如同举着何娇娇小姐交来的难题,一时不知怎么办好。
何娇娇说,别把眼睛翻得像鱼白,好像我在虐待弱智儿童。
我们说,真要给你虐待一回,大家心里也好受些。
何娇娇挥挥手说,行了,行了,咱们谁跟谁呀!我有同学在里面当领班,可以带我们进去的。你们陪着我,别再惹我生气就行了。
我们一阵欢呼。为何娇娇的大度,也为她给我们安排的陪客角色。须知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晃着膀子当陪客呀。
隋朝往事在城市的北郊,瘦狗巷在城市的南侧,中间隔着二十里地,不通公交车;我们也没有自行车,自行车都给父母驮着小商品摆地摊去了。但这些都不成问题,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也有悠闲的习惯,我们可以走着去。
我们走在路上,边走边看风景。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打架,一辆面的和一辆摩托打架,一条狗和几个联防队员打架;我们看见一个半阔不阔的人拎着大哥大,用一百分贝的声音说话,恨不得站上交警的指挥台亮相;我们看见三个女人的六条大腿,肥美无比,我们的目光像黏腻的蛇信,从她们的脚趾滑到她们的膝盖,再滑到她们的大腿根。我们最后看到一个傲慢的板刷头。
孟千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朋友,隋朝往事怎么走?
板刷头横了孟千一眼说,我呸!你口袋里有几个小钱?
孟千嗷地一声跳起来,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他拼命地拍打着身上的梦特娇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出门就给狗眼看。我孟百万什么没有,就是钱多呵!我打个喷嚏都能提炼出黄金。你小子有没有屌?
板刷头说,有。天字号第一大屌。下地就能耕田。
孟千说,有屌咱们就比一比,把你的家私都搬出来,百元大钞我十张你一张地烧,谁先手软,谁是孙子,吃爷爷一碗大粪。
板刷头两眼放光,连说了三声“好”,撒腿就往巷子里跑。回头又指着孟千说,别溜,溜就是婊子养的。给老子抓到,打断你的狗腿。
孟千当然不愿被打断狗腿,吼一嗓子“撤”,拉起我们就跑。跑出半里开外,林志引说,不对。隋朝往事在北边,这是往东。
何娇娇说,去隋朝往事做什么?
我们吃惊地盯着她,说,去听崔健演唱会呀。你不知道?
何娇娇说,不看了。
不看了?你是说不看了?我们把头皮搔得直冒火星,为什么?
何娇娇说,那是崔键演唱会,不是崔健演唱会。
哇!太恶心了。我们呸呸地朝地上吐唾沫,把腮帮子都吐酸了。
现在,我们进了一家公园。公园里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人。太阳无精打采地挂在天空,像林志引父亲煎出来的油饼;风在裆下蹿来蹿去,刚好像不怀好意的小偷。我们在一张石桌边坐下,掏出身上的扑克牌,每人发了一百亿筹码,赌起了梭哈。我们嘴角叼着烟卷,眯缝着眼睛,一亿一亿地下注,像黑社会里的老大。筹码赌光后,我们就押上自封的司局长头衔,奋力扳本。几个回合下来,我和孟千两手空空杀(金羽)而归,林志引面前则堆了一大堆战利品。
林志引摩娑着战利品感慨说,这要是真钱该多好呵。
何娇娇说,除非是冥币,可你用得掉吗?
林志引说,假如我们真的有钱,我是说假如,你们最想干什么事?
孟千说,我要用金子做一套西服,用鳄鱼皮做几条内裤。
我说,我要把钱捆在身上,从二十层楼上跳下去,看能不能摔死。
林志引说,你们太自私了!我要有钱,第一件事就是把柴鱼变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我要给她换上梦露的眼睛,费斐丽的鼻子,索菲亚·罗兰的嘴巴,赫本的皮肤,最后给她装上简·方达的丰乳肥臀。柴鱼,你高不高兴?
我们一齐去看何娇娇。何娇娇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像通了高压电,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然后,她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有钱,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准备三副棺材。
三副棺材?
我们沉默了。
我们适时地选择了这个机会沉默。我们利用沉默的间隙发发呆。就好比鲸鱼每隔一会儿要钻出来透透气,我们用发呆来补充脑子的能量。我们茫然地看着四周,表情空洞,像摄影师手下的一幅作品;而我们周围,另一些意味深长的画面正在定格——
一个老人拖着口水在打瞌睡,一对小青年在接吻,一位母亲牵着孩子呀呀学步,一辆灵车响着铜管乐缓缓前进。接着,灵车上的纸幡被风吹断,风筝一样飘进了公园,掠过老人、谈恋爱的青年和我们的头顶,最后落在小孩脚下。小孩捡起来,迎风举着,格格格地笑,像举着一面旗帜,母亲气急败坏地追上前,一把打掉……
你们谁想吃饭?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我忽然问。
问之前,我又望了望天上的那个油饼,它的旁边出现一些混浊的液体和一些灰色的斑点,像全了孟千父亲做的酒酿水脂——一块油饼带一碗酒酿水脂,多么丰盛的午餐呵!我的肚子咕噜咕噜直叫。
孟千说,我们有钱吃饭吗?我们总共十块钱,买了一包烟,只剩下三块二。
我指指附近的某家酒店说,那一家怎么样?我们去吃个简单的四菜一汤?
林志引说,四菜一汤好吃,可是吃完呢?
我说,拍拍屁股抹抹嘴走人。
何娇娇说,我们没穿制服又没戴大盖帽,老板要是不让走呢?
我就把桌子一掀,把老板抵在墙角说,吃你一餐饭是看得起你,别不识抬举。几个臭钱,先记在帐上。
孟千说,老板要是不信邪,拿出一把菜刀拦在门口呢?
我就把颈子伸到刀下说,朝这里砍,别发抖,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当然了。我也可以把柴鱼推到他跟前说,随便挑个地方,摸一把,这位姑娘的出场费是干的一百,湿的二百。
何娇娇笑眯眯地骂,干你妈的头!随手把一团卫生纸塞到我嘴里。林志引不失时机地在我痒处挠了挠,我就把这团来历不明的东西吞掉了。
半小时后,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午餐。我们用三块钱买来六个大馍,两个肉包子,四串麻辣烫,又用捡来的矿泉水瓶接了两瓶自来水,敞开肚皮吃。我们一个个吃得响屁喧天。然后,我们头枕石桌,面朝公园的蓝天,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像许多喜爱养生的人们一样,我们有睡午觉的习惯。
爬起来后,我们做了如下的几件事:(一)在墙边撒一泡尿。墙上写着斗大的市民公约,但我们看这里更像一个露天厕所;(二)给灯箱女郎画二撇小胡子,在她裸露的胸脯上盖一层黑泥做的遮羞布;(三)向停在路边的奥迪车上甩鼻涕,在它轮胎下放一堆碎玻璃;(四)重点讨论了下午要逛的场所,又一一加以否定:Ⅰ)去周瑜点将台,看城墙上留着多少块三国的青砖。否定理由:墙上贴满了性病广告;Ⅱ)去赵敬德玩鞭亭,看看那根不怒自威的正义鞭。否定理由:正义鞭被霸王馆请去做了猛男标本;Ⅲ)去莫干岭看大老鼠,看它像不像一辆长了尾巴的坦克。否定理由:莫干岭一带是市府所在地,闲人免进。
我们是在一个疯子的吸引下走上淮海路
的。我们没想到这使我们做出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我们站在交叉路口,时间大约是下午三点,附近的餐馆酒楼开始冒黑烟,配菜间里传出嚓嚓嚓的剁骨声。我们知道许多丰盛的晚餐已开始筹备,一些阔人们坐在办公室里,正利用先进的通迅工具呼朋引伴。我们拿不准往哪个方向走,虽然条条道路都通瘦狗巷,但我们不愿回去得太迟,更不愿回去得太早。
这时,一个疯子跳出来喊:打倒王二杆!
疯子手举内裤做的小旗,额头上刻着“恨”字,白衬衫的前胸写着“我得了乳腺癌,别惹我,”后背写着洋洋洒洒的血泪书。我们判断他是疯子的标准是他没穿裤子。
我们跟在他后面,伸着脖子看血泪书,像被钓饵钓出来的一串王八。血泪书以一段歌曲开头:“都说那海水又苦又咸,谁知道刘浪(他的名字?)的悲惨辛酸,遍体的伤痕,满腔的仇怨,哦,刘浪的心中呵,血泪斑斑。”血泪书接着控诉了王二杆作为贪官污吏的种种罪行。除了常见的一些表现,比方说让工人吃不上饭,王二杆还勾引走了他林青霞一样的老婆,他去告状,王二杆就派人请他吃大粪,吃完大粪回家,他可爱的女儿失踪。血泪书最后总结说,如今,王二杆荣升上级主管部门领导,我却气出了乳腺癌,同志们那,天理何在!
我们一齐抬头看天,天上果然暗出了一块。我们低头看地时,发现已来到淮海路的一堆人群中。
——准确地说这是一堆静坐的人。他们把道路拦腰切断,淮海路像患了肠梗阻的病人陷入瘫痪。一些漂亮的小汽车成了呆头呆脑的甲壳虫,动弹不得,喇叭声和抱怨声响成一片。我们没见过这种场面,我们的腿也很酸,于是在人群中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我们坐了没多久,人群出现骚动,有人站上高高的板凳,严厉地咳嗽几声,开始拿腔捏调地与大家对话。我们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很有份量的一付肚子。他的中气也很足,与嘈杂的人声比较一点也不逊色。
我们不喜欢这种对话,它像某种无聊的游戏,天然地具有催眠的效果,使我们昏昏欲睡。可是身边的人群越来越激动。激动的高潮是疯子吼一声“打倒王二杆”,一把跳起来,辟面把凳子上的人拽下地,其余的人犹豫了片刻,蜂拥而上……
前面说过(也许没说过),我们是几株蕨类植物,不习惯出头露面,被人注意,但我们也有混水摸鱼的癖好,尤其是这种时候,大家的手都很痒,我们忍不住挤上前,朝这个满肚子肥油的男人施了一顿拳脚。
这以后的结局如何,不得而知。我们被一群防暴警察驱散了。防暴警察们下手还是很有分寸的,他们只不过在我们的额角或屁股上留下一个个小包,就像为这件有意义的事留下的标记。
我们终于捱到了天黑。对着西下的太阳,我们松了一口气——漫长的一天结束了,一天里过得很充实,这实在不容易。
我们经过这座城市最繁华的民生街,霓虹灯五颜六色,把这一带装饰得很小康。明亮的光影里,一些体面的男人挽着他们体面的太太或情人走来走去。我们自惭形秽,缩进阴暗的屋角下踯躅。我想起父亲时常对我说的话,他说你不应该叫一碗好菜,你应该叫歪屎菜。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这会儿我突然有点懂了。
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在三家店面门口,我们做了短暂的停留。我们不着边际地研究了一下:体委开的奥林匹克牌艺馆,灯箱上闪着一筒九万和五条,对联上写“爱我中华,弘扬国粹”,是不是就是麻将馆?光线暧昧的贵妃洗头房,生意火爆,洗的是大头还是下面的小头?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手拖着捡垃圾的麻袋,另一只手冲爱你金店指指点点。一个女人冲出来甩了她一耳光,又甩给她十块钱,老太太为什么含泪唱心太软?而老太太竟然长得像何娇娇,也令我们始料不及。我们对何娇娇说,你老得真快呀。何娇娇的脸严肃得像一片干缩的树叶。
我们走进一片黑暗——这是我们居住的瘦狗巷。我们家的房子卧在那儿。就像是瘦狗屙出来的屎,又硬又小。我们听见一个老头在吆喝“卖鱼喂……新鲜的大鲫鱼喂”——那是我的父亲,他的声音这时候听起来有些像唱戏;旁边一个拐角里传来何娇娇父亲汽咚汽咚的打豆腐声,又像是乐器的伴奏;而一只垃圾箱旁,伴随着这奇特的音乐,有几只老鼠歪歪例例地上场,它们吃了孟千父亲倒出来的剩酒糟,表演了一套《快乐的小精灵》之类的舞蹈动作。我们没像往常那样一拥而上去捉这些心满意足的小丑,而是淡淡地看了它们一眼,从它们身边绕开,各自回家了。
这天晚上,我做了两个梦。前一个梦里,我回到了上午去的公园,我们正在吃大馍,一个侏儒坐着小滑车过来讨水喝。我们看见他有一个突兀的大肚子。侏儒说,他原来的形象很高大,因为缺少锻炼,终日不见阳光,被传染上了灰鼠病,学名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这种病有各种表现形式,很难治。传到这一类人身上有这种症状,传到那一类人身上有那种症状。侏儒接着说,我被传上了这种病,肌肉萎缩,骨骼酥腐,形象日见缈小,有人干脆拿我当老鼠看待,可我是个干部呵!——我们立即显得不耐烦,显得缺乏兴趣。我们想,这也太深奥了,扯得太没边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的表现更激进一些,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从梦中醒来,把尿液连同梦境冲进了马桶。然后,我做了第二个梦。我看见自己的手脚像面条一样软,一碰就掉;我的身子开始收缩,越缩越小,最后如同一粒芝麻。我走在突然之间变得阔大无比的马路上,心里充满恐惧。迎面走过的人们的脚掌就像巨大的车轮,轰隆隆从我的头顶碾过。
责任编辑陈晓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