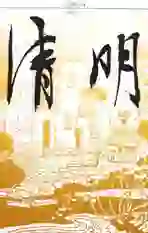此与杀人凶器等(外一篇)
1997-03-24茆家昇
茆家昇
粱绍壬先生和林则徐先生是同时代人,比林则徐小7岁,杭州人,生于乾隆十七年(1792),卒年不详。只知道道光十七年(1837年),他的表弟为其《两般秋雨庵随笔》作序时云,“君之书成,而君之身杳矣”。可见他的卒年当在1837年之前。林则徐湖广禁烟是1838年,鸦片战争开始于1840年。梁绍壬这本书中自然不会有记载,他生前和林也没什么交往。但梁先生对林则徐十分敬重,并且较早地提出鸦片的毒害,随笔中都有记载。今天鸦片之毒有重新肆虐之势,重温前人告诫,该是有益的。
先说说梁绍壬其人。梁和许多明清笔记随笔小品作者一样,也是名门出身、中过功名,但未出仕的闲散文人。其祖梁履绳曾注释《左传》,有《左通补释》传世。伯祖粱玉绳也是大文人。梁绍壬濡染家学,能诗工文,中过举人,未放任。一生游历过许多地方,和许多文学家艺术家有过交往:如赵翼、袁枚、毛奇龄、金农、李鳝、黄易等,为有造诣的画家篆刻家、书法家和诗人。殁后刊行的这本《两般秋雨庵随笔》洋洋三十万余言,有多种刻本,是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
笔者无意在此论述这本书的功过得失,只想提出两件事说一说,借此了解粱先生的感情心态和某些政治见解。
一是本书是随笔小品,本是信手写来,遇事而记,有感而发,文字大多简短洗炼,一般一则只三、五百字,长者一千来字,短者只几十字,而且有叙有议。而本书最长之文,竟是全文收录的《林抚军奏疏》,长达三千余言,文前只有几句简单介绍,文后无一字评议。此书中也有谈奏疏的文章,多很简短,看得出不甚用心,惟独对林则徐这篇长文记录的一字不漏。当时林则徐虽身居江苏巡抚要职,粱绍壬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也不会有攀高枝之嫌;他们个人之间无所交往,也就不存在感情上的亲疏。究竟为什么呢,只有读完林则徐这篇奏疏之后,你才会豁然开朗。
林则徐这篇似乎是官样文章的奏疏,其中也免不了称颂皇上的套话乃至谀词。但骨子里则是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刚正不阿,为民请命不计个人得失的一篇檄文。是林则徐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历程。
事情是这样的:明清以来,江苏赋税甲于天下,民财告匮,苦不堪言。道光十三年水患频仍,当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亲自坐小舟,沿江实地考察,取得了翔实的资料,然后剀切教陈,据实秉报,直诉民间的颠连困苦,请求朝庭“宽一分追呼,培一分元气,”否则恐滋事端。最后林表示:“臣不胜延颈颂祷之至。”林则徐这“延颈”是翘首以待呢?还是准备引颈受戳?古往今来说实话办实事的人的种种厄运,已经有了很好的注脚。
粱绍壬在书中全文收录林公的这篇奏疏,既是对林公的十分敬重,也表达了他本人的政治观点。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虽不能像林则徐那样兼济天下为民请命,但他一颗心是热的。
另一则是粱绍壬为鸦片一事写的一篇专题。这也是一篇妙文,文章开始时引举了有关鸦片的种种知识,诸如产地,色泽,品种,乃至价格等,不无卖弄学问之嫌,也说到了鸦片的耗精伤财,废时失业的毒害,未向深一层挖掘,文后的一首歌行体长诗,认识上深刻了许多,但依然只是从个人及家庭受害角度来考虑,没有提到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危险至深的高度。此文没有标明具体写作时间,从全书分析,大约在道光初年,即1830年左右,是否鸦片之危害面尚不宽,严重程度尚未为世人所识。梁绍壬先生作为有远见卓识的知识界代表,就已经看出了此物的危害,写诗作文呼吁禁毒,也是难能可贵的。也可说明林则徐以后的禁烟销烟,是有舆论前导的,并非空穴来风。
现将粱绍壬先生的这首诗抄录于后,以飨读者。
“窄衾小枕一榻铺,阴房鬼火红模糊,中有鸢肩鹤背客,夜深一口青霞呼。非兰非鲍气若草,如胶如饧色则乌,或云鸟类或花子,运以土化搏泥涂。加以水齐炮制法,文火武火煎为酥,清光大来渣滓去,铄金而液成醍醐。此品来自西域地,居奇者谁番者胡,朝庭严禁官晓谕,捆载来若牛腰粗。关津吏胥岂不觉,偷而赂者千青蚨,况复此辈尽瘕嗜,一见宝若青珊瑚。近闻中国亦能制,其物愈杂毒愈痛,吁嗟黄金买粪土,可为痛哭哀无辜。颇闻此物妙房术,久服亦复成虚无,其气既窒血尽耗,其精随失髓亦枯。积而成引(瘾)屏不止,参苓难起膏肓苏,可怜世人溺所好,宁食无肉此不疏,典裘质被靡不至,那顾屋底炊烟孤,噫嘻屋底炊烟孤,床头犹自声呜呜。”
不知道这是不是描述鸦片的最早的文学作品,起码是鸦片战争前的一篇重要作品。
“此与杀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枪。”此联非梁绍壬所撰,梁先生集来作此文结语十分有力,警世。
小议“居官不听子弟言”
故事是粱绍壬先生那本《两般秋雨庵随笔》里的。先当一回文抄公。
明耿定向《先进遗风》云:杨文定公溥执政时,其子自乡来省。公问日:“一路守令闻孰贤?”对日:“儿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贤。”公日:“云何?”曰:“即待儿苟简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识之,即荐升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文定不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励官方者在此,所以垂家法者亦在此。呜呼,贤矣!
这是一则写得很不错的随笔,叙事简洁,题旨鲜明,全无赘笔,所评也恰当。换个名字,用白话文改写一下,今天的报刊也能用。因为它符合新闻原则。现在接待上级及其亲属已成了一门大学问,学问深的得到上级赏识受到嘉奖,甚至官升三级;不谙此道,胡里胡涂倒了霉的,都大有人在,已不算新闻。倒是得罪了上级的亲属,反而被默记保举而升了官的,古往今来都是少见的。
明代的耿定向何许人也?那位杨文定公何许人也?那位天台范理又是何许人也?我都不知道。既然这则故事记录在《先进遣风》里,估计是事实。这位杨公和范公,一定都是很不错的官员,那位粱某作家也做了件好事。所以几百年后,粱绍壬还要感叹:呜呼,贤矣!又过了一百多年,今天能再发表出来,也还会是有益的告诫。
不过,世上的事是复杂的,撇开这件具体的人和事,就这种现象来分析一下,就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上级考察下级德政,就听儿子一番话,不问正面反面来判断,都是有失偏颇。就拿儿子说的那句:“待儿苟简甚矣”来说罢,情况就可能各式各样的:因为上大人的公子只是路过一下,那位下大人一时简慢,可能当时地方政府出了比接待上大人公子更重要的事,如发生了天灾人患,下大人无心接待;也可能当时地方上来了比上大人公子权势更大的人物,下大人忙那一边去了,这种事现在也常有,出差在外临时来了要员,要让房间甚至搬出宾馆,开会时说好某某要到场,临时某某去陪了要员都是常有的事。我们百姓无所谓,遇到上大人公子那样的人就受不了了;也可能这位上大入公子索勒甚巨,欲壑难填,未能满足,不欢而散;也可能下大人想在上大人公子身上打什么主意,未得目的,有意简慢之;也可能是下大人未摸透上大人公子的秉性,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如公子爱的是金钱女色,你偏要陪他去看什么名胜古迹,公子当然不高兴;也可能上大人公子是庶出,下大人知道了底细,未把他放在眼里;也可能朝庭里有了朋党之争,下大人看不清形势,怕多走一步受到牵连;或者干脆他已风闻上大人已失势,他先做一点姿态,向对方邀功;也可能下大人就个性鲠直一点,其实才干平平,当个县令还马马虎虎,去当府台就不能胜任了;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下大人摸透了上大入的脾气,投其所好,来个正题反做,歪打正着,玩上一招,曲线攀升。
最后这种可能也并非我凭空想象,这类例子多得很,大能人郑板桥贪吃狗肉被盐商骗去字画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就不说了。还有一个故事是讲曾国藩的,说有一次曾国藩下乡闲游,有人引导“顺路”去一位乡下人家作客。一进门,曾国藩就惊呆了。只见屋内一架架的书,尽是经史子集,还有孤本善本,墙上排的是名人真迹字画,格调十分高雅。与主人一见,更了不得,原来此人是位大儒,不仅满腹经论,而且对朝纲时政了解十分透彻,分析问题鞭辟入里,经世致用。曾国藩兴奋异常,洽谈终日十分投契。曾国藩以为发现了大人材,邀其出山相佐共事,其人坚拒之,后经曾国藩再三诚意相请,乃随曾回曾府。曾国藩委以重任。不久,此人裹重金而去,原来是个贼。那个盐商也好,这个贼也好,其实就一个本领,投其所好。谁能说那位下大人简慢上大人公子,不会也是玩上一招呢?
以上不过是作为一个读者的猜测,姑妄言之,听者也姑妄听之。说真格的,今日接待之风奢靡,岂只是吃喝玩乐,有多少人是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这些人自己清楚。浮夸风、腐败风,常常是在接待过程中表演出来的。真正现在要多出几位杨文定公和范理那样秉公办事的人,则是国家的幸事。不过遇到具体问题,那些握有大权的上级,多想想事情的前因后果,也决非坏事。
责任编辑潘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