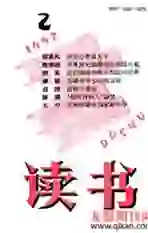“立言”的真义
1992-07-15何必
何 必
《春秋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襄公二十四年)立言虽然排在其次的其次,不过毕竟容易着手去做,不像前面两件那样玄。东汉大儒扬雄写过一部弘扬儒门精义的《法言》,还能写洋洋洒洒的华丽大赋,算是立了言;做了官,只要有政绩,无大过,便是有了功;只是最后,在德的境界上没有拿捏好,当了王莽的臣子。所以后代理学的权威人物朱熹一提到此公,就忍不住摆出一付“存天理,灭人欲”的架势,骂街道:“莽大夫扬雄死!”字字有情,正宗的春秋笔法。
要去立言,当然巴望能立得久些,不要新皇帝一来,自己就成为逆臣。这导致一个后果:专奉教条,亦步亦趋,做的文章渐渐入空、入远、入玄。这是神话。
乱世的情况又不一样,这里有性命问题,士人立言的时间一般比较短,内容主要是捧,主子也比较具体。这时候,立言后面映着刀光,就少了一种欢快的心情。这是鬼话。
正因为立言者存了一个要留芳百代的念头,明知是给别人看的,再无忌,也只是演功好,不容易看出他的真性情。神话浩荡,鬼话连篇,掩盖了人的真面目。
终于有人想要说说人话,可由于立言的惯性,做出的文章、说出的话就出奇的含蓄,需要别人去理解。这就发展了一门中国文化技巧:揣摩。看一幅画,一首诗,初看不懂,后来,一揣摩,二揣摩,到最后,揣了出来,就拍一拍巴掌,说:“是极是极,极是极是”。两相沟通,这便妥了。
如果全是真的,太逼真了,就刺眼。比如小巷壁上涂着的“阿五大王八”,就嫌太直;全假也不好,评论者的口胃是很刁的,人不好骗。就要在半真半假、似真似假、亦真亦假之间,才可以显示出造美方面的功力。所以文坛上向来雅事极多。明明是文人,偏要披一件
曾见到阿凡提、徐文长之类聪明人的故事,大多凭着智慧巧妙,惩恶扬善,损富济贫,虽然使穷人百姓扬眉吐气,仍不过是一个故事。细想:故事里面,财主恶霸都很憨厚,近乎愚蠢,凶残只是一种表象、脸谱。他们一败就认,也重信用,倒是智者们刁钻玩鬼,以为法宝。讲以毒攻毒,要两个都毒,才是公正,所以,故事中所谓的正义取胜,不过是一出借尸还魂的闹剧。自己做了老爷,过一过瘾。
小民何尝不想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唱《垓下歌》、举千斤鼎的西楚霸王,不过是声大力壮的农民,汉高祖当年见秦始皇出巡,何尝不想说:“彼可取而代之也”,他却说:“大丈夫当若是”,骨子里头是一样的意思,不过是心中想着造反杀人,嘴里还捧一捧主子,两相比较起来,刘邦的言就立得相当好,没有破绽,项羽的就太直;两相计较起来,霸王就跑到乌江边抹脖子。
立言本是一种理想,只是由于现实的压迫,终于沦落。在这里,立言的真义,便成了谋生的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