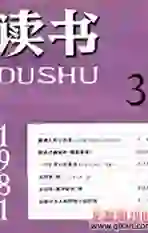俞振飞谈读书
1981-07-15谷苇
谷 苇
你看过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先生的《太白醉写》吗?那是多么地富有书卷气啊!
俞振飞扮演过许多“有书卷气”的角色:《游园惊梦》中的柳梦梅;《贩马记》中的赵宠;《金玉奴》中的莫稽;《玉堂春》中的王金龙;甚至《临江会》、《群英会》中的周瑜,……不论是在昆曲中、在京剧中,也不论他扮演的是“穷生”、“官生”、“雉尾生”还是“鞋皮生”,因为他所扮演的角色多系念过几本“四书五经”、背得出几句“诗云”“子曰”的人物,就应该都有几分书卷气。当然,这“书卷气”也因人而异,要恰当地反映人物的身份、性格、风采和气度,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服务。俞振飞积六十年舞台之经验,深知欲达到其目的,必须掌握表演艺术的规律,一切从人物出发。这里,只是就“书卷与书卷气”一隅,记述俞振飞先生自述的读书心得,或可名之曰:“一个演员的读书经验”吧!
俞振飞先生今年正好八十岁。一九八○年,国家和人民为他隆重地举行过“舞台生活六十年”的纪念活动。
回首前尘,俞振飞说:我总忘不了在我的艺术生活道路上,指点过我向前一步步走过来的老师们。
俞振飞的昆曲是“家学渊源”,主要得力于他父亲俞粟庐先生的亲自传授,京剧则多半靠程继仙的教导。昆京艺坛中还有许多前辈和朋友的帮助,他也是永远记着的。除了表演艺术而外,他也十分注意读书和文化学习生活、书画艺术修养等。
“第一个为你开蒙的是哪一位啊?”
“第一个开蒙教我读书的,是我的父亲粟庐先生。”俞振飞回忆起童年生活,脸上浮现出一片近乎天真的笑容。
“我父亲在他五十六岁的时候,才生下我这个‘老莱子。但不幸我在三岁的时候,就丧了母。从此我父亲就‘又做老子又做娘,一直把我带在身边。晚上睡觉,我常常想娘想得哭起来,有时在梦中也会哭醒。父亲就在身边一边拍着我,一边为我唱‘催眠曲。这‘催眠曲就是汤显祖的名作‘临川四梦(《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中《邯郸记》里的一段‘红绣鞋。说也奇怪,只要他一唱‘红绣鞋我就不哭了。所谓‘耳熟能详,慢慢地也就学会唱了。所以,《邯郸记》是我学唱的第一支昆曲,也是父亲教我读的第一本书。虽然,我还不识字。”
大概到了五、六岁的时候,俞粟庐先生就开始教俞振飞学习写字。起先学习写“碑”。因为俞粟庐老先生认为“北碑南帖”之中,学“北碑”便于打基础、见功力,因此只让他的孩子学“碑”。直到一九三○年粟庐先生去世,俞振飞才开始临“帖”。嗣后,俞振飞放弃了在暨南大学教书的职务,正式“下海”唱戏,写字的时间就不多了。但因为演戏出了名,各方面人士慕名来求索“墨宝”的多了起来,由于“盛情难却”,他就常常“借他人的纸张,练自己的笔墨”,至今练得一手飘逸清新的行书。识者认为功夫在“米(芾)赵(孟
当然,读这两部分书,都非老师口授亲传的。俞振飞也有他的“正规”的读书学习的生活经历:也许因为思想守旧,俞粟庐从小不让俞振飞进新式小学读书,先是自己教他读“四书五经”。教到九岁时,差不多“四书”已经读完了,父亲就把儿子送到苏州“拙政园”旁边一个姓张的人家去“附读”。这张姓人家是个大地主,雄有资财,而又附庸风雅,因此请了俞粟庐去做“清客”,帮着鉴定书画,写点文字。张家请了当地有名的吴润之塾师来家“教馆”,经过和东家情商,俞粟庐就带着俞振飞来张家“附读”。
“这位吴老师对我大有帮助。”俞振飞回忆起当年情景,至今还十分感激师门的教诲。他说:“吴老师的教书方法很特别。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他就问我读过点什么书。我回答说已经读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他马上摇头,说要全部放弃,从头来过。”
从此,吴润之先生就用他自己的教授法来教他的学生。俞振飞记得,老师每天教他四个方块字,但这四个字却分“乎”、“上”、“去”、“入”四声,一边教,一边念。这样经过了两年,俞振飞就懂得了“四声”。他说:“这对我以后唱戏、做诗,都大有好处。因为,不论你唱京戏还是唱昆曲,都讲究发音吐字,懂了平上去入,就很有帮助。相比之下,如今的青年演员们却缺乏这种学习机会了。”
俞振飞能够写诗、填词作散曲、小令,则还得归功俞粟庐老先生。他从小不教俞振飞读《三字经》、《千字文》,却从钟嵘的《诗品》入手,又教他读《古诗十九首》、《唐诗三百首》。这样,他十几岁时就学会做诗了。俞振飞说:“这大概就是俗话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诌吧!”
俞粟庐先生喜欢读书,家中藏书颇丰。俞振飞从小就喜欢钻到父亲的“四壁图书”的书房里去,拿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先看经、史、子、集。这些书看完了,就看医书。医书看完,就看各种“杂书”、“闲书”。从“气功”一直到“麻衣神相”,连陶宗仪的《辍耕录》都是当作闲书看的。同时,他还看了许多昆曲典籍,如《度曲须知》、《乐府传声》和李笠翁《十种曲》等等,有的还不止看过一遍。真是三教九流的知识,他都“吃”了下去,“熔于一炉”了。今天回头想想,这种“见书就读”的做法,还是有好处的,俞振飞先生知识面的广博,就大大得力于读书的广泛。当然,少年时候,也不是什么书都能读得懂的,但是不懂就问。有些问题,问到粟庐先生,就能得到满意的答复。遇有专门学问中的难题,就去请教学有专长的前辈,例如词曲大家吴梅(瞿安)、诗词家朱古微,这些“父辈之交”常给他以教益。后来与他也成了“忘年之交”了。由于他善于学习,也就慢慢地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文化修养。正因为他肚子里的“书卷”日有所增,以后他在舞台上表演的人物的“书卷气”才会自然地流露出来。
说到这里,使人不能不想起俞振飞在《太白醉写》中的精湛表演。在这出戏中,诗人李白从头至尾只有一句唱词。开始,原已微醉的李白奉召进御花苑,在沉香亭畔吟就《清平调》三首,讽刺了杨贵妃。接着,又在“万岁赐酒”的过程中,饮得酩酊大醉,并且借酒戏弄了高力士,让他不得不“屈尊”为自己脱靴。最后,他烂醉如泥地公然躺在当今天子驾前。在剧中,俞振飞活生生地再现了千余年来人民传说中的理想人物的洒脱形象。诗人坦荡豪迈,敢于蔑视权贵;又诗才横溢,即景生情就可以挥毫写出那么清新、隽永的不朽诗篇。在这出戏的表演中,李白要经历从“微醉”到“大醉”,从“大醉”到“烂醉”的“三部曲”,而仅有的一句唱词,是无法提供全部的表演内容的。推究演出的成功,就不能不看到“书卷”对于演员的作用。开始奉召时微醉佯狂的表演,使人想到“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醉吟《清平调》时,几乎使人回想起白居易的整篇《长恨歌》;最后,烂醉的李白被宫人扶掖下场,令人联想的甚至可以是诗人整个坎坷不遇的一生。这样丰富的表演内容,只可能来自艺术家对诗人的深刻理解,而这种理解首先是而且归根结蒂也只能是来自读书。读李白的诗,读有关记述李白的史书——正史与野史,读历来赞扬李白的诗文——同时代的与后人的……正是这一切的融汇贯通,才使艺术家达到这样令人陶醉、使人神往的艺术创造境界。也才使他演出的人物,浑身都能洋溢着“书卷气”。
——年轻的艺术家们,爱书吧,多读些书吧!——这正是俞振飞先生读书给我们的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