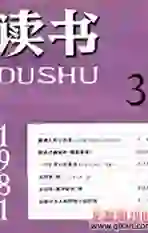怎样看《飘》?
1981-07-15杨静远肖穆黄颂康
杨静远 肖 穆 黄颂康
《飘》的中译本在一年前重印出版,曾经引起一些议论。我们认为,一部有过一定影响的外国文学作品重印出版中译本是可以的;但是,关于《飘》这本书究应如何评价,却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互相讨论。这里发表三篇有不同看法的评论,供读者参考。(原作均较长,本刊有删节)
编者
《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杨静远
早就听说《飘》的观点是反动的。一九七五年,我开始读了一遍,觉得它的反动性果真名不虚传。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又力所能及地查阅一些外文资料。我惊讶地发现,这本得过文学奖金的烩炙人口的畅销小说,有关它的评论竟如此之少。一些文学史或文学手册中,不是根本不提,就是寥寥数语带过,而没有专门的详尽的评述。
例如,《牛津美国文学手册》(纽约,一九五六)中虽然收进了该书及作者密西尔的条目,但在重要作品年表中却没有《飘》。
《现代美国小说。评论文集》(纽约,一九六三)中,无只字提到《飘》和它的作者。
《从一六四○年至今的美国作家与作品》(纽约,一九六二)中,对它的评价是一句话:“最成功的一本现代畅销小说”。
《美国文学手册。从殖民地时期至现时概览》(纽约,一九七六)中谈到关于美国内战前南方生活的神话时,稍带提到了《飘》,说:全世界都通过《飘》的作者知道了这个“迷人的景象”,“但是全世界也应该知道,她只是维护了几乎一个世纪以前就树立起来的神话”。
《爱国的热血。美国内战文学研究》(纽约,一九六二)中认为,有些北方人后来也接受并且迷上了南方的“神话”,其结果便是《飘》的空前畅销;这本书对于《汤姆叔叔的小屋》起了一种“奇特的抵销作用”。
甚至《美国历史小说》(纽约,一九五八)这样一本专论历史小说的书,都没有把《飘》作为专题来评论。
有些书中宁肯把《飘》算作重大社会现象,而不算作重要文学作品。如《二十世纪作家。现代文学传略》(纽约,一九四二)、美国现代史巨著《光荣与梦想》等。
美国学术界对《飘》的评价,由此可见一斑。我不由得感到,严肃的学术界似乎是以沉默来对待这本书的。这种情况,更明显地表现在教育界。早在四十年代,《飘》就进不了美国的中学英语课程和大学的文学课程的教学。直到今天,据我了解,情况仍然如此。相反,同样是一本畅销书,《根》从一开始就被大、中学校所接受。广大美国人民人心的向背,这是极好的例证。
这种种迹象说明,一本畅销书,并不就是一本在文学史上站得住脚的作品。《飘》尽管驰名全球,四十多年来保持畅销而不衰,尽管它的出版者不遗余力要把它塞进古典文学名著的书目,它却始终未能入流,它的地位始终没有超出一本流行小说的地位,终究得不到正式的文学史的承认。
《飘》之不被承认,原因究竟何在?我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来解释。但我推想,一个原因可能是内容太反动——它明目张胆地替声名狼藉的美国黑奴制翻案,名誉实在不佳。另一原因可能是,它在艺术上也不过尔尔。
其实,对《飘》的批判,并不是我们的创造发明。首先指出《飘》的反动本质的是密西尔女士的美国同胞。早在一九三六年这书出版时,在一片捧场叫绝声中,就可以听到比较清醒的声音。有些人明确指出:
“《飘》是纯粹从南部的现实出发来写的”;
《飘》的作者“抱着狂热的地方主义的偏见来写此书”;
“《飘》是种植园传奇的一部百科全书……然而这个传奇一部分是虚假的,一部分是愚蠢的,从总的效果看,对今天南方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是恶劣的……我永远、永远不会说,她写了一本伟大的小说……”。
《美国百科全书》(一九七四年版)在客观地介绍了《飘》的内容后,也加了几句评语:“……把真正的南方人(指奴隶主)写成高尚的、不可屈服的;把北方佬(指反奴隶制北部人民)描绘成恶毒、腐朽的。奴隶制被看成一种仁慈的制度,而黑人则不是极端忠于他们的主人,就是野蛮兽性的东西。这本书是一曲对旧日南部的赞歌,它认为旧日南部是一种具有高度的美、秩序和风雅的文化……”
《英国百科全书(十卷本)》(一九七四年版)说:《飘》是“关于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的小说,是从南部的观点出发来看的”。
《苏联大百科全书》(一九七四年版)尽管赞扬《飘》“有巨大的艺术力量”,但也指出它“把种植园生活方式理想化了”。
可见,《飘》是纯粹站在南部奴隶主的立场上写的,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不应有什么分歧。
谁都知道,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是一个进步,而封建主义对于奴隶制度又是一个进步。美国的奴隶制还不是一般的意义上的奴隶制,它是社会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时特殊条件下的畸形产物,可说是一种社会的返祖现象;它兼有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恶性,因而更为反动。唯其消除了奴隶制,美国社会才会有后来的长足进步。而《飘》则是要把历史往回拉,无怪它为一切进步人类所不齿。
至于《飘》的艺术性,我感到,既然这本书流传了那么久,吸引了那么多的人去读,若说它没有丝毫艺术性,也不符合实际。《飘》是有一定的魅力。它的魅力,我以为,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作者的激情。有激情,就能产生感染力。尽管她所哀叹的那个失去的乐园是非正义的,是建筑在奴隶累累白骨之上的少数人的天堂,然而由于她怀着强烈的奴隶主阶级感情,一往情深地追念旧日的南部生活,给它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氛围,忧伤的情调,这就赋与了它某种诗的境界;她对战争、黑人和北部革命人民的切齿仇恨,又使她把抑制不住的心头怒火倾注在笔尖上。这种强烈的激情,便产生了相当的艺术感染力。然而说到底,这是非正义的激情;正是在这里,感染力愈强,欺骗性也愈大;思想内容的谬误,决定了艺术形式的虚妄,因而这种艺术性是不可取的。
另一方面,《飘》的艺术性表现在几个人物的塑造上,主要是男女主人公斯嘉莱特·奥哈拉(旧译郝思嘉)和瑞特·巴特勒(旧译白瑞德)。这两个人不是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大变革中背弃了失败的旧统治者——奴隶主——的原则而向胜利的新统治者——资产阶级——蜕变的类型,是作者所不齿的。他们不是英雄,而只是“反英雄”(antihero)。作者用另一些“老卫士”的“宁为玉碎”的精神来对比这两个人的极端自利的投机家嘴脸。其实,在小说人物的族谱里,斯嘉莱特不过是利蓓加(萨克雷《名利场》女主人公)的美国姐妹——摹临和翻版。然而她们又不尽相同。萨克雷笔下的利蓓加是个始终一贯的“反英雄”,是讽刺批判的对象;而密西尔笔下的斯嘉莱特则是个自相矛盾的人物,一个具有不可调和的双重性格的人。本质上,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为了捞钱,她没有使不出的手段,没有不能出卖的准则。这种人,不知道爱情或痴情为何物;然而她对爱施利的感情却是那么缠绵,象个情窦初开的纯洁少女。她也不可能有友谊和信义的;然而她临危不惧担着风险救护自己的情敌梅兰妮,却象个义肝侠胆舍己为人的朋友。她本是只图个人发财的小人,对南部同盟的“大业”漠不关心,然而她在“劫后”的塔拉庄园排除万难奋发图强的精神,却表现出真正的勇气和英雄气概。一方面,她寡廉鲜耻地出卖色相,诈骗钱财,粗俗得如同丑角;另方面,她的侠义和英勇又使她象个悲剧中的受难女英雄。然而她绝不是那种复杂、多面的“圆形”人物。她身上这种截然相反、不可调和的气质的并存,破坏了这个人物的完整和真实。(瑞特身上同样也存在着这种矛盾。)看起来,作者原意是要批判一个人物,但在创作过程中却被这个人物迷住了,不由自主地美化了她。因此,就人物塑造而言,斯嘉莱特有她的特色,但总的说来不是成功之作。
总的来说,我并不根本反对这书的翻译出版。相反,我倒认为,象这样一本举世皆知的书,我们没有理由不让读者看到。看看这本书,知道什么叫奴隶主意识,也是从一个角度了解历史。但既然它是这么反动的一本书,在翻译出版和阅读时,应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必要的知识准备。有限度、有引导地出一些,是可以的,但不宜当一本不朽的文学名著来欣赏。
美国南北战争与《飘》的认识价值
肖穆
从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对于美国小说《飘》的评价,几乎没有不说它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据一些评论看,大致有以下几点理由:一、它歪曲了南北战争,把这场革命战争描绘成一场灾难、浩劫,把站在正义立场的北军描绘成一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强盗,把反动的南方军队描绘成慷慨赴义、维护正义的军队;二、它讴歌和美化南方奴隶制庄园,把奴隶制庄园说成是黑奴的天堂,把奴隶主描写成关心黑奴家庭、爱护黑奴的恩人;三、它丑化黑奴,把奴性十足的黑奴称为好黑奴,把跟着北军离开庄园的黑奴称为懒汉、贱骨头、坏黑奴;四、它同情郝思嘉这个奴隶制庄园主的女儿,在失去“天堂”后,挣扎着跻身于新兴资产阶级所作的努力,对她的丑恶灵魂加以美化。这些理由究竟成立与否,很值得研究。
《飘》着力塑造一个被南北战争的疾风暴雨冲毁了家园,而又不甘毁灭,努力挣扎,走向资产阶级化的南方奴隶种植园主中一个女性典型。作品通过她的生活经历,她耳闻目睹的一切,她的行动和思想,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战前南方奴隶种植园的生活,以及战争风暴给南方社会和各种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道德观念所带来的变化。按照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评价《飘》这部作品,一是要看它所描写的人物是否典型,二是看它所描写的人物生活的环境是否典型。如果,它所描写的人物是典型的,作品主人公的生活环境也是典型的,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就可以说它是现实主义的,是成功的。
《飘》的第一章到第七章,描写了郝思嘉去卫希礼的庄园参加大野宴的情景,描写了郝思嘉父亲的陶乐庄园生活,说明郝嘉乐这个奴隶主,从一个亡命之徒变成拥有几百名黑奴的庄园主。这些描写与历史情况是一致的。以下关于十二根橡树庄园大野宴的描绘形象地表现了奴隶主们过的确是“天堂”般的生活。但从陶乐庄园黑人管家阿宝一家的遭遇可以看到,这庄园并不是黑奴的天堂。阿宝是郝嘉乐靠赌博赢得的黑奴,当了庄园的管家,地位已经不同于一般黑奴。但是,他的妻子蝶姐和女儿百利子却是另一个奴隶主的财产,被当作货物在出卖。以后郝嘉乐把蝶姐和她的女儿一起买下了。有的评论说,书中这样写是美化奴隶主。这样的批判是不正确的。郝嘉乐把蝶姐和她的女儿一齐买来,是为了使阿宝和蝶姐能够更一心一意为他卖命,决不是什么“仁慈”、“恩惠”。正好象他说以后再不让自己庄园里的黑小子同别处女人结婚一样,决不是对黑奴婚姻的关怀。须知当时南方有的奴隶主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常常强迫男女黑奴“交配”,甚至强制未成年的女奴与男人“交配”,能说这是关心黑人的婚姻吗?当然,由于当时奴隶主的法律、习惯都允许任意拆散黑奴的亲骨肉,当郝嘉乐把蝶姐和她女儿一齐买下时,蝶姐这个还没有觉悟的黑人自然会把这当作白人老爷的“恩典”。这并非丑化黑人,而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的。
极端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使南方社会陷入重重危机,同时它也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工业在美国的发展,废除奴隶制度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汹涌的浪潮,南方奴隶主为了保住他们的“天堂”,悍然宣布退出联邦,并且发动了武装叛乱。内战的最初两年,由于林肯政府的犹豫不决、妥协退让和将领的无能,曾使南部叛军连续取得了军事上重大胜利,他们更是气焰嚣张。他们中只有少数人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对胜利没有信心,多数人盲目地认为北方是不堪一击的。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扭转不了的,南方的奴隶主终于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物资耗尽了,兵员枯竭了,甚至不得不把老人、孩子征集起来送上前线,以图挽回败局。《飘》的作者对南方奴隶主从叫嚣“教训天杀的北佬”到不得不强令老头儿、小孩上前线的描绘是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历史进程的。读了这些人们并不会因此就认为南方奴隶主是“慷慨赴义”的正义之师。同样,《飘》的作者所描绘的北方军队烧杀破坏的情况,也并不是对北方军队的丑化和对南北战争的污蔑。因为历史的真实正是这样的。为了彻底打垮南方奴隶主叛乱,当时在东线作战的谢里登将军在联邦的“全军大将军”格兰特的允许下,在南方领土上曾采取了破坏政策,指挥西线北军的谢尔曼将军在给林肯总统的备忘录中,也提出要把战争进行到有足够的南方奴隶主、种植园贵族被杀死为止。正是北方军队的恐怖政策毁灭了奴隶主的庄园,同时,随着北方军队的到达,除了少数被奴隶主选作管家、
南北战争的疾风暴雨冲垮南方的奴隶制度,南方的各种人,包括奴隶主和黑奴中间各种人,在这个大变动下,无论生活方式、思想、习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的适应这个变化,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有的感到困惑,无所适从,有的则始终怀念着失去的“天堂”,徒呼奈何,被历史所淘汰。《飘》描绘了郝思嘉这个昔日娇生惯养的奴隶种植园主大小姐劫后的生活道路:从痛惜昔日“天堂”的毁灭到为生存而挣扎,从憧憬往日陶乐庄园的大片棉田到进入城市热中于经营锯木厂,这正是战后南方一部分奴隶种植园主的生活道路,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南方奴隶制的废墟上建立与发展的一个生动的形象。
南北战争也给南方广大黑人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北方大军进入南方领土,黑奴中间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方面是人数众多的从事田间劳动的黑奴纷纷逃离庄园,这些黑奴过去受着最沉重的压迫,白人奴隶主只要棉花种得大,就强迫黑奴无休止地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另一方面是人数很少的在奴隶主家中充当管家、工头、仆役的黑奴。他们虽然也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但由于受奴隶主欺骗与偏见的影响,却往往也看不起作田的黑奴,而庆幸于自己的地位。他们往往忠顺地跟着奴隶主。黑奴中间这种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一八二二年登马克·维赛在组织黑人武装起义时,被他吸收加入组织的都是在土地上劳动的奴隶,因为他认为在奴隶主家庭当仆役的黑人奴隶是不可靠的。《飘》里写到的陶乐庄园黑人管家阿宝、嬷嬷、蝶姐和韩媚兰家的赶马车的老黑奴彼得伯伯正是后一种黑奴,他们是白人奴隶主的忠顺奴仆,他们看不起那些“下贱的”作田黑奴,而自认为身分要高于作田黑奴。
有的评论者对于书中写了阿宝、嬷嬷这些毫无反抗精神的黑奴,便说是丑化黑人。按照这种观点,好象只有把所有的黑奴都写成是有高度觉悟,勇于反抗奴隶主的,才算是正确的。这岂不是违反历史真实吗!
对那些深受剥削、压迫,长期以来又被奴隶主视为最下贱的作田的黑奴,在内战中及战后的生活,《飘》里也作了描绘。书里讲到的解放了的黑奴并没有真正得到什么权利,北方资产阶级最关心的是巩固他们对南方的统治,把选举权给黑人是要为自己赢得选票,而对于黑人命运并不真正关心。贫困严重威胁着刚获得解放的黑奴,把他们再次抛入被奴役的地位。大批黑人涌入城市后,“拥挤在那些龌龊不堪的小木屋里,以致天花、伤寒、肺病一样样地暴发出来”;“自由人局里的人,看见这种黑人愈来愈多了……便又设法要把他们送回他们的旧主人那里去”。虽然作者在写到解放了的黑奴时确实暴露了她轻视黑人的白人种族主义偏见,但书中所描述的这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黑人的遭遇:表面上黑人已经是自由了,但实际上还处在极端贫困、毫无保障的地位。
内战摧毁了南方奴隶制度,但是被打败的奴隶主并不甘心,他们还在伺机卷土重来。他们一方面组织“三K党”进行恐怖活动,一方面千方百计企图通过选举的合法程序夺取南方的统治权。不管作者对奴隶主政权的复辟持什么看法,她所描述的北方共和党人的蜕化、分裂与失败和南方奴隶主政权的复辟的过程还是符合历史的。
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七三年,这是美国历史上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年代,玛格丽泰·密西尔在《飘》这部著作里,通过对主人公思嘉的性格的深刻的刻划和内心思想活动的细致的剖析,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从奴隶种植园主成为资产者的女性典型,同时还生动地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美国南部历史画卷的一个侧面。虽然,由于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作品中还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错误,如对黑奴解放所持的某些白人种族主义偏见等。但就全体而言,它对作品主人公及其活动环境的描写还是典型的,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是现实主义的,至今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我们不能要求作者象写南北战争历史那样全面地叙述与评价当时发生的事件以及各阶级的状况,因为这是文学作品,只能通过对它所塑造的主人公行动的环境的描述来反映历史的一个侧面。我们也不能责备作者没有写出一个反抗奴隶主的南方黑人或白人废奴主义者的典型,而说她歪曲了历史,因为作者的任务就是向读者展示一个奴隶主的女性典型,只能描写她在那个历史环境的活动,而在她那个环境里只能接触到奴隶主、资产者和黑人奴仆。我们也不能象有的评论者所说的,因为作者所塑造的这个奴隶主女性典型的灵魂不美,不值得仿效,就否定作品的价值。因为作品主人公的灵魂美与丑,是否值得仿效并非评价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我们也不能离开对作品的分析而从作品写作出版年代的社会状况来判定它是迎合某种政治需要的,是应肯定或否定的。如有的评论说《飘》是适应美国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间,严重经济危机时,一些南部复辟派作家打算退回到奴隶制农业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因而判定它是反动的。但事实上,作者是从一九二六年就开始写作此书的,她又怎么能预见到几年以后将发生的经济危机呢?
对于《飘》这样一部在作者本国以及国外有较大的影响,至今读者不衰的作品,简单地用“反动”二字加以否定是不妥当的。这里顺带说一下,这部书并不象有的评论者所说“在美国也不过风行一时”,“现在几乎已经被遗忘”。此书出版四十周年时,美、英一些在图书评论方面较有影响的报刊还专门载文纪念,有的评论文章称它的出版是一种“不朽的现象”。在美国,它每年还要出版数十万册。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这样一部作品。
从历史角度看《飘》和《欢乐的节日》
黄颂康
《欢乐的节日》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文学教授玛格丽特·沃克尔(一九一五——)于一九六六年出版的,也是一部以美国内战和重建为背景的小说。作者说这本书是根据她的外祖母口述的真人真事写成的,书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的曾外祖母。小说中说,女主人公薇蕾是个长得和白人一样的混血女奴。她的生父约翰·达登是种植园奴隶主,由于阶级立场和种族偏见,至死不认她为女儿,也不给她自由。内战前夕,薇蕾和铁匠魏尔结了婚。由于铁匠一去七年没有消息,她又嫁给了一个忠厚、善良的黑人农民。内战后,魏尔找到了薇蕾的新家。小说的最后几节描写薇蕾的一篇感人的讲话使她的前后两个丈夫得到和解。魏尔离开了薇蕾的新家,奔向争取黑人彻底解放的新的征途。这部小说是美国六十年代的畅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中译本。
《飘》和《欢乐的节日》这两部著作都以美国的内战、重建为背景,《飘》为奴隶制的覆灭悲叹,把南部的叛乱看成是一场维护州权的战争;《欢乐的节日》却真实地反映了黑人的苦难历史,写出黑人在自己的灵魂深处保存着人类所能具有的最高尚的品德;在艺术上也以朴实、真挚、含蓄见称。有人认为,《飘》虽然歪曲了历史真相,但不能抹煞它的艺术性和文学价值。不过文学和艺术毕竟不能脱离现实而独立存在。一部历史小说在情节上可以虚构,但在精神上必须反映历史的真实。故事的发展虽不必实有其事,但必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发生和发展的可能性,才有说服力、感染力。否则尽管词藻娓娓动听,人物栩栩如生,情节引人入胜,也只不过是“巧言以饰非”。它嘲弄历史,因而迟早会被历史所唾弃。这里,我们想通过《飘》和《欢乐的节日》这两部小说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关于奴隶制的本质
大家知道,奴隶制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剥削方式。可是在密西尔笔下,奴隶劳动制比雇佣劳动制优越,黑人生活稳定,劳动轻松,心情愉快。例如奴仆总管阿宝“这几年来过惯安逸舒适的生活,从没有人管束他,因而也把骨头懒掉了。”(第57页,引文均见傅译本,下同)思嘉的乳母黑嬷嬷更是受到全家极大的尊敬和信任,主奴关系亲密无间,以致于谢尔曼大军打到亚特兰大的前夕,思嘉家里的几个奴性十足的忠仆竟恶毒咒骂参加解放战争的黑人是“下流坯子”,宁愿和主人共患难,维持旧秩序,不愿获得自由(第482,491,801页)。
《欢乐的节日》则以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血泪叙事,揭穿了关于奴隶制的谎言。小说以薇蕾的母亲黑人女奴赫塔的死亡为序幕,揭开了薇蕾苦难的童年和坎坷身世。薇蕾七岁时被送到奴隶主(她的生父)的大院开始奴隶生活的那天,就目睹了一个刚买来的奴隶男孩得鼠疫而死的惨景,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奴隶共同命运的永久伤痕。两星期以后,薇蕾由于打碎太太的精美磁器,被太太用皮条吊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间里,由于惊怖痛楚而昏死过去,直到被她的生父解救下来。
生活在奴隶主的大院里,薇蕾目睹了奴隶主对奴隶种种灭绝人性的迫害事件。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凶残、横暴和贪婪的奴隶总管格兰姆斯的形象。他对奴隶操有生杀予夺之权,他的管理方法就是鞭笞、酷刑。他枪杀了不顺他心意的黑人马车夫。他活活烧死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田奴……奴隶主约翰老爷虽然表面上“宽厚”,但归根到底他和奴隶总管的分歧不过是一个要给奴隶些许的喘息机会以便长期榨取劳动果实,一个则不管奴隶死活只顾完成眼前任务以换取主人的信任和奖金。这些描写和进步史学家根据大量有关种植园的原始资料和文献所写成的著作是一致的。
二、关于逃亡奴隶
对奴隶制本质问题的不同看法决定了《飘》和《欢乐的节日》对逃亡奴隶问题的对立观点。《飘》矢口否认奴隶逃亡的事实。女主人公思嘉下面这段言论,就是作者抹煞奴隶逃亡史实的奇文:“那些北佬女人从前听说南方地主家都养着凶猛的猎犬,以备追逐逃走的黑奴之用,便都信以为真……他们又问到那种给农奴脸上烫字的烙铁,以及那种虐打农奴用的九个齿儿的铁蒺藜,其实南方地主并没有这些东西,都不过是北方人宣传的资料罢了。”(第795页)
与此相反,《欢乐的节日》正确地把逃亡奴隶问题作为奴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书中描述了巡逻队带着一群猎犬在沼泽地追捕逃亡奴隶,以及猎犬将逃奴撕碎的惨景;女仆路西逃亡被捕后脸上被烙逃亡字母R的残暴场面;还有路西在同伴帮助下巧妙地掩饰了脸上的烙印第二次逃跑成功的英勇事迹;薇蕾的第一个丈夫魏尔的逃亡以及薇蕾为了追随她的丈夫带着两个孩子逃亡的失败。奴隶主约翰·达登并没有因为薇蕾是他的亲骨肉对她“怜悯”、“宽恕”。为了维护奴隶制度,杀一儆百,薇蕾受到专门雇来施刑的奴隶看守疯狂的鞭笞,被打得血肉模糊失去知觉。
美国内战前四十年的南部报纸,几乎每天都刊载着成版的缉捕逃奴广告,广告中对逃奴特征的描写又几乎照例都有奴隶脸上的烙印,胸、背部的鞭痕、伤疤等记号。还有广告出售经过特殊训练专为追捕逃奴用的猎犬!这些历史见证,充分说明了《飘》的虚伪性。
三、关于内战的性质
马克思说过,美国内战是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斗争,《飘》显然是反对这个论断的。它认为战争“实在并不是为黑奴的……黑奴不过是一种借口罢了。”(第308页)它用整个一章的篇幅描写一次南方奴隶主为支援前线而举行的募捐舞会。当乐台上奏起《美丽的蓝旗》一曲时,台下顿时响起了几百人的合唱:“哈拉!哈拉!为着南方的权利!哈拉!哈拉!为着美丽的蓝旗,要那一颗星儿长明不灭!”(第196页)
作者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竭力丑化低毁联邦军队。说什么“……人人知道北佬对孩子们的残暴是比对妇女还要利害的”(第388页),说北佬要强奸女人,拿刺刀戳小孩的肚子,放火烧杀老年人……”(第399页)作者把谢尔曼海洋进军这样一个对南北战争胜负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行动描绘为毫无目的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北军打到琼斯博罗附近思嘉的老家陶乐时,“刹那之间,她记起了饿狼陀(亚特兰大)最后一天晚上的恐怖了,记起那些沿路已成灰烬的人家了,记起一切关于强奸、虐害、屠杀的故事了。”(第544—545页)
《欢乐的节日》则对内战的正义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真实的描写。特别是对北军少将宣读《解放宣盲》的庄严场面写得极为生动感人。书中描绘道:“一八六五年五月的一个早晨,恰似雷声隆隆,乌云滚滚——原来是谢尔曼部下的一支骑兵奔驰而来,在鼓声和军号的伴奏下他们引吭高歌。”这时达顿种植园的老爷、少爷已经从军战死,太太也因惊忿去世,只剩下莉莲小姐和两个女黑奴以及薇蕾和她的两个小孩。少将对莉莲小姐说:“我奉命要你所有的奴隶集合在院子里,当着你的面并在这些士兵的见证下,向他们宣读《解放宣言》。”当薇蕾在冗长的文件中听到“将要……永远自由”这个神奇的字眼时,好象坠入了幻梦般的境界。当文件刚读完,薇蕾十岁的男孩立刻激动地抓住他的六岁的妹妹一面跳舞,一面用黑人土语唱起歌来:
“你自由了,你自由了1
米娜你自由了!
你象一只展翅的鸟儿一样地自由了!
啊!欢乐的节日,你自由了!”
四、对三K党的评价
这个问题最能暴露《飘》的反动性。三K党是内战结束后在南部形成的一个法西斯地下王国,但是《飘》却把三K党装扮成保卫白人妇女的侠义团体。整个第四十五章描写了三K党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小说中所有的“真正的南方人”都参加了三K党:媚兰、希礼,以至连思嘉的第二个丈夫——那个“向来精神萎靡,无所作为”的甘扶澜——也是三K党员,而且为了给自己的受了黑人袭击的老婆报仇,“光荣殉难”。
《欢乐的节日》对三K党的暴行不但通过艺术处理使之再现,并且指出三K党的本质和目的在于阻止被解放的黑人参加政治活动及投共和党的票。小说描写了魏尔由于参加共和党的政治集会被三K党暴徒打得半死。在昏迷中魏尔听到他们一面乱打一面咆哮:“黑鬼,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自以为和白人一样,和白人平等了,穿着白人的衣服出入州议会大厅,还想占有我们的好地。你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一钱不值的黑鬼吗?我们知道怎样对付象你这样一个得意忘形的又大又丑的黑狒狒。”薇蕾和她的第二个丈夫英尼斯·布朗为了在解放以后获得一片未开发的土地安家立命,历尽千辛万苦建造的一所比较宽适的家在一个晚上被三K党放火烧掉了,全家人仅仅由于碰巧出外才免于烧死。三K党的肆虐是南部重建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魏尔最后不得不退出政治活动,他愤怒地控诉道:“三K党在南部各级政治中都有代表。他们在参议院中有席位,……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回到奴隶地位,或者把我们杀死,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意图。”
五、所谓南部文明问题
南部种族主义者把奴隶制说成是南部文明的基础,并且把这种建筑在黑人白骨之上的物质文明用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掩盖起来。为奴隶制招魂的《飘》念念不忘的是宴会、跳舞、游猎、赛马、决斗、争取州权、鄙视“北佬儿”、炫耀自己的奴隶财产……再加上温文尔雅的风度——这就是南部自豪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欢乐的节日》则以淳朴的语言,揭露了南部文明的吃人本质。其中最精采的片断为女奴赫塔之死。这里描写了奴隶主约翰·达登对赫塔一生的回顾:父亲把赫塔给他的时候,“她看起来象一个从刚果来的非洲女王。她的脖子细而长,头抬得高高的。他想,也许她幻想自己是在非洲充满棕榈树和瀑布的丛林中,颈上带着金圈。”赫塔还是个女孩时就作了少爷的牺牲品,就是在少爷成婚以后,赫塔也还是他侮辱和损害的对象。赫塔在无言和忍泣中度过了十几年非人的岁月,她死时年才二十九岁,却已生了十五个小孩。这里面蕴藏了多么深刻的悲哀,多么炽烈的愤怒!然而,这一切却是南部“文明”认可的,算不了什么罪过!
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飘》和《欢乐的节日》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前者继承了美国种族主义的史学观点和文学传统,而后者则继承了美国废奴主义史学观点和进步的文学传统。我们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时,必须全面了解这一作品的主题思想,研究作者的思想观点,认真选择。忽视作品的思想性而盲目推崇某些作品,将会产生不好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