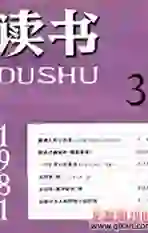王蒙的《海的梦》
1981-07-15木令耆
木令耆
我曾经写过,中国小说的形式至今仍旧受“小说”这两个字的限制,跳不出一种“你一句,我一句”的圈套。最近,我却有惊喜的发现。那便是王蒙的近作:《蝴蝶》、《海的梦》、《风筝飘带》。其中《海的梦》尤其突破旧传统的小说形式。
王蒙的小说多是叙述式的浪波,也带有海潮的节拍,有高潮也有退潮,一个又一个浪头打来,忽而浪花溅飞,随后等浪退了,海岸又恢复平静。
《海的梦》故事的历史背景是:“作为一个搞了多半辈子外国文学的研究与介绍的专门家,五十二岁的缪可言,却从来没有到过外国,甚至没有见过海。他向往海”……“五十二岁了,他没有得到爱情,他没有见过海洋,更谈不上飞翔……然而他却几乎被风浪所吞噬”。……“当他因为‘特嫌和‘恶攻而被投放到号子里的时候,当铁门哐地一声关死,当只有在六天一次的倒马桶的轮值的时候,他才能见到蓝天,见到阳光”……“还有什么‘特嫌、‘恶攻、‘反标这些古老的汉语的生硬的缩写,出现了崭新的不通的词汇,但他感谢这种离奇的缩写,它给那些荒唐的颠倒涂上了一层灰雾……”。
这故事的主要精神主题是“他向往海”此四个宇。可是,令人惋惜的却是“故事情绪”——“大海,我终于见到了你……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思恋,经过了许多磨难,你我都白了头发——浪花!”……好一个浪花!“然而,激情在哪里?青春在哪里?”
故事的主角缪可言来到海滨的疗养所,他终于看到了海,又投向海,因为“大浪激起了他的精神……面对着威严地向着他扑来的又一个浪头,又一次把头低下,冲了过去。……就在他兴高采烈地几乎自诩为大海的征服者,乘风破浪的弄潮儿的时候,他的左小腿肚子抽了筋。………他愤怒了,他不情愿,他觉得冤屈。于是他奋力挣扎。……没有被江青吃掉的缪可言,也没有被海妖吞噬”。在这上面他用的文字是既具体又超具体的形象化,如“大浪激起了他的精神”,“乘风破浪……小腿肚子抽了筋。”不但文字上有“实与虚”的对比,在故事的情节上也有此对比——“没有被江青吃掉的缪可言,也没有被海妖吞噬。”如此的对比,其实也是作家创造的结果,事实形象化,具体事物经过抽象的幻想而升华到另一艺术境界,因此突出的艺术作品,都常有它的“诗意”。
王蒙的“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条水平线……限制了他的视野,真象是‘框框的一个边。”海是被向往的自由,也是自由的障碍,这也是故事含蓄的矛盾。这也是生命的矛盾对比——自由与限制,青春与衰老,生与死。但是,面对着这种矛盾对比却是一阵海浪式的冲动魄力,“一到这时,他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脱下衣服,游过去”,“不管风浪、不管水温、不管鲨鱼或是海蜇,不管天正在逐渐地黑下来……”对着矛盾冲锋!这是王蒙的创作精神,《海的梦》便是这精神的使唤者,招魂者,为了“向往海”的梦,憧憬的、俱往的“青春”、“爱情”追索着——“啊,我的充满了焦渴的心灵,激荡的热情,离奇的幻想和童稚的思恋的梦中的海啊,你在哪里?”
“可是,缪可言已经过了作梦的年纪!”他年已五十二,已经过了“激情”,“跃跃欲试的劲头”,“欢乐和悲痛的眼泪的热度在哪里?”这样,“他找不到一个游泳的伴侣。”“那无法变成二十五的五十二个逝去了的年头!”所以,“他想离去。梦想了五十年,只呆了五天”。是的,缪可言只在海滨呆了五天,他找寻不回青春的梦呢。在这疗养所,有栽着的许多花,有好的伙食,也可望海,可是“那么,他究竟缺少了什么呢?”他坚持要走,“他好象长大了,不愿意守着母亲生活的孩子,在向母亲请求宽恕。就走了,他说”。他悟到那遗失掉的青春,那孩童的梦,因此他将过去遗留在海滨疗养所,他已成长了,不须再向以往的梦留恋。
在离去的最后一晚,他又悄悄一个人走到海滨向“海的梦”告别,这偏偏是月夜。“一切的是一片浑然的银光……海在他即将离去的前一个夜晚,装扮好了自己,向他温存、向他流盼,向他微笑,向他喁喁地私语。”缪可言的海此时是他青春时的爱情,他追不返的爱情,可是他却不禁叫喊出:“海——呀——我——爱——你——!”当他终于呐喊出心中的渴望和失望,他的呐喊也惊动了在海滩上的一对青年男女。“他非常懊悔,却又觉得很高兴……海和月需要青春,青春也需要海和月。”
缪可言开始感到兴奋,他的失望也变为希望,“他看到了在他刚离去的岩石下面,似乎有两个人在游海。难道是那两个青年下去游水了么?他们不觉得凉么?他们不怕黑么?……喔哟,看,那两个人已经游了那么远,他们在向着他向往过许多次,却从来没有敢于问津的水天相接的亮晶晶的地方游去了呢?”
他此时的小我化于天、海、人的大我中,他看到他“海的梦”,自己遗失了的梦被两个青年人追求着,比他更勇猛的向往冲着海阔浪波游去。“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
王蒙的小说不但在形式上突破,在创造精神上也突出,这里看不到危危一息的古国,也不是漠然妥协,将就过去的涂几笔故事轮廓而已,也不是“一把辛酸泪”,更不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里不是小家碧玉的诉泣,小题大作的故卖情节,又无真正情节的“小说”故事。他的小说突破“故事”框框,并不是他学了些什么洋泾浜“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他没有让他的小说戴帽子,而是在文笔上、文字上、形式上、感情上放松的写去,如海浪海潮的冲打过去。但是如果他没有“海量”的幻想力,既是放松了,也滚不出海潮来。他的幻想力有出奇的浪花,他的文笔又带着向浪头冲游过去的力量,但是最突出的是他勇于跳入大海,让创作的精神在无边的惊涛上荡浪,当幻想力的浪潮退了,当一个小说框框的海潮收缩时刻,他的幻想创作力停止时,也是这小说结尾时。王蒙的小说没有出奇的幻想风云,创造的血液足,精力沛,这种小说出于流落新疆二十年的作家,表示中国人的不灭精神。王蒙的小说达到现代化,比中国的科技还更早一步。
(王蒙:《海的梦》,原载《上海文学》一九八○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