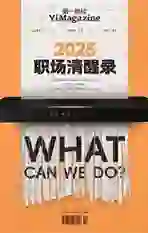林垚:心有余力的人要尽可能地多做一点点
2025-02-19林垚

Yi:YiMagazine
L:林垚
01
Yi:你曾经说过,“对男性而言困难的不是读多少女权主义理论,而是有没有做到。回头来看,之前没有做好。”当时发生了什么,让你产生这样的反思?
L:不仅是一件事情,回头去看整个人生,总会觉得我之前可能有什么做得还不够。你会发现很多人把女权主义理论说得很好,但在日常生活中反而还不如一个没读过多少书或者看起来很保守的人参与到家务、育儿的程度高。我爸爸初中都没有读完,但他会主动做家务。我上大学后去拜访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到了他们家发现都是师母在做饭,男老师就翘起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跟你讲大道理。我非常震惊,在家里居然可以有人颐指气使,这和我从小的成长经验是不一样的。
02
Yi:阅读《空谈》和你其他面向公众写作的文章,能感受到你有很鲜明的判断、观点,这和其他学者所写的面向公众的文章不太一样,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写作风格?当你强调规范论述的重要性,不希望简化问题,与主流的观点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时,这种坚持有没有令你受到两边的攻击?
L: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曾经有一段时间读过很多社论、时评,那些时评写得很畅快,里面有很多排比、比喻,但是读完后你不会觉得他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很多时候这些社论是打马虎眼的,我上大学时就觉得很不满意。而这些时评慢慢衰败的原因,除了审查、阅读习惯的改变,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作者的说理非常粗糙含混,不够细致,他们可能对具体的政治生活中的复杂面相、知识有结构性缺陷,很容易被人抓到把柄。所以如果真正要跟公众对话,我认为必须要把很多东西讲清楚,而不是为了追求畅快、追求篇幅上的简洁而牺牲掉这些部分。我觉得论证和思想的传播本身更重要。第二个问题,任何参与公共讨论的人都会在某些时候遭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有些人会很洋洋自得地说,你看我被左边、右边的人攻击,可见我多么遗世而独立,可见我们的思想多么超脱于党派之类。但我觉得除非你真正站在了光谱的最极端,没有人比你更左或者更右,否则你肯定左边有人,右边也有人。所以要心态放平和,如果要参与公共讨论,尤其在网络时代,网络会让你的声音更容易传递到无数不认识的网民那里,所以做好心理预期,只重视那些有理有据、能够促进你思考的东西,无视某些比较无效的攻击、谩骂,做好自我的心态管理。
03
Yi:你的妻子在给《空谈》写的序里,提到阅读你的文章让她“卸去玫瑰色眼镜”,对民主的理解超越“聚众成一”式的宣言。你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自己创建《选·美》这个播客节目的初衷,是代替之前中文舆论圈里流行的关于美国的浮光掠影、理念先行、想象代替事实的叙事。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大家的观念究竟是在被什么影响?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能轻易地找到“同声相应者”,并且笃信自己是清醒的那一拨。声浪大的人占据了更多地盘,其他人也有吃有喝。“掰扯清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吗?
L:掰扯清楚当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从个人的角度说,参与公共讨论需要个人付出很多的事情。但参与公共讨论就是这样,如果觉得吃力不讨好,觉得累了,也可以退出。我也没有觉得自己一直100%投入在做这些事情,我自己也会有觉得疲劳、时间精力不够分配的时候。包括最近这几年,在写作上我其实就倦怠了,基本没有怎么写东西。当然,主要是因为时间、精力不够分配。但我也不觉得好像我自己退出了天就塌下来了。肯定会有其他愿意做这些事情的人继续参与。如果他们累了,可能有别人再顶上去,或者我缓过劲儿了,我再参与下去。
但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困境。如果每个人都觉得吃力不讨好而不付出,那公共讨论的质量就会更加下滑,你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就会更加难受。所以心有余力的人都尽可能地做一点点,也许这个环境会变更好一点。当然,在这背后还有“房间里的大象”,大环境在政策、网络算法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大框架上都限制了公共讨论的质量和方向。也许在水质越来越糟糕的池塘里扑腾会越来越困难。
04
Yi:讨论空间越发逼仄,极化也是全球性的现象。你在书中提到特朗普的登台部分原因是打破了党内狗哨政治的潜规则,温和派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但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看待现在的处境?
L:可能是很多因素正好凑在了一起。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有可能在某些问题上走错方向,加剧国内的经济焦虑或者贫富分化,老牌民主国家内部的问题也在加剧。很多国家出现的极化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文化霸权的体现,美国的右派采用的挑起文化战争的方式会很快被其他国家的右派模仿、习得,那些国家会慢慢采用同一套话语方式去讲述某些议题,或者把某些本来不应该有的议题变成一个重大的议题。
包括中国有些男性网民对杨笠的抵制,他们采用的很多话语都是来自于美国的非自愿单身男性社群—美国有一些男士觉得女人看不上他们,他们被社会抛弃了,他们对社会、女性有很大的怨恨,这样的群体在过去十几年里壮大得很快,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构建了一套话术分析社会现象。这些话术经过多轮的转移和演绎在网上传播,中国男性网民讲的东西一点都不新鲜,也是从美国那些社群中演变来的,所以这个过程中,互联网的存在加速了传播。
05
Yi:你的求学经历横跨生物、哲学、政治学和法学四个领域,关注的方向包括身份政治(性别、种族、民族)、政治哲学等,此外你还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公共写作中,从功利角度看这是不是对你在学术领域的发展不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做?
L:也不是说天天都在做公共写作,因为我现在很大部分的精力是放在论文写作上的,考虑到晚年不要太凄凉,你要努力在学术阶梯上够到一个比较稳固的位置。如果完全不做公共写作,可能早在几年前我就已经拿到长聘副教授。当然,我喜欢做学术研究,也喜欢在大学里面教课,但是除此之外公共写作是我热爱的事情,我也想做很多别的事情。中间有段时间我放弃了自己的学术事业,在家带孩子,后来等到爱人博士毕业,稳定下来,我觉得我可以重新回到这条道路上。这个过程肯定要比别人慢很多,有人可能很在意,但我也不是很在乎。人就活这么一辈子,我还是想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06
Yi:你有想过先集中精力拿到副教授职称之后,再把精力都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中吗?
L:这是很自然的想法,很多人也曾这样说。但很多时候,你一开始想好这几年要为了无意义的KPI奋斗,可能已经反映出了拿到教职后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曾经有很大的理想,觉得真的拿到职称后要敢说话,只是要先低头。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被系统规训,等到六七年之后,你已经习惯了做一个伏低做小的人,你不会再为更年轻的学者说话,你不会再为其他的公共事务说话,你已经习惯了谨小慎微的方式。
而拿到最高职称也不意味着一切的完结,你还要维持在这个领域里的声望,不然很快会被人遗忘。方式就是继续提高发文数量,这只能通过发一些容易“出活”的东西,也就是你可能一开始觉得没有意义的东西实现。国内很多高校在你拿到正高职称以后还要三年一评,如果没通过就要降级或者降薪,你需要拿项目;美国的学术系统虽然没有这么严格,但是也会在你成为终身正教授后把行政事务匀给你,这也很耗时间。如果你不愿意做,学校可能会因此削减你的研究经费。
07
Yi:之前的采访里,你提到2015年左右,在海外求学那段时间,对学术界的知识生产机制产生了很大的质疑,一度身体出现抑郁,直到在线下做一些法律援助的工作才开始好转,所以帮助你的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在寻求什么样的“意义感”?
L:对我而言,金钱、名望、地位都没有什么意义。看到学术圈里有些人长年累月靠生产学术垃圾,也就是对世界其实起不到什么帮助的东西在这个学术体制内不断往上爬,我就觉得比较绝望。所以法律援助当时是一个自我拯救的手段。看到自己在切切实实帮助身边有血有肉的人,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而非虚耗人生,也是很多人很强烈的内在自我需求。
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连接—你希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让身边或者更遥远的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一点。所以不管是法律援助还是公共写作,还是真正在学术上推进一些更新的思考和讨论而不是纯粹为了写论文,我觉得都是可以产生意义感的。只不过在我自己觉得特别绝望、特别抑郁的那段时间里面,我需要一种更加切身,看得见摸得着的,短期能够出效果的意义 感。公共写作、学术产出的反馈是更长久的。一篇文章从开始写到投出去到发表,再到有读者被这个文章打动或者能够推进讨论等,周期很长。但是做法律援助你可以不断跟进案件,每时每刻看着这个案件发生变化。案子如果打赢,会对被援助的对象有更直接的改变,能够看到他们生活上的变化。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对我有很重要的救赎作用。
法律援助和公共写作、学术研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每个人性格不同,热爱的东西不一样。
对有些朋友而言,做法律援助是能够支持他们一路走下去,走完这一生,获得根本性意义感的事业。但对我来说,写作和教学是我获取意义感的源泉。
08
Yi:作为1980年代从福建小县城成长并经历1990年代父辈下岗的典型的一代人,你对个人命运怎么看?“感同身受”是不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你觉得你的学生这一辈人跟你自己有很大的不同吗?
L:个人命运当然要看历史机遇。很多人说靠着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时候,其实背后都预设了某种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大背景。包括改革开放的前二三十年,社会阶层还没有重新固化,像我这样的小城镇的、农村的年轻人,有了上好大学的机会,仅仅靠读书好像就可以完成阶级跃迁。但这是要时代允许才可以的。
换一个时代,经济甚至社会条件发生变化,阶层越来越固化的时候,对像我这样出身的孩子,这条道路就越来越窄了。而且在我们考上好大学、走出小镇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在我们身边的人是被时代牺牲掉的,他们做了其他人的垫脚石。比如我下岗的父母,我身边很多人也经过了很多挣扎浮沉。所以我早早就跟那些自由主义派别里宣扬“一切都可以靠个人奋斗,你不行都是你不努力”的人分道扬镳。
回头来看,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幸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会让我保持一种自我警惕:是不是忘记了和我从小接触、一同成长的那个群体,忘记了和他们共情?是不是离他们太远了,离开太久后就忘记了他们的处境?我讲的一些自然而然的道理,他们会不会因为缺少相应的社会化过程,很难真正习得或者接受这套话语?
我能够理解当代的学生,那些躺平的年轻人。政治、经济大背景都发生了变化,经济上大家越来越看不到出路了,1990年代的那种心气现在越来越难看到了。但是大家也很迷茫,因为有很多话不能讲,也有很多人不会意识到很多话不能讲,因为他们可能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各种规训是更加严苛的。现在比较年轻的孩子们,我接触的其他高校的一些学生们,他们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比我们那时候更强烈地内化了某套宣传话语。想从这中间挣脱出来,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机遇。政治、经济上的双重桎梏,确实会对时代风潮造成影响。当然,每一代人内部的差异我觉得都远远大于代际之间的差异。
09
Yi:你在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内地都教过学生,在你看来,国内的学生跟其他地区的学生相比有哪些不同?
L:我们学校是全英文授课,所以学生需要读的东西跟国内高校非常不一样。我比较开心的一点是学生有很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同时也想要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这是很难得的品质。你读那么多理论,还要能把它跟现实关切、现实发生的事情挂上钩,这非常重要。而我在美国教的学生,他们思想也很活跃,上课时也愿意发言,但他们眼里只盯着美国,觉得这个世界只有美国,很多时候我会觉得他们的盲区非常大。
10
Yi:如果让你预测未来10到20年,你觉得我们普通人的整体际遇会是怎样的?应该怎样规划自己?
L: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别说让我回到20年前,5年前我都想象不出现在的样子。我觉得把日常中能做好的一点一滴做好,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遵从本心就好了。你不可能做到事事保险,在做人生规划时你当然可以选择一条非常保险的道路,但你的人生会因此少了很多可能性。就做自己最感兴趣的、最想要做的事情,走最想探索的道路就好,其他的东西船到桥头自然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