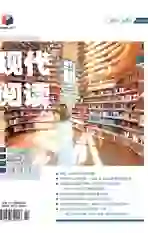1946—1947年民国书业免税事件始末
2025-02-16褚浩源贾欣然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第二年,百废待兴,中国社会需要恢复并发展文化产业,但国民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决定加征税赋,出版界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情绪。发生在1946年年底到1947年的民国书业免税事件,正是在经济重建时期,行业与政府之间的一次博弈。最终,出版界争取到了部分税赋的减免,缓解了行业压力,让战后的文化产业发展得以喘一口气,但对于当时的出版业来说,更像是一针安慰剂,对于整个行业的衰退局面于事无补。
本文根据1946到1947年间的新闻资料,采用文献分析法系统梳理1946到1947年民国书业免税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其影响,旨在全面讲述战后出版业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呈现出这一事件的完整脉络,探讨其意义与影响。
战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全方面重建的艰难时期,国共两党的争端在战后又浮现于水面上,解放战争爆发在即。战争和冲突严重影响了基础设施与工业建设,导致国民经济萧条,人民生活艰难。国民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需要通过税收来补充财政,文化产业里的出版业更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出版业在此期间的发展情况,可以从书籍的出版量窥见一隅。1941年全国出版图书1890种,1943年为4408种。在抗战艰苦困顿的环境之下,图书出版量还能有如此大幅增长,令业界对出版业的未来抱有期待。然而1946年,统计数据却骤降至1461种。 [1]这无疑给出版界的期待泼了一盆冷水,也证明出版业确实在这期间遭遇了困难。
出版业面临的困境
“文化中心,印书不易,穷乡僻壤,读书更难。”这是《大公报·出版界》副刊中,出版界人士对于当时的行业困境所作的评语。 [2]这句话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战后中国出版业所面临的双重挑战:在政治经济中心,物资匮乏导致印刷生产成本高昂,印刷出版书籍已不是件易事;在偏远地区,受交通、经济限制,想要购买书籍更是难上加难。
当时的出版界,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便是书籍印制成本的提升。印刷设备与技术的相对落后,以及纸张价格、工人薪酬的不断攀升,使得一本书的出版成本高昂。面对这一窘境,很多有设备而无资金的出版企业都将目光投向了有利可图的商业广告品印制上,导致很多优质刊物夭折,出版商面临亏损和倒闭。 [3]当时民众消费能力的低迷也对出版业的发展构成影响。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解放战争又笼罩在刚获得和平不久的民众头上。书籍购买力的虚弱导致出版商不得不减少同一批次书籍的印制数量,这反过来又导致书籍印制成本的进一步
上升。 [2]
筹集资金又是一道难事。面对出版业的衰颓之景,有心出版之人无力筹集如此之高的资金投入,即便是拥有足够资金的人也会为较长的回本周期而再三犹豫。私人资金难觅,政府当局对各行业提供的粮贷、盐贷、茶贷等资金支持主要集中在基础民生行业,对于出版业提供的支持仅限于教科书,导致部分出版人士只能无奈借助高利贷筹得
资金。 [3]
此外,书籍的流通困难更是一大难题。战后一些基础设施虽得以修缮,但城市之间的通行仍较为不便,且战争的风险也时刻威胁着交通。书籍从大城市向外埠的邮寄费用较为昂贵,使得小城市、乡村与偏远地区获取书籍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
迫在眉睫的危机
1946年底,出版业持续衰落、岌岌可危已是业内人士有目共睹的事实,原因离不开国民政府针对出版业的严厉征税与邮寄费用的屡次提高。这些重担不仅引发了出版业从业者的广泛不满,也直接威胁到了文化传播和教育出版。出版商、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出版业行将垂毙,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书籍,特别是教科书的价格会大幅上涨,将对文化传播和教育普及产生深远且长久的负面影响。 [4]
为应对这一严峻情况,出版界迅速团结起来,向政府就出版业税赋过重一事发起强烈抗议,请愿的内容是书籍因特殊性应当得到政策上的税收豁免。出版家、作家、翻译家徐调孚在《大公报·出版界》书税特辑中明确指出五点理由:
1.出版业和其他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业不同,担负有推动文化进步的使命。向书籍征税就是向精神征税,政府应予以免税,以示扶持文化事业的本意。
2.“捐税转嫁”是一般商业的共通原则,出版业的对象为学校或个人,购书后均直接使用,不像其他商品有再度贩卖之举。政府不应针对出版业的对象再度征税,而挫伤人民学业积极性。
3.上海出版业在抗战期间损失惨重,然战后物价水涨船高,成本倍增。政府若能免税,可降低出版业压力,书价降低从而有益于文化及经济。
4.营业税向来是地方税,由地方政府决定收缴与否。上海市参议会已于1946年9月决定免征营业税,中央应当尊重地方的决定,免征营业税。
5.财政部于去年(1945年)10月起对粮食业免征营业税,书籍作为人民的精神食粮,政府应一并豁免书业营业税的税赋。
书税特辑
在出版界及诸学者、知识分子共同为免征出版营业税而奔走之际,当时的行业“期刊”《大公报·出版界》副刊也连续多期刊登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文章,并于1946年12月15日推出了书税特辑,专门报道当时的业界焦点—书税减免一事。
书税特辑一期共五篇文章,有两篇直接呼吁免征营业税。如翻译家、作家姚蓬子的《请从免征书业营业税做起》,通过详细分析图书出版的盈利体系,表明书业盈利本就微薄,再无力缴纳更多税赋。文学家、编辑范泉的《为书业界呼吁》论述具体反对征税的原因,并号召出版从业者、文化工作者与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团结起来支持书业。徐调孚的《书业的免税运动》为读者详细讲述了书业免税事件的前因后果,同样也给出了抗税的缘由。文学家、出版家孔另境撰文《也算是“苦口婆心”》,用真实的上海书业现状为例,劝说国民政府减轻出版税赋。此外还有编辑、作家潘际坰的《英国怎样击退书税的?》一文,详细讲述了1940年英国出版界与学者、知识分子共同反对英国政府为应对战时需求新征书籍购买税并取得胜利的过程,启发当时的民国出版界、学者与知识分子共同反对书税。
英国书业免税运动情况
对于民国出版界而言,最好的结果莫过于能争取到与英国同僚相似的结果。1940年6到7月间,刚刚历经了在法国战场惨败与敦刻尔克撤退后,英国财政部提出了一项新的税务改制议案。提案中包括对书籍增收购买税,从而提高财政收入以应对战争。但这项提案一经公示便引发轩然大波,书商、作家、社会名流等奋起反对。
对于这项议案,有的驳斥者认为会影响教育系统,从而危害到人们获取知识的能力;有人认为加征税应根据商品种类加以区分,不能对书籍和马靴征同样多的税;更有人提出书业利薄,如果贸然加征新税,很可能导致整个产业走向衰败。英国各大报刊也纷纷对新税提出质疑:书业即便加税,所得也并不多,如若为了这蝇头小利而破坏英国文化产业发展,其后果会与战争失败同样糟糕。
不单是业界舆论,这项提案在议会中,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有一百多名议员反对这一提议,社会名流诸如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科学家亚瑟·斯坦利·爱丁顿、剧作家乔治·伯纳德·萧等纷纷支持抗税运动。英国文化界在伦敦文具厂进行了四五天的会议后,决定向财政部联名呼吁请免书税。最终,英国财政部撤回了这一提案,出版界得到了完全的胜利。这是英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胜利,更是面对他们的敌人、焚毁书籍以控制思想的希特勒纳粹哲学的胜利。 [5]
进京请愿
1946到1947年间,在英国业界同僚的激励下,民国出版界联合学者、知识分子一同向国民政府发起数次请愿。
第一次请愿是由上海市书商业同业公会几家领袖,于1946年春委托中国民主同盟委员、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沈钧儒,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中国民主同盟第一任主席黄炎培等著名民主人士,联名向国民参政会致函,提议给予书业免税,但因未收到政府答复而不了了之。
第二次请愿仍是同业公会方面出面。1946年11月,由公会理事长、商务印书馆经办人李泽彰牵头,同公会理事长郭农山等十余人前往南京请愿。一行人先后拜访了国民政府财政部、经济部、教育部和财政部直接税局等有关政府部门,提请书业免税事宜。面对出版界汹涌的民意,各部门部长均表示同情,国民政府也对减免书税这一事有所重视,但能给出的答复仅仅是国定本与教育部核定的教科书免税,其余书籍照常征税。
出版界对于这一结果并不接受,决定紧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进行商讨,会议决定于12月24日第三次派出代表团进京请愿。而就在第三波请愿人士动身之际,国民政府财政部突然下达指示,表达前一次请愿情况已收到,财政部已经给予了缓征宽待,并说明:“书业关系教育文化至为重要,而战时书业损失奇重,一时恢复不易自属实情。为推行国策维护文化事业起见,对于书业有予以扶持必要。”但同时财政部也指出书籍种类繁多,并不是所有的书籍都是重要的,一律免征营业税未免有失偏颇,更会引起其他行业争相模仿请愿免税,影响税收。财政部承诺尽快给出答复。
对于财政部的让步,出版界并不满意,认为业界所出版书籍,无论题目皆有其价值、不分轻重;对于财政部担心其他行业效仿的解释,提出英法各国对化妆品业课以重税,但不曾听闻化妆品业因为英法书业免税而有异议。是以在公会再度商议后,原已准备动身的第三波请愿代表稍做休整,改定在1947年1月2日再度赴京,向财政部表达工会对于免税需求之迫切与必须。 [6]
请愿结果
最终,财政部在1947年1月6日颁布了减免书业税的新政策,出于出版业关乎教育文化事业,较其他行业而言有其特殊性,做出了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大学课本等书籍免税,其他书籍营业税减半的决定。 [7]
这一结果体现了国民政府在文化发展与财政健康上的平衡与妥协。尽管并没有像业界所期待的那样取得完全免税政策,但仍然标志着出版业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后续影响
出版业所面临的危机已在上文提及,可以作此判断,当时出版业的困境并不是营业税减半甚至完全免税能够力挽狂澜的。抗日战争带来的伤痛还未远去,解放战争又迫在眉睫,时局的动荡与社会的混乱使得出版者不敢出书、作者无心写书、读书者不敢花钱购书。
国民政府税收减免政令的初衷是鼓励文化传播与教育发展,但本就萎靡的市场与竭尽全力降低成本的书商使得大批出版商蜂拥而至教科书这一免税赛道上,都期盼着免征营业税且不乏刚性需求的教科书能够挽救他们摇摇欲坠的生意。 [8]这一时期,唯一还算得上畅销的便是文艺类书籍。正如1947年河南省一小书店店主张学堂在《大公报》上刊文所述,其眼见故乡仅有的两家书店所售书籍仅有两大类:“四书五经”与医、卜、星、相,以及武侠爱情类小说。张学堂决心打破这里污浊的风气,自己开了一家书店,专卖新出的杂志以及他认为比较高尚的书籍。但他的志向在书店第一个月的经营中就被打败了,新文学书籍鲜有买主,学术书籍更是无人问津,与之相反的,来找蜀山剑侠与卜筮正宗书籍的则大有人在。
据统计,文艺类书籍在1946年的全类别图书销售中占据一半份额,这虽然离不开当时读者对于此类书籍的兴趣,但更多是由于社会的颓态与生活的重压让读者仅满足于文艺书籍对情绪的麻痹。与之对应的是科学类书籍销售占比之低,在全类别图书销售占比由1941年的7%降至1946年的4%。这无疑对当时亟须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中国而言是违背时代的退步。 [1]更有甚者,一些仅图销量的出版商还推出带有刺激性的书籍及诱惑性的色情书籍,而一些真正有益于文化事业的大家作品,如鲁迅的《呐喊》、曹禺的《北京人》等,不是被当局没收,便是受到警告被禁止销售。 [8]此外,纸价与人工价格居高不下,邮路对于书业的负面影响都没有解决,或者可以说是无法解决。经济不稳定、开销高涨、邮路不畅等问题,直到解放战争全面爆发都一直未能解决。
结 论
以上对1946到1947年民国书业免税事件的回顾,展现了战后经济重建背景下,出版界与国民政府之间博弈。面对出版业的困境,书商、教育界与知识分子共同呼吁书业免税,虽然最终未能取得完全胜利,但通过教科书的营业税豁免与其他书籍的营业税减半,出版业在艰难环境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显示出,减税政策虽然给出版业提供了短暂的发展时机,但国内市场对于文艺类书籍的偏好与教科书市场的“内卷”竞争,使得真正能推动文化进步的书籍难以在市场上获得应有的关注。读者购买力不足、图书市场的需求偏颇、图书流通困难等问题依旧困扰着行业发展,业界人士正本清源的理想在形势惨淡的现状下也只能沦为空想,出版业陷入一种经济效益与文化使命之间无法平衡的矛盾之中,难以从持续的萎靡中重振。
研究这段历史,不仅可以看到动荡年代下出版业的艰难困苦、感受到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不易,更为当下出版业面临的经济政策调整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
参考文献
[1]端木锡琦 . 当前图书出版事业检讨(上)[N] . 大公报 ,1947-04-13(10)
[2]唐然 . 书业营业税问题[N] . 大公报 ,
1946-11-17(12)
[3]吴泉连 . 当前出版事业的危机(上)[N] .
大公报 ,1946-12-08(12)
[4]蓬子 . 请从免征书业营业税做起[N] . 大公报 ,1946-12-15(12)
[5]潘际坰 . 英国怎样击退书税的? [N] . 大公报 ,1946-12-15(12)
[6]免征书业营业税 ,财部已允予考虑[N] . 东
南日报 ,1946-12-25(8)
[7]减免书业营业税[N] . 中华日报 ,1947-01-08(6)
[8]兆莘 . 谈谈出版界的自救和刷新[N] . 大公报 ,1947-02-09(12)
作者褚浩源系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文学硕士毕业生;贾欣然系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