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与错层之间
2025-02-14赵洋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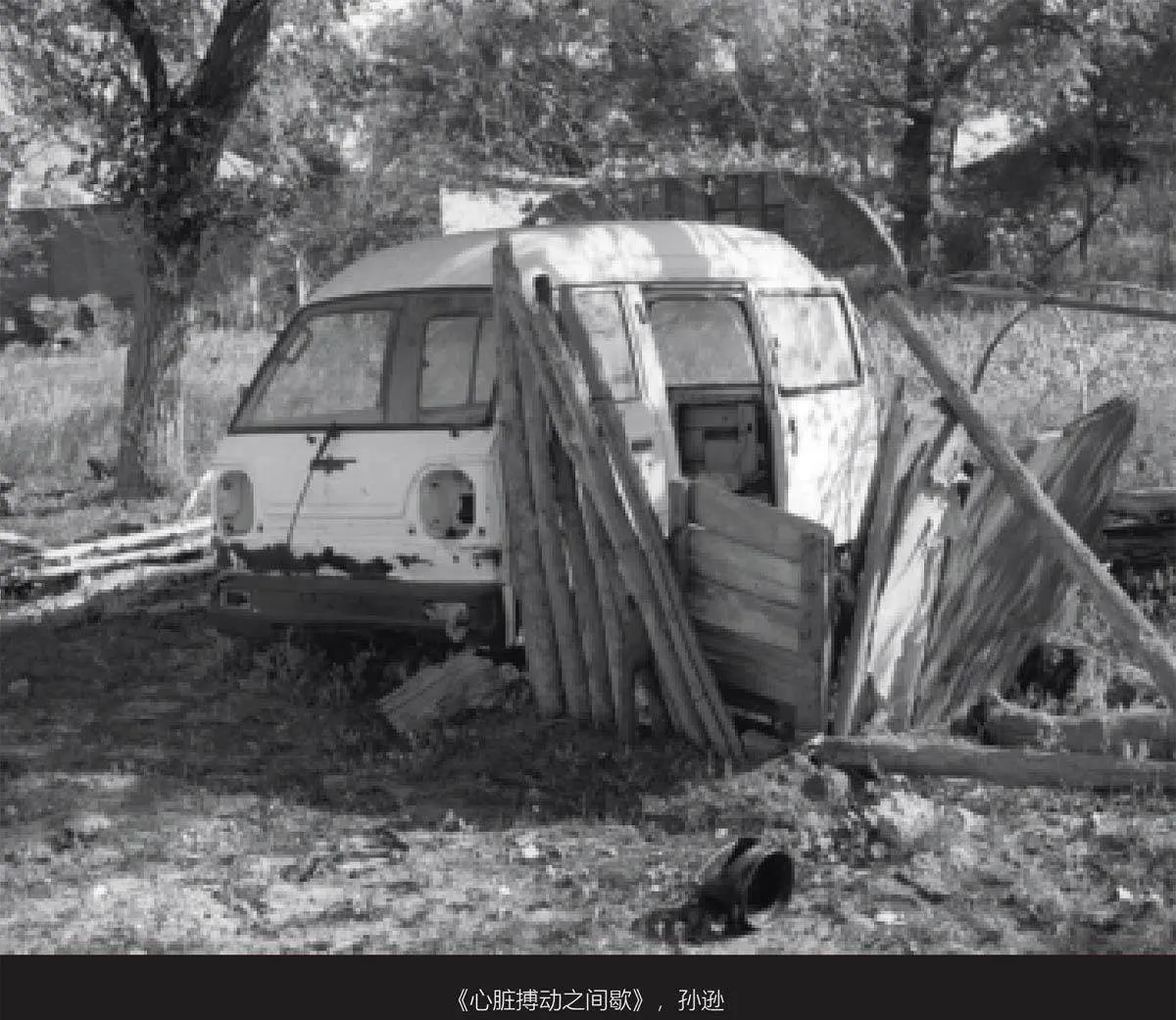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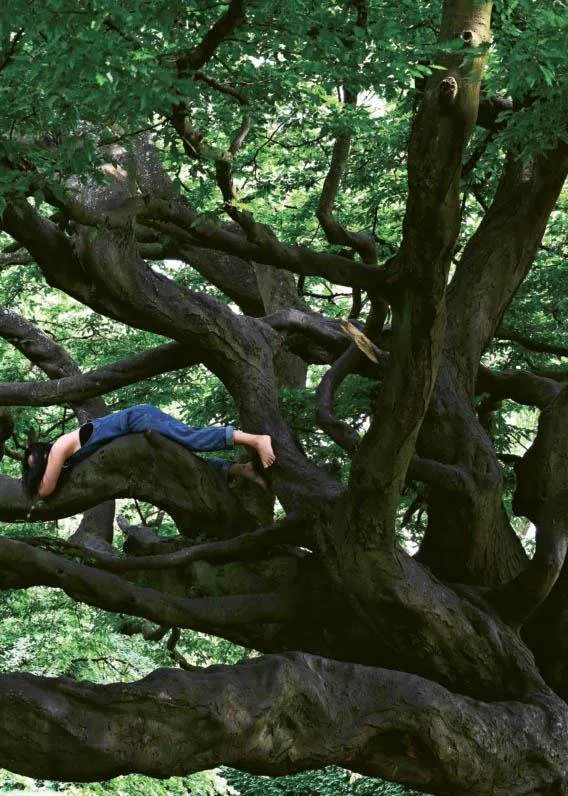

在1999年,中国普通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开始正式实施,其“目标是增加我国年轻人的高等教育获得机会”,而随着扩招政策的实施,中国的普通高等教育也在短时间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迅速地从“精英教育”阶段转向为“通识教育”阶段。但是,如果回望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史,其自身的转变似乎并不像数字增长这样简单。其中,以媒介自身作为专业划分的标准算是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一个传统/ 特色——高等摄影教育便是其具体的案例,而“摄影系”则是其具体的形态。从逻辑上讲,以媒介自身作为专业划分的标准应该是“精英教育”的一种具体模式,它可以让学生短时间内在单一的媒介领域里做到精深与纯粹——基本功好、水平高、技术全,但这样可能就无法让学生学习和使用其他的语言媒介,从而形成极强的媒介壁垒。在2000年之后,随着经济、科技以及文化等的迅速发展,大量的“摄影系”开始陆续地在国内的众多高校中被建立。但是,因为先天的历史因素,它们在建立之初就处于了一种尴尬的“大过渡”的状态里——由“精英教育”阶段向“通识教育”阶段过渡。而且,在这种“大过渡”的状态下,各个“摄影系”却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具体的反应——大部分的“摄影系”依然在沿用“精英教育”阶段的理念来应对“通识教育”阶段的现状。所以,随着高等摄影教育的陆续建立,一种复杂的割裂性也就蕴藏在其中了。当然,在高等摄影教育建立的早期,“摄影系”也的确积极地发挥了自身的重要作用,为国家培育了无数的摄影人才,但随着经济、科技以及文化等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当下的“摄影系”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高等摄影教育的新发展和新变化了,甚至,其开始逐渐成为当下高等摄影教育的阻碍与束缚。
而“1839摄影奖”于2019年设立,那么,从时间的维度看,其刚好与中国高等摄影教育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的阶段相吻合。所以,当我们对“1839摄影奖”及其入围/ 获奖作品进行仔细观看时,便能够比较清晰地观看到这种“复杂的割裂性”所带来的具体影响: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要求学生以按部就班的方式对“摄影”展开认真的学习,而在创作的过程里,我们却希望学生能够以多元的形式对“摄影”展开深入的讨论。这样就制造出了一种“悬空”的尴尬状态——我们既没有很好地继承摄影文化中的“传统经典”,也没有很好地掌握其他媒介的“语言语法”。在2020年——“1839摄影奖”设立的第二年,国内的一名艺术与摄影批评家就曾因为“1839摄影奖”中的视频类作品的比重过大问题写了一篇名为《视频类作品的比重太大了》的文章——“之所以感觉看这一届的作品不轻松,原因很简单,就是视频类作品的比重太大了。一个大奖和十个优秀奖,其中有七个是视频类作品,只有四个是纯图片摄影。顺着看下来,几乎以为自己在看实验电影节或者影像节。看的同时还要不停地再去翻阅文字说明,试图去理解这些看上去有些晦涩难懂的影像作品。到最后看二十位提名奖时,才稍稍找回看摄影的感觉。……尽管摄影和电影有着天生的近亲关系。但是从语言上来说,两者还是有着显著的差别。摄影最大的优势还不是它的记录性和叙事性,而是它瞬间的整全性,或者叫瞬间的永恒性。它是在一瞬间让所有对象同时在场,一镜显现,不需要时间的绵延和跌宕。摄影的这个特性看着简单,但非常符合长久以来,人类心灵对永恒性的追求和渴望。可以说是‘瞬间即出,心灵即达’。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照片能持久地震撼人心的原因。陈华感慨现在的照片都不打动人了,大概就是他找不到那种能一击命中他心灵的瞬间了,这难免让人失落。”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影像这个大的语境下,我们对于所谓的“媒介纯粹性”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执念”。
所以,在经历了大量的学习和反复的实践之后,最终,我们还是将“摄影是什么?”“你能用摄影做什么?”以及“你与摄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抛给了学生。
早在几年前,基于对国内高等摄影教育的切身感受以及对“1839摄影奖”等与国内高等摄影教育有着密切关联的摄影奖项的观察,自己便曾对国内高等摄影教育里所逐渐显现的“方法论”问题提出过质疑——越来越多的学生作品中开始呈现出一种模式化的趋向,而原本应当凸显的实验性却在逐渐消解。如果究其原因,其必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中国高等摄影教育的具体状态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近些年, 不知为何,“ 学院派摄影”(Academic Photography) 逐渐成为国内摄影领域里的一个流行名词。如果究其源头,大概率是藉由人们对于“学院派艺术”(Academic art)的粗暴认知而衍生出的一个“新”名词——在当下,很多人会简单地将由国内高等摄影教育所生成的摄影定义为“学院派摄影”,但其实,在艺术史的体系中,“学院派艺术”是专指“那些在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中,受法兰西艺术院订立的标准所影响的画家和艺术品,以及跟随着这两种运动并试图融合两者作为风格的艺术”。但是,众所周知,文化总是处于一种发展和变化的状态里,那么,如果我们将“学院派艺术”进行“适当”的延展,让其回归自身的基本假设——“艺术是可以通过将其系统化为一套能够被传播的由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相结合的文化系统来进行传授。”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将所有的、被艺术院校所影响的艺术都称之为“学院派艺术”,而以此类推,“学院派摄影”似乎就可以被引申为受摄影院校所影响的摄影——这似乎是一种“将错就错”的结果。而且,无论是“学院派艺术”还是“学院派摄影”,因为都是基于“学院”而衍生,所以,与高等艺术/摄影教育一样,其并非是一种简单的艺术/摄影的形式,而是一个系统,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其既包含由学院构成的教育组织,也包含由学院构成的教育组织所运行的机制与惯例——例如,定义艺术/摄影的内容与规则,学习艺术/摄影的方法和工具,批判艺术/ 摄影的路径与逻辑等等。但是,当我们在兴高采烈地讨论“学院派摄影”的时候,却总会不自觉地忽视一些现实性问题——中国的高等摄影教育是在2000年之后才开始逐渐建立的,那么,在这短暂的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高等摄影教育似乎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成熟体系。所以,从逻辑上讲,中国高等摄影教育就不具备——或者说不完全具备——构建我们所讨论的基础——“学院派”,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学院派摄影”时,其必然掺杂了一些“想象”的成份,而这也便成为中国的“学院派摄影”的一种特色。
当这些具体的现实问题被提出后,其是否意味着对于中国的“学院派摄影”的讨论便没有了意义?但恰恰相反,在中国高等摄影教育经历了短暂的“春天”之后,其原本隐藏的意义才重新被显现了出来——在这种“掺杂了一种想象的成份”的中国的“学院派摄影”里,其实酝酿着多重的、特殊的矛盾性:其既包含了“学院派艺术”的“痼疾”——1816年,泰奥多尔·席里柯(Théodore Géricault)便曾对“学院派艺术”作出这样的批评:“这些学校让他们的学生始终处于模仿的状态……我悲哀地注意到,自这些学校建立以来,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为成千上万的平庸人才提供了服务……画家们太年轻时就进入了这些学校,因此,这些学院留下的个性痕迹是难以察觉的。我们可以看到,每年大约有十到十二幅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几乎完全相同,因为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原创性,这着实令人懊恼。一种绘画方式,一种色彩,一种对所有系统的安排……”也包含着中国“学院派摄影”里所特有的建立与消解并存的“新症”——在“网络时代”与全球化新阶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起步时间较晚且基础薄弱的中国高等摄影教育不得不反复地实验和修正自己的教育系统。
此外,在国内,每当人们提及“学院派摄影”,那么,与之相对的“非学院派摄影”也必然不会被遗忘。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与普及,“影像时代”与“网络时代”开始真正到来。而随着“影像时代”与“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方式与状态也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摄影开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行为,而影像则开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在“影像时代”的直接刺激下,越来越多的人便开始对摄影产生出浓厚的兴趣。而且,作为一种兼具技术与艺术/客观与主观的视觉媒介,摄影也具有着特殊的直接性。而且,在互联网的助推下,人们接触摄影的途径和学习摄影的方式也开始变得多元,并逐渐呈现出片段化的趋势:我可以喜欢或者学习某一种摄影形式/风格——这种摄影形式/ 风格可能来自于“学院派摄影”,而不必接受/ 建立完整的摄影知识体系。那么,在没有由摄影知识体系所构建出的规则的束缚与干扰后,就很容易形成强烈的实验性和自我性。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将2000年作为中国高等摄影教育的起始,至今,其已经存在了24年之久,那么,在这漫长的24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高等摄影教育对中国的摄影产生了多少具体的影响?这似乎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面对如上这些具体的问题,我们的摄影该如何应对?这似乎才是核心问题的所在。我们总是将过多的意志强加于摄影之上,从而忽视了摄影自身以及人自身的意义。作为一种让人与现实世界产生直接关联的媒介,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其回归一种与生命相连接的状态?毕竟,“艺术充满于生活之中,贯穿于生命的一切历程;反过来,生命的展现、延续及其自我创造,不但离不开艺术,而且,艺术本身简直就是生命赤裸裸地本质表现。艺术和生命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参照性,使艺术和生命双方都同时包含自由创造和导向审美境界的特征。”诚然,从这个方面看,“1839摄影奖”似乎不可能为我们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但是,作为一个与高等摄影教育密切相关的奖项,“1839摄影奖”却能为我们观看高等摄影教育的具体状态提供一个具体的样本,而且,因为“1839摄影奖”的面向对象是全球高校的在校华人学生——“第六届‘1839摄影奖’共征集到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加拿大、比利时、捷克、俄罗斯、新西兰、韩国等全球近200家院校的近千组作品。”那么,这也让我们的观看又多了一个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