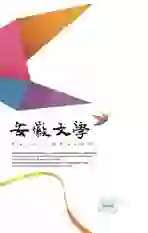一只锅的隐喻
2025-02-11葛取兵
1
冬至,拉开了寒冬的序幕,时光已是腊月——一年中最后一个季节了,春节的气息随着雪与风的脚步迫不及待,“哒哒”作响了。当你想念一场雪的时候,雪如约而至,银装素裹下的村落、田野、小径、菜园、枯荷,美好得像是一幅画……
雪是年的灵魂。不下雪,似乎就没有过年的味道。
雪来了,年就来了。少年的我焦灼地闻到了年的香味,这是一年的企盼呀。做糍粑,打谷糖,炸薯片,炒豌豆……谷糖是少年的最爱,做成了一个个圆圆的苹果大小,外面还裹了层爆米花。将秋天晒制好的红薯干用砂炒熟,抑或用菜油炸,金灿灿的红薯干也是过年最受欢迎的美味之一。母亲收藏了多时的豌豆和花生,一年到头才能买的新衣新鞋,还有少年最爱的“噼里啪啦”的鞭炮,终将如期而至。
意念一动,年就给了我一个暖融融的拥抱。
村庄里渐次升起的炊烟无处不在,香味像少年的我在每一个角落里欢呼奔跑,牛栏里打盹的老牛也惊醒了,它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亮光,寒冬中的麻雀模仿少年的模样四处串门,呼朋引伴,想享受人间的几许美味。我开始咂动嘴巴,回味每一道想象中的美食佳肴。桃林丰锅,跃上心头,格外清晰而又温暖。我相信只要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出生的桃林人,一定记得这道菜,不但对它津津乐道,而且对它心生敬意!这只是湘北一道简而不单的菜单,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是在那个时代,却是一道美味佳肴,成为桃林百姓骨子里的记忆与情结。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童年、少年和青年,始终环绕着这道菜的身影,一直到现在,伴随一生。应该说是这道菜影响着我的成长。那时节,能吃上一口丰锅,非客即节。过年过节,或者婚嫁丧娶。当然最隆重的是过年,弯弯曲曲的桃林河上上下下、村村落落就开始热闹了,家家户户杀猪打豆腐,为的就是这一只锅。随便走进一家院落,富裕也罢,贫困也罢,都可以领略到年的鲜香与生动。仿佛一锅在手,细碎鲜活的日子便能过成一条绵延的河。
桃林丰锅的做法其实很简单,简单得人人能动手。在乡下每一个成人都是做丰锅的大厨。一块猪肉,一盘豆腐,一篮白菜,一捆粉丝,刻意堆积在一口大铁锅里。乡下的土灶,秋天山上拾捡来的柴火,大火烧开,小火慢炖。干柴烈火,遇上这些乡里的“土菜”,再加把秋天腌制的红辣椒,菜园子扯一把大蒜和香葱,桃林丰锅便堂堂正正地出台了,有红、有绿、有白,生动而又鲜香。鲜,有时候很锋利,像把刀子直戳进你心窝。
吴獬老爷是桃林河畔的名人,饱读诗书,奶奶说他是满肚子经书,听说当过县官,后弃官从文,育弟子数千,享誉百年。历史的吊诡,每每让人感到意外。我家与吴獬老爷隔河相望,他是我的偶像,对他我一直心生敬意。少年的我们都是读着他的《一法通》长大的,一法通,万法通,盛传百年而不衰。充满了人生的哲学,简洁而又明了。吴獬老爷著书立说,立一家之言,生前虽无赫赫之功,身后却有不朽之名。他说:“丰锅一餐毕,忘却天下珍。”可见丰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桃林河从药菇山麓起源,流经文白、忠防,再到桃林畈这个小小的平原,后又七弯八拐,经长塘、西塘、乌江、筻口、新墙,最后抵达洞庭湖。曾经是湘北地区路南片的交通要道,让桃林古镇成为人口、财富的汇聚之地,因水而兴。高低错落的民居沿河而建,码头石埠错落有致。白天,三两妇女临窗面水,咿呀些琐碎闲事;傍晚,几处船家橹声灯影。有河,有月,还有思乡的渔歌。一条河就是一部史书,记录了一方山水的风土人情,记录了这里千百年来的乡土厚重与鼎盛繁华。正是因为这条河,又成就了桃林豆腐的水嫩鲜香。
每逢过年,父亲必做一口丰锅菜,沿续至今。丰锅菜始于何时,又究竟历经多少年,无从考究,但至今桃林河畔家家户户保存着这种原始的饮食习俗。
腊月三十清早,天还未亮父母亲就早早起了床,放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开门,清扫院落。一个早晨,整个村子就是在爆竹声中醒过来,我也是。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终于盼来了,所以醒得格外早,爆竹声一响,呼啦啦全都起床,再冷的天气也不冷了。忙着帮父亲贴春联,刷米汤。识字后,还能帮父亲分清上下联。再后来,贴春联就是我的分内事了。灯笼对于门楣来说是最好的装饰,大红灯笼一挂,配上一句“飞雪迎春归”,隆重而热烈,年就拉住了你的手,温暖如春。
贴完春联,父母就开始准备年夜饭,母亲指点江山,父亲依令行事。大年三十的早饭和午饭简单地吃一点绿豆粉皮,或在灶膛边炕几块糍粑。我们则是当小工打边鼓。一早父亲就忙着杀鸡剖鱼,一年中难得吃一次。鱼,一定要买大一点的,那时节只有白鲢,三五斤重,刺多,但却有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母亲提着竹篮子去菜园子摘青菜、大蒜叶。青菜是那种个头高、叶大、梗粗的土品种,不是现在的上海青之类的改良品种,菜是自家土地上“喝”粪水,“吃”土灰长成的鲜白菜。打了霜的白菜,脆甜醇厚。
青菜被大姐背到桃林河边去洗。一口泉水,冬暖夏凉,长流不息。此时,冒着腾腾的热气。洗衣洗菜,一点不冻手。人多的时候大家依次排队。可惜,这口泉水后来被污染了,流出来的水发黑发臭,无法饮用。这是后话。
母亲则在厨房里忙着洗肉,自己喂了一年的土猪,食人间潲水,由田地百草和蔬菜滋补而成的纯正土猪肉,肥瘦相间嚼出鲜香。也有我的功劳,那时周末,我经常随大姐去田园里寻猪菜。肉选排骨和五花肉,一大砣一大砣,码在锅底,大致三四两,再在上面放一层青菜,再铺一层豆腐、粉丝,有时也放点干黄花菜,荤素搭配一锅煮。一层肉、一层豆腐、一层粉丝、一层青菜,依次加入,容纳万千,层次感分明。调味时只需加一点点的盐和味精,温柔的火候会让所有味道在炖盅中融为一体,细腻的香气缓缓弥漫开来,香了整个村落,也香了我的记忆,永恒。
“二十四,打扬尘;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去赶集;二十八,打糍粑;二十九,样样有……”这是小时候最耳熟不过的一首童谣。桃林豆腐,由颗粒饱满的桃林黄豆配上清冽甘甜的五峰泉水,石磨磨制而成,色泽洁白,细腻润滑,鲜嫩可口。丰锅菜,因为桃林豆腐,才有了真正的家乡味,有了灵魂。粉丝是土生土长的红薯、黄豆、绿豆等原料加工而成。
二姐帮着烧火,灶膛里的火苗在锅底起舞。丰锅用木柴烧才有灵魂。先是热气升腾,慢慢地,一股香气弥漫开来。我和小妹则是东奔西跑,当起了情报员,不时跑回家报告情况,谁家的兄弟姐妹回来了,谁家的鸡已经杀好了,谁家又开始炒菜了。乐此不疲,来回穿梭,其实心里却最是挂念着家里的丰锅菜。
丰锅菜关键在一个“熬”字。丰锅菜不是炒菜,做法很简单,家常吃法,把几种家常菜蔬一起放进大铁锅或煮或炖,讲究的是慢,耐心和韧劲,成就了美味。桃林人过年多是吃年夜饭。一锅菜,从上午到下午,熬炖出来鲜香浓郁:白菜熬得立不起身;豆腐炖得挺不起腰,鲜嫩生动;粉条烀得站不住脚,滑溜溜的,一嗍就下了喉。而肉和排骨更是咕嘟得松松垮垮。熬煮中各种蔬菜相互沾光借味,杂而不乱,多却不琐碎。一种混搭,一种绝妙的碰撞。这种混杂着各种食材的丰锅,在高温的烹煮之下,食材之间散发出各自的味道,融合沁入,常常让人不忍放下碗筷。这是一道很斯文的清汤锅,不肥腻,无调味,有的人家甚至拒绝辣椒,吃的是肉与菜的火热与新鲜。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一般是在下午四点多钟开始,陆续就有炮声响起。乡里人讲究的是吃饭不落后。隔壁邻居总是相约一并开始,东家放完炮,西家又开始,村庄里渐次响起,这是一年中最热闹、最温暖的时刻。在我的印象中,始终记不起往年的冰雪有多厚,天气有多冷。所有的记忆中只有热闹与温暖。放完炮,关上门,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饭,热热闹闹,和和气气,甜甜美美。桌子中间就是丰锅菜, 再配上土鸡汤,鱼。再后来家里条件好,一定要摆十道菜,寓意十全十美,当然必不可少的是丰锅菜。火烧上了,锅架上了,菜拼好了,酒摆好了,一家人围着锅,一边聊天,一边听锅内白菜豆腐与肉在翻滚唠叨。大家相对一笑,相约围炉,动箸开食。香味弥漫,传承赓续,一家人迎来别样的收获,也是一种最朴素的厚望。
一个鲜香无比的现场,是我们这代人的儿时记忆。从未有一个节日能如春节般牵动人心,它是团圆的,是热闹欢畅的,也是满满当当一桌子年饭将大家聚在一起的五味丰满。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我排行老四,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小妹。记得大哥招工到县城工作,后娶妻生子,嫂子家在忠防镇,与桃林镇毗邻,一个在河之上,一个居河之下,正如一条藤上的两只瓜。大哥大年三十赶场子,中午到岳父岳母家吃年饭,然后再沿桃林河步行上十里路回桃林赶夜饭。自然我们年夜饭要推迟到五点左右。此刻周边的鞭炮声四起,我们就有些心急了,母亲说,好饭不怕晚。其实就是等着全家团圆,一个也不能少。这才是年最动人之处。
日子就在灶台前移动着,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季节轮换,日月更迭。时光远去,岁月已不再回头。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大姐、二姐、小妹先后出嫁了,我也外出求学工作,成家立业。原本一个七口之家,终于分成了六个小家三十五口人。正是一口锅,在生活艰难之时,支撑着我们,挺过一个又一个低谷,这些琐碎但温馨的记忆,弥足珍贵。有一种幸福叫父母在,家就在。年年春节,回家过年,最爱吃的是父亲做的丰锅菜,因为它早已霸占了胃,抢占了心,渗透了血液,浸润了骨头。再后来,父母年事已高,他们又随我们进了县城,安居一隅。如今父母八十高寿,生活自理,时常煮一锅丰锅菜,慰劳我们的胃。这何尝不是一件幸事。母亲时常说,现在的日子好哩,比起那个时候,真的是天天过年哟。是的,如今过春节,最主要的不是吃,而是团圆是相聚,是感情唱主角。陪陪父母,兄弟相聚,一炉火,一壶茶,一张桌,重温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温暖。一口锅上桌,所有的美好,就藏在这一口丰锅里,滋味绵长。
家,又回到最初的样子。源自苦寒,向阳而生。
2
一口丰锅,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
其实,在大地之上,每一种美食的背后一定有无数个传奇故事,每一道菜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桃林丰锅也是如此。少年时,常常在夏夜乘凉或冬夜围炉,听老人讲古,聊坊间逸话,自然而然会讲到丰锅。每一张嘴中都有一个版本,都有一种说法,在民间口耳相传,是与非,真与假,都已无妨。或许隐秘也是一种传奇。
譬如,桃林丰锅与李自成的故事。闯王李自成兵败,逃到湘北地区,在田野围炉煮丰锅,天寒地冻,身心却是暖的。李自成,一个为民族大义和天下苍生而战的英雄,在那个时刻却是何等的悲壮激昂。又譬如当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征战湖湘,过长江,饥饿中尝到桃林丰锅,称赞:“味美,丰盛也。”他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波折,从乞丐起步,最终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成为历史的佳话,一口锅让他赞不绝口。又譬如桃林名人方升,原本一介草民,苦读诗书,明成化进士,在朝为官到监察御史,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常以丰锅为食,豆腐白菜,一清二白。又譬如湘军名将曾国藩为率兵战长江城陵矶,居守临湘,百姓送丰锅犒劳将士,也是一段佳话;又譬如吴獬老爷,晚清进士,曾任广西荔浦县七品芝麻官,辞官不做,回乡从教,却把桃林丰锅留在广西,一口锅成为荔浦人的念想……
悠悠千年,英雄安在?唯独一口锅始终悬挂在百姓的灶膛上,炊烟不断。
历史总是充满了未知和悬念。传说终归传说,关于丰锅,民间故事终究有着美化和虚构的成分,事实上,菜肴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代演变,桃林丰锅亦然。追根溯源,桃林丰锅这道菜品的由来,还得从千年前祖先南迁说起。
循着祖辈的味觉记忆,或许能揭开丰锅的由来。据说,临湘人的祖先是古长安人,一场安史之乱,打破他们的安宁,四方逃难,故土成了背影中的苍茫。漫漫南迁路,栖身之所一变再变,但味觉的记忆却难以割舍。在逃难的过程中,砍柴伐薪,摘茶采药,腹中饥饿,则在林间空地架一口石锅,围炉食之。一旦有敌情,封锅而逃,或许这就是“封锅”最早的来由吧。
越长江,终于得以喘气歇息,定居繁衍。一乡一俗,乡音渐变,习俗已改,但这一口锅却长留千年,南迁先祖的离愁别绪孕育了“煮”的技法,一道丰锅菜,抑或是苦难的见证与记录。沧海桑田,不变的是生活在土地上的生灵对生命的渴望。每一道食物皆因一方水土的物产与人情共同塑造,丰锅之所以能念念不忘,正是因其承载着先祖千年来一路漂泊而累积的深深乡愁。
一口锅,藏着一个古镇的历史,酸甜苦辣,俯拾即是。
其实,丰锅的形成,更多的是因为一方山水的独特地理因素而成。行走湘北,山水相间,处处皆景。北有长江环绕,湖泊众多,如同一只只眼睛,镶嵌在大地之上。南有药菇山、五尖山,峰峰相连。山也清,水也秀,枝繁叶茂地长出稻子、油菜、花生,长出白菜、萝卜、南瓜,也长草长树。人,也是大地的庄稼,生根,发芽,抽枝,长叶,慢慢地硕大。民以食为天。先人在稻谷、大豆、白菜等这些农作物上做文章,变着花样打破原始材料的性状,大胆地混搭组合。这也正是丰锅的绝妙所在。一粒黄豆,到一块豆腐,在双手的揉搓中,一年又一年,一顿又一顿地重复制作中,讲述着历久弥新的故事。生活在大地上每个角落的人,都有着自己的智慧和生存的经验。我始终敬重每一个在劳动中成长的人,他们才是土地的根脉。
一口丰锅,穿越千年,折射着先人躬耕劳作的侧影。
丰锅的实质就是火锅。据历史记载“火锅”的最早雏形是周代“鼎” 器,而战国时期的“陶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火锅”。翻阅《中国食物记》,才知晓在古代,对食物的烹饪讲求的是“脍”与“炙”,“脍”就是用水煮,“炙”就是用火烤,所谓“脍炙人口”由此而来。诗人苏轼曾写过“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就是对这一场景的生动再现。读史书《韩诗外传》,我们可以想象到古人聚会的热闹景象:将食物放入鼎中煮熟,“列鼎”而食,围炉畅饮,丰锅场景何其类似。白居易的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可见一斑。将红泥火锅放在火炉上面,将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放入锅中。一边喝着“绿蚁新醅酒”,一边与友人吃着火锅,这种感觉既舒适又怡然自得。一个简简单单的日常生活,在诗人的笔下却是如此诗情画意,温馨惬意。宋代诗人陈藻曾写道:“白秫新收酿得红,洗锅吹火煮油葱。”其意为用刚收获的白糯米酿造红酒,然后将锅刷洗干净点上炉火煮油葱。诗句里所描写的场景,其实也是宋人吃火锅的一种方式。杜耒的《寒夜》“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何尝不是一件雅事。
到后来,“封”也罢,“丰”也罢,辛勤耕作的农人心中的祈盼是锅里的菜越来越丰盛,田野的庄稼也越来越丰收。丰锅,是寒冷冬日里的精神信仰,更是艰苦岁月、不畏苦难、快乐生活的见证,更是对寒冷冬日的尊重。一口锅的背后演绎的是“和而不同”的传统锅食文化。这或许就是丰锅的秘密所在。
千百年来,桃林人爱丰锅,做丰锅,吃丰锅,相沿成俗,久盛不衰。吃丰锅已是桃林河畔一种淳朴且原始的饮食习俗,更是在外游子思乡的愁绪。宰杀家猪,余温热乎的五花肉入锅,一堆人围着,一只丰锅可抵所有。大杂烩,一锅煮,吃的是肉与菜的鲜香、清甜,喝的是荤素久煮升华的醇厚汤汁,其乐融融。
当然,时代在变,丰锅也在变。老味新生,生生不息。如今在城里独家独户,自成院落已是奢侈,电梯房,三室两厅,逼仄的空间何以架灶烧柴呢?原始、粗犷的铁锅炖丰锅,已无可能。改良版的丰锅应运而生。不论时代如何演变,丰锅的官方标配少不得五花肉、豆腐、大白菜、粉丝。我经常在家做丰锅菜,尤其是寒冬初降,煮一盆丰锅菜抵挡严寒。首先,把五花肉整块煮,肉煮紧,油析出,切成厚厚宽宽的大肉片,半肥半瘦,再上锅炸至外焦里嫩炒香,放辣椒、大蒜、豆腐。豆腐是菜市场买来的,再用煮了五花肉的汤压豆腐,高压锅将白豆腐块煮成蜂窝状,再配上粉丝、白菜等合着煮,最后将肉盖在配菜上,用电火锅盛着。窗外寒风呼啸,室内却是温暖如春,一锅上桌,闻到那股豆香、肉香、菜香交杂的美妙滋味,会心一笑。
一口锅已经成为桃林人的“味觉暗号”。围炉聚炊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邀三五好友,桌上一口丰锅,手上一杯谷酒,檐下一盏灯火,亲与情、温与暖就这样握进了掌心。千言万语,尽在一只锅中。
腊月又到,瑞雪将至,迫切地思念着回乡下过年,炊烟袅袅,一口丰锅正蹲守在灶膛之上炖煮……
而乡下的农人却在思考大地的秘境,勤奋的农具也在跃跃欲试,在一亩三分地中梳理草木生长的密码。
责任编辑 夏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