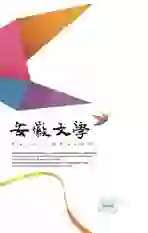在故乡,曾有过的读书生活
2025-02-11徐迅
1975年的读书
在老家翻旧书,翻出了几部儿童文学作品:《向阳院的故事》《小闯》和《红军万岁》。有趣的是,在每部书的扉页上我竟都留了自己的签名,分别有“1974年6月”“1975年购于岭头”“1976年元月21日于余井”的字样。余井和岭头是我的老家,那时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安徽省潜山县余井区岭头公社”,后来又叫“余井镇岭头乡”,再后来——也就是现在,因为撤乡并镇,就直接叫作“余井镇”了。
《红军万岁》是一本宣传红军英雄事迹的儿童读本,1974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上画了一个胳膊孔武有力,浓眉大眼,充满朝气的儿童团员。他把衣服甩搭在肩,一副大无畏的革命的少年形象。书里收录了《枪》《我们的红军》《草地夜行》《红军万岁》《红军妈妈》几篇作品,写的都是“童子团”(即儿童团员)机智勇敢,缴获白匪(又叫“白狗子”)的枪支和保护“红军万岁”标语的事;还有写红军战士舍己为人,歌颂红军母亲高贵品质的。
《小闯》这篇小说写的是1943年发生在淮北平原的一个抗日斗争故事。当地民兵队长的儿子小闯,受到革命前辈影响,小小年纪就当了一名儿童团长。他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在父亲被捕的情况下,深入虎穴,在当地县大队和新四军的支持下,与敌人斗智斗勇,不仅智取了敌方的情报,还揪出了叛徒,与小伙伴小星、秋霞、淮生等一起,在残酷的斗争中逐步成长为革命战士。
与小说《小闯》一样,《向阳院的故事》也是一部中篇儿童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位名叫“铁柱”的少年儿童,响应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革命前辈、老工人石头爷爷的帮助下,利用暑假支援当地的公路建设——当然,也揪出了一个阶级敌人。这部小说语言鲜活生动,既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也洋溢着作者的文学才情。书的作者徐瑛,后来我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上见到了,很是亲切。只是不记得当时我是否向他说:我是读《向阳院的故事》长大的。这是应该说的。
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算了算,1975年我已经12 岁,正是读儿童文学作品的年龄。由此看,那时我对书也是如饥似渴的——只是奇怪的是,我这3本书上的签名,都不是我一打眼就能认得出来的笔迹。这个时期的签名,让我有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的字体,让我在感受生命成长的同时,还感觉到人生的一些变化是有某种突变性的。我的这种文字书写的变化,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而这可能就是读书带来的。
创刊号
老家不仅有些旧书,还有不少旧的报刊。在我青年回乡时,正是文学报刊异常兴旺发达的时代。这个时代,说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也很贴切。在旧杂志里,我翻到了3本文学刊物的“创刊号”——《散文选刊》《振风》和《大时代文学》。
《散文选刊》创办于1984年10月。里面发表了曹靖华、秦牧、魏巍、魏钢焰、于黑丁、郭风等人的贺词。除了贺词,还有一份“振兴当代散文的发刊词”。当期发有著名作家巴金、艾青、王蒙、茹志鹃、黄宗英、贾平凹、冯骥才以及安徽著名诗人陈所巨等人的散文作品。这个杂志后来选发过我的很多散文,主编与我还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现在杂志仍是当代散文界的重镇,说起来也是步入了“不惑”之年。
《振风》杂志由我所在的安庆市文联出版。出版日期是1981年7月,双月刊。我看总期数是13期,应该是经历过了一年的试刊。刊物设有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文学丛谈五个栏目。这份杂志后来改名《法制文学选刊》,很是红火了一阵。然后,又改名为《满江红》。似是伴随文学时代的兴衰与经济大潮的冲击,沉沉浮浮,不停地停刊,又创刊。现在又恢复了叫《振风》,是安庆市文联的一份文学内刊。
与《振风》一样,改名频繁的还有《安徽文学》。手上这本《大时代文学》杂志是1991年4月创刊的。实际上,它的前身就是《安徽文学》。在改刊号上,发有作家许辉的短篇小说和潘小平的散文《乡村落日》。《乡村落日》由《天火》《父亲的事》和《二奶的死》三篇组成一个系列。当年就读过,这次一翻,又一下子被迷住。于是再读。
读《天火》里一个句子:“天火……在这片广阔的平原上,它悄悄地消失了。”我就感觉了一种人世况味,沉痛,且耐人寻味。而作者笔下“天火”以前是这样的:
……说是谁谁,良田千顷,骡马成群,日子过得那个红火。一天,后晌,正下着雨呢,门外闪进一个人来,白衣白裙,鬓边插一朵铜钱大的白绒花。女要俏,一身孝。掌柜的也就四十来岁,哪里见过这个?拥了怀里,就荒唐。过后,才恍恍惚惚想起,那么大的雨,怎么就没湿了她的鞋呢?
作者写到她父亲回忆母亲,写到了二姑的死……也如“天火”燃烧,自有一种神秘的文字魅力。散文叙事之美,语言之美以及生命之美,浓缩在只言片语,让我至今读来,感觉依然是好。于是给潘小平先生发了一条信息:“在老家翻到了创刊号……(这篇)写得真好!”——我这样兴奋地给她发信息,是因为我们曾一同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过。她任支部书记,我任支部副书记,有了一段共同美好的文学时光。
在一堆旧书刊里,我还翻到了两本《征文作品》和《安徽文艺》。前者是“安徽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办公室编”的,1972年试刊,当年9月便改成了《安徽文艺》试刊。1973年5 月正式出刊。编者是安徽省文化局《安徽文艺》编辑组。《安徽文艺》与《安徽文学》有什么关系,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安徽文学》除了改名为《大时代文学》,还叫过几年的《文学》。由此可见《文学》也可能有创刊号的。
我没有报刊创刊号的情结,但偶尔也会有收藏。我还收藏过一本《中国煤矿文艺》创刊号。这份杂志创刊于1993年10月,1998年改名为《阳光》。对这份杂志充满感情,是因为我在其中工作了很多年。我想,这可能是岁月对我生命的一种美好馈赠。
也读画
这些旧的报刊,有我自己掏钱订的,也有从一位当老师的亲戚手里拿来的。我订过一段时间文学刊物,大概是1980年至1983年之间。订的刊物有《小说月报》《希望》《安徽文学》《青春》《萌芽》和《雨花》……都是些文学刊物。
作为一位文学青年,那些年我喜欢看刊物里发表的小说和诗歌,有时也看画。那时刊物的封面开始发一些画,例如,安徽的《希望》《江淮文艺》和《安徽文学》就有著名画家韩美林画的熊猫、猴、兔、鸡等动物。这些动物画作,想象奇异瑰丽,经常有让人眼睛一亮、耳目一新的感觉。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工作时,还和当时“爱知书店”的崔老板去过王府井韩美林先生的画室。韩先生送了一幅动物画给我,只是画是批量印制的,当时也没有找他题签什么的。
看刊物上发表的画,喜欢的,我偶尔还会临摹。当时自觉临摹很成功的是江苏《雨花》杂志的封面图:“鬼敢来乎?庚申春节。”实际上是《钟馗打鬼图》。临摹之后,我把它贴到我家的墙壁上,惹得当时很多人以为是我画的。我因此也得意了好久。这回重新看到《雨花》杂志,知道画是著名画家田原先生的杰作。一位名叫樊秋华的评价他,说:田原精绘钟馗题材画《鬼敢来乎》,作品漫画色彩浓厚,人物造型、线条的运用都不乏幽默之趣。又说:且看钟进士浓眉立,目如电,须髯如戟,帽翅颤而怒视;其腿脚曲伸,大腹蟠然,俨然酒足饭饱姿态;斩魔剑从轻发落,坐卧之间,真真有鬼亦不敢来谒。
小品画面清新奇巧,正气扑面而来。
由此我也知道了田原先生,字饭牛,原名潘有炜。1925年生,卒于2014年。祖籍江苏溧水潘家村。曾任《江南日报》《新华日报》美术编辑30年,1979年调入江苏省文联工作。出版有《狼外婆》《报晓鸡》《宝井》《饭牛闲话》《三百六十行图说》《田原硬笔书法》《牛蹄痕》《郑板桥集外诗抄》,美术片《熊猫百货商店》等作品,画集不下七十种。他画过不少钟馗打鬼图,题以“浩然正气”四字形成作品。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钟馗打鬼”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个绘画题材。有人以此揣测,说人们经历十年风雨,对社会正义的迫切渴望,希望有专门打鬼的钟馗来降妖除怪,因此便借钟馗打鬼以譬喻。关于《钟馗捉鬼图》,我还听过另一则故事: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画家徐姺画了一幅《钟馗捉鬼图》,落款时,写了一个“鬼”字,便不好落笔。画家黄养辉见之,建议她改画题为:鬼敢来乎?一下子便化腐朽为神奇。徐姺以后只要画钟馗打鬼,题款都是“鬼敢来乎?”……但田原先生这幅“鬼敢来乎”是刊登在1980年8月的《雨花》杂志,也即是庚申年。应该比那个故事还要早。画家黄养辉本是南京市人,按说,他受田原的启发,也未可知。
一部志书稿
翻出了一部志书稿,是《安徽民俗志》的征求意见稿。1989年元月由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印。因是打印本,书稿很厚,有309页,估摸17万字。书的编撰者是何鹏、肖荼夫妇。因志书编纂有自己的体例,志稿前有一篇“概述”,然后全书分为婚姻、生育、寿庆、丧葬、服饰、饮食、居住、行的、器用、文娱、生产、季节以及民俗,共13章。
1986年至1990年,我在家乡《潜山县志》编辑部做编辑。当时我的领导开明,知道我喜爱文学,除了让我担任几个专业志的编辑外,还把县志里人物传、民俗志编撰工作也交给了我。那时,何鹏先生除担任安徽省民俗志的编撰,应该还负有指导全省民俗志编辑工作的职责。因我主编《潜山民俗志》,所以领导安排了我与他对接。这样,我便认识了他。那时,美丽的天柱山风景区尚在开发中,我陪同他们夫妇在山中好像还住了一宿。
印象里,何鹏先生身材高大魁梧,戴了一副茶色墨镜。说话轻言细语,和蔼可人。肖荼老师夫唱妇随,慈祥得像一位老祖母。那时他们都七十多岁。何鹏先生是我们邻县太湖人,早年创办过白沙中学,后来一直从事的是文化工作。他编辑过《民大学生》《前进周刊》《通俗文学作品》《新理论月刊》《青年知识丛书》《皖北文艺》《大众科学》《安徽历史学报》《安徽史学通讯》《安徽史志通讯》等。是一位老编辑,也是一位文史学家,著作有《抗战文谈》《抗战文艺活动诸问题》《民国二十八年的抗战文艺活动》《学习鲁迅论集》《论吴敬梓与儒林外史》《论楚史与楚文化》《施闰章论集》《楚史参考资料》《楚国(族)八百年大事记》《王国维之文学批评》《何鹏文史论集》《通俗文化运动简论》《文学常识》《新兴艺术论》等200多万字。但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些,只当他是省志办的负责人,一位学者。
意外的是,这部志稿里竟夹了一封信,当时并未读到:
华主任并徐迅同志:
你们好!
上次寄去民俗志稿一册,想已收到。此稿很不成熟,缺点很多,至希你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
华主任对张恨水先生生平很有研究,希望能挤出时间,组织力量,对其作品和思想作探索与研究。
徐迅同志年轻有为,才华过人。希望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多写点好文章出来。
匆匆草此,顺询撰安!
何鹏,9.8
信可能是华主任转给我的。华主任即《潜山县志》的总编,也就是我的领导华日精先生。看信封,这部志稿是何鹏先生1989年8月11日寄来的。而他写信的时间9月8日也应该是1989年,说起来也有35年了。但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他在信中曾这样谬赞和鼓励我。
读过“三毛”
年轻时,我每到一处首先便是逛书店。我手头有两部台湾作家三毛的散文集。一部是1987年8月11日买的《三毛作品选》(海峡出版社,1986年3月版),另一部是同年10月29日买的《万水千山走遍》(漓江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后者是在家乡一个叫源潭的小镇上购买的。但不知怎么,书里还夹了几页抄录她“随想录”片段的纸——这里我说读三毛的作品,是因为我刚获得过一个以三毛命名的“三毛散文奖”。我还想说的是,三毛的作品,我以前应该是喜欢并且认真读过的。
她有一篇题为《西风不识相》的散文。说她年幼时,以为世界上只住着一种人,那就是她“天天看到的一家人、同学、老师和上学路上看到的行人”。对此,我也深有同感。记得小时候,我也觉得这个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是像我们那样的村庄。这个村庄也只有一种人。印象深的是这个村庄的人只穿两种鞋——布鞋和解放鞋(即黄色军用鞋)。以至于后来我见人穿着锃亮的皮鞋,就十分诧异,而对家里一双白色球鞋也耿耿于怀多少年。
凑巧,当时我们班上有位同学就穿了双白色球鞋。看到她穿白球鞋,也有不怀好意的同学,给她取了一个“小白鞋”的绰号。对这个绰号,大家充满讥笑。但对白色球鞋却又充满着新鲜和好奇。我也没有例外。后来发现家里木楼上的箱子里就有一双,我很想穿。于是找母亲要,母亲当然不给——那鞋后来不知谁穿过,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问了问母亲,母亲坚持说她记不得了。
这当然是个题外话。我读三毛的作品,显然书里她的丈夫,大胡子荷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屋及乌,对三毛与荷西那有着异域风情的爱情,我们充满了想象,也充满遗憾。但现在翻出《万水千山走遍》这本书,唤醒我的却是对家乡源潭小镇的温馨回忆——我的老家在余井镇岭头乡,一条公路自北向南横穿而过,一边连着我家所辖的余井镇,一边连着源潭镇。这是当时我们县两个较大的行政区。买了《三毛作品选》后,我在源潭镇又买了她的《万水千山走遍》一书,这应该是我喜欢三毛作品的实证。
我抄录的“三毛随想录”有二十条。这里,我选上三条:
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显现时,才成就那份完美。
挫败使人苦痛,却很少有人利用挫败的经验修补自己的生命。这份苦痛就白白地付出了。
批评朋友,除非识人知性,不然,不如不说。
我想,这三条也就是当下人们所说的那种“金句”吧?查了查,这些作品都是源自三毛在大陆另外出版的一部《随想录》。只是找了半天,我没有找到这部书。
2024年9月8日于安徽潜山岭头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