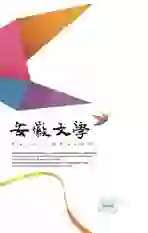青山之阳
2025-02-11毕亮
在飞机上看着太阳慢慢西落,直至隐到云层深处。云层之厚,让我又仿佛走在伊犁昭苏冬天没膝的雪地里。穿过一层层云后,天变得暗青,如同青山在远处矗立。落日的余晖慢慢后退,退至一条线后消失不见。我着手收拾小桌板上的水杯和平板电脑,未关的屏幕上正显示着一首诗,它所写的和此时竟然如此契合:
太阳升起之前,蓝天透出绿意。
闪耀的落日西沉,余下一片蓝白。
真实之色只能由眼睛去看,
月光返照时,非白实灰,灰中带蓝。
很高兴我用的是眼睛,
而不是用了读过的书本观看。
——《在太阳即将升起之前》(费尔南多·佩索阿作品,杨铁军译文)
待飞机降落在合肥新桥机场时,夜幕已经降临。飞机下降时俯瞰合肥这座数次来往匆匆的城市,灯火通明如水流,分不清是车流还是路灯流。出了机场,则直奔青阳而去。
是的,我此行为青阳而来。
车上高速,出了合肥,路两边墨色笼罩。一路高速公路上偶尔闪现几个地名,似梦还醒间记住了几个:舒城,庐江,汤池,军埠……熟悉中夹着陌生,更多的是陌生里夹带着一点点熟悉。每一个地名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在流传。十个小时前我还在几千公里外的伊犁,那里的地名我多是熟悉中夹杂着一点点陌生。
路边一闪而过地亮着一个招牌:桥头饭店。想着,该有一座桥要过了吧。司机李师傅在专心开车,邻座正闭目休息。我点开手机高德地图——车正行驶在铜陵长江大桥上。车上了桥,过了长江,就该是皖南了吧。可惜是夜里,未曾见到江边两岸风情。顺手刷朋友圈,有人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暮色四合的照片,配文是“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我是暝色过长江。再看车外时,已经到了青阳县城。刚下过一场雨,地面湿漉漉的,夜色中的县城,鲜有往来人流。车出青阳县城,高德地图显示,车一直在沿着青通河而行,然后就到了朱备镇,我们将住在朱笔村。往朱笔村走的路边,路灯下长长的跑道让人心生欢喜。
入住的是山脚下的民宿,环境自然是极好的。住的小楼名为观山,实也为观山。小楼共四层,分别以水、田、林、山来命名一楼、二楼、三楼、四楼。那几天,从上田下田,给人一种少时下田插秧割稻的感觉。而此时,正是稻熟的季节。房间里、阳台上是竹编的藤椅,也都是少时熟悉的家具。夜色里,面对九华山后山,童年记忆里“嗑九华山瓜子,过神仙日子”的广告标语偶尔还能想起来。
入住的第一晚,就滴滴答答地下着雨,坐在阳台的竹椅上远眺,只能看到山的轮廓,雾气雨气丛生。宋朝的杨万里大概也曾见过此景,有诗为证,题目即为《过青阳县望九华山云中不真来早大雾竟不见其全》。
雨落青瓦上,在深夜听起来反而有一种静气在其中。清晨早早醒了,太阳还在山尖处移动,出门跑了半个小时回来,太阳又离我近了几十米。躺靠在椅子上,开门见山,山外有山,山山青秀,山山清秀,山山云雾缭绕。
从青阳回来后读诗,读到北宋穆脩的《和毛秀才江墅幽居》:“江墅幽居好,名山对九华。疏篁十余亩,古屋两三家。碓下鸡争黍,篱根虺逐蛙。水边闲送目,独鸟在秋槎。”想到的就是在观山居住的几日。此诗写的是民宿之景,或者说,民宿依穆脩的诗而修建。再追寻青阳几日的记忆,仿佛是一场梦,梦里缥缈,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书里夹着一张便笺,证明这场“梦”是真实存在的,便笺是民宿房间里的,有我用铅笔手抄的《九华山歌》。当年刘禹锡到九华山,“惜其地偏且远,不为世所称”,于是作《九华山歌》“以大之”。
后一日晨起,沿着青通河慢跑,比平时的配速要慢很多。一边跑,一边东张西望。听河水声,听鸟鸣声,听风吹声。不时有三五成群的女人男人蹲在河边洗衣服。此时此刻,用浣衣可能和此景更搭一些。清泉石上流,明月还未完全落下,我这也是在秋之山居啊。
“好竹连山觉笋香。”山脚的警示牌上写着“禁止挖笋”,不远处的竹子有孩童饭碗的碗口粗了。生在新疆的小儿,对家乡所寄去的吃食多不感兴趣,独爱干笋。做红烧肉时,放上温水浸泡后的干笋,是他的所爱。于是,每年春天,在家乡的老父亲多了一项事:满村满山找竹笋,以前很常见的东西,现在成了稀罕物。村里的田地被外来的承包商种了水稻,山地被承包种上了经济林,以前许多家门口的小片竹林,也都被挖去整理成了菜园。竹,或许将要慢慢从吾村离开了。老父亲将挖出的春笋晾干后快递寄来,干燥的新疆实在适合存放此类干货。
将眼前的竹林拍给妻看,她让多拍几张。小儿本周的国画课正是学画竹子,还没见过竹子的他只能照猫画虎,胸无成竹。于是拍了几张整体及局部特写发过去。
又一日清晨,天清气爽。早早起来沿着青通河边跑步,跑到一座只供行人通行的旧桥,试着跑过去就进入了一个村子。桥头的草丛里立着一个警示牌:“盗采河沙路不通,一旦一查一场空。”又仔细看看杂草丛生的河道,这样的河里有河沙吗?抱着疑问过了桥,是白底黑字的麻园介绍,最底下的黄色字体“行走在麻园" 思念回童年”则让我止住脚步,看起了这份介绍:
麻园初建于东汉年间,原叫小舟上,青通河直流经江村老街曲折回旋,在巷里形成大弯(今上麻园),人气兴旺,烟囱三百,中间有八角长廊一座,连接小舟上(下麻园)和巷里(上麻园)。宋末元初,勤劳勇敢的小舟上人,用乌排和竹排泛舟至大通,经营蚕桑和茶叶生意,长期形成港口——小舟上。木材10吊铜钱8根的价格和质优价廉的玉麻成为畅销品,当地商人顺流而下,把木材运出,运进玉麻在当地销售。由于玉麻紧俏,于是商人便把玉麻种带回小舟上种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玉麻种植很快便普及开来,小舟上人用聪明才智使小舟上成为远近闻名的市井商埠。巷头巷尾人口积聚到2000多人,行商富贾众多,此地即被命名为“一都”。徽商重儒,相传明朝振兴时期此地有七十二麻篮书香出门,并建有纸字楼(石垒),为书生烧毁废字纸,建有响廊为书生读书。清末,小舟上人反对天平天国红毛鬼子烧杀劫掠,小舟上人大部分出逃避难,人口凋零。战争结束后,小舟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吸引了外姓人前来生产生活,从而形成了今天的麻园。
简介给人留有充分想象的余地。麻园在青阳的朱备镇,朱备镇为当年朱元璋备兵之地。如今朱备镇还有个将军村,为纪念朱元璋手下大将常遇春将军而命名。我们坐在车上从将军村疾驰而过,见有将军湖,湖名为金庸所题写;还有一尊雕塑,当为常遇春。
白墙黛瓦的麻园,让人心生惦念。如果沈从文看到这份介绍,大概在给张兆和的家书中会说到:这个人要是写起文章来,肯定不差。在青阳的最后一个早晨,我又专程往麻园跑了一趟,东张西望地走在村里,一看就是一个外人在逛荡。然而在我溜达的半个多小时里,村中遇见的也不过就二三老翁老妪,他们在喂鸡食、晒衣服。出村时看了看时间,上午八点四十多。
没想到在青阳会遇见屈原。青阳的陵阳古镇,屈原竟然还在这里待过。陵阳现有一个简陋的“青阳屈原纪念馆”,简陋一如当年屈原发配在此地的生活。“公元前286年—公元前278年,屈原放逐于江南陵阳,居陵阳东山湾九年,创作《哀郢》《招魂》《远游》等传世佳作。2300年后,陵阳人在东山湾改造屈原纪念馆,以缅怀屈原事迹、弘扬屈原文化、传承屈原精神。”
馆内,墙上喷绘着屈原的诗句。
馆后还有一馆,为当地廉洁教育馆。
馆外的广场上,有一座屈原的雕塑。我们这一群舞文弄墨之人,蹲坐在屈原雕塑前和老先生合影。
出了纪念馆的大门(也如纪念馆般朴素的门)就是两块稻田。饱满的水稻黄中带青,低垂的稻穗,“被稻谷压弯了腰”,许多人跑进去拍照,脸上都是丰收的喜悦。
屈原在陵阳过上了陶渊明想要而不得的“割稻陵阳里,悠然见后山”的“诗与远方”的生活。陶渊明后来游历至青阳时,可曾想过他的前辈屈原?
除了青阳屈原纪念馆,陵阳还有太平山房。没去太平山房前,听名字以为是一座书院。皖南多书院,青阳之地应如是。太平山房在陵阳镇的所村,所村当年“由陈姓先人聚族而居形成”,在叫所村之前,此地名为“陈村”,明哲宗时改为所村,原来太平山房是陈氏祠堂,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后经明末清初、乾隆三十六年(1771)、咸丰二年(1852)等数次扩建,后来作学宫之用。
进到太平山房,看着四个径尺大字“积善流芳”,看着砖塑浮雕上的戏文典故,摩挲着顶梁而立的圆柱,仰望画枋彩绘……总有一种似曾见过的感觉如影随形。待看展板上的宣传文字,一幅电影海报揭开了谜底——太平山房曾是电影《渡江侦察记》取景地之一。走在太平山房,仿佛回到了童年,电影《渡江侦察记》是童年的关键词之一。
从太平山房出来,拐进了一户农家。四水归堂式的建筑,在这里比比皆是。进屋,墙面、家具……古旧之气扑面而来。堂屋里,两个老人静静坐在竹椅上干着手里的活,对我们一行人的到来似乎是司空见惯。老妪姓陈,老两口干着一样的活,一边剪着手里的鞋帮,一边回答我的问话。“剪一个三分钱”“一个人一天六七十块钱”“闲着也是闲着”……我用桐城话问,她用青阳话答,互相听起来一点都不隔阂。进到厨房,灶台上的铁锅里正焖着什么饭菜;新摘下的嫩南瓜搁在锅台上,青绿得需要一撮红辣椒丝来素炒。
在白墙黛瓦马头墙的陵阳古镇,好山好水好桥好人家孕育出的好吃食,让我多吃了一碗饭。在天下粮仓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我就着陵阳一品锅、陵阳豆腐干等陵阳菜,先吃了一碗,然后又加了一碗饭。如果时间回到几十年前,得几张粮票才够我中午之食吧。有如此之想,是吃饭前才从天下粮仓的粮票博物馆出来,这座隐藏在陵阳古镇的博物馆,竟收藏着20多万枚全国各地的粮票。
清朝生活在陵阳的诗人陈芳写过一首《陵阳镇陪随园老人望九华》,随园老人就是写有《随园食单》《随园诗话》的袁枚,妥妥的吃货一枚。他在陵阳吃到了陵阳一品锅、沙济毛豆腐、陵阳豆腐干吗?在《随园食单》中未找到踪迹。在《随园诗话》中,他倒是记下了生活在青阳“不事科举,以吟咏自愉”的诗人沈正侯和陈明经(即陈芳),以及他们的赠诗。
青阳山多,水多,桥多,老祠堂多。我的脚步所抵达的,不及百分之一。
许多人到青阳,是奔着九华山去的。我绕着九华山而行,青阳几日未登山,因为还没做好准备。
在青阳也读了几页书。读《桐旧集》,记住了一句“乡山千里月”。在青阳的几个晚上,都没看见月亮,难道是被山挡住了?写青阳、写九华山的诗句,写“月”的地方不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可能也照着古人吧,只是他们没有写下来,抑或写了没有流传下来。文学之道,到底是时间的艺术。
在青阳,听师友谈到如今的散文写作,一直在场者,他举了作家黑陶的例子。黑陶对江南的书写,一直是我了解江南的重要来源之一。他的一本本江南之书,让我对青阳有了另一种理解。
晚饭后散步,远处村庄传来了《苹果香》的歌声:“六星街里还传来巴扬琴声吗……”让我仿佛置身伊犁。寂静中,音箱声音空旷,远山模糊,近山幽暗。我就是从伊犁的六星街伴着歌声而来。青阳有青阳腔,我未专门去听。住在山脚时,听的都是手机里的视频音频,因为不懂,听不出所以然,只能听个热闹。虽然听不懂,但听着不隔,听出了青山的浓密,浓密中有溪流蜿蜒而下,这是皖南的腔调和山水底色,不像我们在伊犁草原上见到的水流,横冲直撞。
临走前的上午,坐在阳台的竹制藤椅上,远处青山巍峨,手里拿着的是本地友人所赠阅的《大家写青阳》。在青阳,想找一本“历代诗人咏青阳”之类的书而未得。李白三到青阳,得诗九首。李白以前,李白以后,来青阳写青阳者何其多,也不多我一人,也不多我这一篇。
毕竟,青山之阳的青阳,有我对皖南的想象和惦念。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