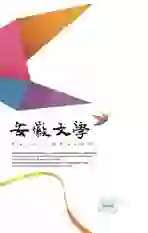敬个礼,握握手
2025-02-11霍君
1
枝萍在二十七岁那年拥有了爱情。
从未谈过恋爱的枝萍,简直被爱情给砸晕了。结婚好几月了,还晕乎乎的,整个人一直处在微醺状态。有时候,来饲料厂找冬哥,好朋友枝花夸张了语气赞叹,“呀,爱情的力量真强大,瞅瞅把你美的哟。”可不是嘛,枝萍何时画过眉毛,又何时涂过口红。不知道是枝萍技术不够熟练,还是眉笔的质量有问题,眉毛总是不够流畅,疙疙瘩瘩的。枝萍的一颗门牙像淘气的孩子,非要脱离牙齿的队列,朝嘴唇的方向凸起。这就导致嘴唇上艳丽的口红,沾染到牙齿上。枝萍一说话,那颗红色的牙齿便在嘴里跳跃。
枝花不觉得枝萍疙疙瘩瘩的眉毛和红色门牙有多丑,恰恰相反,在疙疙瘩瘩的眉毛和红色门牙的加持下,枝萍的幸福感更加肆意。它们从枝萍的眼睛里,从枝萍身体的毛孔里,往外喷溅。站在枝萍身边的人,都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幸福让枝萍成了移动的喷泉,走到哪里喷到哪里。枝花被喷得连心都湿润了,潮潮的,要长出苔藓来的感觉,有一点不适感。枝花不愿意承认,那种不适感叫作羡慕,或者嫉妒。做了二十多年的朋友,她怎么可能会嫉妒枝萍呢,简直是国际玩笑。
枝花和冬哥同在饲料厂上班,有一天傍晚下班,枝花说回妈那里,与冬哥搭伴而行。到妈那里,需要路过枝萍和冬哥的婚房。“去看看枝萍走了不。”枝花便跟着冬哥,进了院儿,又进了屋子。没发现枝萍的影子,却见一张纸条,用筷子压在饭桌上。冬哥拿起纸条先看了,然后递给枝花。
“亲爱的冬哥,我去上夜班了。悄悄地告诉你一句话,真想你呀。不看见想,看见更想,你说羞不羞?”
“她喜欢留纸条。”冬哥的言外之意是,枝萍明明可以给他发短信息,或者直接打个电话。显然,在写纸条渐行渐远的时代,自己的女人用传统的方式来传情达意,冬哥也是蛮享受的。习惯了看枝萍纸条的冬哥,微笑着把最新的纸条转手递给枝花,不无炫耀的成分吧。他的女人如此甜蜜,如此缠绵,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还不是他有魅力?!
冬哥没有注意到,读纸条的枝花,脸上变了颜色。
她的心在咚咚跳。她从来不知道,女人对自己的男人,可以这样赤裸裸地表达。在男女关系上,她是矜持的,傲慢的。以为说情话的话语权,掌握在男人手里。作为女人,只需享用就可以了。因此,当自己的男人说“你太冷淡了”,她依旧认为是男人的错。没想到,枝萍给她上了一课。
那样的表达,别说男人,连她枝花都心潮澎湃。看似羞答答的文字,却炙热得把人心烤到滚烫。每一个文字,都像燃烧的炭火。
这个枝萍,把一世的情,都用到了一个男人身上。如果不是她,枝萍怎么会遇到冬哥?说到底,是她枝花,给枝萍创造了一个燃烧自己的机会。
2
枝花跟冬哥是同事。之前,枝花和枝萍同在养鸡场上班,婚后才去的饲料厂。原因是婆家的那个村子,离饲料厂更近些。枝花去饲料厂时,冬哥已经在那里了。冬哥不是普通员工,是销售部门的负责人。在饲料厂,无论年龄长的还是年龄小的,见了冬哥,都喊一声“冬哥”。枝花便跟着大家,也喊冬哥。冬哥给枝花的第一印象,很特别。这个三十四五岁的男人,身上有一种莫名的沧桑感,好像经历了很多事情的那种。不管见了谁,他总是先微笑。沧桑感不妨碍他微笑,微笑也遮盖不住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沧桑感。它们好比孪生兄弟,在冬哥身上共存,又相互影响。在微笑的加持下,沧桑感更有味道。
除了是销售部门的小头头,除了可以分泌有味道的沧桑感,好像也没什么太多引起枝花注意的。彼时的枝花,需要适应婚姻,需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冬哥对她来说,不过是比她职位高一些的打工仔。枝花知道冬哥的一些事情,是在她歇完产假,再次进饲料厂上班之后。其实,一个打工人,哪里来的产假。只要枝花愿意,她可以无限期地歇下去,在家专职带娃。枝花是读过高中的,自然不肯和周围的小媳妇儿一样。把娃交给婆婆,她要出来寻找自由和独立。二进饲料厂后,与同事们熟络起来,一些私密的话便往枝花的耳朵里灌。
跟冬哥有关的如下:冬哥老家是河北的,口音和枝花这种本地人相近,因为他的老家和枝花所在的梦城接壤。说白了,听着挺远,实际上就是邻居。冬哥好像离过婚,有没有孩子不清楚。离婚的原因,好像跟进那个地方有关。那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就是人犯事儿了,才去的地方。
“好像”这个词语最可疑。然而,无风不起浪。冬哥也的确很神秘,从来不谈和老婆孩子有关的话题。不出差的日子,就住在厂里的宿舍。
一天下午,在养鸡场上班的枝萍来找枝花。也没什么事儿,两个好朋友有些日子没见,枝萍想枝花,就趁着值夜班,提前从家里出来了。两个好朋友正嘀嘀咕咕说着悄悄话,冬哥的身影从她们面前飘过。枝萍的目光落在冬哥后背上,追出去很远。
“好像单身,好像进过那个地方。”枝花的口气,有些惋惜。
“太好了。”
等到枝萍向冬哥发起攻势,枝花才弄懂枝萍“太好了”的含义。她不在乎他的过去,不在乎他有多神秘,只想让自己的目光,永远深情地落在他身上。枝萍的勇敢,惊到了枝花。在枝萍的目光落在冬哥身上的前一秒,枝萍还在跟枝花说,她这辈子,认了。只要男方能满足她的要求,条件差一些也无所谓,反正就是结婚,不是所有的婚姻都像枝花那样两情相悦。枝萍的话充满了无可奈何,令人心疼。
在村里,二十七岁没有嫁掉的女子,已经算大龄了。枝萍虽不漂亮,在二十七岁之前把自己嫁掉,还是不难的。之所以把自己熬成了大姑娘,和枝萍的那个要求有紧密关系。枝萍择偶的对象,须是周围的几个村,最好是本村的人。距离近,方便她日后照顾娘家。这个标准,按说不高,由枝萍提出来,就堪比攀登珠峰了。适龄的未婚男,纷纷望而止步。包括枝萍说的“条件差一些”的,也没有胆量应下这门亲事。当然,条件差到一定程度,嘴歪眼斜,或者需要“扶贫”的,不在枝萍考虑的范围之内。
枝花想劝枝萍,干吗非要委屈自己。劝人的话好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呢。毕竟,狗屎一样的现实摊放在那里。
枝萍想照顾的娘家,有一个半拉身子不能动的母亲,还有一座摇摇欲坠的茅草屋。她想护住茅草屋,不让它倒下来,砸到屋子里那个有巫婆气质的老太太。那座茅草屋,即便放在整个镇上,也是最惹眼的风景。它像易碎的老古董一样,摇摇欲倾地横陈在街道上。老古董到底多少岁了,恐怕村里最老的人,也未必说得清楚。谁都怕不小心碰碎了它,人绕着走,房子也都绕着盖。绕来绕去,老古董前边组成一排房子,后边组成一排房子。只有它自己,孤零零地在风中摇摆。泥巴墙,苇帘门,茅草顶,让人恍惚穿越到上个世纪的某个年代。
“认了。总不能把她掐死吧。”每次枝花想劝枝萍,枝萍都有预感。她无可奈何地守着易碎品,无可奈何地让易碎品成为婚嫁的砝码。婚嫁的砝码太重了,没有人愿意冲过来,帮她分担。
3
“小骚精,都是你给克的……你咋不嘎嘣儿了呀……”
那是一个母亲对八岁女儿最恶毒的咒骂。
六岁那年,枝萍跟着半拉身子不能动的母亲,入住这座全村最破败的茅草房。全村最破败房子的主人,是全村最老实的光棍。除了祖上传下的茅草房,他还有一头老黄牛。枝萍原来不叫枝萍,叫招弟儿,枝萍的名字是继父给她取的。“枝”是枝萍那一辈儿的排行用字。沉默得如那头老黄牛的继父,对枝萍和半拉身子不能动的母亲都很好。他的好,就是接受她们,从不苛责,从不挑剔。他甘心和黄牛一起,为这个多出两口人的家劳作付出。患有哮喘病的枝萍妈,和面烙饼,面盆里揉的仿佛是金面团。揉几下停下来,喘息一阵,嗓子里拉风箱。“我来吧。”耕地回来的继父说。“你来就你来,我留着劲儿,给你生个大胖小子。”枝萍妈顺水推舟的同时,给老实疙瘩许愿。
一年多过去,枝萍妈的肚子真的大起来。妈的半拉身子不能动,需要养胎。继父干不完的活,都是枝萍干。枝萍养大的鸡,下了蛋,全用来给妈补充营养。“招弟儿,你摸摸,这回肯定是个弟弟。”偎在炕头被垛上的母亲,唤着枝萍的乳名,让枝萍去摸她的肚子。
枝萍妈怀孕七个月时,枝萍继父突然去世了。继父拉着黄牛去地里,中午都过了也没回来。妈差枝萍去找继父,枝萍在地头看见黄牛在吃草,却不见继父。往大人高的玉米地深处走,枝萍发现了继父。继父躺在地上,身下压着倒伏的玉米秆。不知道继父经过了怎样的挣扎,几十棵的玉米秆都被他压倒了。锄草的锄头,悲伤地和继父遥遥相望。八岁的枝萍知道死亡的含义,那是她第二次站在亲人的死亡现场。第一次,是自己的亲生父亲。相似的场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再现了。
枝萍竟然没有哭,跑去把消息告诉了母亲,说继父死了。
好不容易养到七个月的胎儿,不知是不是被死亡的消息吓到了,非要提前出来。都说七活八不活,枝萍七个月的弟弟,却违拗了这一规律。一出母体,便死了。村里有传言,是枝萍妈命硬,克死了两个男人。枝萍妈找了个算命先生,算了一卦。算命先生果然给出了新说法,是枝萍这孩子命硬,克死了两个爸爸和弟弟。
“该死不死的。”每次挨骂,枝萍会小声反抗。枝花第一次听到当妈的那样骂自己闺女儿,特别气愤,恨不得扇骂人的两个巴掌。也是从那时起,对枝萍产生了同情心。暑假结束,枝花和枝萍都成了一年级新生。两个女孩在村里一个姓儿,同属于“枝”字辈儿,又同岁。刚开始,同情枝萍的枝花,也不敢跟枝萍一起玩儿。小孩子比大人更会传谣,大家都觉得枝萍不吉利,跟她在一起,说不定突然就会死掉。枝花当然也怕死,不敢贸然接近枝萍。后来老师说,谁把谁克死了,是迷信的说法。老师的话,并没有改变同学的看法。枝萍脏兮兮,头发奓着,很久不打理的样子。大鼻涕几乎流过了河,才用袄袖子一抹。冬天,没套外衣的棉袄前襟儿和袖口处,被一层一层的污渍腻住,僵硬得跟铁板似的。
课下,同学们踢毽子,没人带枝萍。跳皮筋,也没人带枝萍。孤单单的枝萍,站在一边看着同学们玩。同学笑,有时会跟着一起笑。笑着笑着,好像想起什么,就不笑了。
那次老师带着同学们玩找朋友的游戏。找朋友的同学们,唱着“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唱到“敬个礼”的时候,证明朋友已经找到了。边唱,边向着好朋友敬礼,握手。枝花找的好朋友是枝萍,当枝花蹦跳着,唱着歌谣,在枝萍身边停下,枝萍简直喜出望外。她将手掌在衣服上蹭了蹭,才握住了枝花伸过来的手。
这一握,开启了两个好朋友的友谊征程。
4
为了证明枝萍是枝花的好朋友,枝花在本子上郑重写下:枝萍和枝花是好朋友。
枝花的字迹与众不同,笔画特别重。每一笔都用了很大劲儿,有种力透纸背的既视感。掀到下一页,本子的空白处,清晰地印着上一页的字痕。“枝萍和枝花是好朋友”可不是写着玩的,从小学到中学,枝花和枝萍都是好朋友。
中学和小学一样,枝花的择友范围比较广,却独独和枝萍的关系最好。即便到了中学的枝萍,依旧不怎么受大家的喜欢。她经常迟到,匆匆忙忙地踏进教室,手上沾着没洗干净的面粉。上着自习课,突然从书包里拽出一根胡萝卜,咯吱咯吱啃起来。十几岁的女孩子,一点不注意仪容仪表。青春萌动的男生,都不正眼看枝萍。好像正着眼儿看了,会损失几两尊严。
“你俩一个村的,她家啥情况?”
不喜欢,并不代表不好奇。这个问题,枝花回答得很巧妙,她并没有说枝萍家是全村最穷的,穷家里还有一个经常骂大街的婆子。都是一个乡里的,想知道哪个村谁家的情况,一点儿也不难。何况,枝花枝萍的村,又不是只有她俩在中学读书。知道真相的同学,对枝花有了敬意。这才是朋友该有的样子,不在背后搞事情,维护朋友的形象。
这点无疑给枝花加了分。枝花早就发现,和枝萍做好朋友,利绝对大于弊。在枝萍的映衬下,枝花如出水芙蓉一样怒放在校园里。班上好几个男生,都将初次对女生的心动,给了枝花。枝花真的如一朵花,在青春的枝头绽放。心动的男生,都想凑近些,再近些,闻闻花香,观观花蕊。
“别往后看,那个讨厌的人,准在后边跟着呢。”
放学的路上,枝花对枝萍说。枝花说的“讨厌的人”,比琼瑶笔下的男主还痴情,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心意。每天放学,都尾巴一样,在枝花后边尾随着。蹬车的速度,由枝花决定。枝花快,他也快;枝花慢,他也慢。车子和车子之间的距离,总是不变。
枝花的语气多惆怅,多无奈。实际呢,她的嘴不怎么对着心。那一时,内心的小虚荣那叫一个满足。坚持尾随的,是一个脱颖而出者。她多希望,再多几个这样表衷情的。他们为她坚持,为她决斗。真正的勇士,才配她正视。
“是挺讨厌的。”
枝萍说罢,捏了座下叮当响的破自行车车闸。跳下车子,将车子横在马路上,拦住后边的尾随者,“脸皮咋恁厚呢,再跟着我们,把你扔道沟里去。”
枝花先是一惊,随后捂嘴笑,身子都被笑压弯了。
枝花的笑,给了尾随者勇气,他回怼枝萍,“谁跟着你呢,也不照照镜子。”
多伤人的话,枝萍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也许枝萍想过,从此和枝花保持距离,不再做好朋友。可是班里只有枝花不嫌弃她,自始至终对她好。没有了枝花,她会更加孤立。那么多男生喜欢枝花,却没有一个男生喜欢枝萍,枝萍心里很难过。用自行车拦截尾随的男生,并非全是为了保护枝花。她在借着这个行为,发泄内心的情绪。同样是人,怎么就那么不同呢。
枝花一边上学,一边忙着接受男生的宠溺。枝萍一边上学,一边深陷忙不完的家务中。继父的老黄牛卖了,卖的钱用于母女的生计。枝萍妈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又置办了冰棍箱子。她经历了男人去世和流产,半拉身子更加残败,好像连骑车子的力气都没有,便推着挂有冰棍箱的车子,到学校附近,趁着孩子们上下学,有气无力地吆喝,“冰——糕”。
卖冰糕的枝萍妈是有功的。她有病,但仍旧在努力地养着枝萍。否则,枝萍早吃不上饭,更别说上学了。所以呢,她这个功臣,到家吃枝萍做的饭,是理所应当的。枝萍把所有的家务做完,再去读书也是天经地义的。枝萍做得再好,也有达不到功臣满意的时候。或者,功臣明明知道枝萍做得很好,她情绪不好了,想发脾气了,便尖着嗓子把枝萍臭骂一顿。骂得可有底气了,一点也不像半拉身子的人。骂得越凶狠,越能表明,如果不是枝萍,她会辛苦地跑到大街上卖冰糕吗?
“该死不死的。”
枝萍每次都会低声回骂。
作为母亲,她养了她多少呢。哪个暑假,自己不是走村串乡地吆喝卖冰糕。多热,都舍不得吃一根。拼命地挣钱,给自己挣读书的学费。考上高中,然后考上大学,离开这个易碎的茅草屋和茅草屋里的婆子。希望的光芒,遮住生活的阴暗。她假装忽视易碎的茅草房,时刻需要她来支撑这个现实。
5
冬哥才不管,枝萍妈敢过来骂枝萍,他就守在院门口,手里拎了一块板砖。只要枝萍妈的脏话出口,冬哥手里的板砖真的飞出去。枝萍妈到底怕了这个上门姑爷,落荒逃回到茅草屋里。
“老牲口。”
在冬哥看来,那样骂自己亲闺女的,不是牲口又是什么。枝萍明白,母亲跟她找茬儿,其实是对冬哥不满。经过几次交锋,母亲自知惹不起姑爷,便拿枝萍开刀。枝萍妈和冬哥矛盾的爆发点,是外孙小豆子的姓氏。
冬哥跟着枝萍,在村里落户。两个人的婚房,在茅草房的后排,相距也就几十米。房子是花两万多块钱从村民手里买的,简单收拾了一下,便成了爱巢。歪歪拉拉的枝萍妈,依旧住在茅草屋。
“是不是那小子不让我搬过去的?”
“是我不让的。”
枝萍的话,母亲不信,坚持认为,是冬哥从中作梗,才把她自己留在茅草屋。
“死丫头,你就怕他吧。”
“真是我不让的。”
爱情的果子熟了,冬哥给取了个乳名,叫小豆子。大名的姓氏随了冬哥。这回枝萍妈不干了,正面和冬哥交锋。他是上门女婿,小豆子要随枝萍的姓儿。而且,小豆子不能管她叫姥姥,要叫奶奶。
“全冲我,别理她。”背地里,枝萍哄冬哥。
自从生了小豆子,枝萍就不再上班了。她不愿把小豆子交给母亲带,一个是母亲病病歪歪,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姥姥太多影响。小豆子是她跟冬哥爱情的结晶,枝萍爱得不得了。小豆子长得像冬哥,小酷哥一枚。这样的娃娃,她想生一窝。有冬哥和小豆子陪着,生活中其他任何的噪声,枝萍都不觉得刺耳。她愿意承受和忍受它们。
小豆子五岁那年,枝萍背着冬哥实施一个计划。悄悄去医院摘了节育环,想和亲爱的冬哥,再生产一个小豆子出来。也是那年,枝花把婚离了,住到了娘家。枝花下了班经常来找枝萍,枝萍把自己的计划耳语给了枝花。
“你可真幸福噢。”
枝花的话酸酸的,像被老醋泡过。枝花怎么也想不到,会轮到她羡慕枝萍。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她低下傲慢的头颅,学着枝萍那样,对自己男人甜言蜜语。终究,一切努力付之东流,输给了婚外的女人。不甘心拱手相让,枝花找到那女人,给那女人讲她和男人的故事。遥想当年,男人是一条粘在她身后的尾巴,赶不走,剪不断。那女人说,这些她都知道,男人给她讲过,而且讲得比枝花动情,都掉了眼泪。
枝花落败而归。
那个悲伤又沉重的时刻来了。枝萍给冬哥洗衣服,洗之前习惯性地掏空各个口袋。即使什么都没有,也要掏一掏,万一有呢。真的掏出东西来了,是一张折叠的纸。枝萍以为是票据,冬哥经常出差,各种票据少不了的。看着不像,枝萍便展开了。
“亲爱的冬哥,即便这辈子无法拥有你,我也要说出心底的话:喜欢你,想你。每一天,每一秒……”
没有落款。圆珠笔落下的字迹,笔画非常重。把纸片翻过来,枝萍用手去触鼓凸出来的印迹。每一笔,每一画,皆如刀似剑,将枝萍的心割得鲜血淋漓。
强忍着疼痛的枝萍,洗完衣,做好晚饭。将饭菜给茅草屋的母亲分出一份,送过去。送饭回来,枝萍走到院门口,刚好一阵风兜过来。身子便借着风势,慢慢倒下去。冬哥把枝萍送到县医院,脑部CT的结果,令人胆战心惊。医生说,瘤子不是一年两年了,原来不过是没症状,现在到了爆发期,会发展得很快。虽然是良性的,但长得位置太特殊了,做手术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了。冬哥想瞒着枝萍,哪里瞒得了。报告单在那里摆着,枝萍心里明白得很。
也不是一点症状都没有,只要一生气,一思虑过度,头便会疼。枝萍没往心里去,吃五谷杂粮,头疼脑热的不是很正常吗。她这个家庭状况的人,更没有那么娇气。
6
枝萍妈到处打听,请来一个女大仙儿。
“我姑爷儿能挣钱着呢,他的钱就是我闺女的钱,闺女有钱肯定亏不了当妈的。”枝萍妈怕大仙儿担心她付不起费,眨巴了一对小三角眼,嘟嘟噜噜地吐出一串词儿,证明她是有钱的。女大仙儿在茅草屋前转了一圈儿,又站在枝萍家房前左看右看……
结果居然是姑爷的命,比枝萍的命还硬。两个命硬的在一起,博弈了数年,最终枝萍落败。枝萍妈要不是怕挨姑爷的板砖,早打上姑爷的门儿了。噼噼啪啪扇姑爷几个耳光,再把一口老唾沫吐到姑爷脸上,给闺女和自己报仇。只是想想罢了,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茅草屋前,呜哇呜哇地哭上一通。
“我还没死呢,就开始号丧。”
枝萍剜了一眼母亲,鼻子有些发酸。母亲疼人的地方不多,但毕竟生了她。
自从枝萍生病,枝花来得更勤了。一来,就帮着做这做那,小豆子的衣服,枝萍和冬哥的衣服,她都给洗了。找药锅子,熬药,也都是枝花干。刚开始,枝萍还拦着,说这些活她要是干不动了,那可真该死了。枝花赶紧呸呸呸地啐几口,让枝萍把不吉利的话收回去。
“咱们谁跟谁,一辈子的好朋友。”
是呀,一辈子的好朋友,干就干吧。枝萍只负责陪着小豆子,和小豆子一起游戏,给小豆子讲故事,教小豆子做人的道理。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一块儿一块儿的,过出十天十个月的效果。
“小豆子!”
“小豆子!”
“小豆子!”
那是最宝贵、最甜蜜的三个字。一天里,枝萍不知道要喊多少遍。明明小豆子就牵在手里,却要大声地喊。五岁多的小豆子纳闷,妈妈还是那个妈妈,咋就突然和过去不一样了呢。
“冬哥,给我借个相机好不好?”
冬哥对枝萍百依百顺,果然借来了相机。枝花帮忙,给枝萍拍全家福。拍照前,枝萍认真地化了妆。眉毛用一支新买的眉笔画的,效果特别好,之前的疙疙瘩瘩消失了,线条非常流畅。口红也是新的,颜色不似过去的那么艳丽,内敛了很多。枝花在镜头里看见,枝萍笑的时候,那颗特别的门牙上,还是会沾上一些口红。拍完了全家福,又给枝萍和小豆子合影。搂着的,亲着的,母和子都笑得咯咯的,快乐柳絮一样到处飞扬。冬哥说,让枝花给他和枝萍也拍个合影照,这么多年,还是结婚时拍过合影照呢。枝萍笑笑,拒绝了,说累了,以后有机会再拍吧。
枝萍看来真的累了,自己去床上歇着,让冬哥枝花小豆子三个继续拍。枝花掌镜,拍冬哥和小豆子。冬哥掌镜,拍枝花和小豆子。枝花真是喜欢小豆子,也像枝萍那样,搂着小豆子拍,亲着小豆子拍。小豆子快乐极了,清脆的笑声像一颗颗豆子在滚动。
听着欢笑声的枝萍,伸手去枕套里摸索,取出那张没有署名的纸片。闭上眼,用手摸纸片背面凸出的字痕。一颗一颗地摸,直到把眼角的两行泪水摸出来。
刺啦,刺啦——明明是撕纸条的声音,怎么觉得是心撕裂了呢。
7
医生的话如魔咒。枝萍的病,以不可控的速度朝着魔咒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都对魔咒无可奈何。
在肿瘤的侵袭下,视力越来越模糊。记忆力也开始出现问题,有时候刚吃过饭,枝萍就忘了,问小豆子是不是饿了。小豆子挺着鼓鼓的小肚,让枝萍摸。枝萍这才知道,自己的记忆力出问题了。
“小豆子,抱抱妈妈。”
小豆子果然笑哈哈地去抱妈妈。他的小手臂还太短,不能将妈妈合拢起来。妈妈咋了呢,身子在发抖。伸手摸摸妈妈额头,又摸摸自己额头。他有病发烧,妈妈就是这样摸他的。
“小豆子,妈没事儿,挺好的。”
“小豆子,妈妈问你,枝花姨姨好不好?”
“好。”
“小豆子,让枝花姨姨当你干妈好不好?”
“好。”
小豆子又哈哈笑。他管枝花姨姨叫了干妈,枝花姨姨往后肯定更喜欢他了。给他买喜欢的玩具,给他买好吃的。
枝萍就把小豆子认枝花干妈的事,分别跟冬哥和枝花提了。冬哥说,认啥干妈,就这样叫着不挺好吗。枝花说,认不认的就是个形式,我早就拿小豆子当亲儿子待了。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有多大区别呢。
枝萍说,认了好,还是认了好。
让小豆子给枝花磕头,磕了头叫干妈。小豆子觉得好玩,一边磕头一边咯咯笑。枝萍不笑,枝花不笑,冬哥也不笑。
枝萍又跟冬哥说了一件事,让冬哥帮忙找一家养老院,把老太太安顿好了。冬哥搂着枝萍的肩膀直落泪,我的好媳妇,瞎说啥呢。
枝萍的状况越来越糟糕,随着视力的彻底消失,疼痛也越发气势汹汹。输液的针头,把手臂都扎烂了。冬哥明白,枝萍生命的大限快到了。请了假,专门在家陪伴枝萍。一辆三车轮,冬哥蹬着,枝萍和小豆子坐着,绕着村子转悠。好温柔的春风,不知道跟田野酣睡的冬小麦耳语了什么,醒来的麦苗,浑身都是成长的能量。
“小豆子,跟着麦苗一块儿长大吧。”
枝萍听到了春风的耳语,听到了麦苗成长的誓言。呀,春天真好。
“好哇,我使劲长,长大了开大汽车拉着妈妈。”
妈妈看不见小豆子,小豆子很忧伤。忧伤的小男孩,已经懂得哄妈妈开心了。
厂里有重要事情,枝花就请假顶上来,照顾枝萍。像冬哥一样,踩着三轮车,拉着枝萍出来散心。
“你是谁?”
“我是枝花,你最好的朋友,小豆子的干妈。”
过了会子,枝萍做恍然大悟状,“哦,想起来了,你是枝花。”
枝萍一阵清醒,一阵糊涂。
转哪转哪,转回到村里。很多村人对枝花赞不绝口,“瞅瞅,这就是活雷锋啊。”经过枝萍妈的茅草房,巫婆气质越发明显的枝萍妈,勾着老腰,几乎被上眼皮子盖住的小三角眼,发出的悠悠光芒,往枝花的肉里钻,“枝花呀,你没安好心眼儿吧?”
枝花怎么会跟那样一个老太太计较呢,她问枝萍,“想吃啥?新鲜的。”
“那个又香又臭的。”
“啥东西又香又臭的?”
三轮车进了枝萍家院子,枝花猛然灵光一现,“我知道了,你说的是榴莲。”
8
“回来吧,枝萍不行了。”
这通电话,是冬哥打给枝花的。
接到电话的枝花,请了假匆匆往枝萍家里赶。此刻的枝萍,好像睡着了,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任凭周围人呼唤,都打扰不到她。在村里白事知客的安排下,枝萍一身簇新的寿衣。左手中指戴着一枚冥界的大钻戒,显得特别富贵。坐在床边的冬哥,不时把身子探下去,查看枝萍的呼吸。呼吸在的,只是过于微弱了。游动的丝儿一样,若有若无,需细细地捕捉。对面凳子上坐着的知客,看冬哥的表情,只要冬哥一摇头,便指使人把逝者往门板上抬。
枝花踉跄而入,扑到床前,一把抓住枝萍的手,“枝萍,我来了。”
听到枝花的声音,安睡的枝萍竟然睁开了眼睛。空茫的眼睛睁开着,一眨不眨。她的嘴在嚅动,好像要说什么,已经没有力气把话送出来。
“是让我给你化妆吗?”
在冬哥面前,枝萍那么爱美,一定不想冬哥看到她素颜的模样。枝花以为读懂了枝萍的唇语,就要准备给枝萍化妆了。却不对,枝萍的唇嚅动得更快了。
“放心吧,往后小豆子就是我亲儿子。大妈就是我亲妈,给她养老送终。”
还是不对,枝萍的眉头皱起来。细密的汗珠儿,从鼻尖儿上往外沁。猛然,她的右手努力上移,移动到头部的位置,做出一个敬礼的动作。
枝花瞬间明白了。
枝花站起身来,在枝萍的床头唱道,“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枝花对着枝萍敬完礼,俯身握住枝萍的手。
轻轻地,枝萍吐出最后一口气,慢慢闭上眼睛。
经过一个夏天,又经过一个秋天,枝萍妈已经下不了地儿了。老太太要睡热炕,枝花每天晚上都会过去给烧。
“你这个骚精,占了我闺女的窝儿,还天天装好人。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我是大仙儿,能掐会算。”
枝萍妈在里屋炕上骂骂咧咧。枝花往灶里填完最后一把柴,低声回骂,“该死不死的。”
回骂的语气和神态,和枝萍一模一样。
责任编辑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