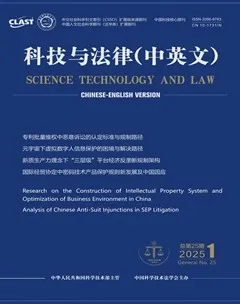元宇宙下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2025-01-03熊进光张峥
摘" " 要:元宇宙下虚拟数字人信息与元宇宙用户信息实时传递,具有同步性,但相较于以自然人为主体的个人信息保护,虚拟数字人信息缺少相应的监管与保护措施,泄露风险加剧。现有立法无法对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适用范围、责任认定等核心内容提供精细指引。基于此,当前应立足民法保护、算法技术归责以及行业规范三维路径。首先,确定虚拟数字人法律主体地位、厘清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范围;其次,建立算法数字技术归责体系,明确责任承担方式;最后,确定元宇宙平台的准入标准、明晰企业的权利义务。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数字人;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权;平台准入
中图分类号:D 911"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2096-9783(2025)01⁃0026⁃12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正式发布,旨在推进数据分级分类确权授权使用[1],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2]。报告还指出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而作为新兴领域的元宇宙,其高速发展不论是对数字经济还是对个人信息保护都提出一定的挑战。
元宇宙(Metaverse)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所创作的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在2021年随着Roblox市值爆发与Facebook更名为Meta而迅速成为焦点,引发各界的研究热潮[3]。元宇宙的本质是通过整合多种新技术,包括区块链、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4],用户则以虚拟数字人的形态在其内活动。虚拟数字人是元宇宙用户在元宇宙的活动载体与交互媒介,为现实世界与元宇宙提供了“人格互通”的钥匙。因元宇宙是高度发达的虚拟世界,虽独立于现实世界,却又具备交融性、文明性与沉浸性[5],所以元宇宙与现实世界之间保持同步,虚拟数字人与元宇宙用户的个人信息也保持一致,实时更替。但与此同时,元宇宙收集、使用、存储虚拟数字人个人信息的行为能否适用现实世界中自然人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以及虚拟数字人个人信息受到侵害时要如何寻求救济是目前的一大难题。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往往仅针对元宇宙用户可能存在的侵权现象以及虚拟数字人在各行业的应用进行梳理与分析,而鲜少涉及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的信息保护问题。基于此,本文在分析元宇宙运行原理及虚拟数字人特性的基础上,将结合我国现行立法与行业规定,尝试在民法保护、算法技术归责以及行业规范三个维度提出可行的因应对策,以期对元宇宙下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研究有所裨益。
二、元宇宙下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逻辑起点
虚拟数字人指存在于非物理世界中,基于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由计算机图形学、图形渲染、动作捕捉、深度学习、语音合成等计算机手段创造及使用,并具有多重人类特征(外貌特征、人类表演能力、人类交互能力等)的综合产物[6]。虚拟数字人具有媒介属性,元宇宙用户通过与之唯一对应的虚拟数字人形象在元宇宙内存在并进行一定的活动。可见,虚拟数字人为元宇宙用户的化身且具有同步性,虚拟数字人与元宇宙用户之间存在信息共享,且前者的个人信息具有保护的法理逻辑。
(一)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特殊性
相比于自然人,虚拟数字人的信息保护呈现诸多典型特点:
第一,个人信息主体的虚拟性。元宇宙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但其本质仍为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虚拟数字人则是通过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技术呈现的全新载体。虽然虚拟数字人承载着元宇宙用户的意识,但其本体仍具有虚拟性,这是虚拟数字人与现实世界自然人不同的特性之一,也对个人信息保护造成了挑战。
第二,个人信息的数字性。元宇宙是整合多种新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被描绘为“下一代互联网”[7],其基于扩展显示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8]。虚拟数字人作为元宇宙的主体,依附元宇宙世界而生存,其与元宇宙用户之间所互通的信息全部存储在元宇宙之中。因此,虚拟数字人的个人信息对于现实世界而言,是存储在区块链上的各类网络代码,即虚拟数字人的信息具有数字性。相对于实体而言,数字性的个人信息虽可以通过加密系统等加以保护,但是该系统一旦被破解,虚拟数字人的所有信息将完全裸露在大众眼前。除此之外,数字性信息存在被调整的风险且实施者的隐蔽性更强、实施行为的痕迹性更弱,故而虚拟数字人的信息与现实世界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存在差异,对其规制不能直接适用传统个人信息保护的思路。
第三,个人信息的时空同步性。元宇宙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连接,具有沉浸性、虚拟现实性与时空同步性等特征[9]。虚拟数字人与其对应的元宇宙用户也存在同步性,即虚拟数字人的状态会随着元宇宙用户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而发生改变,而元宇宙用户以虚拟数字人身份在元宇宙中进行的活动也会影响现实世界中的自身,两个世界的主体状态同步变化,基本保持一致步调。因此,虚拟数字人的个人信息也会受到现实世界的影响,这意味着保护虚拟数字人的个人信息,需要兼顾元宇宙与现实的双重因素。
(二)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理论证成
元宇宙基于自身运行逻辑与独有特征,收集并存储了海量现实世界的信息,但同时也面临着信息泄露的风险[10]。而虚拟数字人个人信息具有数字性与时空同步性,与元宇宙用户相对应,因此,面对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在保护现实世界自然人个人信息的同时,保护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的个人信息也十分重要。
首先,基于元宇宙的背景与特征,虚拟数字人信息具有保护的必要性。虽然目前元宇宙依旧没有官方、统一的概念界定,但其所具有的“沉浸性”特征基本上获得了一致认可。而沉浸性的特征需要通过三维建模、三维显示、三维音频以及体感交互四大技术相互协作[11],且这些沉浸式技术需要收集眼球位置、肌电图、脑电图、心电图等各种生物信息,涉及用户的各类隐私与个人信息[12]。同时,基于元宇宙身份认证具有唯一性,每位用户都有唯一且确定的虚拟数字人与现实人设直接关联[13]。因此,沉浸式技术所收集的各种生物信息将在用户所对应的虚拟数字人身上映射出现。故而,在元宇宙视阈下,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问题是应对个人信息泄露风险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其次,基于数字时代的发展与需求,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是急需解决的问题。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与元宇宙虚拟数字人相关的侵权案件已然出现。2021年,一位21岁的女性研究员表示,她在Meta公司开发的游戏《地平线世界》(Horizon Worlds)中遭到陌生男性虚拟数字人的性侵。无独有偶,2024年1月,英国一名未成年少女报案称,自己在元宇宙中设立的虚拟角色被一群陌生的成年男性进行了“轮奸”。这两起与虚拟数字人相关的案件侵害了虚拟数字人的人格权,对用户的心理与情感造成巨大伤害。虽然目前侵害虚拟数字人个人信息的纠纷尚未发生,但用户的虚拟形象和数字分身威胁用户隐私安全的趋势已经出现[14]。目前,元宇宙尚处于初始阶段,但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虚拟助手Sora已在2024年年初进入大众视野。Sora的推出能够为元宇宙提供助力,为用户提供全新的智能交互体验,是推动元宇宙发展与实现的重要工具[15]。在元宇宙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虚拟数字人信息侵权的趋势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因此,基于数字时代的发展与需求,为了在推动元宇宙等数字技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合法权益,我们应充分考虑并解决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相关问题。
(三)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价值
虚拟数字人是元宇宙与现实世界实现时空同步的纽带,是元宇宙用户进入元宇宙世界的凭证,是实现虚实共生的新型人类社会的媒介[16],因此虚拟数字人的个人信息与现实世界、元宇宙世界以及元宇宙用户之间都存在着牵连关系。
首先,虚拟数字人信息与元宇宙用户个人信息具有保护的同一性。因元宇宙沉浸式特点,每一位用户在进入元宇宙后都有与其相对应的虚拟数字人,该虚拟数字人具有特异性与唯一性,承载着该元宇宙用户的意识以及其个人信息。如果忽视对虚拟数字人的信息保护,其所承载的元宇宙用户的个人信息同样有泄露、不当利用等风险。事实上,黑客完全可以基于元宇宙的身份识别、沉浸性等刚性准入要求,锁定与虚拟数字人相对应的现实世界的元宇宙用户,再以虚拟数字人为媒介,将元宇宙用户的个人信息进行破解并收入囊中。而这一侵犯虚拟数字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将因元宇宙的虚拟背景及技术壁垒,难以被用户察觉。即使在一段时间后被发现,也已依据被窃取信息的重要程度对用户造成一定的损失,且加大了追责难度,如此必将对元宇宙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造成巨大冲击。
其次,保护虚拟数字人的信息有助于维护现实世界的秩序。因元宇宙与现实世界具有时空同步性,所以虚拟数字人在元宇宙中所发生的事情也会对现实世界造成影响。如果对虚拟数字人信息不加以保护,黑客可以基于虚拟数字人信息的数字性对其进行盗用、传播甚至篡改,而这些相关数据将因元宇宙的时空同步性而影响现实世界,对元宇宙用户的现实信息造成消极影响。当信息波动的范围不断扩大,波及的元宇宙用户越来越多时,现实社会的正常运转必将受到冲击,而此时因元宇宙与虚拟数字人的虚拟性,现实世界的法律制裁调整数字信息的行为效率过低且复杂程度较高,从而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此外,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避免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大范围出现,必须确立符合元宇宙逻辑的秩序体系。而元宇宙中行为的法律边界和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政府的干预又处于上位法真空状态,需要元宇宙成员(虚拟数字人)达成定分止争的治理规则并自力执行,以应对成员身份和行为发生的深刻变化[17]。基于此,为了抑制元宇宙中侵权现象,提高规制的效率与效果,在处理元宇宙纠纷时,应当区分用户与虚拟数字人,以虚拟数字人为主体构建新的秩序框架。而当元宇宙内在规则出现失灵的状况时,则需要现实世界的外在规则进行特殊干预。
最后,对虚拟数字人的信息保护同时保障了元宇宙世界的有序发展。虚拟数字人是元宇宙的活动主体,其个人信息是元宇宙正常运转的底层基础。如果虚拟数字人的信息不受任何保护,则一些虚拟数字人可能会因好奇或利益冲突等原因去探寻其他虚拟数字人的个人信息,从而导致冲突不断。除此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如果虚拟数字人信息不受保护,一直纵容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虚拟数字人在元宇宙中将没有隐私可言,元宇宙用户进入元宇宙中也将以“全裸”的形态出现,如此,元宇宙用户必将舍弃元宇宙平台,虚拟数字人的数量将不断减少直至消失,元宇宙的存在也将毫无意义。
由此可见,基于元宇宙的沉浸性、时空同步性、虚拟现实性等特征,虚拟数字人的个人信息不仅关系元宇宙世界本身,还涉及与其存在映射关系的现实世界,因此,虚拟数字人信息具有合理保护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三、元宇宙下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困境检视
元宇宙下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不仅关系现实世界中公民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等权利的保障,还涉及元宇宙世界信息收集标准的分级与制定。由于元宇宙世界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且是数字时代的新兴产物,我国对元宇宙的安全风险把握不足,在推进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进程中陷入困境。
(一)我国对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归责模式
元宇宙的运营需要搜集虚拟人的诸多敏感信息,又因元宇宙具有跨地域性,一旦发生信息泄露,危害不容小觑,这也意味着当前亟待对虚拟数字人信息构建有效的监管机制。但目前而言,我国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体系性的保护模式,而是将其作为附带义务,把责任归属于相关平台或相关责任人,以此达到保护虚拟数字人信息的目的。
1.元宇宙平台归责模式
目前保护虚拟数字人信息的方法之一是基于元宇宙平台所承担的义务而确定元宇宙平台所需承担的责任。元宇宙技术尚处于初期,元宇宙世界也处于雏形阶段,所以很多制度都没有确定,对流入元宇宙的各类信息缺乏监管。但是,目前要进入元宇宙世界中,必须借助元宇宙平台这一渠道,故而元宇宙平台作为进入元宇宙世界的唯一途径,其在用户体验元宇宙世界的过程中收集了海量的用户数据。而用户数据是信息的载体和传输方式,同时用户信息承载着用户隐私的具体内容,所以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关系着用户的隐私权是否得到保障[18]。毫无疑问,元宇宙平台负有妥善保管这些数据的义务以保护元宇宙用户的个人信息与隐私。因此,当虚拟数字人信息在元宇宙中被非法盗取,造成数据泄露时,元宇宙平台将因其没有尽到妥善管理的义务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元宇宙平台承担责任后,其可基于虚拟数字人唯一性特征而找到实施侵权行为的虚拟数字人所对应的元宇宙用户,向其追究补充责任。
2.虚拟数字人所有权人归责模式
虽然元宇宙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但目前元宇宙仍不适用现实世界的法律规定,能否将元宇宙中的主体虚拟数字人认定为现实世界的法律主体也仍存在争议,目前的认知是将虚拟数字人认定为技术产品,即认定为由元宇宙用户延伸而出或是由元宇宙平台基于多种技术而创造出的高仿机器人。而关于因虚拟数字人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从责任承担角度来看,虚拟数字人研发者、生产者或经营者显然具有更强的赔付能力,为了更好地救济与保护受侵害者的权益,应追究他们三者的相关责任[19]。
基于元宇宙的存在、运作与发展原理,虚拟数字人是元宇宙用户通过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技术在元宇宙中的延伸,承载着他们的意识,因他们的存在而存在并始终与其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虚拟数字人相当于元宇宙用户的虚拟化身,而元宇宙用户则是虚拟数字人的本体与所有权人。故而追究元宇宙用户的侵权责任是目前保护虚拟数字人信息的另一种方法,即通过追究虚拟数字人所有权人的责任来制裁元宇宙中的潜在侵权行为,达到保护虚拟数字人信息的目的。
(二)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困境
元宇宙的发展属于新兴数字领域,目前尚处于雏形阶段,对于虚拟数字人的定性与监管也处于摸索阶段,因没有成熟的规制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在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方面面临诸多困境。
1.虚拟数字人主体的人格认定存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二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基于此条规定,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首要困境就是虚拟数字人作为元宇宙中的活动主体,其能否成为现实世界中的法律主体,在个人信息保护中能否享受一定的权利以及承担相应的责任。
目前关于这一问题还没有定论,学界关于虚拟数字人能否成为法律主体存在肯定说、否定说以及折中说三种观点。肯定说认为应当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将虚拟数字人拟制为人是解决侵权法律问题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只有赋予虚拟数字人法律主体地位,才会涉及是修改立法还是通过法律解释等途径去规制其侵权行为的法律选择问题[20];其次,虚拟数字人承载元宇宙用户的意识可溯因至元宇宙沉浸性与同步性,可以认为虚拟数字人具有自主认知能力,该能力是自然人意识的延伸。可见,虚拟数字人做出的决定就是元宇宙用户意志的体现,只是将行为与场景从现实世界转移到了元宇宙世界,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所以虚拟数字人可以等同于元宇宙用户,应当具有自然人的法律主体地位。
否定说基于以下三点原因,认为不应赋予虚拟数字人法律主体地位。首先,元宇宙与虚拟数字人发展迅速,如果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不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否认虚拟数字人的人格主体更具客观性且更加理性[21]。其次,虚拟数字人是存在于数字世界中的人工智能,法律的作用不是为其无节制发展保驾护航,而是将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控制在人类的预测范围内[22],而且虚拟数字人的过度发展有威胁人类安全、扰乱当下社会秩序的风险,所以不应该赋予其独立的法律人格[23]。最后,虽然虚拟数字人具有自我认知能力,但他的本质是数字代码,且活动范围局限在元宇宙这个虚拟世界中,无法参与人类的社会活动,对虚拟世界中的主体进行法律规制与处罚,比起法学来说,更像是科幻的主题[24]。而且元宇宙与现实世界存在一定的差异,现实社会的法律无法延伸到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不能被相关法律调整与规制,因此虚拟数字人与元宇宙用户存在本质差异,不能具备法律上的主体地位。
折中说认为,虚拟数字人是自然人基于元宇宙底层技术所创造出来的认知型人工智能,其法律地位可以适用“电子人格说”。“电子人格说”首次出现于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立法建议致欧盟委员会的报告草案》,该学说的观点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并非最初产生就自动获得,而是需要有关机关颁发资质执照从而取得法人资格,即需要由人类为人工智能赋权[25],通过赋予最精密的自主机器人“电子人格”,从而解决机器人自主决定或其他独立于第三方交互的案件[26]。
2.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范围模糊
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另一困境在于没有明确保护的范围。因元宇宙与现实世界存在映射关系,在其运行与发展的进程中,采集现实世界及元宇宙用户的相关信息是无法避免的行为,而 “法无禁止即可为”,如果没有明确具体的信息保护范围将会导致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成为一纸空谈。
首先,数字身份体系的信息是否属于保护范围。元宇宙虽然是虚拟的数字世界,但是元宇宙中的主体虚拟数字人是承载着元宇宙用户的真实意思,即元宇宙用户可以虚拟数字人的形象在元宇宙内生存与交互,虚拟数字人是元宇宙用户的数字身份。而数字身份管理是数字世界安全事务的核心,为鉴别、授权、访问控制、账户访问及其他各种与用户属性相关的应用提供支持[27]。当元宇宙用户以虚拟数字人身份进行交互时,虚拟数字人的身份信息至关重要,但是我国目前没有建立起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官方数字身份体系[28]。其次,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是否需要模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即只保护元宇宙内虚拟数字人的各类信息,还是需要把现实世界中元宇宙用户的信息一并纳入保护范围。如果只保护元宇宙世界内的数字信息,如何把握好元宇宙与现实世界映射性与同步性是十分关键的因素;如果把元宇宙用户的信息一并纳入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则涉及现实世界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及元宇宙平台对信息汇总与转换的责任义务。最后,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程度与种类也亟待明晰。虚拟数字人产生于元宇宙用户本身,也将因元宇宙用户的年龄而出现未成年虚拟数字人与成年虚拟数字人,对二者的信息保护程度应当加以区分。此外,因现实世界与元宇宙世界存在映射关系,二者会保持同步,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交互必不可少,故而对信息保护的种类也应当加以划分。如果对虚拟数字人的所有信息均采取限制性措施,将对元宇宙世界的发展造成巨大阻碍。
3.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侵权责任认定不明晰
面对亟待解决的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问题,除了虚拟数字人主体地位存在争议以及信息保护的范围没有确定的问题之外,基于元宇宙的特性而导致的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侵权责任难以认定也是一大挑战。
首先,虚拟数字人个人信息过度公开化。映射性与同步性是元宇宙的显著特征,虚拟数字人与元宇宙用户也保持着实时信息传递,这意味着在元宇宙世界的运行模式中,所有的信息将以数字的形式向所有玩家、所有地区公开,不会进行筛选与排查。因此,元宇宙背景下的过度开放会涉及数据主权的相关问题,从而给侵权责任的认定带来巨大麻烦。元宇宙开放的属性,意味着虚拟数字人的信息不再仅仅存在于中国,其将难以受到本国政府的监督。我国虽然是数据大国,但与美国、欧盟等相比,缺乏清晰可行的数据跨境流通规制框架[29]。所以一旦发生信息被窃取或数据被破解的情况,将严重影响元宇宙用户的个人隐私权保护。同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缺乏考虑数字企业从境外获取个人信息的途径与规则[30],元宇宙平台在信息过度公开的背景下,将很难监管元宇宙世界中国内外信息的输入与输出,更难以把握境外黑客的动态,甚至在虚拟数字人信息被境外势力侵犯后,难以查明该信息是在何时何地被何人所窃取。基于此,元宇宙平台将很难查明并认定各方侵权责任的承担,也很难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即使公权力机关出面维护被侵害者的利益,也可能会因管辖权冲突等问题而陷入僵局。
其次,虚拟数字人个人信息难以彻底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七条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等条文都已规定,自然人可以查阅、复制个人信息,对其个人信息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更正权与删除权。但是,元宇宙的底层核心技术之一是区块链技术,而不可篡改性为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特征,这意味着虚拟数字人个人信息在元宇宙中的情况与个人信息删除及信息更正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31]。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意味着虚拟数字人的信息只能进行“增”和“查”而不能进行“删”和“改”。虽然这一情况保障了虚拟数字人信息不会被随意篡改,但是也带来了新的侵权责任认定问题,即当虚拟数字人或元宇宙平台发现自己涉及信息侵权,且双方都及时采取了必要措施却因元宇宙的刚性准则而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时,侵权与否以及侵权责任认定依旧存疑。
最后,虚拟数字人个人信息保护的认定缺失法律标准。因元宇宙是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同的虚拟数字世界,所以元宇宙中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公开的。而为了保证元宇宙用户的沉浸性及其与虚拟数字人的同步性,二者的大部分信息也都是需要公开并进行对接的。如此一来,虚拟数字人的哪些信息可以供所有玩家知晓,哪些信息是可供所有玩家使用,而又有哪些信息涉及其隐私权而不可被侵犯是平衡现实世界与元宇宙世界个人信息保护及进行侵权责任认定的重要因素。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出台相关法律或达成行业共识以规范虚拟数字人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正是由于上述认定标准的缺失,导致虚拟数字人信息被侵犯时,其所有权人或其所对应的元宇宙用户难以救济,侵权行为的责任认定也一直处于模糊状态。
四、元宇宙背景下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路径
行文至此,至少可以明确虚拟数字人信息是元宇宙用户的个人信息在元宇宙中的映射,关系元宇宙用户的隐私权以及现实世界与元宇宙世界的社会秩序,其信息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下文将结合元宇宙的发展现状与现实世界的法律文本,提出保护虚拟数字人信息的针对性对策,预防可能出现的侵权现象。
(一)明确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定位与范围
法律具有强制性与权威性,是保护公民权利与义务最重要的手段与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公民可以通过《民法典》人格权编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不受非法侵害,同时,我国于2021年开始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来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但并没有针对元宇宙的法律规制细则,虚拟数字人的信息没有得到合法保障,因此,我国必须弥补相关法律的空缺,对于关键性因素给予法律上的认可。
1.明确虚拟数字人的法律主体地位
虚拟数字人到目前已出现很多种类,根据种类的不同,学界对其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也持不同态度。比如有学者认为,对于“中之人”虚拟数字人应赋予其自然人所拥有的法律主体地位[32];也有学者认为,对于“非智能驱动型”虚拟数字人具有数字生命[33];还有学者认为,只有“强AI驱动型”虚拟数字人才存在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可能性[34]。而本文仅讨论是否应赋予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法律主体地位。
首先,笔者认为,赋予虚拟数字人法律主体地位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应通过法律明确其主体地位。虚拟数字人是元宇宙用户在元宇宙中的虚拟化身,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依旧没有改变。在网络时代,自然人以互联网为载体实施盗窃等行为时,自然人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虚拟数字人也是如此,只是将以互联网为载体转换成了以元宇宙、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为载体而已。基于元宇宙的特点,侵犯虚拟数字人信息其本质是窃取元宇宙用户的个人信息,如果不赋予虚拟数字人法律主体地位,而仅作为新兴技术,以侵犯一个“技术”或一个“衍生物”的相关信息进行规制,似乎难以达到罪责刑相适应,难以给予个人信息合理程度的保护。除此之外,虚拟数字人的数字身份与用户的现实身份在形态、特征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元宇宙与现实世界的底层逻辑也大相径庭。同时,数字身份民法定位从客体发展到主体,表明数字身份的法律地位不断独立[35]。基于此,由于虚拟数字人既非财产,亦与自然人人格存在差异,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自然人与虚拟数字人应在各自的世界中独立参与民事活动,享有一定的民事权利并承担一定的民事义务。
其次,赋予“非人”生物法律主体地位并不是无稽之谈,有一定的现实与理论依据。2016年,欧洲议会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应当考虑为复杂的自主机器人创设特殊的法律主体地位[36];2017年,沙特授予机器人Sophia沙特公民身份[37];2017年,欧洲议会发布《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赋予机器人“电子法人”法律主体地位[38];同年,俄罗斯《格里申法案》提出将机器人以类似于法人的定位,赋予其民法主体地位和民事权利能力[39];而我国也早在2017年就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指出应当解决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问题,明确权利、义务及责任的内容,为其提供法律制度的支撑。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上“人”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为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创设一个特殊的法律主体地位也是顺应时代的因应之策[40],为解决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难题提供新的视角与新的方法。
最后,在明确赋予虚拟数字人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可行性之后,该特殊法律主体地位是归属于自然人还是法人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虚拟数字人作为一种强人工智能与同为“人格拟制”的公司相比,在功能与形式上都有较高的相似度[41],可以借助法人的赋权逻辑,赋予其法人的法律主体地位[42]。当区块链、算法等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虚拟数字人可以与公司一样具备意志的执行能力[43]。对此,笔者持赞同意见,虽然虚拟数字人的三要素之一是智能驱动支撑的心智内核,意味着虚拟数字人具有“类人”的心智特征[44],但是元宇宙背景下的虚拟数字人基于虚拟现实技术,承载了用户的意识,是现实自然人的意志与能力在元宇宙中的延伸与拓展[32],其行为由背后的元宇宙用户决定,服从于现实自然人的意志[45],即元宇宙用户通过虚拟数字人在元宇宙世界中表达并执行自己的意志。公司也是如此,创始人借助公司章程等文件通过公司传达并执行自己的意志。故而,虚拟数字人在未来实践中所具有的执行能力及内在赋权逻辑与公司法人十分相似,可以将虚拟数字人的法律主体地位等同于法人的法律主体地位,享有法人所有的权利,也承担法人需承担的义务。此外,不论是俄罗斯的《格里申法案》还是欧洲议会的《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都是赋予机器人类似法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基于此,赋予虚拟数字人法人法律主体地位不仅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依据。
2.厘清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范围
在确定虚拟数字人的主体地位后,如何划定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界限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难以给予个人信息合理程度的保护不仅会影响虚拟数字人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还会阻碍元宇宙世界的运转与发展。然而,要明确信息保护的界限不仅需要法律层面的规制,还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撑,国家介入保护的同时必须将底层技术纳入考量范围。因此,对于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范围,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两组关系:
第一,元宇宙发展与个人隐私权益的协调关系。目前,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于数据分级分类的方法不同,欧盟将数据分为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46];美国仿照欧盟的方式,基于数据的内容与性质将其分为敏感与非敏感两类[47];而我国则是将数据分为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两类,采取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保护体系双轨化,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将数据分为一般数据和重要数据,同时又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明确了敏感个人信息的范围[4]。元宇宙的发展离不开各方海量的数据与信息,但是过度收集又对虚拟数字人信息造成侵害,因此法律应对虚拟数字人与元宇宙用户信息相关的数据进行精准分类[48],即可基于影响对象、影响程度与数据等级数量三方面因素[49],将虚拟数字人信息分为一般信息与敏感信息并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所谓敏感信息,是指一旦该信息被泄露或者被非法使用,就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50]。而对于虚拟数字人而言,敏感信息不仅是其在元宇宙中的身份认证媒介,还是构建其数字身份的生产资料[51],所以应当严格保护虚拟数字人的敏感信息。一方面,应该严格贯彻“知情同意”规则,将“范围同意权”交于虚拟数字人自己,即当元宇宙平台需要虚拟数字人的收入、基因、医疗等敏感信息时,必须得到其同意才可进行收集与应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算法”技术进行保护。虽然单一数据很难被识别出是否为敏感信息,但是元宇宙中汇集足够庞大的数据时,就能关联出大量的敏感信息[52],此时可以通过隐私计算技术对敏感信息进行脱敏处理,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让数据和信息适度分离[53]。
第二,要把握虚拟数字人信息与元宇宙用户个人信息的牵连关系。一方面,基于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技术的特性与元宇宙的刚性准入要求,元宇宙用户想以虚拟数字人的身份出现必须经过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这一过程。个人生物识别中的“识别”应该解释为“可识别”与“已识别”[12],但是我国学界往往默认为“已识别”,而且立法中也没有明确阐述“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含义。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对其进行了一定的阐述,即其在圈定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当属于自然人的身体、生理、行为特征方面之后,进一步指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当能够识别或确认识别自然人[54]。只有规范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才能有效厘清虚拟数字人的定位,保护好虚拟数字人的隐私信息,故而我国法律应当加快明确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步伐,而不仅仅是处于有扩大的趋势这一尴尬定位,从而遏制元宇宙平台或相关技术人员过度收集虚拟数字人隐私信息的乱象。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保护虚拟数字人个人信息,应当明确规定侵权行为的补救措施与适用。基于虚拟数字人与元宇宙用户之间存在时空同步性,故而一方的信息被窃取也意味着另一方信息的泄露,那么处理方式是仅限于元宇宙中还是现实世界里也要加以惩处呢?笔者认为,对于民商事案件,基于虚拟数字人具有法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应当在现实世界与元宇宙世界中同时采取规制措施。当涉及损害赔偿问题时,若双方当事人有约定,则从其约定;若无约定,则由侵权者自由选择以现实世界的人民币或元宇宙世界中数字货币进行赔偿,亦可分别进行赔偿,但赔偿的总数额不得过度超出所造成的损害。如此则可以在避免重复赔偿的同时,对虚拟数字人个人信息进行高效率的保护与救济。
(二)确立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归责体系
算法是信息运行系统中的核心技术,是元宇宙中的关键技术之一。在算法架构中,数字信息是喂养、训练算法的基础原料,自动化运行是算法应用的具体方式,目标价值是算法运行的核心,元宇宙平台是提供计算、存储、传输功能的载体[55]。毫无疑问,正确、合理地运用算法技术能够使元宇宙世界正常运转并提高虚拟数字人与元宇宙用户之间信息对接的效率与准确性。但是如果不当使用算法技术,将会出现数据滥用、算法歧视、算法黑箱以及算法操作等问题[56],从而导致虚拟数字人信息被严重侵害。因此,我国必须完善算法技术侵害虚拟数字人信息的归责机制。
目前,对于侵权行为主要有三种归责原则,分别为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以及无过错责任。笔者认为,面对算法技术,可以以其风险程度作为衡量,即将元宇宙中的算法技术分类为高风险类算法以及中低风险类算法。首先,对于中低风险类算法,笔者认为可以采取过错推定责任。虽然《民法典》中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应当由被侵权人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在元宇宙世界中,被侵权人在举证能力、证明妨碍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57],且虚拟数字人的信息都由数字代码组成,被侵权的虚拟数字人往往难以发现自己的个人信息已被窃取,直到发生重大损失时才有所察觉,这时将很难承担举证责任。相对而言,算法技术的应用人员、元宇宙平台则更易察觉及核实算法技术的异常,且他们与其他虚拟数字人存在借助算法技术实施侵权行为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虚拟数字人信息且更加符合公平原则,应当采取过错推定责任,由算法技术的应用人员、元宇宙平台以及涉案的其他虚拟数字人承担举证责任[58],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没有实施侵权行为。
其次,对于高风险类算法技术,应该采取无过错责任。因为高风险类算法技术可能会产生元宇宙平台及算法技术应用人员所无法预料的危险情况,从而侵害了虚拟数字人的个人信息,但此时考虑他们的过错是没有意义的。对于这类新型侵权,可以在立法上将其确立成一种新型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即只要算法技术在运用过程中因其自身特征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侵害虚拟数字人个人信息的事故,运行算法的元宇宙平台或相关技术人员便要承担全部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不再考虑他们是否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59]。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虚拟数字人的信息并且促使算法设计者不断完善算法技术,将其发展至最优水平。
(三)细化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行业规范
除了通过修改法律或颁布司法解释弥补元宇宙世界法律的空缺和确立元宇宙底层技术的归责体系来保护虚拟数字人信息之外,还可以通过规范元宇宙用户进入元宇宙的途径来加强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即规范元宇宙平台与相关企业的运行模式及行业习惯。
1.形塑元宇宙平台的准入标准
因为元宇宙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法律的监管,所以各类企业都开始构建元宇宙平台以此进行获利,元宇宙平台的资质与安全性缺乏审查与制衡,任何人在满足元宇宙平台利益的前提下,都可以借助其虚拟现实等技术进入元宇宙中,这导致虚拟数字人信息存在被窃取的潜在风险。因此,应当针对元宇宙平台制定一定的准入标准,从而降低虚拟数字人信息泄露的可能性。
首先,应对各个元宇宙平台的主体企业实行先审查后赋权的模式。客观方面,该企业的相关数字技术必须通过安全性与保密性审核;而主观方面,该企业必须具备良好的社会信誉。只有同时满足主客观要求的企业,才能被赋予构建元宇宙平台的资格。其次,为了方便监管与审查,应控制元宇宙平台的数量,实行优胜劣汰的流动性机制,以这种方式倒逼各个元宇宙平台定期检查平台各个参数,并不断发展与强化相关数字技术,提高平台安全性从而强化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最后,国家财政部门与资产管理部门要对元宇宙平台进行资产风险评估。一旦虚拟数字人的信息被窃取,该元宇宙平台能否在第一时间做出应对以及是否能够承担起损害赔偿责任,从而构建起负责的、可靠的元宇宙平台。
2.明确信息收集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元宇宙平台的现状是缺乏系统的监管且呈现垄断趋势,但元宇宙平台作为用户进入元宇宙的渠道,作为虚拟数字人与元宇宙用户之间链接的媒介,其收集、汇总、存储了海量的元宇宙用户与虚拟数字人的信息。为了更好地保护虚拟数字人信息,应该明确信息收集企业的权力与责任,方便国家进行督促与监管。
首先,为了元宇宙的发展与完善,必须赋予相关企业收集信息并利用信息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并不是无限制的,元宇宙相关企业在行使信息收集的权力时,必须时刻遵循“元宇宙发展需要”及“不影响虚拟数字人与元宇宙用户”的准则,而且企业在享有信息采集、管理及利用的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保障信息安全的社会责任[4]。除此之外,对于一些涉密信息与敏感信息,应当采取“知情同意”规则,即虚拟数字人或元宇宙用户对需要被收集的信息种类与内容完全知情,可以在对该类信息具有范围选择权的基础上予以同意或拒绝[60],从而充分尊重虚拟数字人与元宇宙用户的意思自治。而且元宇宙平台不可采用禁止元宇宙用户进入元宇宙或中断虚拟数字人与用户的链接等其他强制性违法手段胁迫虚拟数字人或元宇宙用户同意平台收集相关信息。其次,企业在收集并汇总到一定信息后,必须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与责任,如其必须对虚拟数字人的数字化信息进行加密,不得对外泄露。同时,其必须定期核实信息存储与信息保护技术,确保其正常运作以保障虚拟数字人信息。最后,信息收集企业有义务接受国家的信息监督,须定期将信息保护情况汇报给国家信息监管部门。通过与监管部门的合作,一同查缺补漏,增强数字信息保护力度,将可能存在的虚拟数字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扼杀在摇篮里。
五、结语
元宇宙是数字时代的新兴产物,虚拟数字人是元宇宙中的活动主体。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个人信息的保护与监管,但对于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尚处于起始阶段。虚拟数字人信息一旦被窃取将会对现有的法律体系与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我国必须尽早填补此处的空缺,加强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本文从明确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底层技术的归责体系以及加强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的行业规范三方面出发,提出给予虚拟数字人法律主体地位,厘清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范围、明确元宇宙平台准入标准等切实可行的意见,希望能以此强化虚拟数字人信息保护,遏制不法分子的侵权行为,保障元宇宙世界在蓬勃发展的同时能够维持其稳定秩序。
参考文献:
[1] 许娟,黎浩田. 企业数据产权与个人信息权利的再平衡——结合“数据二十条”的解读[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2):1⁃19.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 周鑫,王海英,柯平,等. 国内外元宇宙研究综述[J]. 现代情报,2022,42(12):147⁃159.
[4] 滕长利. 元宇宙信息采集权与用户隐私权的冲突及治理研究[J]. 上海法学研究,2022,7(1):114⁃124.
[5] 方凌智,翁智澄,吴笑悦.元宇宙研究:虚拟世界的再升级[J].未来传播,2022,29(1):10⁃18.
[6] 侯文军,卜瑶华,刘聪林.虚拟数字人:元宇宙人际交互的技术性介质[J].传媒,2023(4):25⁃27.
[7] BALL M. The metaverse: and how it will revolutionize everything[M]. New York: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22.
[8] 王儒西,向安玲. 2020—2021年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R]. 北京: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2021.
[9] 王卓,刘小莞. 元宇宙:时空再造与虚实相融的社会新形态[J]. 社会科学研究,2022,262(5):14⁃24.
[10] 傅琳雅,邬慧.元宇宙视域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及法规重塑[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3):61⁃68.
[11] 杨青,钟书华.国外“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及演化趋势”研究综述[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43(3):97⁃106.
[12] 张晨原. 元宇宙发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挑战及应对——兼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概念重构[J].法学论坛,2023,38(2):132⁃141.
[13] 周是伦. 元宇宙视域下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研究——以“云端人设”与“现实人设”的统一程度为视角[C]. 上海:《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2年第11卷——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青年论坛文集,202:94⁃101.
[14] 熊进光,贾珺. 元宇宙背景下数字侵权法律问题的境遇及应对[C]. 上海:上海市法学会,2023(5):44⁃56.
[15] 黄欣荣. 从ChatGPT到Sora:生成逻辑、哲学本质及世界图景[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6):72⁃80.
[16] 郭全中. 虚拟数字人发展的现状、关键与未来[J]. 新闻与写作,2022,457(7):56⁃64.
[17] 张钦昱. 元宇宙的规则之治[J]. 东方法学,2022(2):4⁃19.
[18] 闫晴,胡友东. 论网络平台数据报送义务与用户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6):102⁃110.
[19] 韩旭至.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批判[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4):75⁃85.
[20] 周详. 智能机器人“权利主体论”之提倡[J]. 法学,2019(10):3⁃17.
[21] 孙笛. 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资格否定论[J]. 政法论丛,2022,208(3):40⁃50.
[22] 王利明. 人工智能对民法的挑战[N]. 中国城市报,2017-09-11(22).
[23] 王充,董璞玉. 人工智能时代刑事责任主体之再审视[J]. 广西社会科学,2020,306(12):118⁃125.
[24] 储陈城.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归责的走向——以过失的归责间隙为中心的讨论[J]. 东方法学,2018(3):35.
[25] 骁克. 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法哲学基础[J]. 政治与法律,2021,311(4):109⁃121.
[26] 郭少飞." “电子人”法律主体论[J]. 东方法学,2018(3):38⁃49.
[27]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信息安全技术 鉴别与授权 数字身份信息服务框架规范:GB/T 31504⁃2015[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5.
[28] 丁道勤. 元宇宙的法律规制[J] . 财经法学,2022,47(5):20⁃34.
[29] 陈家宁,张建文. 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中国方案以《数据安全法(草案)》为视角[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5⁃40
[30] 徐凤. 网络主权与数据主权的确立与维护[J]. 北京社会科学,2022,231(7):55⁃64.
[31] 王禄生. 区块链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的内生冲突及其调和[J]. 法学论坛,2022,37(3):81⁃95.
[32] 丁凤玲,林冰雁. 元宇宙中数字人的法律地位探析[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2):13⁃22.
[33] 何阳阳. 论数字人的法律属性及其刑事责任能力[C].上海:上海市法学会,2023(6):270⁃278.
[34] 郑飞,夏晨斌. 虚拟数字人的二重法律向度及法律性质界定[J]. 长白学刊,2023(6):89⁃99.
[35] 龙晟. 数字身份民法定位的理论与实践:以中国—东盟国家为中心[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6):110⁃123.
[36] 卞建林. 人工智能审判的责任解构与制度应对[J]. 法治社会,2023(5):1⁃11.
[37] 张唯玮,张武军,孙雍君.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专利性及其制度回应[J/OL]. 科技进步与对策:1-9[2024-06-1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24.G3. 2024 0613.1705.004.html.
[38] 司伟攀. 欧盟和美国人工智能立法实践分析与镜鉴[J].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23,38(7):6⁃14.
[39] 张建文. 格里申法案的贡献与局限——俄罗斯首部机器人法草案述评[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21(2):32⁃41.
[40] 赵磊,赵宇. 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J]. 人工智能法学研究,2018,(1):21⁃228.
[41] 朱凌珂. 赋予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路径与限度[J]. 广东社会科学,2021(5):240⁃253.
[42] 刘云. 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制度需求与多层应对[J].东方法学,2021(1):61⁃73.
[43] 朱程斌. 论人工智能法人人格[J]. 电子知识产权,2018(9):12⁃21.
[44] 简圣宇. “虚拟数字人”概念:内涵、前景及技术瓶颈[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2(4):45⁃57.
[45] 杜骏飞. 数字交往论(2):元宇宙,分身与认识论[J]. 新闻界,2022(1):64⁃75.
[46] European Parliament.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Regulation (EU) 2016/67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April 2016[EB/OL]. (2016-05-04)[2023-06-25].https://eur-ex.europa.eu/eli/req/2016/ 679/oj.
[47] U.S. Congress. Senate. National Security and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of 2019[EB/OL]." (2019-11-18)[2023-07-1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2889.
[48] 商希雪,韩海庭. 数据分类分级治理规范的体系化建构[J]. 电子政务,2022,238(10):75⁃87.
[49] 袁康,鄢浩宇. 数据分类分级保护的逻辑厘定与制度构建——以重要数据识别和管控为中心[J]. 中国科技论坛,2022,315(7):167⁃177.
[50] 王利明. 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问题——以《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解释为背景[J]. 当代法学,2022,36(1):3⁃14.
[51] 林凌. 构建元宇宙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二元机制[J]. 当代传播,2023(2):99⁃103.
[52] 林凌. 生物识别“关联隐私”保护机制的构建[J]. 青年记者,2022(5):93⁃95.
[53] 刘世锦. 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期[N]. 社会科学报,2022-07-28(1).
[54] REGULATION P. Regulation(EU) 2016/67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J].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6, 679: 1⁃88.
[55] 李婧文,李雅文.算法应用及其治理研究[J/OL].大数据,(2024-07-01)[2023-04-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0.1321. G2.20230411.1035.002.html.
[56] BALKl J M. 2016 Sidley Austin distinguished lecture on big data law and policy: the three laws of robo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J]. Ohio State Law Journal,2017, 1217(78): 1237⁃1239.
[57] 陈峰,王利荣. 个人信息“知情同意权”的功能检视与完善进路[J]. 广西社会科学,2021,314(8):106⁃111.
[58] 郭雪慧. 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挑战与应对[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1(5):157⁃169.
[59] 于艾思.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制度的法经济学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2022.
[60] 马晗,刘晨威.节元宇宙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之重塑[C]. 上海:《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2年第11卷——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青年论坛文集,2022:187⁃196.
The Dilemma and Solutions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of Virtual Digital Human in Metaverse
Xiong Jinguang, Zhang Zheng
(School of Law,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virtual digital human in metaverse is synchronized with the real-time transmission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metaverse user.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for natural human, the protection of virtual digital human lacks corresponding supervision and measures, which intensifies the leakage risk. Besides,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is unable to provide detailed guidance o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liability identification and other core contents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of virtual digital human. Based on this, our country should ensure pers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of virtual digital human based on three-dimensional path—Civil Law protection, algorithm technology liability and industry norms. First, determine the legal subject status of virtual digital human and clarify the scop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of virtual digital human. Secondly, establish the algorithmic digital technology attribution system to clarify the way of undertaking responsibility. Finally, determine the access standards of the metaverse platform and clarify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enterprises.
Keywords: metaverse; virtual digital huma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rivacy right; platform access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2023年)重点基金项目“元宇宙背景下虚拟数字人侵权法律问题研究”(23FX01)
作者简介:熊进光(1965—),男,江西宜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民法基础理论,侵权责任法,金融证券法;
张" " 峥(1998—),男,江西进贤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法基础理论,侵权责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