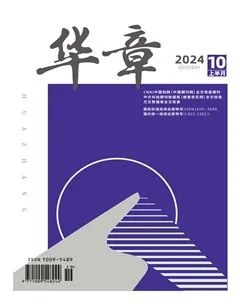以族谱为中心探析清代天津盐商家族教育
2024-12-31吕志豪
[摘 要]清朝时期,天津的长芦盐商都是地方的富商大贾,除了经营盐业和建设地方外,对家族的教育更是不遗余力。近代以前,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众多家族贯彻儒家教育,推动家族向科举家族的转变。与此同时,家族内部有明显的从政或经商等择业分工行为。近代以后,受家国命运和西学东渐的影响,家族开始向西方学习,引进近代教育,以适应时代变化。
[关键词]天津;盐商;教育
明清以来,长芦盐业重心逐渐由沧州转移到天津,康熙十六年(1677年),长芦盐运使司正式由沧州移驻天津,天津正式成为长芦盐业中心,众多盐商家族在此扎根发展。以往的众多研究多关注长芦盐业的发展,例如张毅的《明清天津盐业研究(1368—1840)》。也有关注于盐商与天津当地社会的关系,如关文斌的《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对盐商个体的研究,也多关注于盐商家族的发展,如叶修成的《紫芥掇实:水西庄查氏家族文化研究》、罗澍伟的《天津的名门世家》,其中对姚氏和华氏的研究。在教育方面,张绍祖的《长芦盐商对天津教育之贡献》,则着重研究专注于盐商从古代至近代对天津当地教育的贡献。对盐商自身的家族教育研究存在明显不足。本文希望通过分析族谱等资料,补充这一方面的研究。
天津盐商家族有不少是在明末清初从江浙地区迁居至天津的,这些北迁进入天津的家族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例如,查氏于明末万历年间迁入宛平县,查忠中万历己酉科副榜,家族在清朝前中期产生了3名进士,9名举人。再如,李氏,先祖周麟公,“著书不求闻达,教授生徒发科者甚多”[1]。以及华氏、徐氏等宗族,这些从江浙地区北迁进入天津的宗族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向来十分重视传统的儒学教育,力争让家族子弟进入官场,以求光大门楣。
一、以科举为目标的文化和道德教育
科举取士从隋唐开始,到明清时期教育已经成为科举的附庸,读书完全是围绕科举为官展开的,家族培养子弟进入官场的目的在于光大门楣,提高家族地位,庇护家族,同时也是检验家族实力与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
天津盐商家族并不像晋商和徽商,实行商业教育和儒家教育两条策略。由于盐业“官督商办”的性质,天津盐商家族将盐业作为一种家族基础或者是资本,最终目的无不是出仕为官,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为家族的生意提供官场助力。
同光年间,大量天津士子专注于科举考试,每年参加会试者,不下百人,天下罕见。天津民间参加科举考试的风气如此兴盛,与盐商等富商大贾的推动有紧密联系,家族资本庞大,有能力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中举者中盐商等富商大贾的子弟也占大多数。
第一,遵守祖训,传承为官的传统
宛平查氏支谱原序记载:“吾先祖振寰公,力能为之,时方锐志功名,谓科第旦晚可得……先祖必待身取科第而为之,亦致未能成其志,先叔祖为之……日乾苟非草创以贻后人[2]。”说明参加科举、博取功名这一理念的世代传承,查氏从江西抚州迁到顺天宛平县之后,就始终以科举为目标,族人积极参加科举,北迁第三代查忠是明万历己酉科副榜,查为义、查礼,以及后来的查彬等人或参加科举或通过捐献,都曾获得功名从而出仕为官。徐氏家族在家训十二条中,更有“夫读书虽不专为功名,然古人致身显要,任大事,成大业,为循吏,为名臣,未有不从读书中来者,史云宰相须用读书人”[3]。徐氏家族的后人始终牢记这一家训,坚持出仕任官,直至清末培养出了徐世昌这样的人物。严修之父严克宽曾任长芦纲总,在参加科举失败后,将希望寄托于儿子严修身上,严修最后不负父亲所望,于光绪九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等职。
第二,重视择师,营造浓厚的家族教育氛围
查氏曾聘请浙江余姚邵氏邵坡作为家庭教师。邵氏一族从明代开始就是江南望族,万历年间名臣陈有年认为,邵氏是江浙地区的宗族中,科举成就最为突出的大姓。清代邵氏家族共出进士二十六人,举人七十九人,是当地著名的科举世家。邵坡是当时家族的青年才俊,自小聪慧过人,钻研宋明理学,受到桐城派领袖方苞的赞许。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邵坡中举之后,便在查家做老师,等待会试。查为仁很可能自小就是他的学生。
除了从家族外聘请老师之外,家族内部的优秀知识分子也会担任教师的角色。徐金楷天资聪颖,十四岁时由商籍中举,乾隆戊午科副榜,年少时家境寒苦,但并未放弃学业,而且“教诸弟成名,吾家至今书香流传,实端书伯创也”。徐之柄童试失败后,改从盐业,后成为芦纲京师总理。在治理家务方面,“延名师,以教子侄”,重金聘请名师,教育家族子弟。
其他家族也有族内人物担任家庭教师,亲自教育子孙的传统。华氏自迁到顺天府东安县之后,虽然家境困苦,但十分注重家庭教育,“常勖子以读书为本性”[4]。鼓励儿子始终坚持读书,家庭内有浓厚的读书学习氛围。华世奎之父华承彦屡试不第,所以对其教授甚严,指定书目,亲自教授儿子,在家塾中读书时,上午背诵经史,下午临摹名迹,练习书法。除此之外,每有知交谈话,华世奎必定站在身旁听教,4岁开始学习颜真卿的书法,每日20字,后临摹各家碑帖,冬夏不断,后来成为天津著名的四大书法家之一。
严修自幼喜爱读经史,习诗词,一生中有三种学习方法,枕课、辫课、车课,各以一书为程,日积月累,收获甚多,其长子也学习这种方法。17岁时,学贯中西,并且致力于钻研西学,退居之后,每逢星期一、三、五、日,要求子孙练习形意拳,设乒乓球案和铁饼,周六组织音乐会,而且还请外国教师教授英文。
第三,重视以忠孝为代表的道德教育
宛平查氏的族谱上明确要求子孙报效国家,“吾父垂训之意,以告后嗣,曰:凡我子孙知邀国厚恩,幸而通籍登朝,应忘身忘家,力图报效。”把为国尽忠作为后代子孙的人生一大目标。李士铭在父亲生病时,“公内行肫笃,侍父疾兼旬,衣不解带”。坚持侍奉父亲月余,衣不解带。徐氏家族的家训十二条中,其中第一款就是“孝敬父母”,认为“人伦之道莫大于君亲。书云:移孝作忠,又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是事亲,尤为人之本务也。”此外还有鼓楼东姚家,姚逢年、姚承恩父子同为进士为官。姚逢年曾聘挚友、著名文学家、金石家包世臣教授儿子三人。姚承丰严格教导子侄,常以祖训训诫:“万恶淫为首,不准有非法行为;不准妄取不义之财,资财富有时,喜寿事家中不准唱大戏、叫杂耍;等等。[5]”十分重视对后代的道德教育。
二、教育近代转型
随着天津开埠,洋务运动,以及清末新政的实施,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众多新式学校建立,各大盐商家族作为天津望族,眼界开阔,并且由于天津作为京畿门户,临近日本,各国在天津设有租界,有“九国租界”之称,开近代风气之先,他们较早接触外国事务与教育方法。受教育强国等理念的影响,他们积极适应时代,改变传统教育方法与内容,将族中子弟送入近代学校,甚至出国留学,学习西方文化知识,融入现代教育体系,倡导实用,力争不落后于时代,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
宛平查氏的族人进入不同的专业学校,有助于族人之间互助,壮大宗族。查尔栋于河南法律学校毕业、查禄昌毕业于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查禄百于交通部天津扶轮学校毕业。查禄丰先后毕业于河北省水产学校渔捞专科和河北省警官教练所、查禄畇毕业于天津电报学校。其他盐商家族也是如此,华氏后代多参加政界和军界,进入军校者较多,华世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华世中毕业于保定陆军学堂后被保送至日本士官学校、华世椿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李氏家族的李士锱是北洋武备学堂及铁路学堂第一班毕业生,李士锐也毕业于这两所学校,还是日本仕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徐氏家族更加重视教育,甚至具有前瞻性,徐世襄是英国伦敦大学法律硕士,徐世章是比利时圣路易斯大学商业学士,由于徐氏兄弟的经历和学业,在官场上深受重用,对近代政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制定新政改革方案,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如徐世章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交通银行副总裁、中国国际运输局局长,1922年,随着徐世昌的下台而离职,居住于天津。在近代军阀割据的背景下,这些家族的教育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也有家族传统的影响。但同时在近代的风云变幻中,由于家族没有优秀人物进入政界或军界,大多数传统盐商家族已经趋于没落。
除徐氏家族外,严氏家族严修也十分重视家族教育,在教育方面亦投入很多,倡导学习西方,这与严修自小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严氏家族中具有“重教兴学”的传统,父亲严克宽曾任长芦纲总,文化功底深厚,教出的学生中有举人、进士;严修虽然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是践行的是经世济民的思想,关心民间疾苦,学以致用。严修年少时,严克宽派其随亲友前往乡下清查户口,办理赈灾。1883年,严修为准备考试留馆课,曾谒见张之洞与问津书院山长张佩纶,张佩纶认为,传统学子被经学和词章两事困扰一生,在众多的儒家书籍中钩稽繁引,虽然通经博识,但不能够学以致用。严修深受影响,治学转向以实用为主,开始花较大精力学习《勾股举隅》《格致入门》等数理化书籍,以及《伤寒明理论》《医学源流论》等医书,所涉猎的四部群书也多是经世致用的,如《梦溪笔谈》《齐民要术》等。1894年,严修任贵州学政,在位期间要求学子不仅学习经史、算学,还要兼学时务、政要,甲午战后奏请清廷开“经济特科”。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教育严氏子侄,学生半日读经书,半日读洋书,有英文、数学、理化等科目。1902年,首先在家中办起严氏女塾,学生主要是严氏家属,聘请日本人教日语、音乐、算术,还设有织布、缝纫等手工艺。严修在女塾首先宣传放足,撰放足歌,使学生习唱,开创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1905年,参照日本的模式创办了严氏幼儿园,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严氏家族作为天津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家族,面对近代的大变局,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男女同等学习,提高家族的文化水平,培养适应时代的人才,同时也示范和带动天津地区的教育。
三、影响及成就
随着清初长芦盐务中心的转移,长芦盐商也大量聚集于天津。作为从业者的盐商,对家族教育的投入也是不遗余力,并且也带动了天津地区的文化教育的发展。盐商家族内部分工明确,分别从事盐和参加科举教育。又或者从事一途。例如,查氏长子查为仁早年参加科举,被查出找人替考,科举案平息后,查为仁从事盐业,二弟查为义和三弟查礼进入仕途,盐务也多由查为仁后代处理。严修之父严克宽因盐业起家,严修后来进入仕途,不再参加盐务。徐世昌家族也是如此。
由于家族良好的教育传统和方法,盐商家族的教育成就突出,查氏家族在清朝前中期产生了3名进士,9名举人,家族中以查为仁、查为义、查礼、查善长、查诚、查彬等人成就较高,查为仁著《莲坡诗话》《绝妙好词笺》,查为义著《集堂诗草》、查礼著《铜鼓书堂遗稿》,著作流传于世。李氏家族被天津人称为“李善人家”,在天津有过许多善举,李春城创办寄生所,修建清修院,施送书籍,遇有水旱,捐资助赈;李耀奎在泉州府知府任上,创办救济院、书院,资助贫困学子,奖励理学名儒后裔,严查考试舞弊、贿赂,种种恶习一扫而空,各种人才均得脱颖而出,众多士子十分感激。华氏家族的华兰博通经史,擅长诗画、书法、围棋,著有《皖城集》;华长卿著有《古本周易集注》等书;华世奎是民国天津四大书法家之一,退位诏书就出自其手。徐之柄任芦纲京师总理后,经营数载,“国帑既裕,各商称便”,盐税充裕,盐务便利,被各大盐商称赞;徐炘是乾隆壬子科举人,历任布政使、巡抚兵部侍郎等职,后代世昌、世良、世襄、世扬、世光、世章等人,都接触过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徐世襄是伦敦大学法律硕士,他们在清末至民初的政坛上都曾任各个重要职务,徐世章离开政坛后,致力于实业、教育、收藏,担任天津工商学院、法汉中学、扶轮中学等多个学校董事。天津工商学院在战争期间经费断绝,教会打算停止办学,徐世章慷慨解囊,出任该校董事长,成为当时津门最具吸引力的高等学府之一。这些不仅促进了家族的发展,而且推动着近代天津教育的进步。
结束语
天津自古就有“渔盐之利”,天津盐商凭借家族雄厚的资本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在近代培养出了重要的人物,例如徐世昌兄弟、严修等,对近代天津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同时盐业受政府的指导和管理,家族发展也深受国家的影响。近代以来国家深受外国侵略,盐商被清政府和外国资本双重压迫,盐商家族的辉煌已逝。但是盐商家族的教育方法和理念今天仍可以借鉴,例如,聘请名师,家长的言传身教,遵守家训。另外,严修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关心家国命运;徐氏家训中的孝敬父母;姚氏家训中的不准有非法行为,不准取不义之财,教育内容和方法要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这些对做好家庭教育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钟璘.延古堂李氏族谱[Z].1935年铅印本.
[2]查禄百,查禄昌.宛平查氏支谱[Z].1941年铅印本.
[3]徐世昌.续修徐氏家谱[Z].1908年铅印本.
[4]华承彦,华长卿,华世奎.华氏宗谱[Z].1925年铅印本.
[5]姚惜云.天津“鼓楼东姚家”轶事[J].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89(47):204-242.
作者简介:吕志豪(1996— ),男,汉族,河南洛阳人,天津师范大学,硕士。
研究方向:中国史。
基金项目:2024年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清代天津盐商家族教育研究”(立项编号:2024KYCX095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