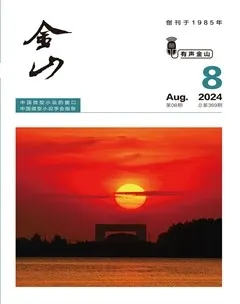老范的煤矿
2024-12-31布衣

老范六十八了,须发都白了,像秋天水边的蒹葭,乱糟糟的一蓬。
老范吃罢饭出门后,总能看到一个人。一个干干净净的小伙子,瘦高个儿,如同庄稼地里的高粱,颇有鹤立鸡群的意思。老范走,小伙子也走。老范停,小伙子也停。小伙子如同老范的影子,亦步亦趋,形影不离。
这引起了老范的注意。老范“哎”了一声。小伙子也跟着“哎”了一声。老范仔细端详小伙子,感觉眉目嘴脸,像几十年前的自己,只是自己没有这般高而已。老范说:“小伙子,你咋老跟着我呀?”
小伙子说:“我没有跟着你。”
老范问:“那你是去哪里呀?”
小伙子嗫嚅着嘴唇说:“四矿!”
“我也是去四矿!”老范像是想起什么,萎靡的身子顿时一震,“我就是四矿的工人呢!”
老范和小伙子所说的四矿,是一座破产关停已久的煤矿。煤矿地处冀南太行余脉一处盆地,往西看是山,往北看是山,往东看是山,往南看是条季节河。煤矿依山傍水,就建在山坳之间。若干年前,这里工厂、市场、俱乐部、工人村、宿舍楼、大食堂等一应俱全,是附近农村购置时兴物品售卖农业产品的集散地,更是比拟城市的繁华之地。甚至很多人自诩:“北京、上海、哈尔滨、四台。”意思是四台能与北京、上海、哈尔滨的繁华比肩。四台就是四矿。
老范在四矿当过裱糊工、瓦斯员、放炮员、检测工、修理工,每天上班下井,下井劳动,一双脚量尽了井下的巷道,走遍了井下的边边角角。哪有通风设施、哪儿回风巷失修、哪有监测设备、哪儿风量不足,老范心知肚明,沟沟壑壑的脑回路像是一张矿井通风系统监测图。矿井的通风副总工程师姓张,老范喊他张总。张总个子矮,人胖,笑起来像弥勒佛,给人一种亲近感。张总画图给他们讲安全监控系统传感器安装位置,老范看了看他画的图,说:“图纸不对,后边还有一道联络巷呢。”
张总说:“哪有回风联络巷?”
老范工作认真,与张总较真儿:“要有咋办?”
老范和张总打赌,赌注是一瓶“赵国春”、一个猪拱嘴儿。喝酒要喝“赵国春”,吃肉要吃猪拱嘴儿。“赵国春”好喝不贵,猪拱嘴儿弹牙筋道不腻。那是很多煤矿工人的最爱,也是最朴素的奢侈品。结局是张总输了。张总忽视了采区后路那道简易的密闭墙。密闭墙密闭的就是联络巷。愿赌服输。张总买了“赵国春”和猪拱嘴儿,还额外加了一条狗腿。志满意得的老范,感觉从没吃过这么香的狗肉,从没吃过这么弹牙筋道的猪拱嘴儿,于是就有点喝多了。老范问:“张总,我们四矿还能撑多长时间?”张总伸出五个手指头,说:“最多七年。”
老范再有四年就退休了。他老了,没想到煤矿也老了。可不,煤矿和他一般大呢。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能不老?老范这么一想,又于心不忍,心里说:“要是煤矿永远不会老该多好啊!”老范宁愿自己老去,也不愿煤矿老去。煤矿老了,那孩子们的工作该怎么办?煤矿没了,又该拿什么养活这方水土的人?
老范娶妻成家,孩子上学,全靠的是煤矿。没有煤矿的恩赐,就没有他的今天。老范感觉亏欠煤矿很多,就退而不休,每天往煤矿转一圈。从家到煤矿,要走五里路。煤矿的路坏了,他就义务铺垫。煤矿的草荒了,他就无偿割草。煤矿的树被伐了,他就自掏腰包栽树。很多人劝他:“煤矿已经闭井了,人都走了,这么做还有啥意义?”
老范直腰抬头,笑出满脸皱纹:“我想保持煤矿原貌,要不那些离开的人,再回来的时候,就看不到煤矿原来的样子了。”
老范甚至还走入废弃的办公大楼。那时候这栋办公大楼是何等气派啊!外墙都是寸许见方的瓷砖,蓝白相间,均匀排列,看上去有些朦胧抽象,又有些花草写意。老范上了二楼,来到一所房间。这是张总的办公室,就是那个打赌输了的人。那个人后来和他成了儿女亲家。那个人的女儿,成了他的儿媳妇。煤矿的点点滴滴,都融入了他的血肉,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
这时候,小伙子和守门人跟了过来。守门人的眉毛胡子也都白了。他说:“范矿生,你咋又来了?”
老范看看守门人,说:“我在这儿上班工作,我凭啥不能来?”
守门人苦笑,“这里啥都没了,再来还有啥意思?”他见老范不理他,又说:“你看看我,还认识不?”
老范仔细端详守门人,摇摇头说:“不认识。”
守门人尬笑,大声说:“我是杜大海!”
杜大海是通风区的大班长,老范和他意见不合,甚至还大打出手一次。老范说:“杜大海年轻,没有胡子,浑身是肉!你这么干巴的人,咋能是杜大海呢?”
守门人指指小伙子,说:“你看看他,认识不认识?”
老范又摇摇头,迟疑地说:“不认识。”
“爷爷,我是您孙子,范家博啊!您咋连我也不认识了?”小伙子哭了起来,说,“杜爷爷,您看我爷爷的病又厉害了,竟然连我也不认识了!”
老范得了一种叫阿尔茨海默症的病,遗忘了家人,遗忘了朋友,却没遗忘工作过的煤矿。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人和事都老了,唯独他的煤矿依旧繁荣兴盛、蓬勃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