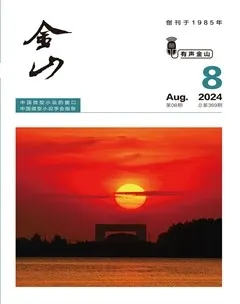城市社区书写的非虚构文学样本
2024-12-31曲云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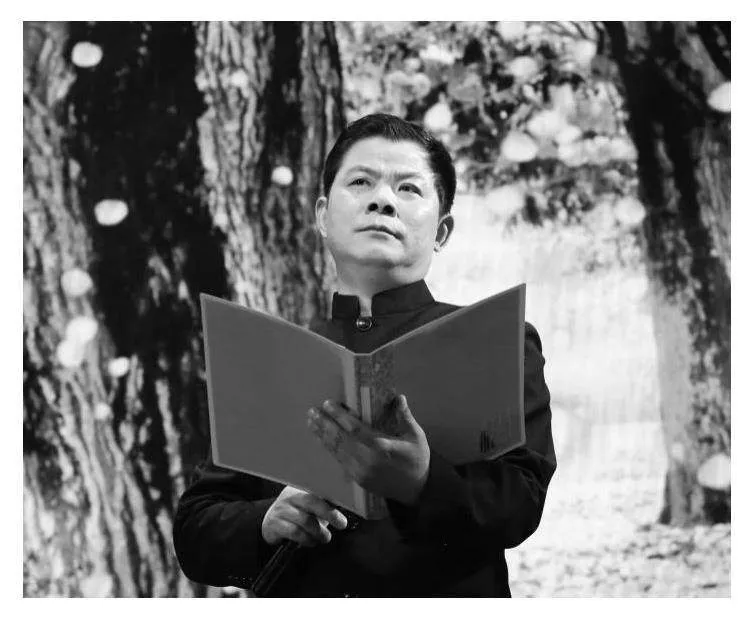
曲云进,江苏句容人,文学学士,管理学硕士,江苏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镇江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镇江市社科专家协会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镇江文化、党的建设等领域的研究,公开发表各类学术论文20余篇以及诗歌、文化评论等,曾于1992-1993年期间主笔《镇江日报》“京口联话”专栏。
董晨鹏之于我,是熟悉而又陌生的。说熟悉,是因为我很早就知道他,曾偶尔见过几面,也听说过他出过好几本书。说陌生,是因为与他从未有过实质性的交流。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我收到了他刚刚出版的新作《最后一公里的守望——七里甸纪事》。可能是出于阅读偏好,以往我不太关注纪实文学作品。没想到的是,当晚我竟然一气儿把这本书看完了。经过仔细阅读与反复揣摩,我认为,这部作品并不只是如译林出版社介绍的那样,是“为社会基层组织的构建运转提供社会学样本”,让我这个长期生活在社区却与社区保持疏离的“单位人”,第一次对社区里的人和事有了真切可感的了解,而且也完全可以说,它为当下城市社区书写提供了一个不多见的非虚构文学样本。
城市是人类聚居的高级形态,是与乡村相对的概念。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城市发展及其人口增加是极其缓慢的。我们今天谈论的城市化是人类发展到近现代工业化之后的必然进程,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应该可以说,自从有了城市,就有了关于城市的艺术表达,其中当然包括城市书写。随着社会轴心和文化轴心逐渐由乡村转向城市,城市生活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就必然促进城市文学的迅速发展乃至繁荣。在我国也是如此。不过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早期的城市化程度是相对较低的,改革开放以后才明显加快。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也几乎与之同步,20世纪80年代大批涌现,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一股比较强劲的文学浪潮,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减弱的趋势。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有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6.16%,全国共有城乡社区约60.6万个,其中城市社区约11.7万个。有人说,几千年的“乡土中国”在短短7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向“单位中国”再向 “社区中国”的变迁。社区已经成为个体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场域,既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也是国家(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关键环节。因而,城市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术领域关注的热点。但偌大的城市文学版图中却鲜见城市社区书写,非虚构的社区书写更是难得一见。当然,不能说城市文学作品中一点儿也没有社区的影子,但是社区往往大多是作为模模糊糊的背景或偶尔必要的活动场所出现的,并非是对社区以及“社区人”有意关照。令人欣喜的是,虽然不多但是已经看到有人开始关注社区并正在进行社区书写,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的邱华栋、王占黑和张夏,但他们都是以小说为体裁来书写各自不同的社区想象。我说非虚构的社区书写难得一见,并不是说绝对没有。梁鸿的“梁庄三部曲”和李燕燕的长篇报告文学《社区现场》就是非虚构城乡社区叙事的代表。“梁庄三部曲”是通过“在场”与“隐蔽”的多重叙述,致力对乡村(梁庄)现实生存图景的还原,属于乡土叙事。《社区现场》则是采取“以人带事”的手法,由来自重庆不同类型社区的30余名社区工作者、居民讲述百姓烟火故事,所选取的城市社区“观察样本”多达十几个。
由此看来,很显然,董晨鹏的《最后一公里的守望》是很特别的。它可以归为城市文学,但瞄准的是我国城市社会的最末端——作为一个“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基层社区以及社区里的人。它属于当代城市社区书写,却不是虚构叙事,而是以真实的姿态、纪实的手法,书写现实社区中真实存在的人和事。它和《社区现场》都是关于城市社区的纪实文学作品,但它所呈现的是“一个”较为清晰、完整、丰富的社区形象,而非多个社区多个故事的组合。
不得不佩服董晨鹏对城市社区题材的驾驭能力以及非虚构写作策略的运用能力。
也许是新闻专业出身以及曾经的媒体工作经历,不仅让他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社会以及普通人的关注热情,而且纪实性写作也成为他比较得心应手以至于惯用的书写方式。他的前两部纪实文学作品《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共和国平民简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前两部作品题材是他相对比较熟悉且有深入采访便利的领域,那《最后一公里的守望》却是一脚踏进了一个与他的工作、阅历、身份等似乎毫不相干的城市社区。读懂中国治理,需要读懂中国社区治理。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不仅是治理体系的基层,更是人民的生活共同体,更能够最直接、最敏锐地感知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七里甸社区是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街道下辖社区,属于城郊接合部的城市新社区,居住人口复杂,既有原来的村转社居民、当地国企职工,也有早年和新近的外来人口,真的是“鱼龙混杂之地”,可以看作是从“乡土中国”到“社区中国”的典型代表。董晨鹏精心挑选了这样一个社区作为观察对象和叙述主体,生动真切地描摹出繁杂琐碎又具体实在的社区工作与社区生活的点点滴滴,呈现给读者一个习焉不察,富有张力的,鲜活的生活领域。也许这并不够理想化,却是充满激情的,是可感可触、可憧憬的。对于人在社区的活动、人与社区的关系、社区对人的影响等问题,作家没有作或简单或模糊或经验化的处理,而是真正地扎进社区,近距离地体察社区居民的家长里短甚或撕扯怒对,感受社区工作者鸡毛蒜皮的工作日常以及酸甜苦辣的生活日常,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展示了社区构造、功效和行动的“中国方式”“中国智慧”。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从“管理”到“治理”、从“单一”到“多样”、从“独角戏”到“大合唱”的社区治理网络正在悄然生长。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社区中,“乡土社会”的气息还在,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现象仍存,居民自治能力“发育”不足,物业服务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不够,要实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正如刘梅所说,“居委会的人哪,不就是妈妈心婆婆嘴,跑不断媒婆的两条腿吗?”在这个意义上说,《最后一公里的守望》的确是为社会基层组织的构建运转提供了社会学样本。
报告文学作家纪红建说:“新闻止步的地方,文学开始起步!”强烈吸引我并改变我对纪实文学看法的,正是《最后一公里的守望》极强的文学性抑或说是“小说味”。
《最后一公里的守望》在叙事方式的运用上恰到好处。对于时间空间的转换、倒叙插叙的转换、不同人物的转换等等,比较灵活自然,几乎看不出人为的痕迹。作品的“引子”“尾声”,着墨不多,寥寥数语,欲言又止;看似闲篇,偏离了主题,却有种“看破不说破”的意味深长。这分明就是小说的“味道”!作品中几位主要人物出场,如生活中本来样子,顺其自然,没有刻意为之,更没有用个人履历式的文字来向读者介绍人物情况。无论是杨小玉、贾名扬、刘梅、吉倩倩、刘妍、陈小军,还是“红睡衣”、老陈、老蔡等人,对他们的过往经历、情感生活、家庭状况等,熟练地运用倒叙插叙,既说清了人物背景,也丝毫不影响当下故事的正常叙述。
董晨鹏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是很用心的,但他的这种“用心”看起来却有点漫不经心。全篇语言平实冲淡,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什么引经据典,更没有胡编乱造或追求新奇。这许是与作家本人的处事态度、语言风格、生活背景等有关。他是平视社区居民的,他熟悉普通镇江人的生活、语言,他把富有镇江城区特色、充满生活烟火气的方言俗语直接写进了作品。好在镇江的语言并不难懂,即便是外地读者,也会有一种“陌生的熟悉感”。从语言的运用来看,作家本人应该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写社区工作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琐碎繁杂,他就好像笑眯眯地站在一旁看着,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即便是写那三年特别紧张的疫情防控工作,文字中也看不到当时心惊肉跳、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反而是三言两语,云淡风轻。间或还出现这样一些句子:“御桥港的两岸,温暖在悄悄地生长,生机在静静地萌芽。”“一只黑白相间的喜鹊在枝头上喳喳叫了几声,扑棱着翅膀飞过了楼房黛灰色的人字屋顶。”这些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突兀,反而感觉到生命的顽强、生活的希望。
《一公里的守望》由一条流浪狗的救助展开,写的尽是平平常常的社区工作、社区生活和普普通通的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壮举,有的只是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和基层社区工作者的尽心尽责。没有什么大人物,出场人物行政级别最高的是区政协主席,有名有姓的人也就十个左右,更多的是有姓无名、没姓没名只有一个代称的人。就是这些人支撑起了国家大厦的基础,成为大国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守望相助”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在长期的语义演变中,“守望相助”一词逐渐成为古代社会处理邻里关系的主要原则,成为维系古代社会秩序的基本遵循,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如今,“一公里的守望”其实已经没有 “一公里”了,这其中,有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守望”,有社区工作者对居民百姓的“守望”,有社区人与人之间的“守望”,还有人与动物的“守望”。猫婆婆与她弟弟的故事,不也是一种“守望”吗?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对“乡土中国”的隐喻?它会随着城市的野蛮生长而消失吗?作家董晨鹏长期坚持在地化写作,同样可以视为一种执着的“守望”。
“城,所以盛民也。”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近2000年前如是解释:“民,乃城之本也。”现在,我们也相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我更相信,让每个人在社区诗意地栖居,生活才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