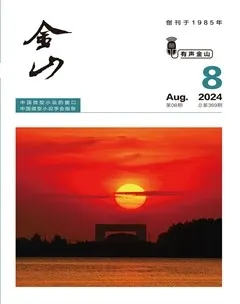碎嘴
2024-12-31王春迪

老街小吃“三件宝”,酥烧薄粉烫面饺。
吃酥烧,老街人习惯到常松家,他家那个“常记”酥烧,表皮金黄,做馅儿的葱,是常松家人一根根挑的,不仅馅儿面恰到好处,馅儿里的葱白和葱叶也比例适中,葱香味浓,咬起来酥脆,吃嘴里发粘。吃薄粉,要数启亮家,薄粉主料是豆粉,乍看像本地人喝的糊糊,却比糊糊亮,又像是南方人喝的浓粥,但比浓粥稠。盛薄粉的碗也有讲究,要用亮堂一点的碗,不用黑碗。薄粉在碗里,静看像碧玉,撩起来又似绿缎,薄粉须趁热吃,一凉就硬。吃之前,要撒点干辣椒面儿,入口即化,满嘴火辣辣的豆香。老街人吃启亮的薄粉,会买常松的酥烧就着,一口薄粉,一口酥烧,再一口薄粉。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食物的关系,启亮家和常松家的关系一直很好。两家人,逢年过节、闭火关炉时,总是要聚聚。
相比之下,做烫面饺的秦大姑就清冷一些。老街人管上了年纪的妇女要么叫大娘,要么叫婶子,从没有叫大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条街,单单就管她叫大姑,少的叫,老的也跟着叫。仿佛她的名字就是秦大姑。
秦大姑的烫面饺很费工夫,需要拿滚烫的肉汤和面,饺子馅用的是猪肉、熟冬笋、韭菜、皮冻及虾子、白胡椒粉,伴着香油、清水、姜面,顺一个方向搅打,整个过程,手捏,鼻闻,眼看,嘴尝,凭的是秦大姑多年的经验,蒸熟后的烫面饺,皮薄能见五颜六色的馅,汁多而浓稠,馅心鲜嫩清香。秦大姑的手臂粗壮,手却并不厚实,看她包烫面饺,是一种享受,几手指头,如同跳舞一般,一合一开,一个饺子就出来了,有人偷偷给她计时,三分钟,秦大姑能包六十多个饺子。
多年来,大姑每天凌晨三点钟就起来忙活,熬汤,包饺,蒸饺……交冬数九,很是不易,加上大姑家老伴走了好些年了,少了个帮手。就有人劝大姑,不如一次包个几天的,放在冰箱里冻着,也省得每天这样忙活。有人甚至出主意,现在有很多作坊都有成品配送,你不如贩一点,掺着卖。
大姑并不理睬,大姑有大姑的规矩,老街有不少爷儿们习惯喝早酒,老街靠近码头,有些晚上工作的船工或者渔民,忙碌一晚上之后,早上收工吃饭,喝点高粱酒,驱驱寒,软软腿,回家补个觉。但秦大姑知道,绝大多数来喝早酒的,不过都是些闲散着手的酒蒙子,没事干,喝完酒回家睡回笼觉的,有的一早就得半斤酒打底,喝多了满嘴跑火车,骂街打老婆。
秦大姑看不惯,只要是你吃烫面饺时,拿个杯子比画来比画去的,被大姑看到,甭管你是熟脸生脸,一准儿撵你。被撵走的爷儿们,肚子里气鼓鼓的,嘴上还惦记着大姑的烫面饺,只好打包,挪个地儿喝去。
不给喝早酒还好说,还不让人扎堆儿聊天!老街的街坊,都是熟头熟脸的,吃个早饭,遇一块儿,天南海北扯一段,不很正常吗。就这,秦大姑也不让,大姑的烫面饺,肉馅,都是用水打的,馅都是抱团的,必须趁热吃,冷了容易变硬,再加热,馅发木,皮发蔫。所以,你端着饺子胡咧咧时,大姑看见了,一准儿要催你。不知道的以为大姑催他们赶紧吃完好腾座位,只有那些熟客知道,大姑是在意你的口感,在意她那盘烫面饺子。
大姑一早出摊儿,忙一上午,下午休息。没事时,大姑喜欢去河滨公园走一圈,那儿花多,一年四季都有几种花在开。她会骑着三轮车去买食材,选个鸡蛋,都得一个一个挑,带斑的,色暗的,壳薄的,都不要,说是老鸡下的,水分大,含钙少。大姑很少去人家串门,她到谁家去,都跟查房似的,瞅着啥不合规矩,嘴就会“碎”,什么卫生间不放梳子啦,床头不挂风景画啦,沙发不放剪刀,柜门要关闭,客厅不放带刺的植物,床底不放鞋子……
其实自己也是好心,但说多了,谁心里不膈应?
大姑已经一年多没去儿子家了。
儿子搬新家后,一次,大姑到儿子家送东西,看到他家的冰箱门正对着厨房的灶台。大姑打电话给儿子,儿子那时还在开会,正忙,挂了。大姑再打,儿子出了会议室,问大姑啥事,大姑告诉儿子,你赶紧把冰箱挪个地儿,冰箱对着灶台,这叫水火不容,将来一家人保准要吵架。儿子哭笑不得,没等大姑说完话,就把电话挂了。大姑一气,便撸着袖子自个儿去挪那冰箱,一不小心,把冰箱上的花瓶打碎了,那花瓶是儿媳妇在日本旅游时,买来的铸铜花瓶,儿媳妇经常会买几朵花插在上面,她发朋友圈里的照片,好些都用那个花瓶当背景。回家后,儿媳妇心疼得眼泪都出来了,心一疼,话就说重了些,大姑自感好心好意,倒落了个不是,也委屈,一扭头,不上门了。
有人到儿媳妇那边和事,儿媳妇说她婆婆规矩太多,眼睛跟尺子似的,整天碎叨叨的,这不是吃饱撑的嘛。
可大姑却认为,现在人太不讲究了,活一辈子,得有规矩,心才踏实,人才体面。
究竟谁是谁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