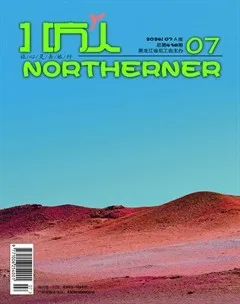在菜场感受城市的呼吸
2024-12-31陈晓卿

一座城市,最吸引我的,从来不是历史名胜或者商业中心,而是菜市场。中国太大,经济高速增长让许多城市的外观大同小异,甚至连旅游商品都面目可憎地趋于一致,只有在菜市场,还能从一些地域性的物产上,分辨出各自不同的风貌。
我去汕头衡山市场,看着卖姜的四十多个摊位,把洋姜、子姜、生姜、老姜等一样样品味过去;在台湾苏澳的南方澳鱼市,凡是没见过的海产我都要尝试一下;千岛湖畔的淳安小菜场,我和商贩一起,抓着清水螺蛳在机器上一个一个地剪去尾巴……像这样的菜场,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流动。在曼谷,在东京,在顺德,在成都,在长沙,这些城市的气味几乎都可以从菜市场里面找到。
我知道作家殳俏正在拍一个关于“地球上的菜市场”的纪录片,从菜市场开始品味那些风格化都市,了解城市人的区域性格。这是太让人期待的题材,角度选得真好。记得当年蔡澜先生给我讲过在那不勒斯的经历:早上五点就被房东叫醒,迷迷糊糊坐船去一个小岛上采购最新鲜的鱼,回来的途中,又去菜场采买和鱼搭配的各种辅菜,然后回到旅馆,安静地等厨师把午饭做好。这种似水流年的感受,我觉得可能是旅游中最高的境界吧。
回到厦门的第八市场。那天一共有三个人陪我去买菜,除了“酱油哥”,还有一位大厨,叫张淙明,他是蔡澜先生很喜欢的一位年轻厨师,有很好的海鲜料理手艺。另一位叫“海鲜大叔”,生物学家、科学松鼠会会员,据说是中国认识鱼的种类最多的人之一,他熟知各种海产成熟的季节、出没的区域以及口味。我们的奇幻旅行就要从这里开始。
第八市场藏身在纵横交错的老街老巷里,三四层高的骑楼绵延不断,外墙的色彩早已被风雨所摧老,露出古朴怀旧的质感。这几乎是我在国内见过的最大的海鲜市场了,几乎汇聚了中国沿海所有的海鲜种类。
厦门的土笋冻有名,我指着水里蚯蚓一样的虫子,问是不是做土笋冻的原料。“海鲜大叔”纠正道:“这是北方的海肠,厦门当地的沙虫叫可口革囊星虫,身上是有Burberry格子花纹的。”再往前走是一家卖贝类的店,有四十多种贝壳,“海鲜大叔”仔细介绍着各种螺的界门纲目科属种以及口感。张厨听着不耐烦,说:“老陈爱喝啤酒,给他选个苦螺就可以了。”
隔壁一家还是水产。有一种相貌丑陋的鱼叫虎鲨,是台湾海峡出产的鱼类,从前厦门人不吃,叫它“狗鲨”,因为它的皮上有很多沙子一样的东西会影响口感。后来,日本从厦门进口虎鲨,需求量很大,厦门人渐渐也开始吃这种东西。摊档里三个年轻人很麻利地把虎鲨进行了切割,交给张厨。两个小时之后,清水煮过的虎鲨鱼片和秋葵一拌,淋上酱油,爽口。
就这样一家一家逛下来,总共五条街,购物袋开始逐渐饱满。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中,这片老的街区或许也要面临拆迁。每天,从第八市场走出去的食物会幻化成无数餐桌上的景观,也会化作袅袅的炊烟,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味道。
即将结束采购,张厨带着我转到一个很深的小巷子,叫河仔墘,巷子很窄,而且只有一个挖牡蛎的老太太。张厨对《舌尖上的中国》拍了汕头的蚝烙一直耿耿于怀,他坚持认为厦门的海蛎煎才更美味,因此要买一点新鲜的牡蛎。只见他蹲在老婆婆身前,笑容可掬地挑了七八两蚝,礼貌地放下钱,和婆婆说再见。老人却旁若无人,自始至终没有搭话。据张厨说,从前卖蚝的是一对老夫妇,这位婆婆特别健谈。每次去买蚝,她都要跟你讲,吃蚝要吃小蚝,个头大的都是外地运来的,本地的小蚝才最甜,适合做海蛎煎。但老太太有一个毛病,每天会长时间地和老伴儿争吵,几乎从开市到收市,在她家买过蚝肉的厦门人都记得他们尖锐的闽南话的交锋。几年前,张厨去进货,发现老爷爷不在,再过一阵,婆婆也不在铺子里了。又过了将近一年,老婆婆一个人孤单地回到了这个挖蚝的小摊档上,自此再也听不见她说一句话,只有头顶的小风扇在不停地转。张厨的故事让大家唏嘘,离开市场的路上,很长时间都没人说话。
还是“酱油哥”善于调节气氛,不紧不慢的闽南话伴随着车辆发动同时响起:“现在是厦门最美的季节,也是最鲜艳的季节,等下拐过弯去,你就能看到大片鲜红的哄房发——哦,是凤,凰,花。”
(摘自文汇出版社《吃着吃着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