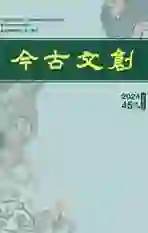“三美论” 视角下《西厢记》英译本对比分析
2024-12-19梁晓斐
【摘要】作为中国元曲的典范之作,《西厢记》以发人深思的核心思想以及经久不衰的美学价值吸引着学者与译者的共同关注。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美学活动,因此在其英译过程中,各译者充分发挥个人主体性,以期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鉴于此,本文基于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理论框架,对许渊冲先生以及熊式一先生的《西厢记》英译本进行深入对比分析,从理论层面分别描述两种译本与“三美论”的契合以及异同,以期对元曲翻译实践有所启示。
【关键词】《西厢记》;三美论;译本对比与赏析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98-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24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农林高校外语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改革实践与理论思考”(项目编号:2022JGZD036)。
一、《西厢记》简介
《西厢记》诞生于盛产戏曲的元代,素有戏曲中的“花间美人”之盛名,全书所反映出的反封建礼教思想以及其精湛的艺术性,吸引了一众读者,极具艺术魅力。《西厢记》为元代王实甫创作,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该书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在探讨《西厢记》时,不得不提及其故事蓝本——唐代元稹所著的《莺莺传》,《莺莺传》在当时的社会中传播度极高,激发了众多文艺创作者的灵感,许多文艺作品也在此时诞生,其中以《西厢记》最为出名。该书记叙了一段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崔莺莺是前朝宰相崔相国的女儿,在与母亲及侍女红娘护送父亲灵柩回家的途中,寄宿于普救寺。张生恰逢赴京赶考,在此途中两人一见钟情,但因礼法束缚,无法直接表达爱意。强盗孙飞虎,听闻崔莺莺的美貌,企图抢婚。崔夫人为保护女儿,许下诺言称退兵者则可以迎娶自己的女儿。张生巧妙寻求了友人杜确的帮助,成功化解危机。但崔夫人却出尔反尔,出于对张生贫寒背景的嫌弃,反悔婚约。张生相思成疾,在红娘的帮助下,两人私下幽会并订下终身。崔夫人被迫接受此婚事,提出张生考取功名后来提亲,最终两人终成眷属。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巧妙地将丰富的古典诗词与方言俗语融合,同时还运用了大量叠词,使得整体文本即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富有韵律感。
然而,尽管《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剧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却远不如莎士比亚的剧作。美是主观的,加之西方戏剧习惯直抒胸臆,而东方文化擅长将情感巧妙融入事物之中,较为含蓄。对此,翻译者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如何在确保译出原诗韵味的基础上,使译入语读者在阅读译本时还能够体验到与原文读者相媲美的审美感受。鉴于本文所选取的两个《西厢记》英译本时间上相隔数十年,且两位译者身处截然迥异的时代与环境大背景下,因此这两个译本可谓是为深入探索其与“三美论”的适用性的绝佳研究样本。
二、关于“三美论”
“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许渊冲仔细钻研鲁迅此“三美”中的精髓,并将其应用到自身长达60多年的中国古诗英语实践中,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三美论”。许渊冲在翻译诗歌方面,主张采用韵体译诗法,以期在译作中充分体现出“三美”原则,即“音美”“意美”和“形美”[4]。“音美”强调译诗时要尽量保留原文音韵形式,应竭力呈现其头韵的巧妙、平仄的起伏以及押韵的精准等,要求重现原诗所特有的节奏感,让译文听起来顺耳好听。而“意美”则侧重于让译者贴切领会并捕捉原文本内部的深邃意境,并做到在译本中将其进行重现,确保准确传达原文的内容时,进一步呈现出文章内部深层次的情绪表达,力求实现与原文本在内部含义之间的高度吻合与深度共鸣,比如双关义、言外义等,使译入语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诗歌中所蕴含的情感力量。要达到“形美”,译者则需竭力维持与原文的形式一致,具体体现在文段长短、格式规范、排列整齐度以及修辞手法的对仗等方面,以尽可能还原原文的整体风貌。
许渊冲认为,若“三美”无法同时实现,则译者可暂不求达到“形美”,尽力做到“音美”与“意美”[5]。由此可以窥见“三美”之间在其重要性上各有侧重,有的占据着更为核心的地位,有的则相对次要。其中“意美”居首位,占核心地位,许渊冲强调在翻译中首先要做到有效呈现诗歌的深层情感和独特意境。其次,“音美”则居第二位,即保留原文的音韵之美。最后则是形式层面美的再现。即是说,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译者要尽力将三者在文本中做到完整体现。
三、《西厢记》译本对比赏析
(一)音美
“音美”的原则是保留原文的音乐性或音韵美,即我们所讲的韵律、节奏、典故、谐音等。由于中国经典内含大量韵词,若不用韵,英译本则无法再现与原文相似的效果。在探讨唐诗翻译时,许渊冲先生倾向于坚守传统翟理思诗体译法,而非采用韦利所推崇的散文译法。由此可见许渊冲在对古典诗词的翻译上极力追求重现诗词的格调和韵律。
《西厢记》韵律和谐,文辞优美,讲究遣词造句,整体语言华丽婉转。《西厢记》中穿插着诸多富有生活气息的民间俗语,增添了全书浓厚的趣味性。对此金圣叹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此部作品在叙事堪称典范,通透而不晦涩[7]。因此,这就要求译者在扎实语言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原文韵律之妙。对此,许渊冲与熊式一采取了各自不同的翻译策略,以期译出原文本的音韵之美。
相比诗歌,曲极其注重每句的平仄押韵,在用字的平仄要求上更加严格。这种严格平仄要求在《西厢记》中可以窥见,该书中的唱词平仄之韵,严谨遵循曲牌规定,词句之间长短高低相称,读起来抑扬顿挫,十分悦耳。具体可见《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惊艳》篇中:“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7]在对此句的翻译中,许渊冲在符合译入语习惯的基础上,力图保留《西厢记》中所原有的节奏美感,尽量还原其原文韵律。许渊冲在前两个短句“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中采用了英诗中常用的抑扬格六音步,跳过中间“东风摇曳垂杨线”一句,继续使用抑扬格六音步,将最后两句“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以同样格律译出,与前两句进行声韵方面的呼应,可谓是做到了前后内容的相得益彰。一般说来,英诗中为达到平仄跌宕之感,常用抑扬格和音步来实现此节奏效果,如此看来,许译不仅符合了译入语的习惯,还做到了对原文语音之美的重现,可谓是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对原文的有效转换。此外,细细读来可见《西厢记》全文的唱词韵脚基本都押韵。如例句中的几个尾字“在”“远”“线”“片”“面”基本都彼此押韵,许渊冲分别将其译为“here”“hear”“breeze”“trees”“disappears”,整体读起来音调整齐划一,和谐优美并且朗朗上口。
对比之下,熊译则没有尽然译出《西厢记》原文所特有的节奏韵律感,押韵部分基本没有译出。熊译中并未采用英式抑扬格,几个尾字“在”“远”“线”“片”“面”彼此之间基本也不押韵。在探讨译诗的音律时,熊式一在其译本引言中亦有所谈及,他明确指出译诗极为困难,自身的译文并不完美,但他愿为准确而舍弃押韵带来的文本改动[10]。可见,熊式一先生在译文中对“音美”方面做了割舍,将更多的精力置于对原文的准确性传达上,并未在译文中全面采用押韵译法,保留原文中的全部音律。从例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熊译在处理文本时力求保证文本高度的准确性,尽量完整地保留原文语义内涵。熊式一在译文中将“佩环声”“垂杨线”做出了完整的释疑表达,分别将其译为“the tinkling sound of her jade ornaments”以及“the branches of the weeping willow”,语言自然流畅,在人面前呈现出了一整幅动态画面,其中“weeping”一词生动表现了“垂杨线”中的“垂”字,而许译中仅用了一个动词“wave”来表现杨柳摇之感,相比之下,熊译的形容词“weeping”则更加自然,更好理解,且可读性更高。熊译本对于原文读者来说会缺少韵律感,在“音美”方面所译不足,但却可以让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便于文本的对外传播。可见,在“音美”方面,许译在保证语言流畅度的同时,传达出节奏起伏之感,将“音美”原则贯彻诠释得更加完成妥当,而在语义方面熊译则更适应译入语的表达,便于译入语读者进行理解。
(二)意美
中国文学美学观不仅强调文学作品的形式之美和音韵之美,更强调意境之美。意美在“三美论”中处于核心位置。所谓“意美”,就是要将原诗的意境美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与西方诗歌简单直接的意义相比,中国古典诗歌的意义是相当丰富的,因为在汉语中,一个词往往传递着几种不同的意义。为了表达诗人内心的情感和感受,译者应该选择最能触动诗人心灵的意义。从概念中看,“意美”主要是指原文深层内部结构的美,而不仅限于肤浅表层意义上的相似。所谓“意似”,就是要表达原文的意思,尽可能做到不误译、不漏译。但有时候“意似”与“意美”却不完全等同,因为有时意境美来源于个人想象或历史原因。
在诗歌翻译的艺术中,追求诗歌美的终极归宿则是实现意境美,意境美亦是译诗的最高境界。而实现意义上的美感再现,并不仅限于对原诗意境的呈现,更重要的是,它还需要渲染原诗的艺术意境。《西厢记》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其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来源于背后的中华文化内涵以及文本内部丰富的联想意义。许渊冲先生与熊式一先生依旧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以期在翻译中实现对原文的意美转换,以便译入语读者深入了解中华经典文化。
正如《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拷艳》篇,在本篇中存在大量中式特色成语典故等,就该篇题目“拷艳”,两位译者分别将其译为“Rose in the Dock”以及“Hung Niang in the Dock”,其中,熊式一将本篇中出现大量篇幅的重要角色“红娘”在题目中译出,即“拷艳”中的“艳”,熊式一按照直接音译法将其译为“Hung Niang”,而许渊冲则选择用“rose”一词对其进行指代,一般在西方文化中,“rose”常常用来指代女性角色,许渊冲这样对其进行处理也可谓是别具匠心,让人眼前一亮,只是如此艺术化的表达形式可能会让译入语读者一时摸不着头脑,无法理解其意一时联想到“红娘”这一角色,对比之下熊译则更加直白了当。此外,如本篇中的“只若是夜去明来,倒有个天长地久。不争你握雨携云,常使我提心在口。你只合戴月披星,谁许你停眠整宿。夫人他心数多,情性绉,还要巧语花言,将没做有!”[7],可见此句中存在大量中式四字成语,分别是:“夜去明来”“天长地久”“握雨携云”“提心在口”“戴月披星”“巧语花言”“将无做有”。成语典故是中华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在英译本中做到对其意义的准确阐释则至关重要。
其中,“夜去明来”原意是晚上离去,天明则归来,形容人们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在此两位译者都将其译出了“夜晚离开,黎明归来”的意味,准确恰当。“天长地久”一词则比较常见,形容时间悠久,许译和熊译分别将其译为“As long as sky and earth”以及“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意义基本趋同,都做到了准确阐释。“握雨携云”一般指男女欢合,此成语中则蕴含着一则典故,这则典故出自宋玉的《高唐赋》,在此也借神女与楚王这一典故暗指主人公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这一典故为人熟知,在过去也常出现在一众古人的诗句中,极富文化内涵,对此,两位译者一齐选择同一做法,均未将这一典故进行明确译出,如此一来则丢失了该成语中的部分文化典故色彩,却更易为读者理解其中含义,两位译者分别采用了意译与较为直译的解释方法将其译出,许渊冲将其译为“But you would bring fresh shower, Each night for thirsting flower”,此处他是借用了雪莱《云》中的句子,将男女欢合之好用“fresh shower”以及“flower”等词进行表达,极现情爱缠绵美好之意,其中用“the thirsting flowers”中的“thirsting”一词也就此表现出等待中的焦急主人公形象。而熊译则相对较短,一个“happy union”即展现出男女之爱,虽也贴切,但在意境表达的艺术化处理方面则不如许译完善。“提心在口”原意形容人紧张、担心,两位译者也均做出了明确释义,许渊冲将其译为“make me feel in the wrong, Gnawed by an anxiety strong”,而熊式一将其译为“made me as anxious as if my heart were in my mouth”,相比而言,许译中的“Gnawed”会比熊译直接译为“my heart were in my mouth”更加生动,体现出抓耳挠腮的焦急渴望之感。“戴月披星”原意是身披星星头顶明月,形容一个人早出晚归地辛勤劳动,抑或是形容人日夜赶路的辛苦疲惫,许渊冲将其译为“have gone and come back by starlight”,熊式一则将其译为“have gone at moonlight and returned with the morning stars”,两位译者都遵循了成语的原意,但许译仅用了一词“starlight”即表达出早出晚归之感,相比之下熊译则用了“moonlight”以及“the morning stars”四个词,从形式上看来更为冗长,但确也符合原意。“巧语花言”原意为辞藻修饰过多而无实际内容的空洞言语文章,现在多形容一个人虚伪动听的假话,对于此成语,许译为“honeyed words”,而熊式一则将其译为“plausible words and specious arguments”,字数方面,熊译依旧多过许译,意义的准确呈现方面,两位译者也稍有不同,熊式一所用的两个词“plausible”和“specious”,均有表示“似是而非”的意思,对成语的原意表达方面准确无误,但许译的一个“honeyed”却更能凸显出成语背后主人公所想要表达的虚假谄媚之意,更为形象。“将无做有”原意把没有的事情当作有,许译为“when there's nothing wrong, she would make much ado”,熊译则为“can make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表意上来看,两个译本表达均十分贴切恰当,均译出了“将无当作有”的概念,但相比之下,笔者认为许译的“make much ado”则更显“无谓的麻烦”意味,对成语的解释则更加生动。除此之外,此例中还有塑造人物性格“红娘”聪明机敏的民间俗语,如“心数多,情性绉”,许译中将其简单表达为“ingenious mind”,熊译则不仅使用“ingenious”一词,熊译另添“staid”一词生动刻画出了红娘聪明机敏、热情泼辣古板的形象。此外,从译本的尾字“night”与“light”、“secure”与“endure”、“shower”与“flower”、“wrong”与“strong”、“mind”与“unkind”等也能看出许渊冲依旧在自己的译本中贯彻了“音美”的原则。相比而言,许译在保证译文“意美”的同时还兼顾了“音美”,而熊译并未全文兼顾“音美”原则,却在阐释本意上略胜一筹。
(三)形美
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地位卓然。在形式上,元曲与词相似,皆以长短句为特色,然而相较于词,元曲的格律更加宽松自由,词语表达上也更加偏向口语化,表达感情更加直接。元曲这一文学形式,可细分为元杂剧与散曲两大类别。其中,元杂剧以其卓越的成就而备受瞩目,因此,在文学语境中,“元曲”一词常作为元杂剧的代名词。元杂剧这一戏剧形式,是基于宋杂剧、金院本及诸宫调等艺术传统发展起来的。它独具特色地运用北曲风格进行演唱,并将唱、念、科、舞等多种艺术手段有效结合,以此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在结构上,元杂剧通常由一楔子引领,以“单人主唱”为核心,辅以“曲白互生”的形式。此外,元杂剧还有一些显著特点,诸如对舞台效果、角色分工的重视等。无疑,作为一种戏曲形式,元杂剧充分体现了戏曲艺术的本质特征。
在探讨译文的“形美”时,许渊冲先生主要关注的是译本在行数、节数以及字数上的要求。简而言之,“形美”旨在追求译本在外观上的整齐与和谐,力求在字数和行数尽量与原诗保持相近的对应关系。然而,由于中英文在表达方式以及语言结构上的差异,要实现“形美”这一目标则颇具挑战。所以,在权衡“三美”的取舍时,我们应首先确保“意美”的实现,其次追求“音美”,最后才追求“形美”。对此,许渊冲与熊式一先生在保证译本“形美”方面依旧遵循了各自的翻译原则。
至于“形美”方面,我们可具体来看《西厢记》第四本第四折的《惊梦》篇。一开头,关于此折的题目“惊梦”,两位译者就采用了不同的译法,许渊冲简单将其译为“Dream”,而熊式一将其译为“A Surprising Dream”,添加了形容词“Surprising”,从形式方面来看明显熊译更符合原文的形式特点,将“惊”字有效译出,而此处许译仅仅译为“Dream”,并无任何形容词的添加,如此一来虽为译入语读者留下了丰富的遐想空间,但相对而言熊译却更便于读者理解此篇主题。深入此篇,如“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惨离离云际穿窗月。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生梦蝴蝶,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7],该句明显采用了“复叠格”的修辞手法,即叠字的大量运用,上述例句中共有八个叠词,分别是:“绿依依”“静悄悄”“疏剌剌”“惨离离”“颤巍巍”“虚飘飘”“絮叨叨”和“韵悠悠”。一般说来,“绿依依”用来形容绿茫茫一片好光景;“静悄悄”用于形容静谧无声的外部环境;“疏剌剌”用来呈现空荡荡的模样;“惨离离”一般用形容离别之苦;“颤巍巍”一般指人或物站立不稳的状态;“虚飘飘”一般用于形容虚无缥缈轻飘飘的事物,如云、风等;“絮叨叨”则一般指人的嘈杂唠叨;“韵悠悠”则一般指从远处传来的悠扬声音。这些迭词形象生动,无论是从形式还是意味方面,大量叠词的结合运用不仅加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在增强环境渲染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让人读起来仿佛身临其境,但是要将这些叠词形式结构在译文中表现出来,则比较难处理。对此,许渊冲依次将其译为“green,green”“silent,silent”
“gentle,gentle”“gloomy,gloomy”“shivers,shivers”“wafts and wafts”“chirps and chirps”“spreads,spreads”,可见许译不仅在形式上对迭词结构进行了保留,还忠实传达了原文迭词的各自含义,其中“trees”和“breeze”,“night”和“nigh”等尾字还做到了押韵,使得译本从整体上达到了“音美”与“形美”的效果。相比而言,熊译仍继续采用直译法将原文内容尽量译出,但并未对原文迭词形式进行保留,将各叠词仅用一词译出,分别是:“Green”“Gentle”“silence”“Melancholy”“Tremulously”“transported ”
“Incessant”“Never-ending”,可见许译与熊译皆译出了原文所要传达的内容,但在保留原文“形式美”方面许译更加完善贴切。
四、结语
翻译作为一种艺术,旨在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精妙转换。通过对比分析许、熊二人的《西厢记》译本,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均在“三美”方面做到了尽力呈现,熊译基本“不损原意”,相对而言许译显然更加注重在韵文方面的翻译统一,有时会“因韵损意”,但相对而言许译的译本更好地遵循了“三美论”的准则,使得音美、形美、意美完美结合。这也昭示了,如要在翻译工作中再现原文的“三美”,我们必须倚赖对词汇的精准运用、句式的巧妙布局,以及修辞格的恰当运用等多种手段。在翻译中,语言的艺术表达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艺术表达,因此译者需深入了解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性格特点,在锤炼语言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时,不忘兼顾经典作品的形神音韵之美的有效传达。许译、熊译皆做到了尊重原文,对原意进行有效传达,也可见“三美论”对经典文学翻译的适用性,这不仅有利于译入语读者欣赏到中国传统戏剧经典中原样的美,深度领会其思想文化,也有助于向世界展现中国经典戏剧文学的独有魅力。
参考文献:
[1]许渊冲.美化之艺术《毛泽东诗词集》译序[J].中国翻译,1998,(04):47-50.
[2]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2.
[3]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
[4]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5]许渊冲.翻译的艺术(增订本)[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6]吴珺如.中国古典诗词曲赋英译的翻译美学思考[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111-116.
[7]王实甫.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8]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9]王实甫.西厢记(中英对照)[M].许渊冲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10]熊式一.The Romance of the West Chamber(Hsi Hsiang Chi)[M].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