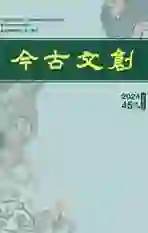粤方言中詈语的文化透视
2024-12-19杨冬青
【摘要】作为人类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詈语不仅是口语交际中常见的语言现象,而且还承载着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文化内涵,是了解特定地区文化特质的重要突破口。根据粤方言詈语的特点可将其大致分为食物类、异物类、鬼怪类、器官类、禁忌类及负面特征类六种致詈方式,探析其语用功能及地域文化内涵,能挖掘出粤方言詈语背后人们的思维观念、社会文化及价值标准,勾勒出粤方言詈语的基本语言面貌。
【关键词】粤方言;詈语;语用功能;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H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11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28
所谓詈语,即是指用来骂人的表达形式。《大辞海·语言学卷》中对“詈语”的定义是“用于骂人的词语和言辞”[1],“笨蛋”“混账”等词便被列入詈语的范畴内。“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总体的组成部分,是自成体系的特殊文化。”[2]作为一种社会民俗现象,詈语作为语言表达形式的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背后往往与社会中普遍否认的事物相联系,能够反映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及文化特质,是揭示社会价值标准的重要语料。目前学术界对于詈语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詈语的本体、修辞、文化、心理、具体方言及社会差异研究,而在汉语方言詈语模块中,粤方言詈语研究成果鲜少。因而文章主要以《广州话俗话词典》、微信调查问卷、知乎等网络平台为语料来源,共收集了200余条粤方言常用詈语,对粤方言詈语的语用功能及文化心理进行深入的剖析,以期从中透视粤方言区独特的传统观念、思维方式及文化内涵。
一、粤方言詈语的语用功能
(一)詈骂功能
詈骂功能是粤方言詈语最基本的功能。“语言是人们表情达意的重要工具,人类的任何情感可能都需要相应的语言来传递。”[3]粤方言区的人之所以说詈语,最主要便是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恨或对对方行为的不满,如否认别人不良为人处世及做事行为时的有:“死蛇烂鳝”“癫狗”“废柴”“两头蛇”“大花洒”等,其中“大花洒”即是詈骂对方花钱如流水,不懂节制。因怨恨诅咒别人的有:“冚家铲”“拉你去屯巴”“雷劈你”等,其中“冚家铲”被粤方言区的人称为是骂人最狠的词,意思是诅咒别人全家都遭遇不幸。以上这些詈骂词具有较强的詈骂效果,能带给詈骂对方带来强烈的人身侮辱。
(二)戏谑功能
有一部分粤方言中的詈语主要是被人们用来打情骂俏、活跃气氛的,本身并没有带着强烈的骂人意味,如“化骨龙”是父母用来说自己子女,字眼上虽带有骂人意味,实际上只是父母对自己子女的一种戏称而已。“马骝”即普通话中的“猴子”,表面上是指骂对方是猴子,实际上在粤方言区的很多人会使用该词来称呼20-30年龄段的男生,本身是为了戏称对方的一些行为像猴子,并不企求对对方造成实质上的语言伤害。“口水多过茶”是说对方话很多,在特定语境中时可划为詈语,但人们在日常交际中更多是用这个词来开玩笑说对方过于嘴碎,自己听得腻了,本身也没有骂人意味。
(三)零功能
在特定的语境中,詈语的一些语用功能会发生转换。零功能即粤方言中的一些詈语既不是为了詈骂对方,也不是为了戏谑对方,而只是表现为一种单纯的口头禅,并没有明显的詈骂意图,是日常交际中使用的一种平常语言行为。如“鸡手鸭脚”“搅屎棍”等词就具有零功能,使用者在使用词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针对个体,或是自己在做事时习惯说的口头禅,或是无坏意地吐槽别人言行搞笑,虽归入了詈语范畴,但在一些特定场合中并无强烈的詈骂意味,受话者内心也不会产生不舒服的心理体验。
二、粤方言詈语的文化透视
“文化是主体和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4]语言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文化,语言是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则是语言的背景,对语言最直观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词汇系统上,“特定的文化观念会在词的衍生缘由、词的构成形式上留下深深的痕迹。”[5]粤方言詈语承载了粤方言区的文化风貌,蕴含了其内部独特的民俗习惯、传统文化及社会规范等多方面的文化特质。因而本文通过分析詈语与粤方言区文化之间的联系,以图达到透视粤方言文化的目的。
(一)粤方言詈语与文化心理
1.人本观念
(1)贬为异物
人本观念在中华民族自古有之,尽管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认知的精进,人们已然知道人并不是自然的主宰,但在心理上人类仍然认为自身处于自然界的顶端,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维护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在现实世界中的主导地位。
“圣人作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人知礼后而后知人自身与禽兽之间的区别,更是印证了人在非生命体前的优越感。因而,人们为了达到詈骂目的,在使用詈语时会将对方人格詈骂至非人的事物。“异物化贬损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类群体对人性的强调和强化”[6],运用动物意象进行致詈本身就表现出了“以人为本”的文化心理。如“癫狗”是贬斥人的行为很癫狂,“猪头饼”是贬低对方在智力上像猪一样,“两头蛇”是斥责人心术不正,见风使舵,见利忘义。为了提升致詈程度,除动物意象致詈之外,无生命体的什物也被人们列为是致詈意象。如“大辘木”是嘲笑对方什么都不懂;“水货”是骂对方很差劲,没有实力;“废柴”是骂人跟废了的柴一样,没有头脑;“搅屎棍”是贬斥人爱搞事情。使用以上詈语的人一般有着强烈的等级观念,骂人的同时也维护了人在自然界中的至高地位,反映了一种唯心主义的人本观念。
(2)审美认知
人们往往带着自己的认识标准对世界各类事物的美丑善恶进行评判,“美丑的评价标准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自我认知判断”[7],在语言表达上人们则会通过詈语表现出自己对样貌、行为、人格、智力等方面的审美标准。粤方言詈语中通过审美标准对人的行为进行评判的有“妖猪扭拧”,在人们的平常认知中,人无论处于何种场合中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过于活泼被视为是上不了台面的行为,在人们的审美认知中此类行为是异于正常人类的,因而评判人们的这种言行举止为“妖猪扭拧”,将这个人的行为与“妖”“猪”行为相提并论,是一种人格上的贬低。对人的道德品质进行评判的有“咸猪手”“大炮友”“孤寒鬼”,“咸猪手”是贬斥人的好色,“大炮友”是讽刺人爱说谎,“孤寒鬼”是嘲讽人的吝啬,都是在说明对方在做人的规范上存在问题,异于常人。
2.禁忌心理
禁忌是人们因缺少对外界与自身能力的正确认知而产生的共有文化意识,此类现象存在于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是人们为避免产生错误行为而做出的规约性禁止,“本质上是一种迷信,人们在设立禁忌的同时更要强调犯禁忌的后果。”[8]禁忌心理在语言表达上指人们会有意识地避开使用指称某些事物或观念的特定词汇或直接使用委婉语来达到规避禁忌的交际目的。“当禁忌语言发展后被用作骂人话时,就成为了措辞厉害的詈语。”[9]詈语是通过言语表达来詈骂对方,人们往往会选用对方或双方都禁忌的事物来增强言语攻击效果,本质上已然是对禁忌进行了突破。
(1)死亡禁忌
在所有的禁忌中,死亡是人们最不愿主动提及的,本能逃避的话题。在“万物皆有灵”观念的影响下,人们认为语言本身带有神奇的力量,习惯于将语言所表示的事物与语言本身等同起来,人忌讳死亡的存在,便不允许言语表达中出现任何关于“死”的字眼,从而产生了“语言的灵物崇拜”[9]。在中国古老文化里,“寿终正寝”被视为是吉祥的象征,其他非自然终结的死亡都被赋予不祥的意味,为避免直接谈及这种晦气行为,人们用“仙逝”“离世”“逝世”等表死亡的委婉语来代替“死亡”。为最大程度地增强致詈效果,人们在詈骂时便会使用与“死”相关的构词方式。在广东粤方言区,人们买房会避免选用与“死”谐音的房间号,如“404”是广东人极其忌讳的一个数字。粤方言詈语中直接带“死”语素的词有“死马骝”“死蛇烂鳝”等,表“死”含义的“冚家铲(冚家富贵)”“拉你去屯巴”等。“死马骝”即是骂对方是“死猴子”;“死蛇烂鳝”是指对方跟死蛇和烂鳝一样;“冚家铲(冚家富贵)”即是骂对方全家都死;“拉你去屯巴”即是指拉某人去火葬场,而火葬场是只有已死的人才会被拉去的场所。以上与“死亡”相关的詈语将被詈骂对方与死亡相挂钩,被称为是粤方言詈语中致詈程度最深的,即骂人骂得最恶毒的,可以反推人们对死亡话题的禁忌程度其实是极深的。
(2)排泄禁忌
除了死亡禁忌,与排泄相关的词汇也涉及人们在日常的禁忌心理。在人们的认知中,排泄物属于污物,是肮脏的象征,因而在日常交际中并不会主动地提及此类话题。粤方言中也有针对人们的排泄禁忌心理进行詈骂的詈语,如“粪箕”是直接詈骂对方就是装屎的东西,肮脏且毫无用处,“食屎”是说人的行为过于糟糕,只配直接去吃屎,“搅屎棍”是直接骂詈人做不了好事,爱搞事情,只有跟搅屎的棍子一样的存在价值。
(二)粤方言詈语与区域文化
1.食物类詈语与饮食文化
广东处于我国南部沿海,西面、东面与北面丘陵环绕,依傍山林,飞禽走兽较多,古籍《岭外代答》中记载:“深广及溪峒人,不问鸟兽虫蛇,无不食之”[10]。且广东是中外交流的必经之地,在古代由于地处边疆,历代王朝对其的控制力弱于内地,由于正统封建思想的影响较小,因而敢于尝试用各种食材烹饪,在广东很多地区,如“狗、蛇、龟、禾虫、鹧鸪、禾花雀、豹狸、果子狸、海狗鱼”等飞禽野味也在人们日常烹饪的清单中。因而人们想通过詈骂别人来发泄自己情绪时,为避免因詈骂产生的直接冲突,降低杀伤力,会选用带有食物的词汇进行詈骂。如“扮叉烧、东莞腊肠、番薯头、蛋散、水鱼、炖冬菇、萝底橙、油炸蟹、卖剩蔗、发呕豆、大头虾、倒瓤冬瓜”等词都包含了与食物相关的语素。同时,在广东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鸡是不可或缺的菜肴,因而粤方言中包含“鸡”一词的詈语很多,如“鸡手鸭脚”是说人行为笨拙,毛手毛脚;“发鸡盲”是责备别人找不到东西;“鸡仔媒人”是指那些爱管闲事的人;“霸兜鸡、霸巷鸡乸”是指霸道的人;“鸡蛋摸过轻四两”则是指人十分贪婪,连鸡蛋的便宜也占。此外,粤人嗜茶好客,饮茶文化发达,因而粤方言詈语中也有一部分含“茶”一词,如“口水多过茶”是贬斥人废话太多,“茶瓜送饭,好人有限”是嘲讽对方不是好人,竟然舍得送茶与饭来,“隔夜茶,唔倒(赌)唔安乐”则是通过谐音的方式詈骂人嗜赌成性。
2.诅咒类詈语与宗族文化
中国的传统宗教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人们詈骂对方要想满足自己的发泄感,自然会抓住被骂者或整个社会看重的东西进行攻击,因而粤方言詈语中有一部分是与被骂者的家庭成员相关的。祖先崇拜是深深存在于中国人观念中的,每逢清明节或其他重要节日,人们都会用祭拜的方式寻求祖先的保佑,在广东一些地区,甚至祖坟位置也被视为是影响家族兴旺的重要因素,因而对他人祖先进行詈骂的侮辱性是很大的。粤方言詈语中与祖先相关的有:“叼得你祖宗十八代”,这里既涉及到性话题,同样也是在侮辱被骂者的祖先。
“中国人作为其家族的一员,既要对祖上负责,以图实现‘光宗耀祖’的最高理想,还得实现延续香火的神圣职责。”[11]人丁兴旺是家族荣誉的一种标志,同时对人丁的品行、素质、能力等方面的评价标准也是体现在宗族观念中的,因而针对家族子嗣进行詈骂的杀伤力也是很大的。粤方言中嘲讽或诅咒家族后代的詈语有“二世祖”,是詈骂某一家族中的后代没有传承好祖先的优良品质,类似于普通话中“纨绔子弟”的说法,此外还有直接詈骂“孝子”,该词是嘲讽子孙空有孝顺之名却并无孝顺之实。这些针对祖先或子嗣的詈语,詈骂程度极深,是对他人人格的极大侮辱,也说明了宗族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重要的存在。
3.负面特征类詈语与实利重商文化
广东在唐宋时代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区,当地商品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除广州、佛山两大商埠之外, “上沂津门,下通厦门”这一说法印证了潮汕商人的商业足迹,形成了当时著名的“潮州帮”与“广东帮”。因而粤方言中则有针对人的赚钱能力及与做生意事务相关的詈语,如“滚红滚绿”暗指人的行为很不老实,爱胡闹、欺诈与胡说八道,“滚”在粤方言中时常是与“利”相挂钩的,“利滚滚来”即是指“钱快快来”,因而“滚红滚绿”即是骂人为了赚钱而毫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卖剩鸭、卖剩蔗、萝底橙”均是从做生意的角度嘲笑那些到了社会普遍认为的适婚年龄却尚未结婚的女性,即社会上所说的“剩女”,“波罗鸡,靠黐”中的“波罗鸡”是老广州郊区黄埔南岗庙头村南海神庙(波罗庙)庙会期间所销售的一种纸制的玩具鸡,相传是为了纪念来广州从商的贡使达奚司空而制作出卖的一种玩具,“靠黐”指靠粘贴而成,现在则引申至骂一些人爱吃白食,占便宜。
三、结语
詈语被视为是粗俗文化的糟粕及攻击性的语言,因而常为人们感到不耻。不文明的话语终将会被社会所抛弃,但是“骂人话的价值观和思想原则却不会轻易消失”[12]。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及文化现象,詈语实质上是对社会语言规范的突破,更是个人本能的宣泄。从这个意义上说,詈语既能暴露人性的本质,也能揭示社会的价值标准,以及隐性引导人们为避免他人詈骂而朝着社会审美认知路线走,从而间接提高社会道德品质。综上所述,本文对粤方言詈语的语用功能及区域文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进而更为深入地了解粤方言詈语与该区域文化之间的联系,也展现了粤方言的文化特质。
参考文献:
[1]夏征农.大辞海·语言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105.
[2]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48.
[3]刘风乐.渑池方言骂詈语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9.
[4]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3.
[5]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224.
[6]冯丽云.梅县客话詈语及其文化心理解读[J].农业考古,2008,(03):193.
[7]吕亚丽,张小兵.陕北方言詈语文化探析[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8(03):119.
[8]毛佳丽.鸡西方言詈语研究[D].牡丹江师范学院,2022.
[9]劳保勤.死亡禁忌与委婉语[J].国际汉语学报,2011,2(01):232.
[10](宋)周去非著,屠友祥校注.岭外代答[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01.
[11]尹群.汉语詈语的文化蕴含[J].汉语学习,1996,(02):37-40.
[12]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211.
作者简介:
杨冬青,女,广东湛江人,西华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