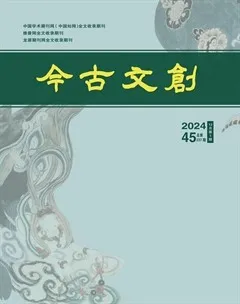明中期赣南地区的社会失序与政区调整
2024-12-19丁扬
【摘要】明中期是赣南政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严重的社会动乱,官方着手进行政区调整。这一举措加快了赣南地区社会秩序的恢复,巩固了明王朝对赣南的政治控制,促进了赣南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变迁,最终保障了国家安全,维护了国家统一。通过研究明中期赣南政区调整的社会背景、具体过程及其意义,可以加深对该地社会发展的认识,并为地方治理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明中期;赣南地区;社会失序;政区调整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77-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19
政区是国家依据人口分布、经济状况、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等因素而划分的地域单位和组织形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亦会将政区调整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加以运用,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明中期①时,赣南地区②陷入了混乱失序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官方亦适时对当地政区做出调整,以期稳定社会秩序,强化政治控制。以往的政区研究多为通史性的综合论述,对赣南的政区演进多是置于江西政区发展史当中去考量,容易忽略赣南社会情况的特殊性。③赣南地处东南腹地,介乎中原与岭南之间,为赣闽粤湘四省往来要冲,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尤其是,随着大庾岭通道的开凿,赣南一举成为南北交通的联结枢纽和战略要地,适应了唐宋以来江南地区的迅速开发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这一时代大趋势。④这使得明中期赣南地区的动乱与政区调整,不仅事关赣南社会的治理和发展,更关乎国家战略安全。
一、山河无定:赣南地区的社会失序
明中期时,明朝由盛转衰,统治阶层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赣南地区也出现了诸如土地兼并、赋役繁重、流民增多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以至于民变四起,势成燎原,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这其中有一些地区的社会动乱尤为严重。
横水、桶冈地区。该地地处大庾、上犹、南康三县交界,众山璧立,路险径僻。正德初年,谢志珊、蓝天凤等自称“盘皇子孙”,并利用畲族民间流传祖先盘瓠传说的“宝印画像”进行宣传活动,在横水、桶冈地区率众起义,设官封号,立寨八十四座,并和其他起义军相互联络,势力绵延赣闽湘三省,坚持了十余年。[1]
安远黄乡地区。这一地区多高山大谷,接岭连峰,有“盗区”之称,其间横亘有绵延三百余里的大帽山,正德以前如张仕锦、何积玉等人皆“恃险凭高,巢窟其中”,后叶芳自广东程乡入境,沿途吸纳其他起义军,“有众七千,分为七哨,自号满总,言满有其众也”[2]。万历四年,叶芳之孙叶楷又于当地招兵买马,征粮筹款,势力“延袤三百余里,田地尽其占据,党与二三万人,四季轮班,四出劫掠,流毒江西闽广地方,难以尽数”[3]。
龙南下历、高砂地区。这一地区临近广东和平县,亦是山高林密之地。嘉靖三十六年,乡民赖清规于下历地区起义。赖清规本为平民,曾随征三浰有功,善为人解纷息斗,常受县官委用,后因郡卒索贿无度而聚众起义,势力遍及信丰、龙南、安远三县,并且“合岑冈贼李文彪、高砂贼谢允樟,号三巢,而清规为雄,啸聚十年”[4]。
通过以上内容,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对明中期赣南动乱的发生特点进行总结。第一,动乱的发生频率较高,尤以正德、嘉靖两朝为甚。据相关数据统计,从洪武(1368-1398年)至康熙(1662-1722年)这355年中,赣南地区的动乱合计142次,其中明中期(正统至嘉靖)51次,占1/3强。而正德、嘉靖两朝计35次,又占明中期动乱的2/3强。[5]第二,动乱的参与人数较多。这一时期,如叶芳、叶楷、赖清规等人发动的起义皆在数千余人以上,同时,在起义发生时还出现了当地民众为之通风报信的情形,说明起义的爆发是得到了底层百姓的支持的。如横水、桶冈起义时,王阳明就发现“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长潭、杰坝、石玉、过步、果木、鸟溪、水眼等处居民,访得多系通贼窝主;及各县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贼之人”[6]。第三,动乱的持续时间较长。从个体上看,如谢志珊、赖清规等人发起的起义都是坚持了十余年才被平定;从总体上看,赣南地区的起义此起彼伏地纵贯了整个明中期。第四,动乱对赣南地区的破坏程度是最为严重的。由于赣南地处东南腹地之中心要冲,这种极为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亦使其成为各方起义军、官军往来的必经之地,使得赣南的社会动荡无论在持续时间上还是在破坏力上都远超周边地区。第五,动乱呈现出了地域上的集中性和影响上的广泛性。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到,起义的发生有其策源地和中心。同时,赣闽粤湘毗邻区在地域环境上山水相连,而各省官员却无越境管辖权,面对起义军时多采取推诿观望的态度,有鉴于此,起义军常常在政治力量薄弱的边界山区辗转作战,相互联络,声势相通,使得起义的影响范围极广。如横水、桶冈地区的谢志珊,浰头地区的池仲容,就曾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等人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使得起义的影响力遍及赣粤两省。[7]第六,动乱呈现出了多族群流民共同参与的色彩。如横水、桶冈等处起义的畲人就是早年因干旱和饥荒从广东、湖广迁入的,并被政府安置于此,长期以来以砍山耕作为生。[8]对此,黄志繁等人认为,“流民”常与“土著”形成概念对应,是指因居住时间不长、没有本地户籍而不被当地社会接受的人群,在官方管理体系中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9]饶伟新则认为赣南流民或为躲避繁重赋役而脱籍的“逋负之徒”,或为未受教化的“蛮夷”,且两者往往相互关联,难以划分界线。[10]总之,明中期赣南社会极度失序,动乱发生有其特点和规律,这为官方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二、因时而变:赣南地区的政区调整
元末赣南分属赣州、南安二路。赣州路下有赣、雩都、信丰、兴国四县与宁都、会昌二州,宁都州下有石城、安远、龙南三县,会昌州下有瑞金县;南安路下有南康、大庾、永清三县。乙巳年(1365),赣州、南安改路为府,州县依旧。洪武初,降赣州府宁都、会昌2州为县,与其下原有县一起改隶于府;并将南安府的永清县改名为上犹。[11]可见,明前期赣南地区只出现了少数政区级别调整和改名的情况,并未有大的数量上的变化。但至明中期时,赣南骚动,官方转而从政区调整入手,新增了崇义、定南、长宁三县,以重建社会秩序。
(一)崇义县
崇义县于正德十二年(1517)设立。这一地区原属上犹县,众山璧立,与外界交流极为困难,故而号令难及。正德年间,横水、桶冈地区爆发了以谢志珊、蓝天凤为首的起义,由于该地介乎三县之中,加上山溪深阻的地理环境状况,使得官方的镇压行动常常难以见效。
正德十二年,王阳明平定了谢志珊起义,监生杨仲贵认为,这一地区过去素为“盗区”,虽暂时戡平,但恐撤兵后残余的起义人员重新聚集起来,故主张建立新县以求长治久安。王阳明也认为应防乱于未发,通过众建县治来安定新民,推行王化,构建起良好的社会秩序:“议照前项,地方大贼既已平荡,后患所当预防。今议立县治并巡司等衙门,惩前虑后,杜渐防微,实皆地方至计……如此,则三省残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无潜匿之所而不敢逃。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仪冠裳之地,久安长治,无出于此。”[12]后王阳明委派领兵知府邢珣、知县王天与、黄文鸑亲往勘查,认为上犹县的横水地处三县之中心,“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设县”[13]。最终析南康之尚德、隆平二里,上犹之崇义、雁湖、上堡三里,大庾之义安、铅厂、聂都三里,置崇义县,隶属南安府。
(二)定南县
定南县于隆庆三年(1569)设立。这一地区向来地处边远,政教鲜及,民风犷悍,极难治理。嘉靖三十六年,下历堡乡民赖清规聚众起义,与高砂谢允樟、岑岗李文彪互为奥援,这其中赖清规的势力最为强盛。嘉靖四十五年,都御史吴百朋亲督官兵进剿下历地区,平定赖清规起义。为善后和长治久安考虑,吴百朋提请在当地设县管理而未获通过,但被准许在下历“筑城建馆,移置捕盗通判、主簿,统兵五百名,专一驻扎防守。其下历巡司移于高砂莲塘,亦筑土垣一座,添兵协防,以遏岑冈”[14]。
隆庆二年,张翀继任南赣巡抚,再次强调增设县治在安民、化俗、防乱等方面的作用,并恳请比照崇义设县之先例,于下历地区设置新县,并委派赣州知府黄扆“亲诣龙南下历等处,将各应割地方逐一踏堪”,自己则“不避劳苦,亲入各巢,备将民情土俗一一齐访”[15],这为后来定南县的析置提供了重要依据。最终析龙南之下历、高砂、横江三堡,安远之伯洪、大石、小石三堡,信丰之潭庆半堡,置定南县,隶赣州府。
(三)长宁县
长宁县(今寻乌县)则于万历四年(1576)设立。该地原属安远,与广东平远、龙川、和平等地接壤,处赣粤两省上游地区,多崇山峻岭,此前如邝子安、黎仲瑞、陈良玉、王霁壤、高安、陈士锦等人皆在这一地区发动起义,故早在正德五年时,该县贡生林大纶就曾提请建立州治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因会议迁延,加之叶楷起义的爆发,错失了设县时机。万历四年,都御史江一麟平定叶楷起义,地方士绅再次提请仿照崇义、定南设县之先例,认为:“然特一时之利,未为永久之规。须趁此机会,开设县治,控制要冲,敷声教而化导之。”[16]官方在听取意见后着手析安远黄乡、双桥、南桥、滋溪、石痕、八富、寻邬、大墩、桂岭、腰古、项山、劳田、水源、三标、石溪一十五堡与会昌长河一带,置长宁县,属赣州府。
结合以上内容,从变动原因上看,首先,赣南政区的调整与当地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关。如赣州府“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粤之北陲,故裹耑一路之兵钤,而外提二境之戎柄,其地重大”[17]。但明中期赣南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却阻碍了官方对这一战略要区的控制。赣南山岭纵横的地理环境也常常导致县域的政区中心偏处一地,地方政府对动乱山区的政治控制极为虚弱,故有必要对原有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其次,赣南的政区调整与山区的经济开发有关。自然地理环境是政区发展演进的基础性影响因素,地形、气候、土壤、水源等要素往往影响一地的开发序列和人口、聚落分布,相应的政区也常率先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平原、河谷地区,但随着赣南经济开发向山区纵深推进,自然环境对政区设置的影响也被逐渐削弱。
从变动规律上看,首先,新县皆由多县割置而成。一者,唐宋以来,赣南经济开发速率增快,并进行了多次县级政区增设。前期县级政区数目较少,辖域较广,以单县析出为主,至明中期时,县级政区划分已较为细密,故不易出现单县析出的情况。二者,明中期时赣南山区成为流民聚集地而得到极大开发,但也因此沦为动乱最为频繁的地区。故无论从常规的经济、人口因素出发,还是从应对动乱的角度来看,山区显然更容易出现大的政区变动,而这些山区多处县境边界地区,故新县皆为多县割置而成。其次,新县皆分布于动乱的中心地带,且与社会动乱间表现出了一种前后相继的时序特征,说明社会动乱作为社会环境变化的典型表征,对政区演进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直接的推动都是以特定的事件为契机出现的,但这些孤立事件却都是明中期赣南社会极度失序的一个重要组成和侧面反映,政区调整正是官方为应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政治上做出的改变。而在维护地方的政治安全和有效统治这一需求下,官方会对赣南山区倾注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从而提高当地的开发速率。再次,新县的设立具有相对滞后性。一者,政区沿革本身就具有相对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二者,新县多处政区边界地带,这就意味设县活动必然会受到相邻府、县的官员和百姓的关注,出于乡土观念、风俗习惯、社会治安等因素的考量,相关方往往会对置县问题争论不休。三者,成立新县常常要经历“前期勘察-地方提议-中央决定-具体实施”这样一个繁琐的过程。最后,在传统政治体制运行下,统治者的个人能力和执政理念是影响政区调整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如王守仁、吴百朋、张翀等地方大员皆主张众建县治以杜渐防微,保境安民,从而推动了赣南政区变动。但我们亦不能忽略地方士绅和民众对于新县设立的诉求。张伟然认为,这种地方的“声音”甚至可以直接影响上级决策。[18]结合上文可以看到,明中期以来赣南的政区调整大多是在起义平定后由地方士绅首先提议,再由巡抚上书通过的。
总之,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政区调整极具复杂性和困难性。但赣南作为战略要地,对其政区进行调整以平息动乱,维护统治,是合乎现实需要,势在必行的。
三、赣南政区调整的影响
随着新县设立,官方亦着手强化对动乱地区的控制和管理,从而达到了消弭动乱、稳定秩序的目的,并促进了赣南的社会发展,维护了国家统一。
(一)稳定秩序,推动发展
增建县治的直接目的就是恢复地方秩序,预防动乱,巩固统治。为此,官方首先会在动乱地区建立官署。如长宁县:“赣抚江一麟檄知府叶梦熊、知县沈文渊建今称老县堂。”[19]建立官署后,官方还会选派相应的行政官员对动乱区进行直接治理,但在人事配备上又与安定区有所差别,如王阳明认为新县官员应当熟知捕盗安民之术和地方的民情土俗,从而保障地方事务的有序开展。[20]其次,官方常于新县的交通要冲设立巡检司,受辖于地方州县,统领一定数量弓兵,稽往查来,打击走私,于增强基层社会控制、消弭动乱都有着重要作用。如王阳明曾提出在崇义的长龙、上保、铅厂等要害地方设立巡检司,并对地方巡检司的分布格局进行相应调整。[13]再次,官方还会在新县修筑城池。如定南设县时就曾遣员于高砂莲塘镇筑城凿池,建成之后“城周围三里有奇,凡四百四十丈,崇一丈有三尺,广七尺。为雉堞七百八十,警铺一十有六,城门三,东曰迎阳,西曰平成,南曰丰阜,各覆以楼,北向面山,南以开门。加砌一台,亦覆楼一座,曰北楼。南门城内,旧有民塘,浚而深之为池”[21]。最终形成了一道以城墙为主体,结合护城河、雉堞、城门、警铺、城楼等设施的系统防御工事。此外,官方还会在新县驻扎大量兵力。如设崇义时王阳明曾主张派遣各隘隘夫驻守横水,“其通贼人户,尽数查出,编充隘夫,永远把守;其不系通贼者,量丁多寡,抽选编佥,轮班更替,务足一千余名之数”[6]。总之,这种直接的行政管理,坚固的防御工事,加上强大的兵力部署,可以极大地稳定地方社会的秩序。
随着县治的增设,地方社会的经济也趋于恢复和发展。首先,大量的人口和土地资源得以整合在一起并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以定南县为例,置县初就从龙南、安远、信丰三县划割了大量的田、地、陂、塘,并在后期通过清丈、新垦等方式使得官方掌握的田粮不断增加。户口亦从建县初的“户三百一十户,口共一千八百五十五”,增长至乾隆四十四年时的“户共一万九千四百二十七户,口共一十二万二千四百六十”[22]。其次,有利于赋役的征收。动乱平息后,大批流民也被国家重新纳入户籍管理,他们也需承担起相应的赋役。因此,设立县治后,官方往往会在当地对田赋徭役的征收标准进行重新额定,并在新县推行里甲制度。曹树基认为,里甲制度兼具赋役管理和行政管理的职能,既有利于对封建社会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控制,又是重要的人口组织形式和政府基层组织。[23]故该法成为官方加强动乱地区管理和控制的重要手段,促进了赋役的征收,同时还有着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成为中原王朝在地方行使主权的重要表现。最后,为便于管控地方和政令的上传下达,官方还会在新县大力修建道路,这既打破了当地重岭叠嶂、封闭险远的地理格局,又加快了人员、物资的流动。尤其是随着商品交换活动的兴起,亦促进了乡村集市的发展繁荣。如定南建县之初尚未有墟市,以至于当地的货产只能运至邻县进行贸易,道路险阻,安全难以保障。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于万历十一年“立墟市于城隍庙前,佥立墟长,较定称锤斗斛,厘戥丈尺,物价照时,每月以三、六、九日为期”[24]。
(二)宣扬政教,变风易俗
这一时期,官方着手在政治上加强对新县的管理,一个重要的表现在于将保甲制度推行到了地方治理当中,这极大适应了赣南地区移民运动活跃、社会动乱频繁的特殊环境。如王阳明认为,要想从根源上杜绝动乱的发生,单纯依靠军事镇压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崇义县积极推行保甲性质的“十家牌法”,并遣官前往查审落实。此法以十家为一牌,将各家的丁口、籍贯、年龄、性别、职业详注于牌,定时查验,并行连坐之法,强制民众相互监督,从而区分良莠、防微杜渐。[25]而此牌法推行后,亦能够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极大地强化了中原王朝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黄志繁认为,明中期王阳明在赣南推行的保甲加乡约的治理模式并没有流于形式,而是具有极强的模式WyEb33cMe0SKqqXFGVuGqQgGP0uEvZm31L+8ai3lSgE=效应并为继任者所沿袭。[26]同时,官方还着手在文化上加强对新县民众的教化。史载赣南地区“(百姓)质朴少文,水耕火耨,竭胼胝之力,食土壤之毛,且山深箐密,易于藏奸,民俗劲悍,任气好斗”[27],说明自然环境不仅可以提供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且能够对民众的行为、心理产生影响,而赣南这种民俗劲悍的社会风气亦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的困难。而学校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在培养人才、教化民众方面有着突出效果,从而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如崇义县学为“王都御史守仁命南康县丞舒富创建”[28];定南县学则由“都御史张翀,知府黄扆建”[29]。但县学的设立更多是为了应举和讲学,加之有人数限制,使其成了服务于少数人的精英教育,与多数普通民众的联系并不紧密。为普及教育,适应普通百姓的经济状况,官方又大力在新置县推行社学教育。如定南“建学之初,设社学二处,一在城西,一在下历城内”[30],加之地方官的后期增置、重修和定期巡查,使得社学教育得以推广开来。最终,通过学校教育大大推动了儒学在新县的传播,促进了赣南儒家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构建,在潜移默化中使赣南民风由过去的民俗劲悍、任气好斗转变为了尚学好文、崇文重教,从而达到移风易俗之效。
(三)经略东南,维护统一
大庾岭通道的开凿,意义深远。经济上,大庾岭通道自唐宋以后逐渐成为中原和岭南间的主要沟通通道,并形成了繁荣的过境贸易,官方也得以获得巨额的商税收入,提高了赣南的交通、经济地位。[31]而随着大量物资通过该通道进行流通,东南与岭南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加深了,史载“北货过南者,悉皆金帛轻细之物,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过南者月无百驮,过北者日有数千”[32]。从中可见,岭南、岭北地区在物资产出和供应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一方面导致了南北商队规模和过关次数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说明岭南与岭北间是存在着极强的经济互补性的,而大庾岭通道的存在无疑加强了区域间的经济一体化。政治上,以往大运河的兴修虽然起到了沟通南北的作用,但这种联系更多局限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间,而随着大庾岭通道的开凿,中原与东南的广大腹地山区乃至岭南地区间的交流往来变得更加紧密了,既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保证了中原对东南乃至岭南财富的控制,在经略东南、控扼岭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军事上,顾祖禹认为“岭据南北之咽喉,为战守必争之地”[33]。但明中期以来,赣南大乱,与闽粤湘地区的起义遥相呼应,整个东南腹地的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统治者一方面担心这种动乱影响到南方经济核心区,动摇王朝统治,另一方面,长期的动乱使得南北交通运输线时常被阻断,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削弱了中原王朝在东南直至岭南的政治控制力。故随着社会动乱的渐次戡平,官方着手在赣南地区进行政区调整,结合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其很大程度上是希冀通过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来牢牢控制南北经济线。这使得赣南政区调整的影响力已不单局限于赣南一地,而是事关对南方的政治军事经略、南北商路的通畅、中外贸易的发展、国家统一的维护等方面的内容,牵一发而动全身,意义深远。
总之,设置新县是达到了应有的统治效果的,并使得明后期赣南社会保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稳定。正统至嘉靖年间,赣南的动乱总计51次,之后隆庆1次,万历4次,天启2次,崇祯8次。[5]基本上达到了拨乱反正之效,为中原王朝稳定东南、控制岭南、维护统一提供了保障。
四、结语
赣南地区战略地位极高,但又长期处于中原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治理不易,明中期时,赣南爆发了剧烈的社会动乱,威胁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安全。为此,官方着手在赣南创设新县,专地专管,并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加强了对动乱地区的控制和管理,改善了当地的政治环境,达到了绥靖地方、宣传政教、向化新民等效果。
总的来说,明中期赣南地区的社会动乱与政区调整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过程,反映了当时赣南地域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脉络,呈现出了极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既可以深化我们对明代历史的认识,又可为相关研究提供极好的个案。这一时期,赣南政区变动多发生在原先山高地僻、经济落后、王化未开之地,这种填补空白式的置县模式说明,政区的实际控制是呈现出了一种由核心区向边缘区,由河谷向山区,由虚向实的推进之势,反映了赣南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侧影。同时,赣南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社会动乱也最为剧烈,但正是在这样重要的区位条件下,赣南地区的政区调整及其治理才显得尤为关键。
注释:
①关于明中期的时间界定,学界一般认为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是明中期的开端,将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进行赋税制度改革视为明中期的时间下限。参考南炳文、汤纲《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17-218页。
②赣南地区,按现行行政区划属赣州市统辖,包括章贡、南康、赣县3个市辖区,瑞金、龙南2个县级市,兴国、宁都、石城、安远、寻乌、定南、全南、信丰、于都、会昌、大余、崇义、上犹13个县,在明代时分属于南安府、赣州府。
③关于赣南政区演进研究,可参考肖忠华、刘有鑫《江西古代的政区建置与历史沿革(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42-47页;吴启琳《传承与嬗变:明清赣南地方政治秩序与基层行政之演化》,复旦大学2011年学位论文;张磊《明清江西新设县厅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学位论文;郭茹霞《江西县级政区的地名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21年学位论文。
④有关大庾岭通道的历史沿革及其在中国交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相关研究,参考郑文《梅关古驿道的兴衰》,《江西历史文物》1984年第2期,第69-73页;胡水凤《大庾岭古道在中国交通史上的地位》,《宜春师专学报》1998年第6期,第36-40页。有关大庾岭通道开凿对促进赣南经济发展的研究,参考黄志繁《大庾岭商路·山区市场·边缘市场——清代赣南市场研究》,《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28-32页;廖声丰《清代赣关税收的变化与大庾岭商路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第85-92页。有关大庾岭通道在沟通南北和促进中外贸易发展方面的研究,参考王元林《唐开元后的梅岭道与中外商贸交流》,《暨南学报》2004年第1期,第128-133+142页。
参考文献:
[1](明)王守仁.横水桶冈捷音疏[A]//(清)黄鸣珂修,石景芬纂.南安府志卷24·艺文七(清同治七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2113-2115.
[2](清)顾炎武撰,黄珅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A]//江西备录·赣州府志·解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82.
[3](明)江一麟.平黄乡疏[A]//(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69·艺文志·明文(清同治十二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1258.
[4](清)顾炎武撰,黄珅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A]//江西备录·赣州府志·解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61.
[5]邹春生.文化传播与族群整合:宋明时期赣闽粤边区的儒学实践与客家族群的形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64.
[6](明)王守仁.立崇义县治疏[A]//(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10·别录二·奏疏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90.
[7](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32·经政志·武事(清同治十二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586.
[8](明)王守仁.立崇义县治疏[A]//(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10·别录二·奏疏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88-389.
[9]黄志繁,肖文评,周伟华.明清赣闽粤边界毗邻区生态、族群与“客家文化”:晚清客家族群认同建构的历史背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4-35.
[10]饶伟新.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与闽粤移民的族群背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4):133-139.
[11]周振鹤主编,郭红,靳润成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30-131.
[12](明)王守仁.立崇义县治疏[A]//(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10·别录二·奏疏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90-391.
[13](明)王守仁.立崇义县治疏[A]//(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10·别录二·奏疏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89.
[14](明)张翀.建定南县疏[A]//(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68·艺文志·明文(清同治十二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1249.
[15](明)张翀.建定南县疏[A]//(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68·艺文志·明文(清同治十二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1249-1250.
[16](明)吴百朋.分建长宁县疏[A]//(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67·艺文志·明文(清同治十二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1229.
[17](清)顾炎武撰,黄珅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A]//江西备录·形胜·赣州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23.
[18]张伟然.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运——以“南湾事件”为例[M].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2-193.
[19](清)沈镕经修,刘德姚纂.长宁县志卷1·官署(清光绪二年修七年重订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225.
[20](明)王守仁.再议崇义县治疏[A]//(清)黄鸣珂修,石景芬纂.南安府志卷24·艺文七(清同治七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2143-2144.
[21](清)赖勋修,黄锡光纂.定南厅志卷1·城池志(清道光五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143-144.
[22](清)赖勋修,黄锡光纂.定南厅志卷3·贡赋·户口(清道光五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256-257.
[23]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58.
[24](清)赖勋修,黄锡光纂.定南厅志卷1·城池志·墟市(清道光五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150.
[25](明)王守仁.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A]//(清)黄鸣珂修,石景芬纂.南安府志卷25·艺文八(清同治七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2210-2214.
[26]黄志繁.乡约与保甲:以明代赣南为中心的分析[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2).
[27](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首,序(清同治十二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6.
[28](清)黄鸣珂修,石景芬纂.南安府志卷5·庙学(清同治七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313.
[29](清)赖勋修,黄锡光纂.定南厅志卷2·学校(清道光五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185.
[30](清)赖勋修,黄锡光纂.定南厅志卷2·学校·书院(清道光五年刊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240.
[31]廖声丰.清代赣关税收的变化与大庾岭商路的商品流通[J].历史档案,2001,(4).
[32](明)张弼.张弼均利记[A]//(清)顾炎武撰,黄珅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江西备录·赣州府志·解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64.
[33](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3889.
作者简介:
丁扬,男,江西于都人,中国史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