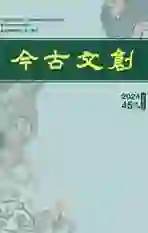牟宗三良知坎陷论的存有指向新探
2024-12-19王月峤
【摘要】坎陷是牟宗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坎陷有两个具体指向:一是“坎陷的外王指向”;二是“坎陷的存有指向”。厘清“坎陷”概念的内涵是理解“良知坎陷”说的关键,但当前学界详细论述外王指向者较多,论述存有指向者较少。为了说明物自身的存有如何开出现象的存有,牟宗三在晚年将坎陷思想用于存有问题,认为道德之心和认知之心都对万事万物的显现和发展有着作用,能够形成各自的存有。至于物自身的存有如何开出现象的存有,牟宗三认为这需要一个下降的过程,而这个下降的过程正是坎陷。本文从坎陷与智的直觉以及物自身的关系入手,论证存有路向上物自身存有开出现象存有的辩证必然性。
【关键词】牟宗三;坎陷;存有;智的直觉;物自身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60-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15
坎陷是牟宗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坎陷”最早出现在《周易·序卦传》:“坎者陷也。”[1]而最早将“坎”解释为“险陷”的是朱熹,他表示“其象为水,阳陷阴中,外虚而中实也”[2]。
坎陷有两个具体指向:一是“坎陷的外王指向”;二是“坎陷的存有指向”[3]。厘清“坎陷”概念的内涵是理解“良知坎陷”说的关键,但当前学界详细论述外王指向者较多,论述存有指向者较少。为了说明物自身的存有如何开出现象的存有,牟宗三在晚年将坎陷思想用于存有问题,认为道德之心和认知之心都对万事万物的显现和发展有着作用,能够形成各自的存有:道德之心形成的存有是物自身的存有,因为它有智的直觉;认知之心形成的存有是现象的存有,因为它没有智的直觉。对于物自身的存有怎样开出现象的存有,牟宗三认为这需要一个下降的过程,而这个下降的过程正是坎陷。
一、良知坎陷与智的直觉
牟宗三对“智的直觉”(intellectual intuition)的诠释主要体现在其哲学体系中,这一概念不仅是其道德哲学的基础,也贯穿了其整个哲学思想。牟宗三在继承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智的直觉”这一概念。他认为,智的直觉是一种先验的、必然的、普遍的具有创造性的存在者,它自己呈现着自己。这一直觉不依赖于人的感性和知性结合,而是主体自己给予自己、直觉自己的创造原则。
牟宗三对“智的直觉”的理解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包括“直觉的解悟” “超理智的认识心” “内容真理之体证”与“本体之智或无限心”四个阶段。这些阶段分别代表了牟宗三在不同思想阶段对“智的直觉”的理解[4]。简单来说,在“直觉的解悟”阶段,牟宗三的思想旨趣在宇宙论的玄思。在“超理智的认识心”的“逻辑的架构”阶段,牟宗三从对逻辑的超越来理解“智的直觉”。在“内容真理之体证”阶段,牟宗三认识到“智的直觉”不只具有形式意义,还具有内容意义。在后期牟宗三建构两层存有论,认为佛老之智的直觉和儒家之智的直觉一样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然而,牟宗三对智的直觉的理解和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有所不同,这在于他在其中加入的道德意义。
“人生而在‘存在’中,在行动中。在‘存在的行动’中,人亦必同时与其周遭的世界相接触,因而亦必有见闻之知。这是一个起码的事实。但人所首先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德行、自己的人品,因为行动更有笼罩性与综纲性。行动包摄知识于其中而为其自身一附属品。他首先意识到他的行动之实用上的得当不得当,马上跟着亦意识到道德上的得当不得当。”[5]21这是说,人在生活之中必定要和周围的世界打交道,所以一定会对周围的世界有所认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身的德行和人品才是首先需要注意的。总的来说,知识和行动只是德性的附属品——牟宗三将此称为德行的优先性。
牟宗三强调道德之心能够创生道德意义上的存有,并且这一过程不依赖于范畴思维,也不受主客体关系的限制。这与康德对于智的直觉和物自身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
牟宗三认为道德之心能够创生道德意义上的存有,这是从道德实践的角度出发的。他强调的是道德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意愿,以及这些动机和意愿如何影响并塑造世界。这种创生并不是在物质层面上的创造,而是在道德和精神层面上的创造。因此,这种被创造的东西不能简单地称为物自体,因为它并不具备物自体那种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性[6]。相比之下,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是指一种能够直接把握事物本质和真理的直观能力,这种直观能力可以独立于感性和理性的范畴之外。而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则是指那些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无法被人类经验所直接把握的客观存在。康德认为,智的直觉虽然可以触及自在之物的某些方面,但无法完全把握其本质。在牟宗三看来,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虽然不需要借用范畴思维,但这种被创造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自在之物。这是因为存有与道德是两个领域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道德之心对外物发生影响,创生的新的存有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物,即染上了道德意义的物而已。这种道德意义的存在是人类主观意识赋予的,而不是客观存在的本质属性。因此,牟宗三所论述的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与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牟宗三强调的是道德实践中的创造性和主观性,而康德则更注重智的直觉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虽然两者都涉及对于存在和认知的探讨,但其出发点和目的却有所不同。在牟宗三的哲学体系中,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更多的是一种道德和精神层面上的创造,而不是在物质层面上的创造。
牟宗三的哲学体系离不开各种概念的价值取向,良知坎陷论也是如此。
在牟宗三的理论中,智的直觉与本心仁体之间的体用关系是一个核心议题。牟宗三认为,本心仁体是道德实践的基础和源泉,而智的直觉则是本心仁体之活动的明觉感通,它体现了本心仁体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作用和功能。
具体来说,智的直觉是本心仁体在活动或实践中的一种直接、无隔阂的感知和认识能力。它不需要借助外在的经验或知识,而是直接洞察和感知事物的本质和真理。这种能力使得本心仁体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和使命,从而指导人们进行道德实践。同时,本心仁体的呈现自我也即是智的直觉之朗照。这意味着当本心仁体在道德实践中得到呈现和体现时,智的直觉也会随之明亮和清晰。因此,在牟宗三的理论中,智的直觉与本心仁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体用关系。智的直觉是本心仁体之活动的明觉感通,而本心仁体之呈现自我也即是智的直觉之朗照。这种关系体现了本心仁体在道德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彰显了智的直觉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价值。通过智的直觉的朗照和指引,本心仁体得以在道德实践中得到充分地体现和发挥,从而推动人们不断地追求道德完善和精神超越。
另外,牟宗三认为,如果智的直觉成为可能,则本心仁体即得以证立。反之,本心仁体的确立即含智的直觉之存在的肯认。道德意识是智的直觉的具体表现,通过道德的进路可以展露本体界的实体。
良知坎陷与智的直觉存在着内在联系。在牟宗三的哲学体系中,良知坎陷是良知在达到高度自觉后所采取的一种主动行为,这一行为体现了良知对于拯救众生的深切关怀和责任感,同时是本心仁体对万事万物的创生,而这个创生的中介就是智的直觉。良知不仅仅满足于个人的道德完善,更有着对于整个社会和宇宙的深切关怀。因此,良知在达到高度自觉后,会主动地进行坎陷,从道德创造和宇宙生化的高度下降到世俗层面,以实践其创生万物、拯救众生的使命。
而智的直觉则是实现良知坎陷这一过程的关键能力。智的直觉使得良知能够直接洞察事物的本质和真理,这种洞察不受感性直观形式和概念的限制,是一种先验的、必然的、普遍的认知能力。通过智的直觉,良知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同时也能够准确地把握世俗层面上的各种问题。
在良知坎陷的过程中,智的直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帮助良知识别出需要拯救的众生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为良知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智的直觉的指引下,良知能够准确地把握时机和力度,以最合适的方式和姿态进行坎陷,实现其创生万物、拯救众生的使命。
因此,良知坎陷与智的直觉是牟宗三哲学中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良知坎陷体现了良知对于创生万物、拯救众生的深切关怀和责任感,而智的直觉则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能力。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牟宗三哲学体系中关于道德实践和认识论的重要内容。
二、良知坎陷与物自身
牟宗三基于智的直觉对康德消极意义的物自身做出了新的诠释,即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认为道德之心有智的直觉,所以可以形成物自身的存有。对于牟宗三来说,其理论是先有智的直觉进而到“物自身”的。牟宗三对智的直觉的论述由他对康德的“自我”的诠释开始。
作为感性纯直观的时间本身是与表象的出现共存的,所以它表现为不同瞬间的继起。离开了对于直观表象之杂多的统一,也就无法构成经验对象。而只有构成一个自身同一物,表象才能被人类所经验,从而成为经验对象。对康德而言,能够给予这种统一性的只有意识[7]。当思维主体(或称为认知主体)觉察到一个形而上的、纯粹本质的自我时,这其实是它意识到了在背后支撑自己的一个真正的“我”——真我。这个真我并非直接内在于思维主体的意识之中,而是作为一个超越性的实体存在。
若将认知主体视为超越的存在,那么这种超越性是局限于认知层面的,即它仅仅是在认知上实现了超越,而非在形而上学或存有论的层面上。这种认知的超越性是横向的,不具备创造性,它基于主客体的对立,并通过设定范畴和对象化的活动来构建知识架构,因此,它限制了人类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然而,真正的超越性是纵向的,它源于真我,具有创造性和无限性。这种超越性超越了认知的局限,揭示了人类真正的无限潜能。从真我的角度来看,认知主体可以被视为真我展现自身的一个曲折过程,即“自我坎陷”。在这个过程中,真我通过扭曲自身形成了一个架构化的认知主体。然而,从真我的纵贯性来看,这个架构化的认知主体也可以被视为真我的一种显现,是一种虚幻的联结,是真我在其通贯呈现或发展过程中展现的一个现象。但这个现象并非通过感官或直觉所能直接感知的,它超越了我们的感知能力。超绝的真我的“现象”取代了认知主体的“我”,表现为超绝真我之“用”,而只有超绝的真我才具有本体性。在牟宗三看来,这一本体正是中国哲学中的心体或性体,于是牟宗三就此将康德与中国哲学联系了起来。简而言之,超绝的真我是根本,智的直觉是工具,“物自身”是智的直觉所揭示出的真理。在这种揭示过程中,智的直觉与“物自身”同时显现,智的直觉对“物自身”的感知正是对物之本性的创造性展现。
在《现象与物自身》中,牟宗三对于“物自身”的表述更加圆融。在这里,“物自身”直接被表述为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牟宗三和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牟宗三将康德的事实概念看作价值概念,认为价值像水银泻地一般润泽万物,而这种润泽正是创生。这不仅是一种以价值为本体的存有论,还是一种非命定主义,牟宗三在《圆善论》中引用“求之在我,求有益于德,而又知其为无穷无尽”,这正体现了以有限创造无限的非命定主义,并且这种依而不即使得道德实践超越了乐观和悲观的对立。康德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中说“意志不外是实践的理性”,实践理性的本质是将主体对象化,而其主体是自由意志,这种主体向对象“输送”的纽带或者桥梁即是智的直觉。
康德认为,智的直觉是上帝所独有的,而在牟宗三看来,超绝的真我具有智的直觉,足以创生万物。牟宗三认为只有当“物自身”被赋予了一种“价值意味”的存在时,它才具有积极的意义,从而使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得以证成。在牟宗三的哲学体系中,“物自身”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更是一个指向事物本质、真实状态的价值指向。
通过赋予“物自身”以价值意味,牟宗三使得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具有了更加深厚的哲学基础。现象作为感知和认识世界的表面层次,常常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而“物自身”则代表了事物背后恒定不变、真实存在的本质和价值。只有当透过现象看到“物自身”,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质和价值。然而这种对事物的“透视”,只是坎陷之存有路向的反向回归。
因此,牟宗三认为,“物自身”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是因为它引导人们超越现象的表面层次,去探索事物背后的真实价值和意义。这种对事物本质和真实价值的追求,不仅有助于人们在认知上更深入地理解世界,也有助于在道德上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行为和选择[7]。
良知坎陷关注的是人的道德境界、认知能力和如何创生万物、拯救众生;而物自身关注的是认识与存在的界限和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在牟宗三哲学体系中,物自身具有积极的意义,能够下降到显现的世界以开出现象,而这个下降的过程就是坎陷,可以说,物自身的存有是坎陷之存有路向的起点。
康德认为,现象的产生是先天形式与后天质料的结合。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只能认识到现象界,而无法直接触及物自身。现象是通过人类的感官和理性能力所呈现出来的,是先天形式(如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与后天质料(即通过感官所接收到的具体信息)的结合。这种结合使人类的经验成为可能,但同时也揭示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
然而,牟宗三对于现象的理解则有所不同。他认为,现象的存有之产生来自物自身的下降。在牟宗三看来,物自身并非完全不可认知,而是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即“坎陷”或“下降”,来显现其存在。在这个过程中,知体明觉如同“水银泻地”一般,将道德的价值赋予万事万物。这种道德价值并非外在强加,而是物自身内在所固有的。因此,当物自身通过坎陷而显现为现象时,它们就具有了道德的属性,成了可以被人们所认知和理解、运用和践行的存在。
在牟宗三的哲学中,物自身在坎陷之前存在于一种不可认知的限制之中。这是因为物自身作为真实存在的本质,其深度和复杂性超出了日常经验的范畴。然而,通过知体明觉的坎陷作用,物自身得以降低其超越性,以现象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这种现象既保留了物自身的真实性和道德价值,又使其能够被所理解和感知、行为和运用。
三、物自身开出现象的辩证必然性
综上所述,物自身的存有开出现象的存有是一个坎陷的过程。道德之心形成无执的存有,即物自身的存有,或者说本体界,因为它拥有智的直觉;认知之心形成执的存有,即现象的存有,或者说现象界,因为它没有智的直觉。如何从无执的存有过渡到执的存有成了一个核心问题,牟宗三的解决办法仍是“坎陷”。
然而这个坎陷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坎陷的存有路向是否具有辩证的必然性?这成了坎陷存有路向的争议问题。
“知体明觉不能永停在明觉之感应中,它必须自觉地自我否定(亦曰自我坎陷),转而为知性;此知性与物为对,始能使物成为对象,从而究知其曲折之相。它必须经由这一步自我坎陷,它始能充分实现其自己,此即所谓辩证的开显。”[5]106前文提到通过事物“透视”到物自身是坎陷存有路向的反向回归,正是因为先有良知自我坎陷的下降过程,才有通过事物透视物自体的认知和观照过程,从而进行道德上的践行。
这个时候,认识心的形成在明觉、良知中停滞了,牟宗三的说法是“停住”了。“所谓‘停住’就是从神感神应中而显停滞相。其神感神应原是无任何相的,故知无知相,意无意相,物无物相。但一停住则显停滞相,故是执也。”[5]107
首先,当良知处于无相的圆融状态时,它涵摄一切,超越了一切分别和相。在这种状态下,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没有任何的界限和分割。这种圆融的状态如同一个完美的珠子在盘子上自由滚动,无论它走到哪里,都能与盘子上的其他部分完美融合,形成一种神感神应的奇妙体验。然而,当良知的知体明觉一旦停滞时,圆融的境界就会破裂。这种停滞并不是指良知本身失去了活力或能力,而是指它在与万事万物的联系中出现了断裂或阻碍。在这种状态下,原本相互贯通的事物开始变得分离和独立,人们开始用一种固定的、刻板的眼光去看待它们,从而产生了执和认知心。
执是指人们对于某种观念或事物的过分执着和固执,认为它是绝对不变和永恒的,牟宗三认为它可以对应为西方哲学中的现象。这种执着往往会导致人们忽视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陷入一种片面和狭隘的认知模式。而认知心则是在执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使人们能够区分和识别不同的事物,但也同时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和想象力。当执和认知心形成后,万事万物就开始以现象的形式显现在人们面前。这些现象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主观感知和理解,它们既包含了事物的本质特征,也融入了人们的个人经验和价值观念。因此,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事物可能会有不同的现象和认知。
“它经由自我坎陷转为知性,它始能解决那属于人的一切特殊问题,而其道德的心愿亦始能畅达无阻。否则,险阻不能克服,其道德心愿即枯萎而退缩。”[5]106可见,坎陷的概念不仅仅是一种简单静态的显现,更是一种深刻动态的输送过程。
坎陷是知体明觉道德价值向下输送的桥梁。在坎陷的过程中,知体明觉如同水银泻地般,将其固有的道德价值赋予万事万物。这使得万物在得到道德价值的润泽后,能够得以呈现和发展,展现出各自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坎陷也是知体明觉保持活力的关键。如果知体明觉始终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那么它可能会逐渐枯萎和退缩,失去其原有的活性和创造力。然而,通过坎陷的过程,知体明觉能够不断地向下输送道德价值,与万事万物保持紧密的联系和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使得知体明觉得以保持活力,还能够不断地吸收新的信息和能量,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自身。坎陷还体现了牟宗三哲学中“良知”与“物自身”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牟宗三看来,良知是超越于物自身的存在,它包含了无限的道德价值和智慧。然而,这种道德价值和智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通过坎陷的过程与物自身相结合,才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因此,坎陷不仅是良知向下输送道德价值的过程,也是良知与物自身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正是物自身的存有开出现象的存有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的体现。
而个别原本为无明的主体通过认知上的观照和道德上的践行,克服原本无明的状态,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从而得以再次自我坎陷以道德之心统摄万物、拯救众生,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个过程起始于个别主体原本的无明状态,通过持续的认知观照和道德践行,逐步克服无明,提升道德境界,最终实现以道德之心统摄万物、拯救众生的目标。
这个过程强调了无明主体通过自我觉醒和认知观照的重要性。在起始阶段,主体可能处于无明状态,对于自身的道德价值和世界的本质缺乏深刻的理解。然而,通过持续的自我观照和认知深化,主体能够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和道德的重要性,开始走上道德自我实现的道路。道德践行是克服无明、提升道德境界的关键环节。主体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德规范,通过具体的行为来体现道德价值,不断积累道德经验和智慧。在这个过程中,主体需要不断反思和审视自己的行为,确保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标准,逐步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
当主体通过认知观照和道德践行克服了无明状态,达到一定的道德境界后,便能够再次进行自我坎陷。这里的“坎陷”并不是指一种消极的沉沦或倒退,而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超越和升华。通过坎陷,主体能够将自身的道德价值和智慧与万物相连通,以道德之心统摄万物、拯救众生。这个过程不仅体现了主体对于道德理想的追求和实现,也展现了主体对于社会和众生的责任和担当。这个过程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体系,随着主体道德境界的不断提升和超越,这个体系也将不断扩展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将不断地观照自身、践行道德、超越自我,以更高的道德境界和更广阔的视野来面对世界和众生。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不仅促进了主体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也为社会和众生的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正是物自身的存有开出现象的存有的辩证性的体现。
四、结语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的哲学理论强调了良知在认知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圆融状态与停滞状态之间的转换。其存有指向强调了道德对万物显现和发生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及高道德境界主体对存有尤其是社会存有的向上回归与正面反馈。这一理论给出了这样的启示:要保持心灵的灵活和开放,避免陷入执着和狭隘的认知模式,以更加全面和深入地理解世界,努力向各个方向探寻道路,以在安顿心灵的同时推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
重要的是,牟宗三在进行康德哲学与儒学的结合时,将道德的建构作为其中的主体一环。比起以形式逻辑理论建构为主的西方哲学,在道德实践中更具经验的是中国的儒学,经过儒学改造的康德哲学与中国本土社会更加契合。牟宗三以道德为基底的存有论对于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人们提供了关于道德行为尤其是对社会回馈的深刻思考,有助于引导人们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并反哺社会。
参考文献:
[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50.
[2]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6.
[3]杨泽波.再议“坎陷”——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一[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1):26-36.
[4]肖雄.牟宗三哲学中“智的直觉”概念的演变[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2):94-101.
[5]牟宗三.现相与物自身[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6]韩朝阳.论牟宗三与康德在“智的直觉”上的分歧[J].今古文创,2023,(15):82-84.
[7]盛珂.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概念的接受与转化[J].中国儒学,2020,(00):189-203.
作者简介:
王月峤,女,汉族,陕西渭南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