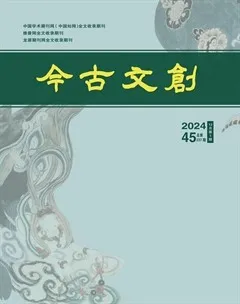李白作品中“摧” 字的妙用
2024-12-19郭树媛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沉淀,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李白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其诗赋具有很大文化价值,杜甫评价李白的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笔者在研究李白作品的过程中,发现其诗赋中频繁使用“摧”字,并且倾向于使用“摧”来表达特定的感情。本文把研究内容锁定在《李太白文集》中涉及“摧”字的诗赋,剖析诗人用字之妙,阐述作者独到的细节处理手法,分析其在运用“摧”字过程中的情感表现。
【关键词】李白作品;“摧”;情感;用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40-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10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LB23-B1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在此背景下,学界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李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大对于李白文化的研究力度,有利于深化对李白作品的认识。通过梳理《李太白文集》中有关“摧”字语句,笔者发现李白作品中对于“摧”字的使用达50多处。“摧”字的频繁使用既体现了诗人巧妙的创作手法,又承载了李白多种思想感情并且与诗文中心主旨息息相关。
一、从文献看“摧”字源流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为“摧”注:“摧,挤也。从手、崔声。一曰挏也,一曰折也。”[2]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读:“《释诂》《毛传》皆曰:摧,至也。即抵之义也。自推至摧六篆同义。昨回切。十五部。挏者,引也。折者,断也。今此义行而上二义废矣。诗。室人交徧摧我。传曰:摧,沮也。此折之义也。”[3]可见,“摧”是一个形声字,左部以“手”表义,下部以“崔”表声。
从字形解读,左部“手”,拳也。象形。在段玉裁本《说文解字注》中解读:“今人舒之为手。卷之为拳。其实一也。故以手与拳二篆互训。象形。象指掌及腕也。书九切。三部。凡手之属皆从手。”[3]因此,从“手”的字多与人的手部动作有关。右部“崔”在《说文解字》中注:“大高也。从山隹声。昨回切文五十三。重四。”[2]在《说文解字注》中解读为:“大高也。齐风。南山崔崔。传曰。崔崔,高大也。此云大高。未知孰是。嵬下曰。山石崔嵬。高而不平也。亦即《毛传》之土山戴石曰崔嵬也。从山。隹声。声字铉无。今补。昨天回切。十五部。按小徐无此篆。大徐此篆在部末。非其次。《玉篇》亦本无崔字。于部末补之。疑许葢本无此。庄子。山林之畏隹。隹即今之崔也。但人部有催,手部有摧,则山部当有崔矣。”[3]可见,“崔”字有高大的含义,可与人部、手部结合形成新字。“摧”,本义是折断,最初见于篆文,隶书与楷书的字形大体与篆书相似。
“摧”字的楷书字形是从秦朝小篆演变而来的,小篆“摧”写作“ ”,象形意味还比较明显,隶书写作“ ”,发展到隶书时期,“摧”字字形已经与现在楷书比较相似,笔画较为圆润。发展到现在就是常见的“摧”字字形,笔画较隶书时期更具有符号化、线条化的特征。
从字音解读,据《广韵》,“摧”,折也,阻也,昨回切,五。[4]与《说文解字》和《说文解字注》中的记音一致,可见三家都主张以声旁“崔”字发音。因此,以《说文解字》来判定“摧”字读音较为准确,并且可以通过声旁来辨义。
从字义解读,“摧”字是形声字,从形旁,可以看出其是与手部动作有关的。《说文解字》中说:“摧,挤也。从手、崔声。一曰挏也,一曰折也。”[2]可见,“摧”与“挤”同义,一是摇晃,一是折断的意思。“摧”本义为折断,后来引申出摧折(折断毁坏)、摧毁、破坏、毁坏。也就是说 “摧”表示一种施加的力,指用力使物体迫近,如推挤、挤压、牵引等。无论是推挤还是牵引,都是某物体对另外一个物体的动作,以此来达到使物理距离变化(方向不定)的目的。而在此过程中,施加力气过猛的话,则会造成物体折断、毁坏等。如:“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1]。
上述“摧”作用的对象仅指物体,但随着语言变化,“摧”也可作用于有生命的对象。如果“摧”作用的对象是人,则它的字义就会发生变化,即由“物理距离的变化”向“心理悲伤情感”转变,故“摧”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了悲痛、哀伤的含义,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1]。在此,“摧”关涉的对象又可以细分,可以是面部各部位,如“摧眉”,使眉毛受到压力,表示忧伤,例如“素颈未及断,摧眉伏泥沙”(李白《秦女休行》)[1]。还可以是人的内脏,如心、肝、肺等,使内脏都受到压力,所施加的力投射到人体内部,以此来形容悲伤至极,这也是古今以来比较常见的表现方式,例如“酷矣痛深,剖髓摧肝”(孙绰《表哀诗》)。
综上,在对“摧”字的字音、字形、字义整理之后,发现“摧”所关涉的对象大体可以从物理层面和人两方面来划分,人这一方面又可以分为面部各部位和内脏。根据关涉部位的不同,所表达的情感也有差异。而通过“摧”关涉对象不同来表达不一样情感的现象,在李白作品中也广泛存在。
二、李白诗赋“摧”字语句分类解读
李白在其作品中善用“摧”字,并且倾向于使用“摧”来表达不同程度的感情。笔者着重研究《李太白文集》中涉及“摧”字的诗赋,将其依据上文中所描述的“摧”关涉对象的三个层面进行分类,解析诗人用字之妙,阐明作者独到的细节处理手法,并分析其在运用“摧”字过程中表现的感情。
根据《李太白文集》有关“摧”字语句整理现状来看,李白作品中对于“摧”字的使用达50多处,对“摧”字进行研究可以反映作者用字精妙之处以及情感表达的巧妙手法。梳理《李太白文集》中含“摧”字的相关语句,依据上述“摧”关涉对象的三个层面,并按照语句中折射出的与人体的距离,可以进一步将这些语句分为三类——体内、体表、体外。
(一)体内
体内这一分类中的诗句指的是李白在作品中使用“摧”字时,将其与人体内脏、内在相关的词语相结合所作的诗句。具体例子如下:
(1)长相思,摧心肝。(《长相思》)
(2)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古风·其三十四》)
(3)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古朗月行》)
(4)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丁督护歌》)
(5)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赠别郑判官》)
(6)但恐荷花晚,令人意已摧。(《寄远十二首·其四》)
这一分类下,作品的中“摧”主要是跟“心”“肝”相结合,来表达作者悲痛的心情,悲伤至极好像是内脏在痛,五内俱摧。这种写作手法使得读者对作者所表达的情感更能感同身受,且该分类表达的情感更侧重于作者自身感受,所表达出情感的悲伤程度较重。
(二)体表
体表这一分类主要包含“摧”与人面部词语相结合的诗句,具体诗句如下:
(1)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天马歌》)
(2)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摧。(《北风行》)
(3)素颈未及断,摧眉伏泥沙。(《秦女休行》)
(4)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在李白作品中,该分类中“摧”仅与人的面部部位“眉”相结合,“摧眉”在其作品中一是表达作者忧伤的心情;二是写自己不能低头弯腰谄媚权贵,有自己的风骨。在这里,“摧”关涉的部位只有面部,与“催心”相较程度更轻,仅是使眉毛皱起。
(三)体外
体外这一分类主要包括作品中“摧”与人体外部事物相关的字词相结合的诗句,具体如下:
(1)叶光摧阴,坤斗主土,据乎其心。(《明堂赋·并序》)
(2)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蜀道难》)
(3)飞文何洒落,万象为之摧。(《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
(4)田氏仓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上留田行》)
(5)拜龙颜,献圣寿,北斗戾,南山摧。(《上云乐》)
(6)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胡无人》)
体外这一分类在李白作品中出现次数最多,所占频率最高。这里“摧”关涉的对象与自身无关,主要是自然界或者其他的人,如例子中提到的“摧阴”“山摧”“敌可摧”。该分类并不直接表达作者内心感情,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通过隐喻等手法来表达作者内心的悲怆、哀伤、感
叹等。
三、凭“摧”字看李白诗赋修辞
修辞是写作诗歌的表现手法,也是诗人在写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手段。李白作品受到人们的推崇与喜爱的原因与其诗歌中的修辞艺术密切相关。李白诗歌中涵盖的修辞多样,常用的有:拟人、比喻、对比、顶真、夸张、衬托等。本文重点分析李白运用“摧”字过程中所体现的夸张、隐喻、用典等修辞,来感受“诗仙”李白巧妙的艺术表现手法。
(一)夸张
一直以来,李白诗歌中的夸张手法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也是世人如此推崇李白诗歌的重要原因。其神奇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随着诗人的思绪而变、而动,呈现出一幅幅奇特的画卷,成就了一首首令人赞叹的诗文。李白在使用“摧”写诗的过程中,多数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且善于用夸张的手法表达相应的感情。如大家熟知的《蜀道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1]这句诗中的“崩”“摧”“死”的程度义较深,诗人在这里以夸张的修辞手法极言蜀道险要的特征,赋予诗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又如《大猎赋》中所写的:“使五丁摧峰,一夫拔木。下整高颓,深平险谷。摆椿栝,开林丛。喤喤呷呷,尽奔突于场中。而田强古冶之畴,乌获中黄之党,越峥嵘,猎莽仓。”[1]这里“使五丁摧峰”里的“五丁”在《华阳国志》中有记载:“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1]“一夫拔木”中的“一夫”在《楚辞·招魂》中有记载:“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王逸注:“言丈夫一身九头,强梁多力,从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枝也。”故“使五丁摧峰,一夫拔木”中 “摧”与“峰”结合,夸张描写五丁力士能够摧倾山峰,其力气之大,令人叹为观止。诗人巧妙地将“摧”“五丁”“峰”结合起来,运用夸张的手法,抒发自己的内心感情与政治抱负。
(二)隐喻
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曾这样定义比喻: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方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16]而比喻又可分为明喻、隐喻、借喻等,在本文中主要研究李白诗歌中带“摧”字语句的隐喻修辞手法。诗歌语言符号之间的隐喻表现是创作主体通过联想,依据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把不同事物间的情感、精神等化为可以言说的形象。“隐喻本质上讲是联想的,它探讨语言的垂直关系,而转喻从本质上是横向组合,它探讨语言的平面关系。”[5] 也就是说,在诗歌语言里,隐喻是发生在作者对不同事物之间相似性联想的基础之上的。李白的诗歌《上留田行》:“田氏仓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1]诗人在此诗中引用了前代典故“三家分荆”。南朝梁·吴均所写的《续齐谐记》中记载了三家分荆的故事:“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议分财。生资皆平均,唯堂前一株紫荆树,共议欲破三片。翌日就截之,其树即枯死,状如火然。真往见之,大惊,谓诸弟曰:‘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胜,不复解树。树应声荣茂,兄弟相感,合财宝,遂为孝门。”[20]在《上留田行》中诗人写骨肉分离之后,紫荆花饱受摧残。诗人以“摧”修饰“紫荆”,写紫荆花被摧残,表面上是对事物现状以及事件的描写,但实际上,被摧残的不是紫荆花,而是诗人自己的内心。诗人的这份感情是隐在的,在短短几句诗赋的描绘中,含纳了心中无限的酸楚与悲痛。
(三)用典
用典意为用事,表现为引用古籍中的故事或词句,其可以含蓄表达相关内容和思想,多见于诗歌中。诗人在其诗赋创作中,大量地运用用典的手法来写自身感情,这也是其诗歌创作的特色所在。在李白作品含“摧”的诗句中,有不少是用用典的修辞手法来表达相关思想感情的,如《上崔相百忧章》:“共工赫怒,天维中摧。”[1]诗人当时因皇室之乱被下狱,此诗一是写当时安史之乱给社稷造成的危害;二是写自己蒙冤入狱。诗人作此诗给当朝宰相崔涣,希望他理解自己,为自己免罪。又如《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1]此诗是李白的绝笔之作,诗人在诗歌前半部分引用大鹏飞天的典故,写大鹏飞至中天摧折气力不济。以大鹏自比,感叹自己一生壮志未酬,抒发自己才能无法施展的惋惜之情。可见,李白善于引用历史上品格高洁的人或事来写诗,在赞扬其人其事的同时,抒发自己的感受。
(四)其他写作手法
李白所作诗赋构思巧妙,除前文所提到的夸张、隐喻、用典修辞手法,李白在其诗歌中还运用其他的修辞手法来进行创作。如运用白描的修辞手法,在《北风行》中写道:“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摧。”[1]生动妙写思妇思念丈夫的情景,使人身临其境。又如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在《胡无人》中写道:“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1]此诗描写汉家将士与胡人军队在战场中遭遇,双方排兵布阵,将士出击进攻,场面激烈。李白在这首诗歌中巧妙地反复使用“敌可摧”,深刻表达了诗人自身希望汉军大败胡兵,彻底消灭胡人的强烈愿望。李白作为名垂千古的诗人,其作品中所用的修辞手法是其思想感情的重要流露途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其作品中的修辞表现手法,来一窥诗人的感情倾向。
四、李白诗赋“摧”字情感表达之妙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图”,这些都说明诗总是情感的产物。[14]同样具有真情实感,不同的诗人抒发感情方式往往各异,如柳永的哀婉凄切,李商隐的情至深韵,李清照的哀婉缠绵。情感的抒发是受诗人的心绪、处境等因素影响的,各人有各人的经历,抒发感情的方式也就多样了。李白作为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歌的情感特征以及抒发感情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诗人所作的诗歌是随经历变换而变化的,诗歌表达意义、情感与作者身处人生阶段有很大关联。李白的人生大致经历了初入长安,入京供奉翰林,入幕、系狱与流放三个阶段。本文研究李白诗赋中含“摧”字语句并结合诗人所处人生阶段,分析了诗人在运用“摧”字写诗时体现出的感时伤世、豪情壮志、愁苦激愤以及离别思念等情感。
(一)感时伤世之情
李白作为一位爱国人士看到满目疮痍的国家,非常痛心,加之仕途不顺,得不到赏识,感时伤世之情愈烈。安史之乱使李白晚期的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给李白诗歌增添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晚期的创作趋于现实主义,诗风由飘逸豪放转向沉静明净。[7]思想内容上,感情更趋深沉,山水诗描摹逼真,情景交融,清新明净,纵酒诗中交织着个人不幸和志欲救国却无出路的民族忧愤,隐居求仙的意念削弱。[13]如诗歌《登高丘而望远》中写道:“扶桑半摧折,白日沈光彩。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1]诗人登高山、望远海,没有写大浪排空,而是写神仙故事的虚妄,以“摧”字写扶桑树的状态,表明诗人内心的失望。后面写到秦皇汉武为求长生穷兵黩武却沦为虚空,这是对此类皇帝的讽刺和批判,也是对当朝皇帝的暗示,表达了诗人内心感时伤世的情感。
(二)豪情壮志之情
天宝元年秋,李白骤得帝王垂顾,供奉翰林,但是这样的时光仅持续一年半,之后被君王赐金放还。李白在得帝王垂顾前几年时,创作诗赋以期谋求官位,此时,这些诗赋中饱含诗人的雄心壮志。在这阶段,李白通过“摧”字来抒发了他的豪情壮志,如《大猎赋》中所写的:“使五丁摧峰,一夫拔木。下整高颓,深平险谷。摆椿栝,开林丛。喤喤呷呷,尽奔突于场中。而田强古冶之畴,乌获中黄之党,越峥嵘,猎莽仓。”[1]这几句表现了诗人心中豪情,可使五丁力士摧峰,一夫九首拔木,可见诗人内心青云之志。又如《胡无人》中:“云龙凤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1]这里写敌军可被摧毁,战争可以胜利,诗人将战争场面描述得豪迈激越,表达了对战争胜利的信心以及对消灭胡军的强烈愿望。
(三)愁苦激愤之情
李白一生身世浮沉,出入长安是满心抱负,但怀才不遇。入翰林没多久便遭馋失宠、仕隐冲突。在五十七岁时李白因入永王幕,导致系狱流放,这段人生更是使李白身心都遭遇重创。能体现诗人愁苦激愤心情的诗歌,大多是在这几个时期创作的。如《长相思》“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1]这首诗通过描写景物表达离人的相思之苦,相思的悲痛就好似心肝被摧残。《长相思》的创作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李白被“赐金还山”之后,大约是他被排挤离开长安后于沉思中回忆过往情绪之作。但是李白极富抱负,被打击之后,写出了这首诗,诗句表面上是写离人对妻子思念之情,但实际上表达了诗人内心愁苦郁闷之情。又如《古朗月行》中:“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1]这句是说,因为月亮为蟾蜍所蚀,才晦暗不明,沉沦迷乱,既已沉沦迷乱,自然也就没什么好看的了。表现了诗人感情上的变化,就像潮水一般,一浪高于一浪,又像群山相叠一样,一山高于一山。望月不成功,只有离去。这里表现了诗人被一种失望和无可奈何的心情占满,更感现实的困难难以战胜,自己内心的希冀无法实现,唯有无限怅惘。从诗人的遭际来看,有不少经历正是如此。结尾两句诗,直接地抒写个人的痛苦、忧愤:“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凄怆”指凄凉悲切,“摧心肝”指心肝迸裂,在这里形容作者内心忧愤达到了极点。
(四)离别思念之情
在人生各个阶段各个时期,李白都面临着离别,离别之情在其诗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塞下曲·其四》:“萤飞秋窗满,月度霜闺迟。摧残梧桐叶,萧飒沙棠枝。”[1] 秋天的时候,萤火虫在纱窗前飞来飞去,月光照耀着闺房,久久不肯离去。梧桐叶在秋天里凋零,空荡荡的沙棠枝更添几分凄凉。诗句“摧残梧桐叶,萧飒沙棠枝”,诗人在这里写的是梧桐叶被风摧残,实际以梧桐叶代指自己的内心,摧残的即是自己的心。这首诗表面写的是妇人对丈夫的思念,实际上是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思念之情。又如《秋思》:“燕支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沙塞合,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蕙草摧。”[1]燕支山上的树木已经干枯黄落,一位女子独自登台远眺,看到天空中青云散尽,单于带着秋色降临。胡人的军队在沙漠边境集结,汉使返回玉门关。在异乡的客人尚未归来,只能为蕙草的凋零感到悲伤。这首诗同前面一样,表面写女子因为萱草被摧折感到悲伤,实际是写女子对于丈夫的思念;表面写女子对丈夫的思念,实际表达了诗人心中的思念之情。
五、总结
本文创新地研究了“摧”在李白作品中的妙用,分析了“摧”字源流,并通过该字考察了作者内心情感以及写作手法。“摧”字频繁出现在李白诗歌中并不是偶然,李白在运用“摧”字作诗过程中巧妙运用了夸张、隐喻、用典等修辞手法,体现了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且“摧”字贯穿于李白所处的各个人生阶段,帮助抒发了诗人内心感时伤世、豪情壮志、愁苦激愤以及离别思念等情感。探析李白作品中“摧”字妙用,既是对经典诗词的深入赏析,也是对李白自身独特的理解,有利于感受诗人自身具有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洒脱飘逸的思想,使后人得以一窥李白的浪漫主义情怀。
参考文献:
[1](唐)李白撰.李太白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周祖谟.《广韵》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6]王腾飞.李白诗歌用典研究[D].暨南大学,2010.
[7]李芸华.李白的人生转捩与文学[D].厦门大学,2020.
[8]胡悠.李白涉胡诗歌研究[D].宁波大学,2021.
[9]李博阳.唐朝河北道与李白的诗[D].北京外国语大学,2022.
[10]陈凯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文本解读与教学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21.
[11]唐宇辰.李白诗歌琴意象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21.
[12]王运熙.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J].文学遗产,1997,(01):48-59.
[13]杨义.李白诗歌用典的诗学谋略[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05):9-14.
[14]王玉璋.论李白晚期诗风的转变[J].青海社会科学,1982,(03):74-80.
[15]何念农,刘正国.真率明朗 酣畅淋漓——李白诗歌的情感显示特征[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7,(05):1-8.
[16]唐新赋.谈谈李白诗歌中夸张、比喻、拟人手法的运用[J].青年文学家,2009,(24).
[17]王敏.论李白诗歌的修辞艺术[J].吉林教育,2016,(33):2-3.
[18]钱志熙.论李白乐府诗的创作思想、体制与方法[J].文学遗产,2012,(03).
[19]杨景龙.李白对唐代之前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继承与超越[J].河北学刊,2022,42(06).
[20]王素美.李白诗“人”意象的文化内涵与天人合一的境界[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8(01).
[21]吴浩军.敦煌写本《报恩吉祥之窟记》校理[J].河西学院学报,2016,32(03):4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