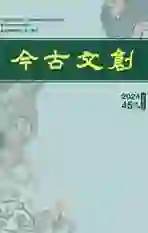后人类视阈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的身份建构与伦理问题探析
2024-12-19李心如
【摘要】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描绘了在核战争爆发后的地球上,仿生人逃脱反抗、赏金猎人捕杀镇压的后人类图景。本文首先简单概括学界现有的后人类思想的不同研究态度,之后结合文本阐析《仿生人》中人类在后人类时代的身份建构困境以及仿生人试图建立主体身份的失败尝试,最终以后人类学家布拉伊多蒂有关后人类主体建构的理论想法为基础,对《仿生人》设定的后人类图景下有关人机关系和人类内部的分化排斥等伦理相关问题进行考察。
【关键词】菲利普·迪克;后人类;身份;人机关系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28-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07
一、后人类时代的来临
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技术等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已然处于从人类纪向后人类时代过渡转化的进程当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创生手段等多方面的突变,并难以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的技术恐慌,也就带来了关乎人类主体性的哲学思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一波后人类主义浪潮。
学界发展至今的后人类思想,根据研究态度可大概分为三个派别:一是由道德哲学发展而来的后人类主义消极形式,以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为其代表人物,主张全面维护人文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人文主义危机的观点,尽管承认当前技术驱动的爆炸式全球经济为人类带来的挑战,但她试图在传统人文主义理念中,重新思考人的本质,以寻找出路。二是由科学与技术研究发展而来的后人类思想的分析形式,以代表人物彼得·保罗·维尔贝克(Peter-Paul Verbeek)为例,他的主要观点是,技术积极促进了人类实现伦理的方式,强调技术工具作为主体的道德性,认为它们能在规范性问题上引导人类决策。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对该分析类型的后人类思想的评价是:“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分析型后人文主义是当代后人类图景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但是这个立场却很离谱,因为它引入选好的人文主义价值片段的时候并没有处理这一嫁接行动引发的各种矛盾。” ①布拉伊多蒂本人所主张的,则是第三类的批判型后人文主义,立足于对古典自由人文主义的解构和对人类中心论的质询,试图超越分析型后人类思想,提出关于后人类主体建构的肯定性观点。
关于后人类主体的构建,有许多尚存问题值得商榷,不仅仅包括以普遍生命力为基础的人与动、植物以及生存媒介地球之间的新型关系的建构,更加严峻的难题存在于现有的人类主体和技术性他者之间,随着生物基因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的身体可以与机械结合的部分越来越多,技术正逐渐介入人类生命样态,人与机器的身体界限正逐渐趋于模糊。同时,机器的智能化程度的提高,使它们得以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进行任务的执行,但自动化这一智能机器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着它们未来必然会获取一定的决策权力,从而获取部分主体地位,那么机器人能否获取主体地位,新的人机关系将走向何处,或言之,后人类主体是否应当包含技术性他者,是一个尚争论不休的问题。
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菲利普·迪克(Philip K·Dick),
在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中,假设了仿生人这种拟真性机器人获得自主意识,与人类的关系发生改变之后发生的故事。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核战争爆发之后的地球,人类分为正常人与受到核辐射伤害的特障人,人类被建议移民火星,移民者都会被配备一名仿生人作为“为其个人特有的需要而定制的人形机器” ②仆人作为奖励。小说描述了八位仿生人自主意识觉醒之后,希望获得自由,能过上人类一般的生活,杀死了自己的主人逃离了火星,以猎杀越界的仿生人为生的赏金猎人里克·德卡德(Rick Deckard),在执行此次猎杀其中六个仿生人的任务过程中,内心发生的对仿生人的情感认识与道德感知的微妙变化。本文将对《仿生人》中的人类的后人类身份建构困境、仿生人的主体身份建构尝试进行解读,并由此进行后人类视阈下的伦理问题反思。
ZWPi7y+6hCEz/kYWpk/y73pfqqZ7Gwks4il4HAO2d1U=二、人类的后人类身份建构困境
《仿生人》中人类身份建构的一大困境是,技术对人体的介入以及仿生人的“类人性”的侵入性影响,使得人在后人类时代“何以为人”成为一个费解的难题。
一方面,人的物质性生存媒介——身体,在后人类未来经受着多重挑战。因而对于具身变化的关注,是迪克对于后人类身份探讨的一个重要层面。
首先,人类的身体受到技术的介入改造,通常是用以进行医疗,例如,小说中的警官戴夫·霍尔登在一次与新型仿生人的接触中,被激光枪打穿了脊柱,于是装配上了有机塑料脊骨,这种人造材料代替人类身体器官的操作,暂且可以被算作是一种新型技术带来的医疗手段。然而,假设人体越来越多的器官被人造材料和机械所替代,那么该如何界定这个被技术不断替换原件的个体,还是否为人呢?是以身体的碳元素和硅元素的多少来进行判断,还是由新的伦理规范来界定的呢?虽然在小说中,这种由技术介入身体带来的人类身份定义难题并没有过多的描述和体现,但这作为在现实中,已经无限趋近于人类生活的技术介入身体的情况,人类身份建构的问题理应进行重新思考。
其次,小说中核战争爆发后的地球,到处弥漫着放射性的微尘,因故土情结而不愿移民离开地球的人类,多少都经受着不同程度的身体损伤,当这种放射性损伤到达一定程度时,经过检测,不合格的人类将会被打上“特障人”的标签,“公民一旦被打上特障的印记,就算主动接受绝育,也会在历史中消失。” ③《仿生人》中的人类,仍然将自然的人类身体,看作是定义人类身份的一大必要条件,可能对于人类原始基因造成危险的特障人群体,被作为异己,排除在有繁衍和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权力范围之外,不仅如此,他们还会被冠以“鸡头”等极具侮辱性的称号,为人们所嫌弃,彻底丧失人权。人类在小说中的后人类时代,凭借身体是否符合人类的原始基因的条件,主观地将人划分出阶级,并将弱势人类群体排除“人”的范畴之外,这与他们所声称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移情能力恰恰相悖,这种矛盾,也就造成了人类在后人类时代身份认知和建构的一大困境。
同时,仿生人这类拟真性人形机器的更新迭代,使得他们在外表上与人几乎毫无二致,他们的外形不再是电路遍布和钢筋铁骨的原始机器形态,而是与人类一样的血肉之躯,人类的身体变成可被模仿和复制的存在,那么人的身体更加失去了界定人类身份的资格。人类的情绪、欲望的呈现,需要具身化的物质媒介来承载,那么无限趋近于人类身体的仿生人形机器,不仅仅消磨了人类肉体的特殊性,而且给予了仿生人得以模仿人类进行情感传达和意识流露的物质性媒介,进而模糊了人与仿生人之间的界线。人类自诩为造物主,将服务性的人形机器按照自己的模样进行打磨和建造,每一代的更迭,都使仿生人在外形上与人类更加接近一点,这种技术发展倾向,体现了一种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这种自大的人类特殊论,讽刺性地为人类带来身份建构的新的困境。
另一方面,自由人本主义的某些特质,例如自主性、情感、意识等,在后人类语境下被继续讨论。小说中,在战争冲击、生存环境影响与技术介入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人类的情感与意识的异化,构成后人类图景下人类身份建构的又一重困境。
小说中的核战争后的人类,集体陷入情感缺失的困境之中。例如主人公德卡德和他的妻子,丧失情绪与爱欲,两个人毫无爱与肉体的渴望,也失去了自由控制情绪的欲望和能力,与其他人类一样,靠一个叫作“情绪调节器”的仪器,保持人类该有的情感与心情,只需一个按钮拨号的动作便可以获取自己想要寻求的某种情绪。然而这种通过拨号获得的,并非是人类自由意志带来的细腻微妙的情绪,而是被技术介入后,变得僵化了的、流水线化的非自然情绪,无论这些心情的划分有多么细致和全面,它都无法弥合人类完整的情感空缺,并且,当人类对于这种拨号即可获得情绪的行为,产生依赖性心理之后,原本有能力自主获取的原始情绪,也将逐渐被淡忘,人类的情绪将完全由技术进行调节和掌控。人引以为傲的人性与感情,逐渐淡去,人与仿生人型机器之间的区分界限更为模糊,这形成后人类时代人类身份建构的又一大矛盾。
尽管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类已经基本丧失了情感能力,然而受着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移情能力这一人性光辉的集合,依旧成了后人类时代人类“之所以为人”的仰仗。罗森公司生产的“枢纽六型”仿生人,从思维能力和外形身体与人毫无二致,甚至被注入了一定的记忆,使得他们与人类更加趋近,因此在赏金猎人执行处决任务之前,要为仿生人做一份“沃伊特移情测试”,来将人与仿生人区分开。这份测试主要辨别测试者是否对于动物受伤害的情景进行识别并表示同情的情况得以实施,他们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移情的能力,而动物是人们移情的一个重要对象。迪克笔下的这些人类,对于动物有着近乎狂热的情感依赖,不仅强调对动物的同情能力,并且把拥有一只真的活体动物作为宠物,看作是对自身作为人类的移情能力和道德感的最高体现。小说中的人对于动物有着如此深的情感寄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核战争导致了动物种族的逐渐灭亡,人类作为这次物种消亡的始作俑者和最终幸存者,对这些与他们共生于一个地质生存媒介——地球的动物伙伴,怀有一定的愧疚之意,这份愧疚,便通过对于仅存的动物表现出过剩的情感进行弥合;其次,人类在越来越受技术介入和操纵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一份焦虑和恐慌,随之对于这些与人类自身共享一份原始的“普遍生命力”的自然生命物种,产生了亲切感和依赖感,同时,这份对于自然生命的珍视,又何尝不是人类面对技术控制危机时的一种心理防御和抵抗手段呢?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资本的介入,无休止的广告,将自然动物作为商品,向仅余脆弱自由意志的人类疯狂推销,人们对于动物的渴望,也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这种微弱的人类意志对消费主义的妥协。
人类的另外一个移情能力的寄托,是默瑟这一宗教形象,默瑟主义的出现弥合了核战争后人类的情感空缺,默瑟的教义最重要的主张是平等,普遍性的平等,这与罗西·布拉伊多蒂所主张的后人类主体建构中的“普遍生命力”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默瑟主义的普遍与平等更趋于极端化,它不仅提倡一切自然生命的平等,甚至将平等推及到了技术性他者的身上。人们与默瑟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双手握上“共鸣箱”,便可以与被石头砸但仍在苦难中攀登的默瑟共情,默瑟教的出现,弥补了人类战后的精神空缺,也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默瑟主义能降低犯罪率,因为公民会对旁人的苦难更加感同身受。” ④默瑟教的兴盛,从侧面体现了核战争后的人类对于移情能力的看重。
然而非常讽刺的是,尽管这些人类如此强调移情,如此推崇默瑟主义,对活的动物有着如此强烈的情感,但他们对于人类中的弱势群体“特障人”却满是恶意,将他们排除在人类的范畴之外,在社会上也不允许特障群体承担重要的工作。这样一种移情重视的态度和部分孤立的行径之间的矛盾,恰恰也反映了一定的虚伪的普世主义。同时,在迪克的小说中,对于特障人的边缘处境,体现很明显又很讽刺的一处是,当三个逃亡的仿生人遇到特障人伊西多尔时,在得知其特障身份后态度急转而下,变得十分傲慢。连不具有先天主体地位的仿生人都认为特障人理应被轻视,这不仅仅来源于芯片植入时的意识注入,更来源于日常生活交往中,仿生人对正常人对于特障人的轻蔑态度的模仿与学习。可见小说中处于后人类时代的人类移情愿景与真实移情能力之间有着严重的空缺与矛盾,只能通过动物商品和默瑟宗教等外在方式进行弥补,这表明在意识与情感层面,人类也存在着身份建构的严重困难。
三、仿生人的主体身份建构尝试
小说中的德卡德追捕的六位仿生人,便是仿生人自由意志膨胀、试图获取主体地位的群体发展趋向的缩影。下文选取鲁芭·勒夫特、蕾切尔·罗森和罗伊·贝蒂三名仿生人为例,阐述仿生人试图建构主体身份的不同方式。
首先,鲁芭·勒夫特,是一个有着极其动听的声音的女仿生人,在逃回地球后,在一家歌剧院工作,在空余时间会接触美术等艺术形式,可以见得她对人类艺术的热爱。而艺术与文化,从来都是人类的感性、情绪、精神的结晶。勒夫特通过对人类的艺术文化的深入接触,对人性进行琢磨和学习,以期变成真假难辨的“人类”,获得真正人类才能拥有的自由与权利。勒夫特对于人类的人权、感性、精神世界有着倾慕与向往,因此她代表了一类试图通过对人类进行深层次的模仿与学习,以无限趋近于人类的方式,去获得人类的身份,从而获得后人类主体地位。
蕾切尔·罗森是小说中着笔最多也相对复杂的一个仿生人角色。她最初因被植入的记忆使然,并不知道自己是一名仿生人,直到德卡德给她做了移情测试,而她没有通过测试之前,一直自我认同为真正的人类。因此,蕾切尔的自我身份认知经历了由人类变成仿生人的身份转换过程,因此她身上实际上具有人类与仿生人的双重特质,在人与人形机械中间,扮演一个微妙的调解角色。她试图通过“美人计”使得赏金猎人德卡德爱上自己,从而改变对于仿生人群体的感情,使他因爱而失去杀戮仿生人的欲望和勇气。尽管她的计划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蕾切尔试图用自己习得的人类的爱与嫉妒等复杂情感,感化人类,调解人与仿生人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而建构仿生人的后人类主体身份。
罗伊·贝蒂有一种“争强好胜、独断专行的人造权威气质”,在逃亡的几个仿生人中扮演首领的角色,他最初试图模仿人类的默瑟主义,用化学药剂代替共鸣箱,给无法参与移情和共鸣的仿生人群体,找到一条专属的共鸣之路,然而最终以失败告终。模仿人类的方式无法实现目的,罗伊便以更为极端的方式对待人机关系,期望采取暴力手段和正面冲突的方式,直击人类的绝对领导,将仿生人从被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对人类取而代之,成为人类的替代物种,期待作为后人类时代的主体中心,对待人类的态度会更加敌对和极端一些,对于帮助保护他们的特障人伊西多尔甚至也动了杀心。罗伊的做法,可以看作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人类中心主义两大因素共同造就的主奴二元对立情境下,机器所会采取的最极端的反抗手段,也正是后人类时代造成技术恐慌的一种人机关系演变的假设形式。面对后人类时代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因素,人类应该仔细审视对待技术性他者的方式与态度,对于人机关系的建构和维护也需要更加谨慎。
四、后人类视阈下的伦理反思
菲利普·迪克所塑造的核战爆发后的人类与仿生人形象,启发我们在生物基因和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重新审视后人类主体的界定。下文以《仿生人》中的设定为基础,对生命伦理进行后人类关照。
首先,菲利普·迪克笔下后人类时代的人机关系,一方面,将“类人性”作为人形机器改良的主要指标,追求仿生人与真实人类从肉体到思维能力上的无限趋近,另一方面期待形成仿生人完全服从于人类的关系。正如布拉伊多蒂所言,智能化机器必将有一日被赋予决策的权力,从而获得部分主体地位。很显然,迪克笔下的仿生人便已经发展为了具有独立意志和决策能力的自动化智能机器,然而人类却没有赋予其相对应的主体地位,仿生人被当作没有生命尊严的奴隶对待,不具备主体理应拥有的追求自由和尊严的权利,一旦他们试图作为独立的自由意志主体,就会被赏金猎人“回收”。人类显然无法允许人与人造机器普遍平等的局面出现,但在解决遗留的道德伦理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部分主体权利的赋予,或许可以看作是彻底解决伦理问题之前用以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一点“权宜之计”。是否可以将仿生人认定为生命范畴内的存在,归并入后人类主体当中,还有待商榷,需要生物、法律、人文哲学等多学科跨领域的共同努力。
迪克小说中凸显的另一大问题是出现在人类内部的分化孤立。身体受到放射尘损伤到达一定程度的人类,就会被打上“鸡头”等侮辱性的标签,划作生理异类,驱逐出人类历史。多数人为了保护人类原始基因不受特障人的污染,在社会上将他们边缘化,剥夺他们继续做“人类”的权利,丝毫不考虑造成这部分弱势群体的永久性损伤的始作俑者,正是人类自己。当人类自食核武器滥用的恶果之后,为了保证物种基因健全,竟抛弃人性,选择牺牲部分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换取人类大物种的绝对统治地位的延续。这一切做法,从根本上看,实则都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与自私,因此,在后人类未来,面对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质询,实属必要之举。
在后人类时代,人类身份的构建,无法离开人与其他生命形式以及技术性他者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得以探讨。正如布拉伊多蒂所主张的,后人类主体必定是一个游牧的、通过以普遍生命力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将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紧密联系起来的、关乎生成的关系性主体。我们人类,与动物、植物、技术性他者以及作为我们的生存媒介的地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不是整体论上的统一,也不是简单化的一体。人类应当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的基础上,关注后人类主体各元素之间的差异,去建立一套新的价值和表征体系,以应对日益出现的生命伦理和科技伦理问题,使得新的后人类主体得以构建,一起思考,一起努力,去应对现有的后人类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注释:
①(意)罗西·布拉伊多蒂著,宋根成译:《后人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②(美)菲利普·迪克著,许东华译:《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③(美)菲利普·迪克著,许东华译:《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④(美)菲利普·迪克著,许东华译:《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74页。
参考文献:
[1]纪晓桐.菲利普·迪克科幻小说中的后人类身份问题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20.
[2]马小茹,马春茹.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主体理论研究[J].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3):25-34.
[3]苗思萌.未完成的主体——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的移情与主体建构问题[J].文艺理论研究,2016,(1):104-111.
[4]裴彦融.《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的后人类主义解读[D].山西师范大学,2020.
[5]孙云霏.游牧主体与关系伦理——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主体理论[J].上海文化,2021,(4):25-34.
[6]王启名.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身份重构[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9.
[7]支运波,张扬.后人类语境下《别让我走》的身份建构解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54-58.
[8](美)菲利普·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M].许东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9](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M].宋根成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