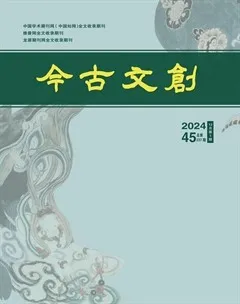空间叙事学下的人物形象分析
2024-12-19卢昱吟
【摘要】小说《温柔之歌》以社会现实案件为蓝本,通过文本中空间的转变塑造人物形象,讲述了一个保姆杀婴的故事。本文以“空间”视角切入,同一人物游移在不同空间来展现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刻画路易丝“友善亲切”和“扭曲压抑”的复杂人物形象综合体。从独特视角出发,利用空间叙事指向悲剧发生的全过程,并呼吁空间下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温柔之歌》;空间叙事;人物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2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06
《温柔之歌》这部由法国摩洛哥裔作家蕾拉·斯利玛尼所著的小说,荣获了2016年龚古尔文学奖。小说以真实社会新闻作为蓝本,讲述了“天使保姆”路易丝是如何在欲望的驱使和精神的压迫下谋杀了雇主的两个孩子。小说刻画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其中对于保姆路易丝的形象塑造更是深刻富有层次。
国内外对于该小说的研究较为丰富,国外学者大多聚焦于女性身份的被塑造与被规训问题,学者Delpierre Alizée以女性身体为基础分析女性角色,指出女性的处境,阐明女性角色的身体如何被塑造并受到局限,并且探究其原因。[1]国内学者更多则关注小说中所体现的社会阶级问题,学者肖华分析了阶级差异导致的不可忽视的矛盾,并指出在当今消费社会背景下,经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依然制造着阶层矛盾,加剧着阶层固化[2];还有学者探讨小说悲剧的成因,学者舒青认为路易丝悲剧的造就不仅在于她人格中的偏激,更在于外部环境对她的压榨侵蚀[3]。
其中,对于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多。小说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侧重展现地理空间和时空空间对于人物的形象塑造,空间化特点凸显。本文将以龙迪勇的空间叙事学理论为依据,从“空间”视角切入,展现空间转变下保姆路易丝的不同人物形象塑造,讨论在空间中对于路易丝的生产生存方式以及道德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像,分析并揭示悲剧发生的全过程,并对路易丝的出路进行探寻。
一、创作空间下心理文化背景
事实上,人类的叙事活动与人类所处的空间及其对空间的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4]小说的灵感源于“保姆杀婴”的真实社会新闻,而小说中保姆路易丝的名字正是源于“路易丝·伍德沃事件”。并且由于作者蕾拉·斯利玛尼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她家里就有请保姆的习惯,于是年幼的她就开始对“保姆”这份工作有着特别的体会。保姆对她的特殊态度以及话语交流让她敏锐的感知到保姆在家里的特殊处境,也让她意识到了她和保姆之间存在的鸿沟。
诺伯格·舒尔兹在《存在·空间·建筑》中提出了“存在空间”的概念,它是指存在于意识深处的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一般是非常熟悉且投注感情了的空间。[5]“存在空间”作为心理学概念,可以理解为“建筑空间”的抽象化,“存在空间”是人将外在于自身的环境内在化。并且它常常会作为文学的出发点而表现在作品当中,对空间书写进行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文本呈现,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迟子建笔下的黑龙江等。而《温柔之歌》中,斯利玛尼就将故事的发生地点放到了自己更为熟悉的巴黎。
创作空间的选择不仅仅是作品的背景,更是作品的实质基础。故事的发生地为法国巴黎第十区,是一个人群杂糅,文化复杂多样的地带。斯利玛尼的地理空间建构不仅展现了雇主一家的拮据中产阶级生活背景和保姆路易丝的下层阶级生存困境,更是在空间与空间的对比碰撞中暗示了法国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可以说,“存在空间”构成了斯利玛尼的创作底色,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都基于存在此空间之上。
就这样,主体性与空间相互连接依赖,复杂的结构成统一体。也就是说,空间本身也是时间或历史的产物,由于人物的典型性格或人物的“主体性”总是与空间的特定历史“绞合在一起”,因此,被生产出来的某一个特定空间就恰好可以成为某一个人物性格特征的表征物。[6]所以,空间也可以展现人物的生存状貌,性格形象等,空间呈现即是人物的外化和隐喻。
二、私人家宅空间下的扭曲压抑
无疑,在各式各样的建筑物中,住宅由于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常常成为叙事者用来表征人物形象的“空间意向”[7]。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认为“家宅”这一空间对人的重要性是无法比拟的,“它确实是个宇宙。它包含了宇宙这个词的全部意义”[8]。家宅作为个人庇护所的存在,它与我们最私密的部分密切相关。家宅空间承载了个人所有的情感寄托,见证了个人所有的形象横截面。没有了家宅,人就会居无定所,流离失所。所以人们对于家的感情很强烈,它构成了人物个性的物质性空间框架。但路易丝的私人住宅却并没有带给她安全与归属,在这样的空间中,她的性格形象与在外所表现的判若两人。
路易丝将她的家称为“非人的小房子”,她对她的家没有丝毫眷恋,只有厌恶和抗拒。她甚至为了晚回去而故意在街头游荡。
她恨这个地方。淋浴间钻出来的湿漉漉的味道包围着她。甚至嘴巴里都是。每个连接处,每个缝隙里都长满了灰绿色的青苔,她发疯般地擦啊擦啊,可一点用也没有。白天擦去,夜里又重新长出来,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9]
她的家里,窗户玻璃上覆满灰尘和黑色长痕,淋浴坏了,盛水盘下面的木架子也腐烂了等等,可以看出家宅本身就已经衰败残破了,并且家宅中还充满着不幸的往事。
不幸的婚姻、破碎的家庭、大堆的债务、拖欠的房租都在折磨着她。她的丈夫雅克尖酸刻薄,毫无品行道德,对于路易丝时常打骂羞辱。他嘲讽努力养家糊口的妻子,自己却每天在家无所事事。并且,作者斯利玛尼虽在小说中并未明说,但也可以通过细枝末节发现路易丝成长的家庭环境也是不幸的、灰暗的。她没有被人正确地爱过,当然她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爱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文化资本的缺失使得他们的孩子斯蒂芬妮的存在和成长更为艰难压抑。雅克死后还留给了她一堆债务,女儿也被逼离家出走,不知所踪。每每回到家,她就会想起这些痛苦的记忆,住宅正是她腐蚀心灵,扭曲性格的真实写照。
在这样的空间下,她内心的扭曲和黑暗就如同这座小房子一样。她从忍气吞声,伏低做小到猛然爆发,蓄意复仇。她热衷于勾起丈夫的怒火,讨取他的羞辱与殴打,致使他的情绪起伏、疾病加重。她也会对女儿施以暴力,“她打在她眼睛上,辱骂她,把她抓出血来。等斯蒂芬妮不再动弹时,路易丝啐在她脸上”[10]。她把女儿作为宣泄口,将她的不幸,负面情绪全都压在这个可怜的小女孩身上。最后女儿离家出走,她也不闻不问。在此刻的路易丝是绝望的溺水者,她被生活的重担压得直不起腰,还要承受精神上的折磨。但这一切的前提是—— “她打开入户的小门,把门在背后关上”[11]。
很显然,肮脏混乱的住宅没有给她带来温暖,她只想逃离。她将黑暗扭曲的自己封锁在那间屋子里,抛之脑后。但失去了归属感的她又需要一个“心灵栖息地”,于是她将自己的寄托与期待转向了雇主的家宅。路易丝越是对自己家宅厌恶,越是展现对于雇主家宅的渴望与依恋。
三、雇主家宅空间下的心理失衡
这位痛苦焦虑的保姆在外的形象与先前所展现出来的截然不同。被门所分隔的独立空间也创造出了泾渭分明的叙事空间,伴随空间的转换,带有被虐与虐待狂倾向的心理病人化身为了体贴而温柔的“仙女”保姆。[12]
在雇主家宅空间下,路易丝的性格形象是颠覆性的展现。路易丝是满足的、自信的、得体的,她的前几任雇主们都说,能够请到她运气真是太好了。
现任雇主保罗一家的公寓并不宽敞,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房屋空间更显拥挤狭窄。但路易丝凭借她的魔力,把公寓整理得安宁、明亮,“安静的公寓尽在她的掌握之中,就好像一个在请求宽恕的敌人”[13]。她像一个将军一样,在视察自己征服的领地。
路易丝决定在某个星期三的下午为米拉庆祝生日。一上午,路易丝都在吹气球,然后挽成各种各样动物的形状,贴得到处都是,从大厅一直到厨房走廊……[14]中午过后回到家中,米莉亚姆(雇主)险些叫出声来,她差点没认出来这是自己的家。客厅完全变了样,到处都是闪亮的金银片、气球、彩纸花环。不过最大的改变是沙发全都掀了起来,这样孩子们就有地方玩耍了。甚至那么重的榉木桌,自从进家后连位置也没有挪动过,现在也被移到了房间的另一头。[15]
路易丝一个人完成了一切的改造,难以想象她纤细好似火柴棍般的胳膊和小小的身体中,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空间的改变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雇主一家惊讶于路易丝的勤劳能干,他们愈加信赖这个勤勤恳恳、尽职尽责的保姆。同时,路易丝也逐渐沉沦于改造雇主家的“满足感”与“掌控感”。
雇主一家对于路易丝赞赏有加,相互之间的依赖也在加深。他们邀请她共进晚餐,一起去海边度假,行为举止超出了雇佣关系的边界。于是路易丝妄图打破边界,在雇主家留宿,在这个家里慢慢地建造起自己的小角落。她想在雇主家筑一个自己的巢,并且沉迷于这种虚幻的想象,不能自拔。
她现在有了一种隐秘的信念,炽热的、疼痛的信念,那就是她的幸福取决于他们,那就是她属于他们,而他们属于她。[16]
在这里,路易丝在外的完美形象第一次出现裂缝,她内心潜藏的狂热与黑暗在雇主家宅空间下展现了出来。
她不懂得雇主对她的感情是基于保姆工作的认可,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而她将她的欲望寄托在了雇主一家,她想要融入这个家庭,找到她的位置并居于其中。
直到雇主一家收到了路易丝亡夫的催款单,由于债额过大,路易丝无法承担只能不断躲避,直至财政部将催款单寄到了雇主家。路易丝的工资被拿来抵债,雇主一家对她态度开始变得微妙起来,许多暗藏的矛盾也随之显现,她的幻想破灭了。于是她内心失衡,开始憎恨仇视他们。
某一天,她在孩子们和她吃饭的小桌子上的盘子里放了一个鸡架。对“内在空间”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家具或摆设进行书写,可以产生意义,从而刻画出人物的典型性格。[17]这个鸡架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种“空间冲突”背后还潜藏着价值和制度冲突。它代表着宣战,这是在雇主家不会出现的东西,它已经不能吃了,她为了报复放在这里,对他们浪费食物行为和嘲笑她过分节约的反击。这时的路易丝是愤怒的、仇恨的、混乱的,她的精神也如这个鸡架般“形态可怖”。两个孩子长大了,她也面临解雇危机,她既不想再次流离失所,又为雇主家的冷漠疏离而悲伤愤怒,她迫切地想让一切都重回旧轨,于是“第三个孩子”成了她的救命稻草。
她无比希望雇主家再生一个孩子,以为这样她就能像以前一样继续工作生活下去,在雇主家庭几次明确拒绝后,她终于走向了犯罪的道路。内心的仇恨再次翻涌,她产生了“杀死这两个小孩,雇主一家就会再生一个,她也就不会失业”的想法,最终走向了毁灭他人与自我毁灭。
在雇主家宅空间下完整展现了路易丝是如何“杀人”的。从外人眼中的“完美保姆”到“杀人凶手”,她既卑又亢,日渐扭曲,她在家里是如此亲近的存在,但并不是家里的一分子。没有人真正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她有什么样的生活,她只能在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下保持基本的生活。她被生活的重担压得直不起腰,还要承受精神上的孤独折磨。她从没有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物理空间缺失,心理空间也坍塌,没有人真正关心她,她是在不断地空间压缩中走向灭亡。
四、大海空间下的自由平等
路易丝在小说中一直以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形象出现。每天的生活都很单调,生活围绕着雇主家展开,两点一线奔波。她的活动范围都是被体现权力与身份的空间所框定的,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打破这种空间秩序的。[18]而斯利玛尼给了路易丝另一个可能性。
雇主一家带路易丝出游其实是一个意外。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保罗(雇主)在喝多后宣称他们一家要去海岛度假,应允路易丝也要同行,于是她才有了这次出行的机会。这次出行代表的是她对于传统空间和既定轨迹的一次突破。
路易丝从未出去过,她十分期待这次岛屿旅行,想看看大海和岛屿。他们来到海边时,她因为不会游泳而被米拉(孩子)嘲笑,保罗对此感到尴尬和怨恨,“他恨路易丝,把她的贫穷和脆弱一并拖到这里来”[19]。但随后保罗带着她去学习游泳的时候,他暗自发笑“路易丝也是有屁股的”[20]。这是第一次保罗将她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以往他只当她是个工具人,甚至根本视而不见。
是黎明的清冷让她醒过来,面对白天的一番景象,她差点叫出声来。那是一种纯粹、简单、显而易见的美。所有心灵都能够感受到的美。[21]
路易丝完全沉迷在岛屿中的美景中,从积累的恐惧压抑中解放了出来。度假的几天,她与雇主一家相处平等融洽,脱离了家宅空间,他们不以“保姆”的身份和她对话,以平等人对她。她明白这是稍纵即逝的一瞬,所以她说,“如果说我要去那里,是因为我再也不想替任何人操心了。想睡就睡,想吃就吃”[22]。
大海空间给了路易丝突破阶级、平等相待的可能。基于她的种族、阶级等,她在先前的空间中始终得不到认同感和安全感,但在这里,她感受到了全新的生活空间和方式。她不再被传统空间的家宅空间和城市空间所驱赶压榨。大海给她提供了个人空间,短暂地消解了她平时的压抑扭曲,她在这个空间下变得平等自由。
五、路易丝的出路探寻
与先前在雇主家与自己家所呈现出的形象都不一样,路易丝在大海这个空间下展示出了自由、欢乐、热爱自然的一面。其实在这里,斯利玛尼也隐喻式地表达了路易丝的结局。
雇主夫妇并非苛刻严厉的人,他们也会设身处地考虑路易丝的感受。他们带她去希腊度假,去看从未见过的美景,品尝从未吃过的美食。他们带路易丝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同时路易丝也知道了自己的生活永远不会有转向另一面的可能了。她的幸福取决于他们,她将这个家当作了实现自己价值、改变境遇的救命稻草。她唯一的念头就是继续在雇主家工作下去,但孩子渐渐长大,路易丝快要失掉她在这个家里的“价值”了。在几次试探交锋之后,她无法说服米莉亚姆(雇主)生第三孩子,加之她负有高额外债的事情被雇主知道了,雇主对她的态度逐渐改观,于是她绝望了。最终,她滋生了杀掉亚当和米拉的念头。
路易丝作为社会底层女性,她受尽身边男性的打压伤害,这是造成她悲剧的成因之一。她不仅承受着丈夫对她生理和心理的伤害,还要忍受房东男雇主等对她的侮辱和不尊重。在家庭生活中,她从未感受到任何物质和情感的满足,反而还要承受丈夫的怒火和遗留的高额债务。她的房东和前雇主也因为她无依无靠而剥削压榨她的房租和薪资。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路易丝内心的焦虑失衡。在这里,斯利玛尼呼吁性别平等。性别平等是要让人们意识到性别的存在,加入争取性别平等行列中来。
并且长久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一直存在,人们往往过于注重“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人”本身。保姆并非冰冷的机器,她们也有人的情感,喜怒哀乐等。比如当雇主一家偶然在街上看到工作以外的路易丝时,他们感到一阵诧异和陌生。
她竟然也在别处生活,独自一人,走路的时候竟然不用推手推车,竟然没有握着一个孩子的手。[23]
他们觉得“保姆”这个词就是路易丝的全部了。他们震惊于她除了“保姆”这个角色之外,居然也会有自己的生活。因此,对于保姆这份工作,希望雇主们能够给予她们“人的价值”,对她们的人格做出应有的尊重。
小说中,“难以沟通”这一问题也是导致路易丝悲惨结局的重要因素。路易丝一直生活在孤独、不幸、贫苦中,她没有朋友,死了丈夫,女儿出走,孤身一人。甚至朝夕相处的雇主一家对路易丝的生活也一无所知。
正如这部小说的译者袁筱一老师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在《温柔之歌》中始终是一个强劲的不和谐音,同时也是旋律动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无望会使得人异常的孤独,这也是现代社会生存境遇中最苦涩的部分。[24]
小说里,人与人的不可沟通不仅仅是路易丝的困境,米莉亚姆也无法逃过宿命,她一直都在抗争,但似乎所有人都结成同盟来对抗她,所有人都指责她过于投入工作,过于信赖保姆,最后造成这样的局面。当米莉亚姆和保罗沟通时,他害怕家庭琐事的负累,便把一切都抛给妻子,还对她进行道德绑架。与路易丝一样,也没有人理解她。在这种情况下,沟通是对真诚,信任和尊重的呼唤。拒绝沟通只会让关系越来越疏远,矛盾愈演愈烈,冲突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无法获得良性互动和深层交流。
性别不平等下的身份践踏,尖锐矛盾下的理智消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困难等等,这些多重压迫系统的累加效应都是路易丝走向悲剧的助推剂。但不可否认的是,路易丝本身的性格也是偏极端的,她没有保持清醒理性,最终释放出了内心的“恶”。但至少,这些外部环境问题的解决也会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些悲剧的发生。
六、结语
《温柔之歌》中的空间叙事建构并未停留于某个特定地域,而是作者在重新整合自己的历史记忆、社会意识和身份认知之后,在现代多元文化共生背景下就现代人的生存境况的探究。[25]《温柔之歌》通过多角度的多层空间转变,以同一人物游移在不同空间来展现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刻画了路易丝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崩溃过程,至此,路易丝的人物形象就此塑造完成。
在不同的空间转变下,路易丝的形象随之一点点被建立起来。她在私人空间下的阴暗、孤独;雇主家宅空间下的完美、自信;大海空间下的自由、生机。它们一起构成了路易丝的复杂共同体。
开篇呈现的命案不仅仅是斯利玛尼出于文学创作的安排,也反映了多重矛盾叠加的严峻性。路易丝作为底层边缘小人物,生活艰辛。路易丝在独自承受生活重担的同时还要被自己的亲人谩骂侮辱,她身心俱疲。女儿斯蒂芬妮就是在紧张不安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家人们都不在意她。随着青春期的她做出了叛逆出格的行为,甚至离家出走,路易丝却毫不担心,甚至在心里认为“她可能已经死了”,冷漠至极。路易丝在保罗家工作时,雇主阶级和保姆阶级之间的鸿沟滋生了她心里的不平衡,甚至是强烈的恨意。而悲哀的是,路易丝所追求的自由平等也只是暂时的。最终,雇主与保姆的矛盾最终导致两个孩子的死亡。
她对于雇主一家的“恨”,实际上并不源于雇主一家,而是来自她所处的这个社会。悲剧的产生除了路易丝本身的性格偏激,还有一部分来自外部环境。比如尖锐的阶级矛盾、性别不平等而使她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等,都成了这场悲剧的导火索,激发了她内心黑暗的一面。她的悲惨经历和最终结局,不仅仅她个人选择的悲哀,更是法国社会阶级撕裂的隐喻。[26]
《温柔之歌》并不温柔,“温柔”俩字反而为小说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残酷的故事让读者感受到巨大的反转,让读者思考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部社会题材的作品,路易丝人物形象的极度分裂赋予小说张力的同时,也暗示出有病的不只是路易丝,更是她身处的社会。小说不仅暗示人性、社会和阶级的反思,更是呼吁空间下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Delpierre Alizée.Disparaître pour servir:les nounous ont-elles un corps?[J].L'Homme&la société, 2017,(1):261-270.
[2]肖华.从小说《温柔之歌》看当代法国社会阶层固化问题[J].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19,(01):77-83+93.
[3]舒青.浅析蕾拉·斯利玛尼《温柔之歌》中人性悲剧的成因[J].信阳农林学院学报,2018,28(02):70-72.
[4][5][6][7][17]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14:41,42,269,273,310.
[8]加斯东·巴什拉.空间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
[9][10][11][13][14][15][16][19][20][21][22][23]蕾拉·斯利玛尼.温柔之歌[M].袁筱一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158,57,83,29,43,42,88,69,71,68,141,140.
[12]陈依.《温柔之歌》的悲剧空间与伦理困境[J].南腔北调,2022,(10):89.
[18]蓝灵.空间批评视域下《温柔之歌》中的生存困境[J].新纪实,2022,(13):63.
[24]席小妮.蕾拉《温柔之歌》中折射出的女性生存困境[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37(10):15.
[25]王迪.空间、命运与抗争:《温柔之歌》的空间叙事与女性主题[J].当代外国文学,2022,43(01):111.
[26]伍倩.《温柔之歌》:空间生产与空间暴力的伦理表达[J].外国文学,2021,(04):31.
作者简介:卢昱吟,重庆三峡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