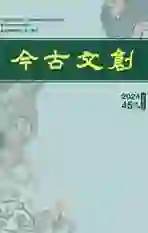“被受压迫者压迫的人”: 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中女性形象解读
2024-12-19闫蕙娟
【摘要】《都柏林人》是詹姆斯·乔伊斯的早期作品,这部作品在描绘都柏林人生存状况的同时,也描绘了一个丰富的女性世界。本文尝试结合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观点,选取其中三篇故事探析乔伊斯这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通过表现男权统治下的悲惨女性形象,对男权制度进行了批判。
【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2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05
一、引言
詹姆斯·乔伊斯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他的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乔伊斯出生时爱尔兰是英属殖民地,战乱不断,平民生存艰难。在家里许多孩子中,他作为长子受到父亲偏爱。19世纪时期欧洲文学宣扬自由思想,爱尔兰盛行文艺复兴运动,青年时期的詹姆斯受到这些的强烈影响,宗教信仰开始动摇。1900年他对于易卜生作品的评论获得易卜生的欣赏,这帮助他坚定了走文学道路的决心。1904年他开始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Dubliners,1914),代表了乔伊斯的文学生涯的开始。这部小说集以二三十年代爱尔兰的首都为背景,以十五个短篇故事描绘了20世纪初都柏林各型各类的中下阶级平民的生存状况。这些故事相互串联,拥有共同的主题,它们都深刻揭示了当时都柏林社会生活中的瘫痪状态。
乔伊斯是著名“意识流”小说家,他的其他作品影响深远,研究者众多。但这部早期作品出版过程一波三折,耗费十年,直到近半个世纪才引起专业评论家的注意,且现有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文本研究方面,其他视角下的研究仍有探索空间。因此,本文尝试结合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观点探析乔伊斯这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对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本、主题、女性主义、跨学科研究等多个方面,总体研究较丰富,视角多样化。
文本研究方面, Chenglin Yu认为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创造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这种创新倾向于对视点的限制,即叙事倾向于通过人物的视点展开,没有全知全能的干扰。在考察了短篇小说的创作背景后,研究者认为乔伊斯的流亡和都柏林人的审查制度是这一正式创新的主要原因。[6]
Suh,Younghwan考察了詹姆斯·乔伊斯的三篇短篇小说《都柏林人》中的自由间接风格(FIS)及其韩译本,并揭示了尴尬感可能是由于韩国译者对FIS的一些重要的,不明显的特征缺乏了解。[4]
主题研究方面,Pedram Maniee,Shahriyar Mansouri 调查了乔伊斯如何描述英国对爱尔兰,特别是都柏林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统治。他们探讨了乔伊斯写作《都柏林人》的动机、后殖民主义的基本原则,还考察了詹姆斯·乔伊斯如何运用象征主义来描述他对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反应。[2]
Yuan SHEN,Hong DONG探讨了《都柏林人》在世纪之交因宗教和政治困境而感受到的瘫痪、孤独和死亡等现代主义主题,分析乔伊斯的顿悟、象征、淡化情节和叙事视角转换等现代主义写作手法,揭示人物的精神微妙和社会复杂性。[7]
女性主义研究方面,Na Zhao聚焦于三个短篇小说中的三个女性角色,运用后女权主义标准来探索她们其他独特的女性叙事,这些叙事挑战和颠覆了传统的男性文化体系。[8]
Paige,Linda Rohrer聚焦于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一书中母亲的形象的塑造、乔伊斯对女性人物的负面描写的禁锢;并举出乔伊斯作品中与母亲人物形象相似的例子。[3]
跨学科研究方面,Monika Kavalir以伊芙琳的语言如何传达女主人公作为一个被动、瘫痪的角色的画面为出发点,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文体分析模式,探讨了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对语篇意义的贡献。[1]罗兰巴特认为符号学是综合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研究语言如何表达世界的。巴特在对巴尔扎克《S/Z》中的“Sarrasine”进行结构分析时阐述了这些符码的五种类型和功能。SEYED ALI BOORYAZADEH,SOHILA FAGHFORI,MARZIEH SHAMSI借助《S/Z》中罗兰巴特的特定内涵代码,试图阐述詹姆斯·乔伊斯的“两骑士”的语义含义不明显的结构模式。[5]
国内对于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题、意象与象征、文本研究方面,总量较少,视角有限。
主题研究方面,高红梅对《都柏林人》中的圣杯追寻主题进行了解读,探析了《都柏林人》中的精神荒原症候和诗性政治,“圣杯”这一意象的隐喻贯穿了整部作品集,既构建了作者这一主体,还构建了虚构人物,其中也融入了文化反思、政治诉求和精神批判。[10]
龙晶晶、李忠华认为《都柏林人》揭露了那个时期爱尔兰的社会矛盾,通过对具体细节的分析探讨了作者传达的思想,并从情感、政治方面将现代人的一些精神现状反映了出来,探析了作品中给予现代人的一些启示。[12]
意象和象征研究方面,崔艳霞对《都柏林人》中“灯”这个意象展开了多方面分析,细致地展现了作者使用特殊语体达到写作目的的文学手法,“灯”这一意象暗示了虚假的希望。[9]
郭雯静通过对《阿拉比》等作品进行分析,发现他对于都柏林人命运展现了极大的人文关怀,通过分析乔伊斯实现创作意图的写作手法和技巧,从象征主义手法分析了“光”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和意义。[11]
文本研究方面,李兴华从现实主义视角对《都柏林人》中的语言技巧进行了评析。[14]
刘林对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的文学讽喻手法进行了探究,通过挖掘“顿悟”的讽喻功能,展示了小说人物如何建构具有精神价值和意义的另外的一个世界。[16]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都柏林人》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法、视角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本土化的研究比较滞后,大部分相关研究文章多是以西方文艺理论为研究范式的;其次是国内对于这部作品的整体研究不足,在作品语言、美学、叙事、女性主义研究等方面还有探索空间;最后是已有研究成果中专著相对较少。当前,西方《都柏林人》研究已进入到跨学科研究阶段,为了在国际上拥有中国学界的话语权,国内学者应该从更多更宽广的视角出发,以更多样的研究框架深入探析《都柏林人》这部文学作品。
三、理论概述
“第二性”这一术语源自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1949 年出版的《第二性》。在这部著作中,“第二性”也就是指女性,是相对于男性而存在和定义的他者。波伏娃通过回溯人类历史、描述两性差异以及神话传说中对于两性关系的构想,深刻揭示了女性遭受压迫的普遍社会现实。波伏娃在这部著作中从多个方面阐述了“第二性”的理论主张。
第一,在父权社会中女性是相对于男性而存在的他者。这一观点是“第二性”概念的核心内涵。
第二,女性并非是属于男性的性爱客体,她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性观念和心理。波伏娃认为当时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着重描绘男性心理,缺乏对于女性性心理的关注,仅仅突出了女性所处的被动地位,认为女性是不健全的。
第三,性别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社会和文化建构的。这一观点区分了性别的生理特征及其社会、文化属性,为女性摆脱生理决定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四,女性难以形成性别意识共同体。波伏娃认为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导致了女性整体在历史上的挫败。
最后,在差异中寻求平等是实现性别平等和自由的理想。波伏娃认为只有坚持“差异中的平等”,才能保持女性个体健全。[15]
四、解读《都柏林人》中的女性形象
目前国内对于《都柏林人》这部小说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精神分析、主题探索、意象和象征研究等方面,女性主义方面的研究较少。考虑到填补女性主义研究空白的需要,本文尝试选取作品中的《伊芙琳》《寄宿公寓》《一朵浮云》三篇故事,结合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关于女性主义的观点分析《都柏林人》中女性形象,为未来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伊芙琳》讲述的是一个年轻女孩伊芙琳企图通过婚姻来摆脱父亲的压迫和家庭的重担,希望获得自由的故事。伊芙琳作为一个年轻女孩没有什么生活阅历。伊芙琳在母亲去世后就独自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伊芙琳完全听从父亲命令,忍受着父权压迫。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她放弃了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独自承担着许多责任,过着一种沉闷乏味、单调无趣的生活,并一直在男权社会中以这种麻木的状态苦苦挣扎。
伊芙琳内心渴望自由与幸福,渴望着逃离这样的生活。遇到水手弗兰克之后,弗兰克对伊芙琳的照顾让她开始憧憬未来的幸福生活。父亲知道伊芙琳和弗兰克交往的事情以后强制命令伊芙琳不许再继续和弗兰克见面。这也可以看出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下女性受到的压迫与传统女性的附属地位。当伊芙琳准备离开的时候,她又开始担心自己和弗兰克私奔以后会被周围认识的人谴责、议论,这其实也能够显露出在男权社会下社会道德、舆论、社会习俗对于女性的禁锢和束缚。
女性主义研究认为,女性发疯是精神被贬抑到某种程度的爆发形式。伊芙琳的母亲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她代表着典型的传统女性,直至最后她发疯死去,家庭都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伊芙琳的母亲完全适应了他者的身份并尽力履行这一身份带来的种种义务,没有对家庭重担和男权压迫有过任何反抗,但是最终她也没能逃脱悲惨命运,成为父权社会下的牺牲品。伊芙琳母亲发疯而死隐喻了父权秩序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制,她的死亡深刻揭露出父权社会的残酷本质,也直接促使伊芙琳逃离当前生活的渴望更加强烈。
但是当伊芙琳准备离开时,母亲临终的意愿牵绊住她,想起家里的弟弟和父亲,她陷入了纠结矛盾之中。琐碎的生活和家庭重担、父母的婚姻状况也让伊芙琳对未来充满了担忧。迷茫的伊芙琳祈求上帝,将希望寄托于宗教信仰,这也从侧面暗示了宗教对当时女性思想的禁锢和束缚。无法预知的未来令她感到茫然、害怕,宗教信仰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也禁锢着伊芙琳,让她失去勇气,最终伊芙琳选择了留在都柏林。
波伏娃的“第二性”观点认为,女性天生在各个方面弱于男性,又长期处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所以认为自己处于劣势地位。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女性习惯于将男性视为社会中心、家庭支柱,而将自身置于男性附属品的位置。
伊芙琳在最后时刻因为内心的怯懦、无法违背对已逝母亲的诺言,最终回归了家庭和原来单调、压抑的生活。伊芙琳在家庭中不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她的生存环境使她只能将父亲视为家庭的支柱,依靠父亲而生存。伊芙琳虽然有想突破父权制压迫的愿望,但是最终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行为,还是屈服于父权制的意识,成为男权社会意识形态下的牺牲品。
《寄宿公寓》讲述了穆尼太太和丈夫离婚后独自经营了一家寄宿公寓,她通过多重谋划最终促成了女儿波莉和房客多伦先生的婚事。最初的穆尼太太和其他传统的爱尔兰女性一样对于自己的婚姻毫无自主权,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嫁给了父亲的工人穆尼先生。穆尼太太的父亲去世后,穆尼先生就变成了家庭新的权力中心。但是穆尼先生整日喝酒,不务正业,还欠下大笔债务,使整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穆尼太太独自一人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穆尼先生毫不悔过,还经常当着顾客的面虐待穆尼太太。丈夫的虐待和生活的压力让穆尼太太不堪其扰。这些都能够体现当时男权社会女性地位低下,毫无话语权,陷入男权压迫的困境。与当时绝大多数的爱尔兰传统女性忍气吞声、忍受男权压迫不同,在经历了痛苦的婚姻后,穆尼太太利用社会舆论的支持帮助自己获得了人身自由,得到了孩子的抚养权以及全部财产,并摆脱了不幸婚姻的束缚。她还开了一家旅店,自此穆尼太太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和独立地位。
都柏林的女性一方面受到父权社会的压迫和规训,另一方面又按照男权社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教育自己的女儿。在经历自己不幸的婚姻之后,穆尼太太仍旧试图按照都柏林的传统为女儿波莉找到合适体面的丈夫。穆尼太太将自己婚姻的不幸归结于无能的丈夫,她虽然突破了传统的父权制的禁锢、有鲜明的主体性,但仍然认为好的婚姻和丈夫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归宿和依靠,她本质上还是受到父权社会思想压迫和影响的。
《一朵浮云》讲述了都柏林一个小公司职员小钱德勒到酒店去和多年未见的朋友加拉赫见面,回想起年少的梦想,满怀希望回到家里,最终在孩子的哭泣和妻子的质问中幻想破灭的故事。乔伊斯在塑造钱德勒夫妇时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诠释,将社会性别与生物性别剥离开来。在这个故事中,乔伊斯开始就将小钱德勒女性人格特征描述得淋漓尽致,暗示了小钱德勒虚荣,腼腆,无男性应有的魄力。在男女性格完全对调的情况下,家庭依旧是以小钱德勒为中心的。本质上妻子安妮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和妻子的角色,始终是以丈夫为中心的。
丈夫小钱德勒在其女性化外表下隐藏的是一颗敏感忧郁、胆怯自卑的心,全然没有男子汉气魄。安妮对待丈夫看似霸道,实则是对丈夫懦弱无能的怨恨和鄙视。安妮憎恨丈夫的庸碌、懦弱,但又没有想过脱离丈夫和家庭,只是用斥责发泄自己的怨愤和不满,转而将自己的期望全部倾注到儿子身上。本质上安妮始终是被父权社会的思想禁锢和束缚的,自我独立的意识并没有苏醒。
五、结语
在《都柏林人》中,詹姆斯·乔伊斯用15个故事展现了都柏林人的普遍心态:“麻痹”,这是社会的核心。而女性角色,作为男权社会的从属和被压迫者,则更加悲惨。在男性看来,女性是他者(the Other),是由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来定义和诠释其存在的客体。《伊芙琳》中的伊芙琳、《一朵浮云》中的钱德勒夫人安妮都是屈从于命运和男权社会的女性角色。伊芙琳意识到了她的渴望和被束缚的状态,表达了摆脱现在的生活、困境的愿望,但缺乏开始新生活的勇气。她有限的知识范围和对惯例的服从促使她做出了这个决定。钱德勒太太对自己日渐衰败的生活不满意,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做出改变。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长大,接受的是男权等级制度的教条,她缺乏追溯自己不满的原因的能力,认为做一个传统的妻子是女人生活的最高信条。
《寄宿公寓》中的穆尼太太虽然摆脱了自己的不幸婚姻,并成功地诱骗了一个男人和自己女儿结婚,但她认为传统观念中的婚姻是女人自我救赎的唯一机会,因此仍然很难摆脱男权社会的压迫,沦为可怜的牺牲品。
从故事中可以看到的是,都柏林的女人是如何逐渐因为令他们失望的婚姻而感到疲惫,并陷入对生活的幻想破灭的境地。像安妮·钱德勒这样嚣张跋扈的妻子和穆尼太太这样控制欲强的母亲,实际上即使给予了她们特权,也是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有效。
乔伊斯通过表现男权统治下的悲惨女性形象,对男权制度进行了批判。在都柏林,女性被贴上了奴隶、仆人的标签,在父权社会中被边缘化。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与爱尔兰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都柏林人》中,一方面,女性由于社会赋予她们的不利条件和低人一等的地位,被迫接受了从属的命运;另一方面,男性利用同一社会赋予的性别优势,借助社会力量来控制女性。被男权压迫的女性,有些由于内在性的思想禁锢而屈服,有些试图反抗,但是由于她们的处境和意识没有改变,她们的反抗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参考文献:
[1]Kavalir,Monika.Paralysed:A Systemic Functional Analysis of James Joyce’s “Eveline” [J].ELOPE:English Language Overseas Perspectives and Enquiries,2016,(13):165-180.
[2]Pedram,Maniee and Shahriyar Mansouri.A Post-colonial Study of the Short Story “Araby” (1914)by James Joyce[J].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2017,(8):201-208.
[3]Paige and Linda Rohrer.James Joyce’s colored portraits of ‘mother’ in Dubliners[J].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95,(32):329-340.
[4]Suh and Younghwan.An Analysis of Korean Translations of Free Indirect Style in Dubliners[J].TheJournal of Modern British&American Language& Literature,2018,(36):217-240.
[5]Seyed,Ali Booryazadeh, Sohila Faghfori and Marzieh Shamsi.Roland Barthes’s connotative code:A new perspective for reading James Joyce’s“Two Gallants” [J].Journal of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15,(5):214-219.
[6]Yu,Chenglin.Narrative Innovation in Dubliners and James Joyce’s Exilic Experience[J].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2019,(9):1287-1292.
[7]Shen,Yuan and Dong Hong.The Modernistic Features in Joyce’s Dubliners[J].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2016,(12):28-32.
[8]Zhao,Na.Feminine Narration:a Feminist Study of Dubliners by James Joyce[J].Proceedings of 3rd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 Culture,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ICCESE 2019),2019,(310):161-165.
[9]崔艳霞.《都柏林人》中“灯”的意象研究[J].语文建设,2016,(32):49-50.
[10]高红梅.《都柏林人》诗性政治与精神荒原症候—— 《都柏林人》的圣杯追寻[J].文艺争鸣,2019,(10):178-182.
[11]郭雯静.《都柏林人》的追寻[J].语文建设,2014,(14):55.
[12]龙晶晶,李忠华.从《都柏林人》探析爱尔兰独立过程中的民族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2019,(3):17-20.
[13]李蓝玉.西方《都柏林人》研究概观[J].外国文学研究,2014,(5):166-172.
[14]李兴华.现实主义视域下《都柏林人》的语言技巧评析[J].语文建设,2016,(11):41-42.
[15]刘岩.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性[J].外国文学,2016,(4):88-99.
[16]刘林.“缺席乃是在场的最高形式”——乔伊斯《都柏林人》文学讽喻手法探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1,(9):98-102.
[17]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