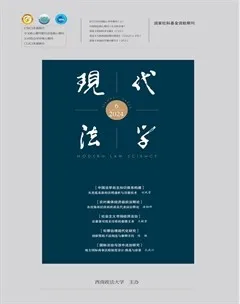论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
2024-12-18王毓莹


摘 要:新《公司法》引入了针对股东出资的催缴制度,解决了长期困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缴资难题,可谓是立法的一大进步。但催缴义务的法律性质、催缴的前提条件、催缴义务的履行、违反催缴义务的认定标准及其法律责任等问题仍有待解释论层面的进一步阐释。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首先应当是信义义务,其次应当属于董事对公司所负的勤勉义务。催缴的前提是需要对股东出资情况进行核查,需要核查的情形不仅包括正常情况下的届期缴资,还应包括出资加速到期、五年认缴期限届至等导致股东提前缴资的情形,因而核查内容应包括股东认缴与实缴、公司是否不能清偿债务等情况。基于对新《公司法》第51条、第52条的解释,催缴义务在实践中可以由董事履行,也可以由任何能代表公司机关的主体履行。当董事履行催缴义务时,基于催缴义务的勤勉义务属性,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宽限期可以依据商业判断进行自由裁量。董事违反催缴义务的认定应当遵循“严格客观标准”,“给公司造成损失”应当理解为公司实际利益的消极减损,董事仅应当向公司承担法律责任,这一责任不等同于代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
关键词:认缴制;催缴义务;勤勉义务;信义义务
中图分类号:DF411.9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4.06.06
近年来,股东认缴出资届期催缴问题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热议,该问题的焦点在于董事应否承担催缴义务,以及未履行催缴义务应否承担法律责任,司法裁判对这一问题呈现出从不支持到支持的态度转变,并形成了“催缴义务—赔偿责任”的裁判观点。这一争议在本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修订中得到了回应。202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第46条明确规定,对于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或者出资不实的情况,公司应当向该股东发出书面催缴通知,该条系回应裁判的观点变化,采纳了一种类似于催告实缴的模式。【参见岳万兵:《公司资本缴纳模式的立法选择》,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12fce5e8901d90c69081cf1340c0bbbf65346c1b7e76b95638b95cc50356cfc7b期,第150页。】但该条所规定的“义务主体”并不明确,理论上,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经理人甚至法定代表人都可能成为催缴义务的主体,故未明确应当由谁来履行催缴义务,往往就会导致谁都可以不履行该义务。有鉴于此,202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第51条将催缴义务赋予董事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以及正式通过的新《公司法》均在第51条中进一步明确,未履行催缴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自此,董事催缴义务正式入法。新《公司法》第51条足以平息长久以来董事是否应当承担催缴义务以及未催缴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争议,也为以后的司法裁判提供了适用依据。但新《公司法》第51条仍然存在解释论上的难题,即董事催缴义务的法律性质为何?董事履行催缴义务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如何认定董事违反催缴义务?董事违反催缴义务的责任范围是什么等等。若不厘清这些问题,那么将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产生争议。因此,本文以新《公司法》为分析文本,重点分析第51条所规范的董事催缴义务,在探寻该义务性质的基础上,为前述解释论上可能产生的系列问题提供解决思路。【董事核查、敦促股东出资的义务在学术界存在催缴义务和监督义务两种说法。从名称的文义理解来看,前者专指认缴而未实缴且已到期的出资,后者语义范围则较为广泛,该义务指向既包含认缴而未实缴且已到期的出资,也包括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值显著低于认缴的出资额的补足出资(通说的出资不实)。但从相应文献来看,虽然名称不同,催缴义务和监督义务实际指向的都是认缴而未实缴且已到期的出资,并且相较于《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新《公司法》第51条所规定的催缴义务并不包含出资不实的补足,因此,以催缴义务来描述本文所指问题更加妥当。相关研究参见邹学庚:《论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兼评“斯曼特”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102-118页;王瑜:《董事勤勉义务在公司催缴出资中的适用——兼评“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公司与胡秋生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载《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9期,第111-116页。】
一、董事对股东出资催缴义务的法律性质
对于股东认缴而未实缴出资的催缴问题,学界的探讨多集中于如何建立股东出资的约束机制【参见郭富青:《资本认缴登记制下出资缴纳约束机制研究》,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122-134页。】、应否建立股东出资的催缴制度【参见黄耀文:《认缴资本制度下的债权人利益保护》,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1期,第162-167页。】以及如何建立催缴制度【参见袁碧华:《“认”与“缴”二分视角下公司催缴出资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202-220页。】等,而鲜有论及催缴义务的法律性质。董事对公司负担的信义义务,主要用以调整发生频率低且类型多样的行为【参见许德风:《道德与合同之间的信义义务——基于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观察》,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第140页。】,主流观点将其划分为以“不得谋取私利、禁止利益冲突”为核心的忠实义务【参见徐化耿:《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中国法上的展开》,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6期,第1582页。】和以理性人标准要求受托人应当尽责、善管的勤勉义务。【参见叶金强:《董事违反勤勉义务判断标准的具体化》,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6期,第79-88页;王真真:《董事勤勉义务制度的利益衡量与内涵阐释》,载《财经法学》2022年第3期,第146-163页。】董事催缴义务究竟属于忠实义务还是勤勉义务,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二者在法律适用上存在明显差异。忠实义务的法律适用关注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谋取私利等行为,并且其法律规范更加完善,证明责任、审查程序等与侵权责任高度相似;勤勉义务则不同,其不仅在是否履行义务、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判定方面更加复杂,而且在部分裁判中,法院还会事先基于商业判断规则对董事责任作出豁免,进而科以原告更高的举证责任。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当明确董事催缴义务的法律性质。
(一)勤勉义务、忠实义务抑或其他义务
目前,对董事催缴义务的认识可以概括为“勤勉义务说”和“监督义务说”。“勤勉义务说”主张,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系勤勉义务。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在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的解释中就指出,公司增资时,对股东的催缴义务属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义务的范围。【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清算纪要理解与适用》(注释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页。】有学者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进行了扩大解释,指出“董事代表公司向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催缴出资是勤勉义务的内在要求”【王瑜:《董事勤勉义务在公司催缴出资中的适用——兼评“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公司与胡秋生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载《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9期,第113页。】,从而将其扩张适用于公司设立时的出资催缴情形。“监督义务说”主张,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系监督义务,而该监督义务可能为忠实义务也可能为勤勉义务。有学者认为,董事不履行催缴义务对公司可能造成损害,因而催缴义务应当属于监督义务的范畴,但该监督义务属于忠实义务还是勤勉义务,取决于董事在客观上对公司可能遭受的损害是否知情,倘若明知公司可能受到损害却有意识地不作为,则应当属于违反忠实义务,反之则属于违反勤勉义务。【参见邹学庚:《论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兼评“斯曼特”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107、109页。】董事是否明知,在实践中表现为立法或公司章程是否明确规定。
上述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论证上的不足或逻辑上的缺陷。针对“勤勉义务说”,催缴义务作为一项勤勉义务的观点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多数肯定,但遗憾的是,对催缴义务缘何是一项勤勉义务,则鲜有论述。虽然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的扩大解释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但应注意的是,该条与新《公司法》第51条存在明显差异,前者规定的董事责任是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而后者规定的董事责任则是董事实际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显然不能发挥催缴义务渊源的功能。针对“监督义务说”,基于董事是否知情而作的区分显然有悖于立法及学理对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划分,仅仅以未尽职就判定董事对公司不忠,进而认定其违反忠实义务,将导致传统上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忠实义务变得模糊不清【See Stephen M.Bainbridge,Star Lopez&Benjamin Oklan,The Convergence of Good Faith and Oversight,55UCLA Law Review559,585-586(2008).】,信义义务的规范价值将被消解,规范性的信义义务将沦为道义义务,这显然不利于对董事行为进行规范。
(二)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是勤勉义务
笔者认为,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是其对公司所负担的信义义务,具体表现为勤勉义务。
一方面,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系信义义务。当前对于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存在“信托说”【See L.S.Sealy,Fiduciary Relationships,20Cambridge Law Journal69,69-81(1962);Justice Joseph T.Walsh,The Fiduciary Foundation of Corporate Law,27Corp Law Journal333,333-340(2002);Leo Strine et al.,Loyalty’s Core Demand:The Defining Role of Good Faith in Corporation Law,98Geo L.J.629,629-696(2010);A.A.Berle,Jr.,Corporate Powers as Powers in Trust,44Harvard Law Review1049,1049-1074(1931);E.Merrick Dodd,Jr.,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stees?,45Harvard Law Review1145,1145-1163(1932);D.Gordon Smith,The Critical Resource Theory of Fiduciary Duty,55Vand Law Review1399,1399-1498(2002).】“委任说”【人民法院出版社编:《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874-875页。】“合同说”【[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中译本第2版),罗培新、张建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0-93页。】等不同观点,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董事对公司应当承担忠实与勤勉的义务。其中,“信托说”的部分论述认为,由于董事与公司实际上存在不对等的地位,董事掌握着公司重要资源的自由裁量权,有着信息上的优势,因而应当负担更高的忠实与勤勉义务。其中,对股东认缴而未实缴的出资进行催缴,即属于对公司重要资源的自由裁量,董事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催缴、如何催缴、催缴多少、设置多久的宽限期等,因此,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系一种信义义务。
另一方面,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系勤勉义务。忠实义务的内容一般包括禁止利益冲突规则(no-conflict rule)与禁止利益取得规则(no-profit rule)。【See J.E.Penner,The Law of Trus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406.】为避免利益冲突与利益取得给公司带来的代理成本损失,各国在董事忠实义务的规则设计中都普遍直接禁止或相对禁止侵占、自我交易、竞业、篡夺公司机会、泄密等行为。【参见周林彬、方斯远:《忠实义务:趋同抑或路径依赖——一个比较法律经济学的视角》,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60页。】相较而言,董事勤勉义务则不以禁止利益冲突或禁止利益取得为前提,即便董事的行为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只要其行为建立在没有利害关系、充分掌握商业信息以及善意决策的基础上,就可以免于承担法律责任。催缴义务要求董事仔细核查股东是否出资以及出资是否到位,在认缴期限届满而未缴纳的情况下,公司应当向股东出具催缴书。可以看出,催缴本身并不涉及董事自身利益,因而通常不涉及利益冲突或利益取得,故不符合忠实义务的特点。但催缴义务也并非典型的勤勉义务,因为在立法已经明确的情况下,董事应当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履行催缴义务,其自主商业判断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不过笔者认为,即便立法没有规定,也不影响其勤勉义务的性质,因为按照私法的原理,立法是否规定与义务的属性之间并无直接关联。此外,信义义务本就具有强制属性【See Melvin Aron Eisenberg,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ion Law,89Columbia Law Review1461(1989).】,立法规定催缴义务,是将勤勉义务的一种类型予以固定,这是一种立法上的进步,而不是将其性质改变为忠实义务。试想,如果立法将勤勉义务项下的某一义务规定下来,就认为该义务由勤勉义务变成了忠实义务,那么勤勉义务与忠实义务的区分将变得毫无意义。
二、董事履行对股东出资催缴义务的前提条件
在明确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系勤勉义务后,如何适用新《公司法》第51条、第52条所规定的催缴制度,则成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法律解释工作。新《公司法》第51条明确了适用催缴制度的条件和未履行催缴导致损害的法律责任,第52条则以专条明确了催缴程序,由此形成了“前提条件—催缴程序—法律责任”的完整规范。沿着这一路径,我们首先需要从前提条件入手,探讨董事对股东出资的核查程序。董事履行出资催缴义务的前提条件为董事会核查股东出资情况且股东出资已届期,不过该条规定仍较为笼统,如何具体落实需要进一步进行法律解释,例如,核查股东出资适用于哪些情形、核查程序如何设置、具有怎样的法律意义等。
(一)董事会核查股东出资情况的适用情形
新《公司法》对于公司资本制度尤其是认缴制的修改除了股东出资催缴制度外,还包括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未届期股权转让责任承担、五年认缴制等,从当前规则来看,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仅限于“发现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这一情况,但该条如何解释、如何与其他规则衔接等问题尚不清晰。理论上,可基于董事会对公司负有资本充实监督的职责而要求其应当对所有涉股东出资事项进行核查,但这些核查是否都会导致董事催缴则不无疑问。因此,此处所探讨的核查股东出资情况的适用情形,亦须以其未缴纳出资必然导致董事催缴为前提。
首先,是正常情况下的股东出资届期未缴情形。学理上认为,董事核查股东出资并在其届期未缴纳的情况下进行催缴默认适用于通常情况下的认缴而未缴,即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缴资期限。认缴阶段的出资自由导致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与公司债权人的信赖利益、营商自由与市场诚信之间的失调【参见汪青松、张汉成:《认缴登记制下缴资难题破解的体系化进路》,载《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5期,第89页。】,催缴制度旨在解决广义上由认缴制带来的上述问题。从立法目的来看,规则的演变实际上彰显了立法者将催缴制度定位于弥补认缴制缺陷的意图,《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第46条中的催缴制度适用情形包括“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和“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即通常所说的届期未缴和出资不实,而《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以及新《公司法》都删除了第二种情形,足见立法者有意将出资不实排除在催缴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外。从立法体系来看,出资不实并非新问题,至少不是2013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以后才出现的问题,可以说自1993年《公司法》颁布至今,针对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问题制定的规则都在不断完善,对出资不实问题的解决不仅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司法实践也已有一套成熟的审判逻辑,此时若贸然将其与催缴制度接轨,进而适用于股东失权,将不利于规则的稳定。
其次,是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情形。新《公司法》第54条明确规定,公司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可以请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基于此,有学者指出,该条同样可以适用于股东出资催缴制度。【参见王艺璇:《董事催缴出资义务的公司法解释》,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101页。】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因为本条明确规定了公司对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请求权,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前缴纳出资即意味着股东出资的期限已经届至,因而满足“未按期缴纳”的前提条件。从审判观点到立法的演变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中非破产加速到期还要满足“已具备破产原因”的条件,而到了新《公司法》,加速到期的适用条件已经修改为“公司不能清偿债务”,这说明新《公司法》充分体现了公司维持的观念,即“为公司生存而合乎商道发展”【杨秋林、杨士民:《论认缴出资的加速到期责任》,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95页。】的原则,“非破产情形下,所谓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本质不是股东丧失出资期限利益而履行约定的出资义务,而是股东应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履行出资的法定义务,是股东有限责任的实质内容”【钱玉林:《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证成》,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114页。】。该认识与催缴制度建立的观念不谋而合,无论是届期缴纳还是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的加速到期,本质上都是以出资换取有限责任,是股东履行对公司出资的法定义务,倘若不履行该义务,自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笔者认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也应当纳入催缴制度,作为董事的核查范围。
最后,是其他情形,包括未届期股权转让和五年认缴制。对于未届期股权转让,新《公司法》第88条第1款规定,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可以看出,本条并未改变出资届期缴纳的本质,而是增补出资责任人,以维护公司的资本利益。因此,未届期股权转让满足新《公司法》第51条规定之情形,适用该条规定。对于五年认缴制,新《公司法》第47条规定,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立法采取强制手段限制股东出资期限设置的自由,因此,无论公司章程载明的股东出资期限是多久,最迟至公司成立之日起满五年,股东就应当缴纳出资。但能否将该条理解为股东出资期限届至?笔者认为,不宜过于纠结文字表述,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中的提前缴纳出资尚且可以理解为出资期限届至,那么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新《公司法》强制规定的缴纳出资更可以理解为出资期限届至。因此,公司成立已满五年应当认定为股东出资期限届至,股东若未出资,可以对其进行催缴,甚至可以适用股东失权制度。
此外,如前所述,新《公司法》对股东出资催缴制度的适用范围,删除了《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中的出资不实情形,因此,从规则演变的角度来看,股东出资催缴制度不宜适用于出资不实情形。笔者认为,股东出资催缴制度的功能在于矫正认缴制带来的缴资难题,因而其与五年认缴制、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存在制度上的相通点,但针对出资不实问题,自《公司法》诞生之日起就早已有之,相应规则也较为健全,不宜再适用股东出资催缴制度。
(二)董事会对股东出资情况的核查程序
符合股东出资催缴制度的适用情形是开启核查程序的前提,新《公司法》仅仅明确了董事会应当核查股东出资情况,至于如何核查、核查什么内容、核查本身所代表法律意义,仍需要进一步解释。
第一,核查主体。新《公司法》明确规定出资核查的义务主体为董事会,直观地解释,“董事会”可能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以会议方式形成的董事会决议,二是作为公司常设机关的董事会。新《公司法》第67条并未明确董事会须以决议形式审查出资情况,而且第52条关于股东失权的规定,也表述为“董事会决议”可以发出失权通知,这表明若公司须以决议形式行使职权时,《公司法》往往会冠以“董事会决议”来特指,因而此处的“董事会”不宜限缩解释为董事会决议。有学者也指出,“‘董事会’不应僵化理解为董事会会议方式,而应区分义务履行的不同阶段,结合各阶段的义务特征及公司章程或董事会自行确定的工作方式,确定义务的具体承担者。”【王艺璇:《董事催缴出资义务的公司法解释》,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102页。】通常认为,董事会是公司的执行机关,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具体职能的承担则落实到每一位董事身上。但“如果公司较大,董事会直接管理公司业务不再可行,将主要进行决策和监督管理,往往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徐强胜:《公司权力的分配、分工与问责——董事会何以治理》,载《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39页。】因此,在实践中实际核查股东出资情况的,可能是公司的董事,也可能是董事会下设的各类机构,抑或公司的经理。但因新《公司法》明确了“负有责任的董事”,这意味着,不论具体执行人员是谁,责任人员比较确定,至于最终应如何认定“负有责任的董事”,后文将予以详述。
第二,核查内容。从新《公司法》第51条的规定来看,核查内容为“股东出资情况”,根据文义解释,“股东出资情况”应当包含公司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认缴出资情况、公司账目中记载的股东实缴出资数额及出资形式、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数额及出资形式、股东剩余认缴而未缴出资的出资期限等。这些内容代表了普遍意义上的“股东出资情况”,但如前所述,股东出资催缴制度的适用范围还包含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未届期股权转让、五年认缴制等情形,因此,核查内容还应有所扩展。具体而言,针对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情形,新《公司法》第54条规定其适用条件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因此,董事会核查内容应当包含公司是否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以及股东是否存在未缴纳出资的情形;针对未届期股权转让情形,董事会除了应当核查上述内容外,还应当核查相应股权是否有转让情况,以便在出资届期时一并主张权利;针对五年认缴制,董事会需要随时核查上述股东的出资情况,并时刻注意其未缴期限是否超过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此外,新《公司法》第51条规定核查的时间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笔者认为,对于该规定的解释,应当扩展至公司股东全部实缴出资之前。易言之,从公司成立后,到股东实缴全部出资前,董事会都应当定期进行核查,建立定期监督机制,而非仅限于公司刚刚成立时进行核查。
第三,核查意义。核查的法律意义包含两个方面:核查的内容本身与未经核查的法律后果。一方面,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系信义义务中的勤勉义务,故“负有责任的董事”完整地履行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理应包含定期核查。但如前所述,在大型公司中,董事会的职能已逐渐演化为监督职能,这意味着证明已尽核查义务的标准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在已建立了监督机制但未能确保该机制有效运行或者监督机制正当运行但公司出现重大财务危机却未能进一步调查等情形下,对于董事是否已尽核查义务并不明确。事实上,董事勤勉义务是一个“义务群”,内容包含知情和参与义务、监督义务以及其他义务【参见王真真:《董事勤勉义务制度的利益衡量与内涵阐释》,载《财经法学》2022年第3期,第154-158页。】,董事中的独立董事还应当持续关注和了解公司事务、审慎调查核实、有效表达意见【参见张婷婷:《独立董事勤勉义务的边界与追责标准——基于15件独立董事未尽勤勉义务行政处罚案的分析》,载《法律适用》2020年第2期,第91-93页。】,因此,勤勉义务并非一种修辞,而系真实的法律义务。【参见王真真:《董事勤勉义务制度的利益衡量与内涵阐释》,载《财经法学》2022年第3期,第151页。】认定董事是否有效核查股东出资情况,应当采用实质主义观念,即董事是否真切地了解股东出资情况以及公司偿债能力,而非仅仅看其是否建立了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倘若董事未履行核查义务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对此,仍应当立足于董事对股东出资催缴义务的勤勉义务性质进行探讨。董事是否违反勤勉义务应当作系统的审查,不仅包含董事是否积极采取措施降低损失,积极向股东发出催缴通知,也包含其前期是否尽职调查、是否知情参与、是否积极监督等。因此,倘若董事因未积极核查而错过催缴时间导致公司利益受损,应当认定其未积极履行催缴义务;倘若董事虽未积极核查,但积极进行了催缴,则不应认定其未履行催缴义务。
综上所述,核查股东出资情况,义务主体应当限于董事会,具体可以表现为董事会决议,也可以表现为董事会的下设机构或者某一特定董事;核查的内容既应当包括股东认缴出资、实缴出资等一般情况,也应当包括公司是否偿债不能、出资时间是否已逾五年等情况;核查的法律意义表现为董事是否履行勤勉义务的认定标准。
三、董事对股东出资催缴义务的履行
依据前述“前提条件—催缴程序—法律责任”的梳理,在满足前提条件,即董事会定期核查股东出资情况,且股东出资期限届至而未缴时,流程将进入催缴阶段。新《公司法》第51条、第52条对于催缴程序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包括发出书面催缴通知、通知上载明宽限期、股东失权等。但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核查股东出资的义务主体,以上两条规定并未明确催缴的义务主体以及适用中的裁量权等问题,因而仍需解释论上的进一步阐释。
(一)董事对股东出资催缴义务的分配
本文对于催缴义务的探讨建立在默认该义务归属于董事的基础上,但现实是,我国新《公司法》第51条似乎对此并未明确。如何理解“负有责任的董事”?这是新《公司法》第51条中最容易让人产生迷惑的表述,该条明确规定,公司成立后,“董事会”应当对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核查,发现届期未缴的,应当由“公司”向该名股东发出书面形式的催缴书,同时未履行该义务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52条中又规定“公司”催缴后股东仍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可以向该名股东发出失权通知。结合来看,新《公司法》第51条和第52条就催缴问题规定了“董事会”“公司”和“负有责任的董事”三类主体,笔者对上述条文涉及这三者的问题总结如下(见表1)。
由表1分析,催缴义务的实际履行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①董事会核查出资情况,发现届期未缴纳情形,董事会作出决议,由董事A对该名股东进行催缴。董事A以公司名义向该名股东发出催缴书,而后该名股东未履行义务,董事A提请董事会作出决议,以公司名义发出失权通知。事后发现,董事A将宽限期设置为一年,期间公司因缺少资金而陷入困境濒临破产。
②董事会核查出资情况,发现届期未缴纳情形,股东会作出决议,以公司名义对该名股东进行催缴,该名股东届期未缴纳,董事会对此作出决议,向该名股东发出失权通知。事后发现,股东会决议催缴宽限期为一年,严重影响公司发展,债权人起诉要求董事承担法律责任,但董事辩称催缴义务已经由股东会履行,自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③董事会核查出资情况,发现届期未缴纳情形,法定代表人(非公司董事)向该名股东发出催缴书,该名股东在认缴期限届满后仍未缴纳,提请股东会作出决议对该名股东发出失权通知。该名股东起诉称股东会无权对其发出失权通知。
从以上三种情况中可以看出,只有董事会核查出资情况属于立法明文规定,其后的催缴、失权通知等都没有完全明确的主体,并且即便立法规定了董事会负有核查义务,实践中也可能出现其他不同情况,如全程没有董事会参与,而全部由股东会甚至只由大股东具体操作。此时可以发现,仅第①种情况中有确定“负有责任的董事”,第②种情况中的董事会只履行了最终发出失权通知的义务,没有确定的“负有责任的董事”,而第③种情况中的董事会甚至都未参与催缴的过程,遑论在其中产生特定的“负有责任的董事”。根据这三种情况,在董事未履行或者未充分履行催缴义务时,股东、公司或者债权人请求董事承担法律责任,应当如何认定?对此,同样存在多种解释。
解释一:指定董事的情况下,由该指定董事承担法律责任。
解释二:无论是否有指定的董事,全体董事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解释三:由具体执行催缴义务的主体承担法律责任。
解释四:无论是否有指定的董事,全体董事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催缴系股东执行的除外。
解释五:指定董事的情况下,由该指定董事承担法律责任;未指定董事的情况下,由全体董事承担法律责任,但催缴系股东执行的除外。
由谁承担法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推应将催缴义务分配给谁,因为如果股东会履行了催缴义务反而要求董事承担责任,显然会陷入“股东犯错,董事担责”的悖论。笔者认为,应当采纳解释五来认定董事的法律责任,理由如下:一方面,催缴义务作为一种勤勉义务不仅仅是某一位董事的义务。若始终未指定某一位董事负责,则应由全体董事共同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在董事会全程未参与催缴而由股东会代为行使职权的情况下,要求董事会再履行一次催缴义务显然不符合实际,实践中,股东会取代董事会而径直经营公司的情形本就十分常见,由此追究董事会的责任显然不妥。依据新《公司法》第180条第3款采取的“实质董事”观念,控股股东若实际执行董事职责,也应承担信义义务。并且,当发生股东会代董事会履行催缴义务的情形时,股东会往往已经履行了义务,但该义务之履行并不妥当,如催缴宽限期过长或者过短,此时应当直接追究股东的法律责任。
(二)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是否有裁量权
笔者在梳理新《公司法》第51条、第52条后,将催缴义务的整体流程及法律后果总结如下(见图1)。
立法对于核查和催缴在表述上均为“应当”,并在其后又规定未履行该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应当为强制性义务。但新《公司法》第52条又规定了“可以”在催缴书中载明宽限期,似乎又为催缴制度设置了弹性空间。对此不免产生疑问,如果催缴书中载明宽限期为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是否合法?宽限期的规定在实践中是否有可能架空催缴制度?又或者,这是否是立法有意为之?想要解答这些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催缴制度入法的商业和立法背景,以及催缴义务作为勤勉义务的特性。
实践中,在新《公司法》颁布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即有公司在章程中规定了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有学者认为,是否必须“催”,应当区分公司内外关系,如涉及公司外部第三人利益,则公司必须催缴;如仅为公司内部关系,则完全交由公司自治。【参见袁碧华:《“认”与“缴”二分视角下公司催缴出资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202页。】这一观点充分尊重公司自治,较为贴合实践中部分公司在章程中规定催缴义务的性质,而且分情况决定是否催缴也比较符合催缴义务作为勤勉义务的性质。但在全面认缴制改革以前,通过垫资等非法途径规避实缴制约束的方式也并不少见。因此,无论是实缴制还是认缴制,商业实践都在不断探索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即便这种方式可能并不合法。“公司法的本质是商事法律制度,公司资本既是法律关注的对象,更是公司本身的事务以及资本市场的焦点,它在商业实践中展开的图像远比在公司法条文中呈现的面貌立体而丰富。”【刘燕:《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商业实践视角的观察》,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34页。】但立法的微小变动又会对商业实践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在对法律进行解释时更应直面商业实践这一鲜活的现实图景,而不是机械地以“应当”或者“可以”来作非黑即白的属性界定。
认缴制可能带来的缴资难题也曾引发学界对认缴制改革的质疑,认为实缴改认缴不仅欠缺合约逻辑和经济逻辑,也不符合我国的文化偏好。【参见蒋大兴:《质疑法定资本制之改革》,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第136页。】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认缴制释放的利好逐渐显现,质疑之声也逐渐减弱,但缴资问题依旧未能解决,由此引发了诸多对加速到期、催缴等问题的热议。事实上,学者关注的缴资问题在实践中可能呈现出不同样态,对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总结后可以发现,股东认缴届期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形。
情形一:公司亟需资金,而股东认缴出资已届期限,倘若不及时催缴出资,公司将难以偿还对外债务或者丧失发展壮大的机会。
情形二:公司发展蒸蒸日上,资金充裕,而股东认缴出资已届期限,催缴与否,在可预期的未来都不会对公司产生影响。
情形三:股东A是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为达成长期利益同盟关系而有偿赠与其公司股份,此时该笔认缴出资已届期限,倘若催缴甚至发出失权通知,公司很可能丧失这一客户,或者股东A系持有标的公司51%股份的母公司,标的公司本就是母公司的代工厂,如果母公司丧失股份,标的公司也将失去全部业务。
针对情形一,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是有能力进行催缴的董事都会以合法途径进行催缴,以避免公司处于不利境地。此时,新《公司法》第51条所赋予的催缴义务就变成了董事手中的有力武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倘若公司亟需资金是为了偿还债务,则无论是依据新《公司法》关于出资加速到期的规定,还是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的规定,相关债权人都可以直接请求届期股东在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此时是否进行催缴已无关紧要。针对情形二,董事是否催缴都对公司没有影响,因其在预期时间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故董事不进行催缴也不会触发新《公司法》第51条第2款的责任条款,所以从实然角度来讲,在董事不催缴且不给公司造成利益损失的情况下,董事并不会受到惩罚。针对情形三,新《公司法》第51条规定的情形会使其陷入尴尬境地,此时公司不缺资金则罢,倘若公司亟需资金,两害相权,则可能导致公司最终仍旧不会选择催缴,此时新《公司法》第51条显然并没有给公司两害相权的机会。由此可以看出,公司如何对届期股东继续催缴应当有权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届期必须严格履行催缴义务并不符合商业实践的需求8gd88Q+eg7s5Be7QMeWSn/ph4pf+yNvgyBC/QgsjRCc=,因而公司设置较长的宽限期并不必然违法,机械地将新《公司法》第51条理解为一种强制性规定,可能会造成法律对商业实践的过度介入。
前述三种情形传达了一项重要的观念,即商业的事应当交由商人去判断,法律不宜过多介入。然而,一旦商业实践的自治程度以损害为目的或者造成了实际损害,法律就需要对其进行干预。由此也可以看出,为何新《公司法》第51条规定只有在“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才会追究董事的法律责任,而并非不履行义务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显然是为了给予公司足够的自治空间。那么,对于设置较长宽限期的情况,将如何进行判断?首先需要假设,催缴系董事会作出的决策或者董事的行为。在这一前提下,如何判断董事是否违反了催缴义务?如前所述,董事催缴义务系勤勉义务,其判断标准应当遵照商业判断规则,即首先认定该行为符合商业判断,进而赋予股东、公司或其他主体以挑战的权利,此时应由董事举证证明其行为符合商业判断规则。判断董事行为是否符合商业判断规则,需要理解和适用新《公司法》第180条第2款,即董事勤勉义务的标准。美国主流观点以“二分法”认定勤勉义务的标准,即司法判定标准和行为标准,前者体现为商业判断规则,是一种类似于重大过失的标准,对注意程度要求较低,后者则停留在应然层面,即对管理者需要以普通人的注意程度来要求。【See Melvin Aron Eisenberg,The Divergence of Standards of Conduct and Standards of Review in Corporate Law,62Fordham Law Review437,437-439(1993).】德国则形成了“专家标准”,相较而言,我国新《公司法》第180条第2款所确立的是“严格客观标准”,与德国的“专家标准”相类似。这一标准适用于催缴义务,即要求董事要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法院应以“严格客观标准”作出判断,倘若董事的行为不符合这一标准,如无限延长宽限期并不符合“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标准,即应判定董事的行为违反催缴义务,并对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
四、董事违反对股东出资催缴义务的法律责任
完成前提条件、催缴程序的论证后,倘若董事未履行或者不恰当履行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应当如何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是催缴义务的最后一环,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前文既已明确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系勤勉义务,对新《公司法》第51条第2款的解释就应当沿着勤勉义务的理念与责任体系展开。但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范并未着意划分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界限,进而出现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混用的案例。【参见叶林:《董事忠实义务及其扩张》,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2期,第17页。】不仅如此,笔者认为,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对于违反勤勉义务的法律责任都未能建立起具有特殊性的规范和评价体系,以至于勤勉义务在实践中仅仅成为说理的工具而非裁判的依据。对勤勉义务的这一固有偏见不利于理解新《公司法》第51条所规定的责任条款,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董事违反股东出资催缴义务的认定标准与责任范围。
(一)董事违反对股东出资催缴义务的认定
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系勤勉义务,因此,对该义务的违反应当适用违反勤勉义务的认定标准。当前,世界各国通行的勤勉义务标准主要有两种,即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其中客观标准又分为严格客观标准和一般客观标准。主观标准早期盛行于英国,即只要董事尽到了其技能水平和经验所要求的一般勤勉,就视为其已履行了勤勉义务。有学者指出,不同董事被赋予了不同程度的经验和注意,因而唯一现实的勤勉义务标准只能是一个主观性的标准。【See A.J.Boyle,Draft Fifth Directive:Implications for Directors’Duties,Board Structure and Employee Participation,13Company Law No.1,at7(1992).转引自任自力:《公司董事的勤勉义务标准研究》,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85页。】不过这一标准陷入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悖论,引发了董事的不满,因而在后来的判例中形成了针对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并根据董事专业资质不同而分别适用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的局面。一般客观标准以美国为主,即要求董事尽到“普通谨慎勤勉之人”的标准即可。德国则采取严格客观标准,即董事在处理公司事务时应具备“普通谨慎之业务执行人或商人”的注意,这里的“业务执行人或商人”对公司事务的注意程度通常要远高于一般人,其实质是一种专家注意标准。【参见马一德:《公司治理与董事勤勉义务的联结机制》,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80页。】新《公司法》第180条第2款首次明确了勤勉义务的标准,即“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由此可以看出,新《公司法》第180条第2款采用的是严格客观标准。
勤勉义务的认定标准表明董事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为公司的利益尽职尽责,适用于催缴义务,就要求董事在履行催缴义务时要尽到一个管理者通常应当尽到的合理注意,即其履行或者变通履行催缴义务的行为应当符合管理者这样一个理性人的标准。倘若董事怠于履行义务而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则其行为显然不符合一个理性管理者所应当具有的合理谨慎,应当认定其违反了催缴义务。
不过,是否违反勤勉义务仍然要遵循商业判断规则,我国司法裁判中对此已有所实践。例如,某案件中的公司总经理判断失误,采购了一批存在质量瑕疵的货物,其公司客户因货物质量不合格不予提货,从而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之后公司以该名总经理违反勤勉义务为由主张其承担赔偿责任。【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640号民事裁定书。】该案的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采购货物存在瑕疵只能说明该名经理存在经营判断失误,并不能证明其主观上具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过错,故不能认定其违反了勤勉义务。再审中,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指出,勤勉义务所要求的尽一个普通谨慎之人在类似情况下应当尽到的合理注意,是经过实践而被逐渐总结出来的标准。面对不断变化的商事交易实践,如果要求每一个经营判断都是正确的,将导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过于小心谨慎,甚至厌恶交易机会,从而降低公司经营效率,最终不利于实现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在不涉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等可能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形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履行经营管理职责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在具体适用商业判断规则的问题上,美国法上的商业判断规则较为典型,其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对董事的保护程度较高,但是案件当事人对于消极事实的举证十分困难,原告作为股东或公司其实很难举证证明董事决策是“非善意”“未经充分知悉”或“非为公司之最大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所需要的商业判断规则应当是一种抗辩规则,即董事在被诉请承担责任时,其可以自行证明决策行为符合商业判断的几方面要件,即便其行为最终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只要该行为符合商业判断,仍然不应令其承担法律责任。
(二)董事违反对股东出资催缴义务的责任范围
董事违反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侵权责任,因为这其中还涉及与股东出资义务的区分、责任承担的对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认定等问题。
1.董事违反催缴义务承担的是独立责任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4款则规定,债权人可以请求未尽信义义务的董事承担“相应责任”,并且董事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由此可以看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虽然明确了董事对增资时股东认缴的出资负有催缴的勤勉义务,但归根结底这一勤勉义务所指向的仍然是股东的出资,董事对其未履行勤勉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相当于一种担保责任。而新《公司法》第51条所规定的法律责任产生的前提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即该法律责任并非指向股东未认缴的出资,而是指向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股东也未履行缴资义务,进而因资金缺乏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这种损失既可能表现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偿还对债权人的债务,使公司资金出现短缺,也可能表现为公司因股东未出资而陷入财务困境,甚至破产等情形。所以,新《公司法》第51条情形下董事违反催缴义务并承担法律责任的逻辑是“董事对公司负担信义义务——董事未履行该信义义务——造成公司损失——董事承担法律责任”,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情形下董事法律责任的逻辑则是“债权人对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代位权【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规定代位权问题的探讨,可参见刘俊海:《论公司债权人对瑕疵出资股东的代位权——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载《中国应用法学》2023年第1期,第44-57页。】——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董事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可以看出,两种责任的逻辑存在显著差异,责任指向的对象也明显不同。
2.董事违反催缴义务应当向公司承担责任
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与新《公司法》第51条的对比来看,董事违反催缴义务所应当承担责任的对象并不相同,前者指向债权人,后者指向公司。在已明确董事催缴义务系信义义务的前提下,违反催缴义务应当承担责任的对象问题实际上就演变成了信义义务的对象问题。通常情况下,信义义务的探讨都建立在董事与公司之间系受托人与信托人的信托关系基础上,但关于公司的各种理论似乎又模糊了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例如,以公司法的团体生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为代表的公司理论即主张董事作为受托人,既要对公司负责,又要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这些理论中,董事虽然是公司的受托人,但同时也是股东、债权人、社会公众的受托人。【See Margaret M.Blair&Lynn A.Stout,A Team Production Theory of Corporate Law,85Virginia Law Review247(1999);Stephen Bottomley,The Birds,The Beasts,and The Bat:Developing aConstitutionalist Theory of Corporate Regulation,27Federal Law Review243(1999).】但这类观点遭到公司契约论的质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要求董事考虑非股东利益,会导致董事在经营决策时无所适从。【参见[美]弗兰克·H.伊斯特布鲁克等著:《公司法的逻辑》,黄辉编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不过公司契约论主张的股东利益至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并不承认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信托关系。依据对信托关系的划分,信托分为对人的信托和对目的的信托【See Paul B.Miller&Andrew S.Gold,Fiduciary Governance,57William&Mary Law Review513,519-524(2015).】,笔者认为,董事对公司更符合一种目的信托,即以营利为目的或者基于公司章程而设定的其他目的。这也能解释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合法性,因为部分情况下的公益行为或者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经济价值,如企业捐赠可以提高企业知名度,为其带来更高的收益。因此,董事只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在这一背景下,董事违反催缴义务,本质上是违背了其对公司负有的信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倘若债权人代位请求董事承担替代股东出资的责任,其原理也应当是董事对公司承担责任后,公司再对相应债务进行清偿。
3.如何理解“给公司造成损失”
相较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的规定,新《公司法》第51条所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容易在实务中与股东未缴纳之出资混淆。笔者认为,“给公司造成损失”应当作广义的解释。其一,催缴义务虽然指向股东认缴而未缴的出资,但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股东也未缴纳出资,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给公司造成等同于股东未缴纳出资数额的损失。如前所述,倘若公司资金充裕、经营良好,即便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也不会给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害。因此,“给公司造成损失”不能等同于股东未缴纳出资,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也不能就此认定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其二,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与“给公司造成损失”之间应当存在因果关系,这一因果关系的认定符合勤勉义务的一般认定标准,即符合严格客观标准和排除商业判断。其三,在完成违反催缴义务和存在因果关系的论证之下,所造成的损失才应当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给公司造成损失”,但这类损失仍应当限于消极意义上的损失,即实际利益的减损,而非公司未来可得利益的丧失。
五、余论
新《公司法》第51条明确规定了董事催缴义务并在第52条辅以股东失权制度,既夯实了董事责任,又加强了董事会的权限,将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学界和实务界的由认缴制所带来的缴资难题。但董事催缴义务与股东失权制度入法并非终点,相反,它也可能带来一系列法律适用上的问题。除了本文所指出的前述问题外,新《公司法》第51条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之间的衔接或协调问题同样也是接下来司法解释应当重点关注的内容。在近些年的司法裁判中,法院经由《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的扩大解释而主张董事对股东出资负有催缴义务,也多是以增资出资与设立出资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为前提。因此,在新《公司法》已正式施行的情况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是否需要修改以及如何修改也将成为董事催缴义务延伸出的一个重要问题。ML
On the Obligation of Directors to Demand Payment from
Shareholders for Capital Contributions
WANG Yuying
(School of Juris Master i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102249,China)
Abstract:The new Company Law has introduced asystem for demanding shareholders to pay their subscribed capital and asystem for shareholders to lose their rights,which has solved the longstanding problem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ields,and can be regarded as asignificant progress in legislation.However,the legal nature of the obligation to demand payment,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obligation to demand payment,the performance of the obligation to demand payment,the determination of violations of the obligation to demand payment,and their legal responsibilities still need further explanation.The obligation of directors to demand payment from shareholders for capital contributions should first be afiduciary obligation,and secondly,it should be adiligent obligation of directors towards the company.The prerequisite for demanding payment is to verify the capital contribution of shareholders.The scope of verification should not only include the overdue payment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but also include the early payment of capital by shareholders caused by accelerated maturity of capital contributions and the fiveyear subscription system.Therefore,the verification content includes the subscription and actual payment status of shareholders,whether the company is unable to repay debts,etc.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s51and52of the new Company Law,the obligation to demand payment can be fulfilled by directors in practice,or by any entity that can represent the company’s organs.When adirector fulfills the obligation to demand payment,due to the diligent nature of the obligation to demand payment,the director’s call for shareholder contributions can be freely exercised based on commercial judgment during the grace period.The determination of adirector’s violation of the obligation to demand payment should follow“strict objective standards”,and“causing losses to the company”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negative reduction in the actual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Directors should bear legal responsibility to the company,and only to the company.This responsibility is not equivalent to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replacing shareholders in fulfilling their capital contribution obligations.
Key words:subscription system;obligation to demand payment;diligence obligation;fiduciary duty
本文责任编辑:黄 汇 武 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