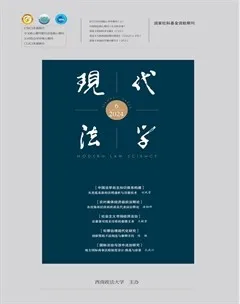刑事一体化视角下的轻罪应对
2024-12-18喻海松
摘 要:我国现行《刑法》未对轻罪作出明文规定,但大致可以将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归入轻罪的范畴,当然特定犯罪除外。近年来轻罪激增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立法层面增设轻罪这一直接原因,也有司法层面基于刑罚轻缓化的政策要求和形势变化的时代背景而提升定罪量刑标准这一重要原因。未来,应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妥当应对轻罪。就贯彻刑法谦抑原则而言,最为紧迫的是通过优化定罪量刑标准有效控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多发轻罪的入罪范围;就推进综合治理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实现行刑有序衔接,既要立足当下通过司法裁量实现“出刑转行”,又要立足长远谋划对《刑法》规定的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允许比照适用,实现“两法衔接”,切实发挥《治安管理处罚法》事实上的“轻罪法”作用;就贯彻程序优先理念而言,要充分发挥审前分流作用,避免轻罪案件“扎堆”进入审判程序,并在降低羁押率的前提下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就完善前科制度而言,可以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突破口,并采取“程序修法先行,实体修法跟上”的具体策略,进一步实现犯罪的轻重有序治理。
关键词:轻罪;行刑衔接;危险驾驶罪;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4.06.12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迈入轻罪时代,此前的犯罪应对模式得以相应调整。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醉驾犯罪对策的调整。①当前,亟须通过从整体层面优化思路、从操作层面强化举措的方式推进轻罪的系统应对,特别是宜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立法与司法并行、综合治理与刑事治理结合的思路,在找准原因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妥当调适轻罪应对模式。基于此,本文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视角,在厘清轻罪范围的基础上,分析轻罪成因并评析当下轻罪应对策略,提出轻罪应对模式的未来改进之道,以期助益体系化治理并务求实效。
一、轻罪范围的厘清
顾名思义,轻罪就是处罚较轻的犯罪。从域外立法来看,一些国家在刑法中明文规定了轻罪概念。例如,《德国刑法典》第12条规定,轻罪是指最高刑为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科处罚金刑的违法行为。【参见《德国刑法典》,徐久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长期以来,我国缺乏区分轻罪与重罪的传统,而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亦未对轻罪作出明文规定。在此背景之下,确有必要对轻罪的范围加以厘清。
(一)以刑罚轻重作为轻罪与重罪界分的基本标准
通常而言,罪之轻重取决于刑之轻重。随着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将三年有期徒刑作为轻罪与重罪的分界线,把轻罪界定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本文亦原则上赞同这种划分,但同时认为刑罚较轻是认定轻罪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有必要讨论的问题是,界定轻罪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划分轻罪与重罪,目的在于对轻罪采取不同于重罪的刑事对策。【例如,就德国而言,“在实体法上,在法律技术上加以简化的两分法是为区分刑事可罚性的等级服务的。因此,重罪的未遂总是应受刑罚惩罚,轻罪的未遂仅仅在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应受刑罚惩罚(第23条第1款)。教唆未遂和其他一些处在参加犯罪之前阶段的情况,在重罪时应当受到刑事惩罚,但在轻罪时一般不会受刑罚惩罚(第30条)。公职资格的丧失和选举资格的丧失也以类似的方式与这个区分相联系(第45条第1款)”。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这就要求纳入轻罪范围的犯罪在罪质上具有相近性,适宜采取相同的对策。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的罪质通常相近,但亦有例外。特别是在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军人违反职责等犯罪中的不少罪名,法定刑配置亦包括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将上述犯罪纳入轻罪的范畴,实际不利于对其采取适宜的政策。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以下简称《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对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在刑满释放前经评估确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作出责令其在刑满释放后接受安置教育的决定。【《反恐怖主义法》第30条第1款规定:“对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在刑满释放前根据其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服刑期间的表现,释放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等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应当听取有关基层组织和原办案机关的意见。经评估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向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安置教育建议,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显然,对于所涉犯罪即使刑罚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亦不应纳入轻罪的范围。
此外,还有必要提及微罪的概念。顾名思义,微罪就是轻微的犯罪。有观点认为,微罪是与重罪、轻罪相对应的概念,微罪与轻罪的分界线应设定为一年有期徒刑。【参见梁云宝:《积极刑法观视野下微罪扩张的后果及应对》,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7期,第36页。】本文虽然原则上赞成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界定微罪的标准,但同时主张将适用缓刑的犯罪也纳入微罪的范畴。从形式上看,缓刑的对象包括被判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形,超过了前述对微罪的刑罚以一年有期徒刑为界的主张。但是,就一般社会观念和实际效果而言,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会轻于一年有期徒刑实刑。基于此,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或者适用缓刑的犯罪都可以纳入微罪的范畴。同时,不宜将微罪作为与轻罪相区分的概念。实际上,微罪应属于轻罪中法定刑较轻的部分,二者属于包容关系而非排斥关系。从立法上看,妨害安全驾驶罪、危险作业罪、侵犯通信自由罪、高空抛物罪等罪名的法定刑均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均可以纳入微罪的范畴;而危险驾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代替考试罪的最高法定刑均为拘役,属于微罪之中刑罚更轻的微罪。将微罪纳入轻罪之中,可以对微罪直接适用轻罪的模式,并基于微罪的特殊性采取更为特别的对策,以促使微罪的应对更为有效。
(二)区分立法成因与司法成因细分轻罪
我国有学者将轻罪划分为了纯正的轻罪与非纯正的轻罪。其中,纯正的轻罪是指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非纯正的轻罪,也可以称为罪量意义上的轻罪,是指无论犯罪的最高法定刑是否为三年有期徒刑,只要该罪的法定刑中包含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该部分犯罪就属于轻罪。【参见陈兴良:《轻罪治理的理论思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3年第3期,第5-6页。】本文虽然原则上赞同上述类型划分,但认为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立法成因的轻罪与司法成因的轻罪。
有效应对轻罪必须做到“对症下药”,这就要求厘清轻罪的成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区分立法成因与司法成因。唯有如此,方能对轻罪的现状作出妥当的评价,同时对轻罪的应对提出有效建议。正如后文所述,近年来轻罪数量和占比的大幅增长,既有立法层面增设轻罪这一直接原因,也有司法层面基于刑罚轻缓化的政策要求和形势变化的时代要求而提升定罪量刑标准这一重要原因。不讨论轻罪的成因,径直质疑当前轻罪占据主导地位的犯罪结构,无疑是不可取的。缘于具体案件的情况比较复杂和司法裁量的需要,《刑法》分则中立法者给多数犯罪设定的法定刑幅度区间跨度较大,从而使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具体犯罪触犯的罪名法定刑配置较高但实际判处的刑罚较轻的情况。以盗窃罪为例,法定刑涵括“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等区间。随着相关司法解释对升档量刑标准的提升和对盗窃行为得手数额规定得越来越低,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盗窃案件越来越多。显然,这类轻罪的形成,应当主要归于司法成因,与立法增设而形成的轻罪具有明显不同。由此可见,区分立法成因的轻罪与司法成因的轻罪具有现实意义,这是深入分析轻罪形成原因和妥当应对轻罪的前提和基础。
基于此,借鉴纯正的轻罪与非纯正的轻罪的区分方法,可以将轻罪区分为立法成因的轻罪与司法成因的轻罪。所谓立法成因的轻罪,是指立法设定的轻罪,即立法规定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此类犯罪在具体适用之中必然属于轻罪。所谓司法成因的轻罪,是指司法形成的轻罪,即立法规定的法定刑虽然包括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但最高法定刑超过三年有期徒刑的犯罪,此类犯罪在具体认定时并不必然属于轻罪,如果具体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则该部分犯罪属于轻罪的范畴。
二、轻罪多重成因的探究
妥当应对轻罪的前提是厘清轻罪现状的成因。轻罪激增不能简单归因于立法层面增设新罪,而是立法、司法、程序等多个层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立法成因:立法体系与轻罪适用
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基于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需要,先后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12部刑法修正案,对《刑法》作了13次修改。1997年《刑法》规定了413个罪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法释〔1997〕9号)确定了413个罪名,《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高检发释字〔1997〕3号)确定了414个罪名。】,历经多次扩充之后形成了483个罪名的现状。在新增罪名中,相当比例的罪名配置的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且个别罪名配置的法定刑为拘役。这意味着我国进入了轻罪立法时代。轻罪立法体系的逐步成型对司法适用中轻罪的数量激增和占比攀升产生了直接影响。
1.基于社会危害考量增设轻罪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领域越来越广,需要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规范加以规制,以有效防范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增设最高法定刑为拘役的危险驾驶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增设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最高法定刑为一年有期徒刑的妨害安全驾驶罪、危险作业罪、高空抛物罪。这些轻罪的增设,缘于对新出现的社会风险防范的需要。例如,增设危险驾驶罪就是为了防范道路危险驾驶行为逐渐增多的风险。
2.基于犯罪治理方式调整增设新罪
新近《刑法》修正体现了犯罪治理方式的革新,最为明显的当属刑法防线的适度前移。具体而言,基于有效防治犯罪的需要,对预备行为或者帮助行为独立入罪处罚。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对网络犯罪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独立入罪,增设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正因为如此,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际上属于兜底罪名(堵截性罪名),即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或者帮助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在无法构成其他犯罪的前提下,可以适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予以惩治,以堵塞刑法规制漏洞。【正因为如此,《刑法》第287条之一和第287条之二的第3款均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作为堵截性罪名,自然不能配置过高的刑罚,否则无法体现堵截的属性。基于此,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定刑均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属于典型的轻罪。
3.基于分流入刑需要增设新罪
新近《刑法》修正所增设的不少犯罪原本系受行政处罚的行为。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例,其重要使命之一即为“做好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法律上的衔接”。【参见李适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说明——2014年10月2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5年第5期,第827页。】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废止了实施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难以适应惩治、震慑所涉行为的现实需要。为了填补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间的“断档”,适当扩张刑法的规制范围,对过去应予劳教的行为适度分流入罪,已是必然。基于此,《刑法修正案(九)》通过扩充罪状、增设新罪等方式,将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就增设新罪而言,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就是合适的例子,即对于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确应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但配置的刑罚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属于典型的轻罪。
4.基于试探性立法属性增设新罪
新近《刑法》修正增设的不少犯罪,并非简单的犯罪圈扩充,而是体现了犯罪规制理念的变迁。例如,与此前规制网络犯罪的立法思路明显不同,《刑法》第286条之一规定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则是在信息网络日益普及的时代背景下,针对犯罪与信息网络交织的情况,基于强化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而增设的专门罪名,旨在通过有效落实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而有效防范信息网络违法犯罪的发生。这实际上属于“新型信息网络犯罪”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犯罪的增设并无先例可循,实际上属于试探性立法,配置较低的刑罚也是务实的选择。缘于此,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属于典型的轻罪。
(二)司法成因:司法激活与轻罪适用
立法是基础,司法是关键。新近刑法增设轻罪属于客观事实,但不能据此径直将轻罪激增归因于立法。毫无疑问,《刑法》分则配置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罪名在全部罪名之中仍有相当比例,即立法层面的罪名仍然以重罪为主。由此可见,对于轻罪激增的现状,除了立法层面的原因之外,更应当关注司法层面的原因。
1.司法对策调整激活纯正的轻罪的适用
立法所增设的纯正的轻罪,亦需要通过司法环节才能转变为实际案件。特别是同一罪名面临较大幅度的适用差异,正是说明司法对轻罪的激增作用不应被忽视。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例,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的最初几年,该罪名的适用并未出现案件激增的情况,甚至可以说案件较少。然而,2020年10月“断卡”专项行动开展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激活”。【参见陈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相关适用问题》,载《人民司法》2021年第35期,第41页。】在立法规定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罪名适用得以激活,原因恰恰在司法层面。具体而言,司法实务改变此前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主要限制在线上帮助行为的立场,逐步对提供“两卡”(手机卡、信用卡)这一线下帮助行为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并最终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法发〔2021〕22号)第7条所确认。这可谓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的重要转折,即从早期的技术帮助行为扩展到线下帮助行为,对相关案件数量快速增长影响重大。
2.刑罚轻缓化激活非纯正轻罪的适用
司法适用中的轻罪不限于纯正的轻罪,还包括非纯正的轻罪。而非纯正轻罪的激增,与刑罚轻缓化直接相关。实际上,轻刑化的趋势一直在持续,重刑率从“严打”时期的47.39%,到21世纪前十年的20%以上,再到2013年以后基本维持在20%以内,2014—2016年甚至在10%以内。【参见卢建平:《为什么说我国已经进入轻罪时代》,载《中国应用法学》2022年第3期,第137页。】刑罚轻缓化的成因当然很多,但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刑法》分则罪名的法定刑幅度通常较大,司法裁量空间就较大,这就使升档量刑标准的提升可以“将重罪变轻罪”。例如,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升档量刑标准为“数额巨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8号)对“数额巨大”的标准作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由此前“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提升至“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这就使相当数量此前应当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盗窃案件转而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法定刑,从而进入轻罪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将诈骗罪“数额巨大”这一升档量刑标准由“三万元以上”提升至“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实际亦起到类似效果。可以说,升档量刑标准提升之后,对重罪与轻罪的转换可谓“立竿见影”,效果直接、显著。
(三)程序成因:查证困难与轻罪适用
轻罪的增多,除了立法层面增设轻罪和司法层面刑罚轻缓化的原因之外,实际上还应当从刑事程序的视角加以考察。细究可以发现,就非纯正的轻罪而言,一些情形之所以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能原因在于侦查难以查明全部犯罪事实;而就纯正的轻罪特别是堵截性罪名的适用而言,可能原因在于侦查所限未能查明全部犯罪事实,进而无法适用更重的罪名。再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例。如前所述,该罪的定位为堵截性罪名。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绝大多数犯罪都与互联网发生关联。有别于传统犯罪的帮助行为,由于互联网的跨地域特性,网络犯罪中的帮助行为往往没有固定的帮助对象,即传统帮助犯一般是“一对一”,而网络帮助犯通常是“一对多”。这就使得对相关犯罪做到全链条、全环节侦查清楚越来越困难,可以查清的犯罪事实往往是碎片化的犯罪事实,得以移送的证据所能证明的也是碎片化的犯罪事实。由此,基于对碎片化犯罪事实的考量,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不能适用重罪,而只能适用轻罪。可以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最近几年增长速度最快的罪名,当然可以反映对网络犯罪的惩治力度不断加大。但是,堵截性罪名的大幅适用,可能是由于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省时省力”,即囿于查证现状而将惩治重点集中于“两卡”环节,而很难做到在全部查实被帮助的电诈犯罪组织者、实施者所涉行为的基础上以重罪处断。
三、轻罪应对模式的缺憾
在厘清轻罪激增成因的基础上,本部分从罪刑均衡、综合治理、附随后果三个方面对轻罪现行对策展开评析,分析轻罪应对模式存在的缺憾。
(一)罪刑均衡方面
就立法层面而言,轻罪增设的整体趋势缘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背景。可以说,通过扩张刑法的规制范围以有效应对风险,实现对法益的有效保护,是现实所需。而就司法层面而言,轻罪激增符合刑罚轻缓化的整体趋势,大致亦应予以肯定。当然,从新近《刑法》修正来看,也存在对部分轻罪处罚过严的问题。
第一,部分轻罪可以通过非刑罚的手段解决。根据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不能单纯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将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纳入轻罪范畴加以规制,特别是对于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实现有效防范的危害行为,更加应当慎用刑事手段。然而,新近《刑法》修正增设的部分轻罪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上述要求。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配置的法定刑为“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属于典型的轻罪。但细究可以发现,通过完善相关管理手段,如建立健全验证系统,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的现象可以大幅减少。因此,这类行为在犯罪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方面似可再作斟酌。
第二,部分轻罪未设置入罪门槛。罪刑均衡要求刑法秉持谦抑性,而“刑法谦抑性……关键是要实现妥当的处罚”【周光权:《论通过增设轻罪实现妥当的处罚——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再阐释》,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第42页。】。需要注意的是,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是我国法律的一贯传统,犯罪的成立通常应当有一定的门槛。然而,为了彰显刑事打击,新近《刑法》修正对不少新增犯罪未设置入罪门槛,如对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行为入罪,未设置“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的限制条件。这实际上是刑法的过度介入,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二)综合治理方面
对刑法的过分依赖,易导致社会管理能力的弱化,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于此,对于危害社会行为,应当坚持多元共治、多种手段并用,避免把所有的任务都推给刑法。
然而,新近《刑法》修正增设的轻罪,就在综合治理方面存在进一步加强的空间。例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刑罚配置相对而言并不重。但必须承认,数以万计的人被打上“罪犯”的烙印,势必影响数以万计的家庭。而“两卡”案件高发,与手机卡、银行卡的管理制度不健全和落实不到位不无关系,实践中不少“两卡”人员实际就是在制度漏洞之下因贪图小利而身陷囹圄。对此,依靠刑事惩治只能治标,必须通过完善社会治理实现治本。又如,在《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纳入危险驾驶罪的规制范围之后,随即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人“处十五日以下拘留”的规定。【参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1年4月2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1年第4期,第433页。】这就使得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没有行政处罚空间,这也对此后醉驾案件的激增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一做法明显不符合行刑衔接的要求,难以适应醉驾案件的复杂情况,不符合综合治理的基本理念,属于将多元措施改为单一措施。
(三)附随后果方面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与重罪相分立的轻罪制度,实际是将适用于重罪的相关规定直接适用于轻罪,这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在这些负面效果之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犯罪附随后果制度。1997年《刑法》增设了前科报告制度,第100条规定:“依法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以前科报告为中心的前科制度,是预防犯罪的基础性制度,也是加强社会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保障性制度。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律政策调整,犯罪前科“标签化”日益凸显,犯罪附随后果过于严苛的弊端日益突出。一方面,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都有对犯罪人员从业的限制性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对犯罪人员有明确的从业禁止或限制,甚至许多社会性组织和单位内部管理规定,都有对犯罪人员从业的限制性规定。这说明,犯罪附随后果的设立依据相当宽泛,存在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嫌疑。【参见张庆立:《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重塑》,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第117页。】另一方面,前科制度在具体执行之中“走样”。有的地方制发规定,使犯罪人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近亲属实际遭受犯罪附随后果的不利影响。例如,有的市辖区议事机构发布通告,对涉某类犯罪重点人员采取惩戒措施,其中对涉罪重点人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近亲属在受教育、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权利进行限制。【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23年12月26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4年第1期,第33页。】
在某种程度上,犯罪附随后果的严苛程度可能超越对犯罪人员科处的刑罚。在轻罪不断激增的趋势下,这就愈发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例如,就危险驾驶罪来说,对被告人判处拘役,处罚的程度并不太重,但偏重的是刑罚以外的附随后果,尤其是职业限制。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的罪犯,与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犯罪附随后果方面没有实质区别,都会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并且在自身和子女就业、报考公务员、参军等方面受到一系列限制。【参见吴春妹、贾晓文、李静雯:《刑事一体化视野下轻罪治理的系统思考》,载《中国检察官》2024年第1期,第6页。】基于此,当下亟须对轻罪的附随后果制度作出调整,尤其是要合理地限制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适用范围。【参见刘炳君:《论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反思与限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第133页。】
四、轻罪应对模式的调适
整体而言,我国轻罪现状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契合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但也客观存在罪刑均衡不够、综合治理不深、附随后果过重等突出问题。基于此,根据实践反映的问题作出调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轻罪应对体系,已是必然要求。未来,应当坚持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研究推进,融理念与实操、实体与程序、法律与政策为一体,更好地实现轻罪应对的现代化。
(一)贯彻刑法谦抑原则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轻罪犯罪圈在做加法的同时,也应当做减法。唯有如此,才能将刑法谦抑原则贯彻落实到位,有序衔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避免将危害社会行为动辄交由刑法规制。
1.合理划定轻罪的规制范围
长远来看,对于部分社会危害不大的轻罪,应当考虑适时推进非犯罪化,在不断健全社会管理手段的前提下,将其交由行政处罚措施加以规制。如果说立法系统推进轻罪的非犯罪化尚属远景目标,那么当下至少应当对轻罪妥当设置入罪门槛,避免适用的泛化。一方面,立法对轻罪要慎用无门槛入罪的模式,以情节、后果等为标准设置入罪门槛;另一方面,司法要通过妥当把握轻罪的入罪门槛,合理确定轻罪的规制范围。
基于行刑界分的要求,无论是实害犯还是非实害犯,都应当要求一定的入罪门槛。特别是绝大多数轻罪都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即将入罪门槛交由司法裁量。对此,当然要靠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处理中切实履责,妥当把握入罪门槛。同时,对于适用频度较高的常见轻罪,也要及时总结司法经验,明确入罪标准。当下,最为要紧的是对轻罪适用“大户”妥当设定入罪门槛,对轻罪数量进行适度调节。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适用的激增,与《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之后该罪的入罪标准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直接相关,而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3〕15号)更是直接固定这一规则。该意见第1条第1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当时认为,“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100毫升是根据我国驾驶人员生理特点,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多方论证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且实践操作多年,已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可以采用”。参见高贵君、马岩、方文军等:《〈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3期,第20页。】而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高检发办字〔2023〕187号)(以下简称《2023年醉驾意见》)采用了多元化入罪标准【参见苗生明:《醉酒型危险驾驶的治罪与治理——兼论我国轻罪治理体系的完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1期,第5页。】,虽然对于具有该意见第10条规定的15种从重处理情节的醉驾案件仍然坚持80毫克/100毫升的入罪标准,但实际上已将常态醉驾案件的入罪标准提升至了血液酒精含量达到150毫克/100毫升以上。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审判工作数据,2024年上半年危险驾驶罪案件一审收案同比下降12.9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24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2024年7月19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38521.html。】由于醉驾在危险驾驶刑事案件中占据绝对比例,所以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随着入罪标准的优化和入罪门槛的适当提升,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进入审判环节的数量已有明显下降,更加符合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
由此,可以将上述模式借鉴应用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其他轻罪。目前看来,对于入罪范围的限制,仅在理念政策层面作倡导性规定似乎难以收到切实成效。例如,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法发〔2021〕22号)实际已经顾及“两卡”案件带来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激增的情况,在第16条强调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把握,要求“区别对待,宽严并用,科学量刑,确保罚当其罪”,并在第3款专门强调从宽处理的情形。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上述规定未能有效控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激增的局面【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审判执行工作数据,2023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数量位居前五,上升23.89%。参见《最高法发布2023年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主要数据》,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2024年3月9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27532.html。】,这与上述规定过于抽象不无关系。为解决这一问题,有效缓解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激增的局面,必须改变对线下帮助行为与线上帮助行为适用统一入罪标准的模式,对前者适当提升入罪门槛。实际上,《刑法》第287条之二所列举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和“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均应系网络犯罪产业链之中法益侵害程度较大的环节,都可以归属为线上帮助的范畴。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涉帮助类型差异较大,特别是对于法益侵害程度尚难与“技术支持”直接相当的“两卡”案件而言,更需要借助罪量要素的考察适当限定入罪范围。基于此,借鉴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应对的成功经验,宜进一步优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入罪标准,特别是对于流水金额较大、获利数额较小的“两卡”案件,应视情况不再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以妥当界分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
2.融合总则与分则适用《刑法》
对于《刑法》分则罪名的适用,不能仅考虑分则条文本身,还应当顾及总则的规定,以决定是否需要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特别是要坚持综合考量社会危害大小,准确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和第37条的规定,坚决改变“构罪即罚”的观念。
一是坚持综合考量规则。综合考量是近年来不少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鲜明特点,具体司法活动中宜准确把握相关精神。例如,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也是近年来适用较多的轻罪。对此,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2号)要求,办理涉野生动物案件,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特别是该解释第13条第2款明确规定“根据本解释的规定定罪量刑明显过重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即允许根据综合考量不再适用该司法解释确定的定罪量刑标准。这实际可以为其他轻罪所借鉴,对经综合考量确实危害不大的行为作出妥当处理,合理把握其入罪范围。
二是准确适用出罪免罚规定。《刑法》第13条划定了犯罪的界限和范围,其考虑到司法实践的复杂情况,专门设置“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但书条款,交由具体办案机关根据个案情况把握。因此,《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具有司法出罪功能。【参见左智鸣:《〈刑法〉第13条但书出罪机制的反思与重构》,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第97页。】同理,《刑法》第37条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行为规定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上述条文实际为司法裁量留有适当空间,可以在具体罪名特别是轻罪的适用之中妥当把握。整体而言,司法实务对但书存在不敢适用的情况,未能使但书应当具备的调节普遍刚性规则和个案复杂情况的立法目的得以实现。司法实务应当综合全案情节考量,对于明显不宜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要敢于适用但书规定。特别是对于一些定罪量刑标准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入罪追究明显背离民众感情的案件,要充分运用但书的规定,避免刑事处罚的泛化,确保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同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行为,也要善于依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
(二)坚持综合治理对策
刑法只能治标,尚难治本。对轻罪应当坚持多元化的治理机制,以实现标本兼治。我国轻罪的刑事对策调适,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由单纯“治罪”转变为综合“治理”。应对轻微危害社会行为,既要靠刑事惩治开路,更要靠健全前置规定和建立长效机制,在慎用刑事手段的前提下实现防范、惩治、治理一体化,实现对轻罪的有效治理。
1.坚持实现防范为主
随着犯罪结构的变化,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大多不再是穷凶极恶的“罪犯”,S4ZkuCA1q09pKwUxCOjm4VIx6Y65bDc+Wp4Cc1H4g9A=而可能是具有正当职业、稳定收入、良好家庭和受过较好教育的“普通人”。可以说,不少轻罪行为实际属于“机会型”犯罪,其之所以发生与相关预防措施不到位有一定的关系。换言之,如果强化相关预防措施,那么完全可以“防患于未然”,有效减少相关犯罪的发生。以盗窃罪为例,当前窃电犯罪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就在于防范措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使防范涉电违法犯罪的效能变得更高、更快、更准。
总而言之,轻罪应对不能止步于案件办理,而应当高度重视源头治理,分析犯罪滋生的原因,以治理方式的完善、治理广度的延伸、治理效果的提升加强犯罪预防。唯有如此,方能铲除犯罪滋生的原因,避免犯罪蔓延。
2.克服“刑法先行”现象
不少轻罪特别是纯正的轻罪,属于行政犯的范畴。就行政犯而言,理想的状态应当是先有前置法律法规规制,后由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的刑法加以规制。然而,实践中不少却是“刑法先行”,这既有碍相关罪名的具体适用,也影响实际效果。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设立之初就是纯正的轻罪,即使增配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之后,具体适用亦主要表现为轻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系行政犯,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为前提。然而,就公民个人信息领域而言,刑法实际先于其他部门法明确了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界限。由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适用存在不少疑难问题。例如,对于公开的个人信息,由于信息已经处于公开状况,获取无须征得同意,对此应无疑义。但是,在获取相关公开信息后进而提供的行为,是否需要取得“二次授权”(在获取相关信息后,提供相关信息需要告知同意),则存在较大争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未对所涉规则予以明确,所以导致实践中对相关案件的定性不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后,相关问题才得以明确。【相关法律否定了“二次授权”的规则。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六)依照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第27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可以说,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真正有效的治理,是在相关前置法健全之后。随着《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前置法律的健全,个人信息通过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全方位保护的体系得以构建,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系统治理才能真正得以推行。
鉴于此,应对轻罪要注意防止“刑法先行”局面的效仿,坚持将行政法律法规的构建“挺在前面”,真正体现刑法的“二次法”属性。
3.实现行刑有序衔接
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发力,是应对轻罪的重要环节。应对轻罪,不是把所有危害行为都交由刑法惩处,而是要为行政处罚留有适当空间。基于此,对危害尚不明显的行为,应当考虑优先适用行政处罚措施,慎用刑法手段。如前所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删去了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适用行政拘留的规定,实际上挤压了对所涉行为适用行政处罚的空间,有失妥当。基于此,《2023年醉驾意见》在优化入罪标准的基础上,拓展了行政处罚的范围。具体而言,其第20条第1款明确规定:“醉驾属于严重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行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在决定不予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移送审查起诉前,给予行为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处罚。根据本意见第十二条第一款处理的案件,公安机关还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相应情形,给予行为人罚款、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可见,上述规定将醉驾解释为严重的酒驾。这实际是囿于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条文规定的“无奈之举”,但符合行刑有序衔接的需要,亦应予以充分肯定。
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轻罪分流方面可以充分发挥效用。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轻罪法”,而《治安管理处罚法》事实上发挥着“轻罪法”的作用。【参见张杰:《行刑衔接视阈下轻罪出罪路径优化探析》,载《法学论坛》2024年第2期,第31页。】关于我国是否需要制定专门的轻罪立法,实际上可以再斟酌。但充分发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轻罪分流作用,实现行刑有序衔接,应无疑义。目前,《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在修订之中,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围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各方都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讨论,促进修订草案不断健全完善。在此,本文认为,就长远而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完善不应限于具体条文的“小修小补”,而应着力在轻罪分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此,应当在如下两个方面实现“齐头并进”。
一方面,立足当下,对于《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的重叠竞合行为,通过司法妥当裁量实现“出刑转行”。申言之,对所涉行为的社会危害进行实质判断,将部分情节较轻的轻罪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围。实际上,对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存在一定模糊界限,刑事惩处必要性不强的行为,通过治安管理处罚的方式加以惩戒,同样可以收到良好效果。以自由罚为例,行政拘留最长可以到二十日,而拘役最短为一个月,二者期限差异实际不大,故对于危害尚不突出的犯罪行为适用拘留措施,在惩处效果方面不会存在明显差异。但是,由于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后果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故前者实际可以避免短期自由刑的部分弊端,特别是犯罪附随后果过于严厉的问题。
另一方面,立足长远,对于《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的缺漏空缺行为,通过比照适用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之所以认为这一主张是“立足长远”之策,是因为本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已经二次审议,再行作出大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故而,对此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在后续再行推进。】《刑法》目前设有483个罪名,而这些罪名对应的犯罪行为尚难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一一对应”,还有不少缺漏。通常而言,较之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刑法》规制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更为严重。按照法理,对于所涉行为原则上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应当作出相应规定。否则,对相应行为,要么处以刑罚,要么难以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这既不符合行刑衔接的要求,也容易引发不当扩大刑法适用范围的问题。可以说,通过比照适用虽然看似扩大了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范围,但由于其适用前提为所涉行为在《刑法》之中已有规定,故实际上可以限定在适当范围内。而且,通过适当扩大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范围,适度限制《刑法》的适用范围,正是通过行刑有序衔接,推进有效应对轻罪的应有之义。总而言之,要立足整个行刑衔接处罚体系,而不能局限在治安管理处罚的范围内思考问题。唯有如此,方能确保结论的周全。
4.做好反向行刑衔接
行刑衔接应当是双向衔接而非单向衔接。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提出双向移送机制,第27条第1款规定:“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关行政机关。”《刑法》第37条亦针对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明确规定可以“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这实际上强调的就是反向行刑衔接的问题,而近年来不少涉轻罪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之中更是强调反向衔接的问题。例如,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7号)第12条规定:“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据此,对于轻罪中的出罪免罚行为,应当做好反向行刑衔接的“后半篇文章”,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免予刑事处罚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避免“不刑不罚”,填补非刑事处罚和应行政处罚间的缝隙漏洞,以“出刑入行”织密法网。
(三)秉持程序优先理念
应对轻罪,必须坚持实体与程序一体推进。特别是轻罪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往往与程序运行的状况直接相关,应当优先在程序方面加以考量,促进问题的解决。基于此,应当坚持程序优先的理念,通过优化程序促进轻罪的有效应对。
1.优化资源配置与推动轻罪快速处理
刑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对轻罪案件与重罪案件的处理不应“平均用力”,而应当在程序处理上设置差异化的制度。相比于重罪案件,轻罪案件的社会危害较小,行为人罪责较轻,社会关系易于修复。基于此,对轻罪案件进行快速处理,实现差异化的刑事程序制度,真正做到“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是合理配置刑事诉讼资源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在实体层面更为妥当处理轻罪案件。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速裁程序,体现了对轻罪案件快速处理的追求。但是,轻罪案件的快速办理,不应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体现在刑事诉讼的全流程,在各阶段推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无论是审前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还是审判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建立轻罪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在程序上对轻罪案件作相对包容的快速处理。应当建立“轻案快立”“轻案快侦”“轻案快诉”“轻案快审”的轻罪诉讼程序【参见王渊:《刑法立法未来趋向:完善轻罪治理体系》,载《检察日报》2017年10月31日,第3版。】,特别是慎用逮捕措施,扩大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为后续实体的相对宽缓处理奠定程序基础。
2.审前分流与检察阶段作用充分发挥
如前所述,基于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对轻罪案件应当更为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避免轻罪犯罪圈的不当扩张。这就要求更为切实地发挥审前程序分流功能,避免轻罪案件“扎堆”进入审判环节。客观而言,寄希望于审判环节成规模对轻罪案件作出罪处理,既不现实,也不合理。
对轻罪案件的审前分流,应当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总的来看,从2019年至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不起诉率逐年上升,由2019年的9.5%上升至2023年1月至9月的25.8%,约增加16个百分点。【参见张杰:《行刑衔接视阈下轻罪出罪路径优化探析》,载《法学论坛》2024年第2期,第36页。】但从实践来看,检察阶段的分流功能还有进一步强化的必要。对于进入审判环节判处非监禁刑的不少案件,实际可以在检察阶段分流处理。总而言之,检察阶段适当扩大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充分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应有功能,是确保进入审判环节的轻罪案件规模适度的前提和关键。
3.扩大非监禁刑适用与降低羁押率
当前,与审前羁押率偏高直接相关联的是对轻罪罪犯大量适用短期自由刑。以危险驾驶罪为例,有学者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2011—2021年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裁判文书进行分层抽样,从中选取了100万份裁判文书为样本进行分析。统计分析显示,虽然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适用三个月以下拘役的占七成以上,但整体上实刑率偏高,适用缓刑率最高的年份,也只有略微超过一半的醉驾罪犯得以适用缓刑。【参见董玉庭、张闳诏:《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实证研究》,载《时代法学》2023年第1期,第15页。】危险驾驶罪系刑罚配置最轻、适用数量最大的罪名,对其大量适用短期自由刑,足以说明当前对轻罪的非监禁刑适用尚有改进空间。
基于对短期自由刑弊端的担忧,对于确有必要予以犯罪评价的轻罪案件,也应当进一步扩充非监禁刑的适用,这既是刑罚谦抑理念的应有之义,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对于进入审判环节的轻罪,应当尽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同时宣告缓刑。除此之外,可以通过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罚来处理轻罪案件,从而大幅度减少对罪犯的监禁,在轻罪应对中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参见周光权:《短期自由刑的适用控制与轻罪治理策略》,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37页。】
基于实体与程序一体考量的要求,不应将目光局限在审判环节的实体处理,还应顾及审前强制措施的适用。《刑事诉讼法》第81条规定的逮捕条件之一即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可见,审前羁押措施的采取实际与审判阶段监禁刑的适用直接相关。可以说,对于审前羁押的案件,在审判阶段再行适用缓刑的概率会明显降低。而在司法实践中,“构罪必捕”“有罪必诉”“一押到底”的观念没有彻底转变,仍存在“以羁押为原则、取保候审为例外”,片面追求有罪判决率,对不捕、不诉设置过度控制程序的情况。【参见孙春雨:《因应犯罪结构变化协力推动轻罪治理》,载《人民检察》2023年第11期,第32页。】基于此,应当将依法少捕慎诉慎押作为办理轻罪案件的具体工作要求,降低轻罪行为人的羁押率,为非监禁刑的适用奠定基础。
需要提及的是,《2023年醉驾意见》对侦查环节取保候审措施的延续适用作了规定,即第24条规定:“在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阶段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时,取保候审期限尚未届满且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受案机关可以不再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由公安机关继续执行原取保候审措施。”这一措施的设置,实际上有利于对醉驾刑事案件取保候审措施的延续适用,避免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续用强制措施的繁琐程序,对于降低羁押率和扩大非监禁刑适用均有裨益。这值得其他轻罪案件借鉴,可以考虑下一步在其他轻罪案件中加以推广。
(四)完善前科制度
实现犯罪的轻重有序,亟须解决的是犯罪附随后果“一刀切”的问题。轻罪与重罪可谓“轻重有别”,不仅应当在刑罚程度方面区分开来,更应当设置多元化的犯罪附随后果制度。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1页。】当前,应当认真贯彻落实上述要求,以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作为突破口,为系统完善轻罪前科制度积累经验。
1.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
前科制度本身具有相当合理性,故在世界各国刑法中多有规定,旨在发挥风险防范和安全维护的功能。然而,对前科制度适用范围加以适当限制,防止对有犯罪记录的人员回归社会进行不当限制,也是必然要求。特别是当前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更是要求前科制度作出适当调整。大量轻罪案件的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在教育和改造完毕后应当允许其及时回归正常生活。然而,在目前的犯罪记录制度框架下,这些轻罪罪犯因为“有前科”“有案底”,“一次犯罪,终身罪犯”,要承受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回归社会困难重重,大大增加社会对立面。可以说,针对当前轻罪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为消除前科制度的弊端,有必要完善轻罪前科制度。对此,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司法现实,并与有犯罪记录人员回归社会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相适应。
对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基于稳妥推进的考虑,本文主张将适用范围限制在轻罪之中的微罪,即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或者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同时,如前所述,应当将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军人违反职责等特定犯罪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2.立法层面的务实选择
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属于立法层面的问题,无法在司法层面自行突破。就立法推进而言,最为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刑法》cd36308455f5c44c60a311291fb9b842和《刑事诉讼法》联动修改,构建起实体与程序相互融合的制度体系。然而,目前看来,短期之内《刑法》修改增设前科消灭制度的可能性不大。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已于2023年12月29日由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并未涉及轻罪前科问题。本次修法之后,短期内再行修改《刑法》的可能性不大。基于此,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可以考虑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方式在程序法层面先行开局,迈出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第一步,待《刑法》再次修改之时再予补充,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有序衔接。
五、结语
轻罪应对是系统工程,涉及立法、司法及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需要共同努力推动。长远而言,应当构建轻罪制度,实现轻罪与重罪的“立法分道”。在立法系统修改短期内难以实现的当下,应当通过立法层面的“小修小补”、司法层面的“较大作为”和综合治理的“深入推进”,实现对轻罪的有效应对。由此,应当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下进一步贯彻刑法谦抑原则,坚持综合治理对策,秉持程序优先理念,完善前科制度,实现对轻罪的妥当应对。ML
Addressing Misdemeanors from an Integrated Criminal Perspective
YU Haisong
(The Research Bureau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jing100745,China)
Abstract:WhileChina’scurrent criminal law does not explicitly define misdemeanors,offenses punishable by less than three years of imprisonment generally fall into this category,with some exceptions for specific crimes.The recent rise in misdemeanors is attributed to several factors:the legislative expansion of such offenses,judicial policies that elevat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 in response to demands for lighter penalties,and evolving circumstances.In the future,an integrated approach is needed to effectively address misdemeanors.To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restraint in criminal law,it is crucial to optimiz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 to control the scope of offenses,particularly for those such as aiding cybercrime,which has become more common.In terms of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seamless coordination between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should be achieved.In the short term,judicial discretion can be employed to transition certain cases from criminal procedures to administrative handling.Longterm strategies include aligning behaviors regulated by the Criminal Law with provisions in the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unishment Law,enhancing the latter’s role as a“misdemeanor law”.Moreover,procedural justice must be prioritized by utilizing pretrial diversion mechanisms to prevent an influx of misdemeanor cases in court,while expanding the use of noncustodial sentences and lowering detention rates.To improve the criminal record system,the introduction of arecordsealing system for minor offenses could serve as abreakthrough,using astrategy where procedural reforms precede substantive legal changes,thus creating amore orderly system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major and minor crimes.
Key words:misdemeanors;criminal justice integration;dangerous driving;record sealing system for misdemeanors
本文责任编辑:周玉芹
青年学术编辑:张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