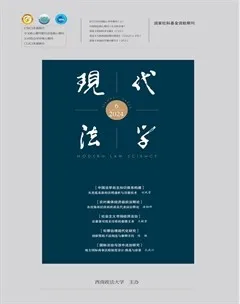近代法典概念的当代回应
2024-12-18汪雄
摘 要:通行的法典概念由体系性、权威性和完备性三个要素构成,这个概念源自19世纪法典编纂运动以来的近代法典。但是这个概念在当代面临诸多挑战:首先,20世纪的民间式法典对权威性造成了巨大冲击;其次,当代社会日益纷繁复杂,法律规范形式更加多样,传统的宏大精密的体系性标准有可能让法典因晦涩难懂而远离大众,也会给法典埋下解法典化的隐患;再次,近代以来,完备性也变得相对化,宏观层面的规范领域的完备性让位于微观层面的规范结构的完备性;最后,法典的形式理性需要面对当代法典编纂中的诸多争议,法典并非纯粹的形式建构。近代法典概念需要扬弃自身,在变与不变之中发展、在挑战和应对中更新。
关键词:体系性;权威性;完备性;法典;形式理性
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4.06.02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步入了法典化时代,生态环境法典、教育法典、行政法典的编纂和研究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无论在民法学界还是在法理学界,目前都没有一个关于法典的统一概念。①西方学者对法典的定义也充满分歧,多达十几种。②概念不清导致我们在分析判断某部法律是否为法典时缺乏衡量标准,也为当下的法典编纂提出概念观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历史时间线拉得更长远一些,同样会面临类似的困惑。例如,日本学者浅井虎夫在《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中采用了最广义的法典概念,在他看来,中国历代成文法都属于法典。【参见[日]浅井虎夫:《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陈重民译,李孝猛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另一位日本学者仁井田陞也支持这种广义的法典概念,他把法典的具体出现时间定在了公元前3、4世纪。(参见[日]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牟发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梁启超也认为我国的法典编纂事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萌芽,魏晋之交,就出现了有组织之大法典。【参见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载《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但是韦伯认为:“中国官方的律令,虽然在编排上尚具某些‘体系性’,但与法典编纂式的法制定无关……”【[德]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页。】很显然,韦伯在这里采取了19世纪欧洲的法典概念,这只是一家之言。在西方语言系统中,含有“法典”含义的词汇有code(英语、法语),Buch、Kodex(德语),codex、caudex(拉丁语),Código(西班牙语),Codice(意大利语),кóдекс(俄语)等,但是仅靠这些词汇并不能加深我们对法典概念的理解,相反会带来一些混淆。并且,如果“法典”仅指以上述词汇命名的法律,那么就可能把一些虽然名义上没有使用上述词汇,但实际上却是法典的法律排斥在外,例如,1794年的《普鲁士通用邦法》(Das Allgemeine Landrecht für die Preuischen Staaten)虽无“法典”之名,却有法典之实。另外,有一些法律虽然使用了“法典”之名,但却没有法典之实,如穗积陈重所提及的韵府体法典,【参见[日]穗积陈重:《法典论》,李求轶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2页。】从表面上看是法典,但其实际上并非法典。所以,仅靠是否具备“法典”之名不能作为判断法典与否的标准,必须从现实的法典之中提炼法典的概念。
按照维亚克尔、韦伯等人的看法,近代法典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其主要代表是《普鲁士通用邦法》《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çais,1804年)、《奥地利民法典》(Das Allgemeine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für Österreich,1811年)。【See Reinhard Zimmermann,Codification:The Civilian Experience Reconsidered on the Eve of aCommon European Sales Law,8ERCL370(2012).】19世纪法典编纂运动以来形成的法典概念是学界通行的法典概念,在判断某部法律是不是法典时,人们往往不自觉地用这个概念来检验。这个概念的构成要素有:权威性、完备性和体系性,这是18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启蒙运动和自然法运动合力推动形成的概念,主导了近三百年的法典编纂活动。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这个概念受到了诸多挑战,本文将重点讨论近代法典概念的构成及其在当代面临的挑战。
二、近代法典编纂与概念争议
(一)近代法典编纂理念的流变
早在18世纪中叶,理性自然法学派相信凭借人之理性能制定出一个完美的体系,甚至不需要对此进行任何的改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将这个体系行之有效地应用于各种各样的条件组合。【参见[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3卷),廖德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48页。】在这种理念的激励下,《普鲁士通用邦法》为了在形式上追求完备统一,遂把宪法之下的所有法律部门,如刑法、行政法、商法、宗教法、税法及私法等,都编在了一部法典之中。这样的法典是“全能”(omnipotenten)的,也叫万全法(pannomion),能把所有的市民生活统摄在一部法律之中。但实际上没有法典能确保万无一失。天下之情无穷,大千世界变动不居,任何法典必定会存在漏洞(lacunae)和滞后性。哪怕《普鲁士通用邦法》洋洋洒洒一万七千多条,也无法实现此目标,反而导致法典累赘烦琐,增加了检索和阅读的障碍。18世纪所谓的万全法只不过是理性自负演奏出的一段插曲,很快就被实践所抛弃和改写。以至于有人认为《普鲁士通用邦法》不能算是法典,因为它经实践检验是失败的。【See Weiss,The Enchantment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 Law World,25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457(2000).】后来的《奥地利民法典》就不再尝试《普鲁士通用邦法》所追求的全面性;此后的历史再也没有关于“总法典”的一元设想,多元法典的趋势势不可挡,学者们开始脚踏实地在有限的部门法领域编纂相对完备的法典。
随之出现的是《法国民法典》(1804年),它被誉为“法典化的理性”和“最高等级的私法法典”。【[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39页;舒国滢:《法学的知识谱系》,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798页;[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充分吸取了《普鲁士通用邦法》的教训,他们很清楚法典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事先规定所有的细节,必须给司法留有余地。其起草人之一让·伊第安·马里·波塔利斯(Jean Etienne Marie Portalis)曾直言:“最好的法典必然有漏洞,法官应该通过法律解释填补漏洞。”【Weiss,The Enchantment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 Law World,25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460(2000).】所以《法国民法典》第4条才规定法官不得以法无规定为由拒绝裁判。但是有漏洞的地方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滥用自由裁量权,他们应受到法律的体系和一般条款的约束。所以法典应该包含一般原则以避免细节和决疑式的内容。【See Helmut Coing,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uropean Codifi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in S.J Stoljar ed.,Problems of Codification,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77,p.20.】也就是说,在实践中,编纂的法典不能像《普鲁士通用邦法》那样为了追求完备而琐碎冗长,也不能像《奥地利民法典》那样过于简洁而漏洞百出,而应该借助体系性来避免漏洞、达臻完备而又不显得臃肿累赘。正是基于这种编纂理念,《法国民法典》在体系性和概念表达的清晰性方面胜过《奥地利民法典》。
《普鲁士通用邦法》《法国民法典》《奥地利民法典》都以启蒙运动和理性法所确立的信念为基础。【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上),潘汉典、米健、高鸿钧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63页;舒国滢:《法学的知识谱系》,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795页。】启蒙主要是理性的启蒙,近代法典都是理性化的结果。理性化开始于所谓的通则化,通则化是相对于决疑术式、个案化而言的,而体系化是以通则化为前提的,“通则化”加“体系化”的法典能以最少的条款和最简洁精确的语言最大限度地规范最多的事情,它是立法技术走向成熟的标志,其典型代表是《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Zivilgesetzbuch,1907年)。《德国民法典》是德国学说汇纂学派深邃、精确而又抽象之风格的产物,其突出的特征是有了总则(Allgemeiner Teil)。学者们对其评价极高,但优点有时也是缺点,其过度追求体系性和抽象性,使用了大量的专门术语、复杂的句子结构和参照性条文,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在编纂《瑞士民法典》时,起草者们有意克服这些缺点,使用简单而不失逻辑的句子,简洁而非冗长的条文,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条文的交叉参引。步入20世纪之后,荷兰、俄罗斯、中亚各国都相继颁布了民法典,被称为“法典理念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 der Kodifikations-Idee)。【参见[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但20世纪的这些法典延续的依然是19世纪的理念,这种理念支配着我们当下对法典概念的理解。
(二)近代法典的概念争议
不同的人对19世纪的法典理念有不同的理解,在对这些理念进行概念上的总结与提炼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以至于时至今日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法典定义,但我们还是需要从这些充满分歧的定义入手寻找法典共有的概念要素。
早在19世纪初,欧洲的法典编纂运动刚刚起步时,英伦对岸的边沁就已经开始了其法典构想。他给时任美国国会主席的麦迪逊写信说,理想的法典应该具备七个特征:第一,清楚性(clearness),即法典用语须清楚明了,尽量避免语义上的模糊与分歧;第二,正确性(correctness);第三,完备性(completeness),即法典必须是充分的整套法律,以致无须用注释或判例的形式加以补充;第四,简洁性(conciseness);第五,精练性(compactness),用最少的法则说明全部的法律,在叙述法律规则时,必须使用严格一致的术语;第六,条理性(methodicalness),这些法则必须以严格的逻辑顺序叙述出来;第七,融贯性(consistency)。【See David Lieberman,Bentham on Codification,in Stephen G.Engelmann ed.,J.Bentham Selected Writings,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p.467;参见[英]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1页。】边沁提出的这七个特征其实不太科学,例如,在实践中就无法区分“简洁性”和“精练性”,也无法区分“条理性”和“融贯性”,有重复的嫌疑。去掉“精练性”和“融贯性”两个重复的特征之后,就剩五个特征,其中“正确性”是实质内容方面的特征,其余四个是形式方面的特征。
现代学者在总结法典的概念特征时,几乎“一边倒”地对实质内容方面的特征避而不谈,只谈形式特征,不过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总结。如齐默尔曼教授认为法典应该具备四个特征或标准:第一,立法性,即制定法典首先是一种立法活动,但它和一般立法活动的区别还在于法典还有后面的三个特征;第二,完备性,法典要从整体上将旧法压缩为零,自法典生效时起,之前的法律世界就被一笔勾销了,所以它必须具有完备性;第三,体系性;第四,文体性,法典有特定的文本特征,现今学界没有人会认为《法学阶梯》是一部法典,哪怕它有法律效力,因为它在文本形式上仅仅只是一本法学教科书而已。【See Reinhard Zimmermann,Codification:The Civilian Experience Reconsidered on the Eve of aCommon European Sales Law,8ERCL371-373(2012);Reinhard Zimmermann,Codification:History and Present Significance of an Idea,3European Review of Private Law96-97(1995).】魏斯教授(Gunther Weiss)也认为法典应具备四个特征:完备性、系统性、简洁性和权威性。【See Weiss,The Enchantment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 Law World,25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435ff.,esp.448–470(2000).】其中,简洁性指法典能被普通人理解。【See Lindsay Farmer,Codification,in Markus D.Dubber and Tatjana Hrnle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imi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388.】其实,魏斯教授的权威性和齐默尔曼教授所说的立法性是一个意思,二者都指法典编纂是有权机关的立法活动,权威性和立法性排除了民间团体或个人的法典编纂。唐克教授(Andre Tunc)也认为法典应具备四个特征:第一,在特定领域是完备的;第二,以普遍规则的形式书写,精心起草的法典不应该包含太多细节性的条款,也不应该包含太多例外条款,这是韦伯意义上通则化的具体表现;第三,以逻辑的方式排列,法典应该由逻辑整体构成,而非由充满美感的事物构成,“以普遍规则的形式书写,以逻辑的方式排列”实际上是齐默尔曼教授和魏斯教授所谓的体系性;第四,起草和编纂基于经验(Code is grounded on experience)。【See Andre Tunc,Grand Outlines of the Code Napoleon,29Tulane Law Review435(1954-1955);Andre Tunc,Methodology of the Civil Law in France,50Tulane Law Review459-460(1975-1976).】
尽管几位学者关于法典的概念特征存在争议,但都认为法典必须具备完备性,只不过唐克教授特别强调完备性仅限于特定领域,自从《普鲁士通用邦法》的万全法理念被实践抛弃之后,完备性仅指特定领域的完备性已逐渐成为共识。但是法典的概念是否应该包含“正确性”,却存在争议。边沁认为应该包括,其他几位学者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正确性”指向实质内容,法典和单行法都是法律的载体,只不过法典是法律的最佳表现形式。【参见[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Manlio Belomo,The Common Legal Past of Europe,translated by Lydia G.Cochrane,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95,p.1-3;[德]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所以,作为实质性特征的“正确性”不宜成为法典的概念特征。此外,齐默尔曼教授还认为法典应该包括“立法性”和“文体性”两个特征,但实际上“立法性”能吸收“文体性”特征,因为现代立法技术日益成熟,立法语言和文体也日益规范,不具备“文体性”很难具备“立法性”。并且,“立法性”是区分制定法与习惯法、判例法等非制定法的关键,也是区分法律汇编和法典编纂的标准之一,所以“立法性”应该是法典的概念要素。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立法权归属于国家,立法是国家机关的权威性活动,所以齐默尔曼教授的“立法性”和魏斯教授的“权威性”是一个意思。法典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在特定的领域取代其它法律渊源成为唯一法源。其前提是具有权威性,权威性能赋予法典排除其他法源的效力。通常情况下,编纂法典属于立法的一种,是国家有权机关的立法活动,毋庸置疑具有权威性。
值得注意的是边沁和魏斯教授都认为法典应该具备“简洁性”,此外边沁还附加了“清楚性”和“精练性”,其实,简洁、清楚、精练是所有立法应该具备的特征,所以他们不是法典而是制定法的必备要素。齐默尔曼教授提出的“体系性”包括了唐克教授所说的法典要以普遍规则的形式书写、以逻辑的方式排列,也蕴含了边沁总结的“条理性”和“融贯性”的内容。“体系性”把法律汇编从法典之中排除出去了,“法典不仅仅是法律规则的集合,但是这些规则集合应该具有内在融贯性”。【Andre Tunc,Grand Outlines of the Code Napoleon,29Tulane Law Review441(1954-1955).】体系性应该是近代法典的核心特征和标准,如果抹掉体系性特征,将法律汇编和法典混同,法典就无法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而存在。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尽管学者们关于法典的一般特征存在争议,但是基本上可以找到法典之必要特征的重叠共识:权威性、体系性和完备性。其中,完备性是法典的基本要求,与其制定出一个不完备的法典,不如暂时搁置法典,先制定单行法。因为“法典化的目标是追求立法的广泛性或完备性”。【Reinhard Zimmermann,Codification:The Civilian Experience Reconsidered on the Eve of aCommon European Sales Law,8ERCL372(2012).】所以,法典(codification)与立法(legislation)的最大不同在于,法典是对整个法律领域的立法,法典追求广泛性和完备性,而立法则无此要求。体系性是为了确保法典的完备性而采用的一些技术方法形成的形式特征。而完备性仅仅是特定领域的完备性,不可能制定一部边沁意义上的万全法典,无论是大法典(maxi-codes)还是小法典(mini-codes)都不合适,完备性是相对的。基于此,法典体系不应该是封闭的,而应该保持适当的开放性,设置一般条款和法律原则,能据此演绎并涵盖社会新情况。最后,权威性是基于来源而言的容易判断的一个标准。接下来我们将结合近代法典的编纂实践考察这三个要素的形成过程及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
三、近代法典概念的形成
(一)法典的“祛魅”与权威性和体系性的出现
在早期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有规定立纲陈纪、命官敷政等大经大猷的制度,才被称为“典”,例如,古希腊的《格尔蒂法典》、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这些法典的神圣性和崇高性使其堪当法典之名,其崇高性源自神。在《法律篇》开篇,雅典异方人就认为克里特的法律源自神(θεóς)而非人。【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第2卷《法义》译文),林志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同样,《格尔蒂法典》开篇会呼吁“诸神”;【参见《格尔蒂法典》,郝际陶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古希腊铭文辑要》,张强译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94页。】刻有《汉穆拉比法典》的玄武石上方会有太阳神沙马什授予法典的浮雕;《摩奴法典》被认为是由梵天(Brahma)亲身启示给号称“出于自在之有”(Swayambhoura)的摩奴一世。【参见《摩奴法典》,迭朗善译,马香雪转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还有印度的《毗湿奴法典》(Code of Vishnu)是由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向大地女神口述而成的。【参见[英]亨利·梅因:《早期法律与习俗》,冷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早期法典带有神谕色彩,常常在法典的起源和神之间建立关联,法典由此获得神圣性和崇高性,从而得以在帝国疆域内推行并被普遍遵守。古代法典从“神”那里获得崇高性的同时,也往往获得了起源意义上的权威,例如,《汉穆拉比法典》源自太阳神沙马什的权威,《摩奴法典》源自梵天的权威。但是,神并不直接向人立法,常常需要一位中间人来口述或转授神的法律,这位中间人一般拥有世俗权威。例如,《汉穆拉比法典》是由沙马什口授给古巴比伦第六任国王汉穆拉比,《摩奴法典》是由梵天启示给统治者摩奴一世。汉穆拉比和摩奴一世都手握世俗权力,法典经他们颁布之后,就同时获得了神圣权威和世俗权威。
此后代表性的法典是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于529年颁行的《优士丁尼法典》。这部法典是纯粹世俗政权的产物,对于在拜占庭的王位上说拉丁语的优士丁尼而言,他一方面希望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另一方面还要阻止东西方之间的撕裂,吸收东西帝国之前的法律及其学说,编纂一部法典是实现其抱负的重要手段。早在528年,优士丁尼就任命司法大臣特里波尼安(Flavius Tribonian)组成十人委员会,清理历代皇帝颁布的敕令,如《格雷哥里安法典》《赫尔莫杰尼安法典》《狄奥多西法典》等,删除其中矛盾和过时的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共10卷。后来优士丁尼还组织编写了教科书《法学阶梯》和历代法学家意见集《学说汇纂》,它们和《新律》共同构成了《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直到6世纪末以前,《民法大全》都是东罗马帝国的主要法律渊源,甚至在优士丁尼去世之后,仍然在拜占庭帝国得到遵行。【参见舒国滢:《优士丁尼〈学说汇纂〉文本的流传、修复与勘校》,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5期,第45页;[意]马里奥·塔拉曼卡主编:《罗马法史纲》(第2版),周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29-732页。】自此之后,欧洲进入一个所谓的法律的“整合化”(sonsolidations)时期,【[意]曼利奥·贝洛莫:《欧洲共同法的历史:1000-1800》,高仰光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14页。】出现了很多汇编型法典。有些由王权主导,有些由教会主导。
16世纪之后的三百年间,科学革命重新定义了宇宙起源,“神”被近代科学一步步地解构,“神”的位置逐渐从宇宙中心退居人的内心。其影响波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法学也不例外,法律“不能再诉诸高居法律之上、自性自存的正义理念以取得其正当性,其毋宁是(与超越事实之正义无涉的)内存事实之目的与手段的产物”。【[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40页。】这是一场法典的“祛魅”运动【“祛魅”是韦伯提出的概念,也被翻译为“除魔”“去魅”“解咒”“去神秘化”等。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集中论述了“世界的祛魅”。他说:“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页。科学革命和理性给法典“祛魅”的同时,也阻断了法典从神那里获得高贵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法系之中,他们的法典就是他们的宗教经典,如伊斯兰法系、犹太法系,这些法系就没有经历“祛魅”的过程。】,法典的“祛魅”是伴随着法律世俗化完成的,法律世俗化之后,两种思潮试图重新为法典奠基,一种是实证主义,另一种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认为主权者的权威是“祛魅”之后重建法典基础的唯一方式,法典必须由有权机关制定和颁布才是有效的,这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科学主义认为,用科学的方法让法典内部宛如一部结构精密、内容完备的体系,法典也可以重新获得基础。所以,莱布尼兹试图用科学方法制定法典,不仅因为他要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法律之中,更在于,当自然科学完成对世界的“祛魅”、瓦解了法典的神圣性之后,莱布尼兹要重新为法典奠基,而其内部结构的科学性和规范的严密性、完备性就成为了重建“神圣法典”的一条出路。这种思潮主导了19世纪法典编纂运动,也促使其更加重视体系性。体系性诉诸科学理性重建法典基础的同时也树立了理性的权威地位。“这个新的法律之神(the juristic god),被称为‘理性’。”【[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理性的权威”取代“权威的理性”成为法典编纂中的主宰者。法典之所以正当有效,不是因为它是权威统治者的理性的产物,而是因为法典本身是理性的体系。
(二)完备性及其与大众性之间的张力
从功能上考察,法典编纂之所以追求体系性,是因为面临着完备性与大众性之间的张力。众所周知,19世纪法典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地方习惯法(coutumes locales)多达三百余个。【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上),潘汉典、米健、高鸿钧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150页。】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减少和取代之前纷繁杂多的法律渊源一直是法典的现实目标。但是,法典要成为这个国家中唯一的法律渊源,有一个前提条件:法典的内容必须具有广泛性和完备性,也即法典要能回答所有的法律问题,并且在回答法律问题时不必诉诸法官的意见、习俗和学者们的智慧。当时的理性主义者为这样的法典理想提供了哲学支撑,以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为代表,他认为运用理性的逻辑,能把自然法的语句从较高的公理到最小的细节无遗漏地推论出来。【参见[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5页;[美]罗杰·伯科威茨:《科学的馈赠——现代法律是如何演变为实在法的?》,田夫、徐丽丽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完备性要求法典是完美而详尽的,严格来说,只有这样的法典才具有“法典出而旧法废”的效果。边沁对法典的完备性有执着的追求,他心目中的法典要能涵盖人的行为的全部领域;一个人只需要翻开法典,就可以了解全部权利与义务及处罚规定。【参见[美]杰拉德·波斯特玛:《边沁与普通法传统》,徐同远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63页。】这要求法典天衣无缝,为了杜绝未来可能出现的漏洞,法典编纂者不得不用更多的条文、更琐细的规定甚至不惜进行重复规定,宁可增加条文数量也不能留下漏洞隐患,最终导致法典的内容无限膨胀,动辄上万条文,《普鲁士通用邦法》就是这方面的巨作,阅读极为不便,远离大众。
同时期的启蒙运动力图通过普及知识,使所有人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其代表人物狄德罗(Denis Diderot)认为新科学力量可以提供一个完备的知识坐标体系,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得关于人、社会和世界的知识。启蒙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能自由地阅读和理解法典。这要求法典通俗化,法律应该是清晰系统、易于理解的。【参见[德]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他们反对“学者法”,反对深奥的法学术语充斥法典之中,呼吁“民众的法典”(les Codes des Peuples),其目标是制定的法典兼顾完备性和简洁性,通俗易懂能让每个人都能理解,每个人都能成为他自己的律师。
当然,追求简洁性会造成法典的缺漏和模棱两可,这就给司法机关的解释与裁量留下了空间,就会出现富勒所谓的“法律大众化的成本”。【富勒说:“人们发现使法律变得为大众所容易理解的努力带有一项潜在的成本,即法院对法律的适用变得反复无常并且难以预测。因此,退回到一种更加平衡的立场变得不可避免。”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4页。】即便有成本,大众化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趋势。在现代法国,法律的通俗易懂甚至成为了一项具有宪法价值的目标。【法国宪法委员会于1999年12月16日的一项判决指出,“法律易于为公众所知晓和读懂”是一项具有宪法价值的目标。参见石佳友:《民法法典化的方法论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其实,早在《法国民法典》出台之后不久,德国的黑格尔和蒂堡都反对“学者法”,倡导法典的通俗易懂,主张每个人都能摆脱学者或其他中介直接与文本沟通。只可惜,《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没有吸纳黑格尔等人的观点。其草案公布之后,人们毫不留情地提出了批评,“令人痛苦的矫揉造作、学究式的咬文嚼字、缺乏通俗性,该法典没有一处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与感受中去:没有任何的东西吸引大众,恰恰相反,许多东西都令大众反感”。【[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后来的《瑞士民法典》吸取教训,努力协调完备性与简洁性或大众性,其核心起草人欧根·胡贝尔为了克服《德国民法典》抽象决疑、晦涩难懂的弊端,立志起草一部易懂易读的法典。一百多年前的腓特烈也怀有和胡贝尔相同的目标,只不过那时编纂法典的体系化技术还不成熟,所以协调完备性与大众性的结果就是庞大的条文规定,但是,“真的要将法律知识传达给大众,靠罗列数万条文的巨作是不可能的”。【[德]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4页。】解决完备性与大众化之张力的成熟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式简化法典,其典型方法就是“提取公因式”(vor die Klammer zu ziehen),也就是体系性的方法。
(三)协调张力与体系性的确立
这里所称的体系指的是规范构成的内部体系,它不是法条的简单罗列,而是以逻辑方式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法典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机整体,它表面上是相对封闭的,但采取了提取公因式的抽象表达,所以能够涵摄所有的事情。“法律的体系性主张,法学应该把所有的法律素材以逻辑的方式安排成一个公理体系,这个公理体系能让我们给每一个具体案例推演出法律解决方案,且其正确性是有保障的。”【Konrad Zweigert,System and Language of the German Civil Code1900,in S.J Stoljar ed.,Problems of Codification,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77,p.46.】与启蒙运动并列的自然法运动为公理体系的构想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按照笛卡尔的看法,人凭借自身的理性,能从认识最简单的对象开始,一步步逐渐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参见[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页。】体系化的方法能协调完备性与大众性之间的张力,它通过逻辑来简化规则,最终形成一个无漏洞的体系,追求涵摄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以实现法典的完备性,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简洁性。例如,《德国民法典》以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创设了“总则编”,它规定分则中共通的概念和制度,避免了冗赘重复,形成一个匀称、简练和融贯的体系,这是法典非常重要的形式特征。“就法典的性质而言,其既非为一项裁判,亦非若干孤立的裁判集合,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Von Savigny,On the Vocation of Our Age for Legislation and Jurisprudence,translated by Abraham Hayward,Littlewood&Co.Old Bailey,1831,p.178.】有机整体观反对把法律汇编看作是法典,因为法律汇编内部的规则与规则之间不具备逻辑上的紧密联系,不构成一个有机体。
值得注意的是,形成体系所依赖的“提取公因式”方法是从数学或逻辑学中借用而来的,为了确保逻辑推理的周密性,对概念的清晰性要求很高。有时,为了避免语义模糊,甚至刻意不使用日常语言中的概念或术语,或者赋予日常概念以全新的内涵,如“处分”“代理”“权利能力”“意思表示”“无因管理”等,但这类概念给普通人理解法典造成了困难。体系化和概念的抽象化程度越高,法典就越不易被普通公众读懂。为了缓解完备性和大众化之间的张力,不得不采取“提取公因式”等方法简化法典,但同时也让法典变得抽象晦涩、充满专业术语,让民众望而生畏,反倒引发了体系性和大众化之间的张力。并且,体系性和完备性之间也有张力,虽然体系性有利于完备性,即通过体系性思维和抽象化语言来避免法律漏洞,拉伦茨曾说:“没有一种体系可以演绎式地支配全部问题;体系必须保持开放。”【[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20页。】但是完备性要求体系的封闭性,即要求体系可以演绎式地支配全部问题。【有民法学者认为,要满足完备性要求,就可能损害法典的体系性。(参见石佳友:《解码法典化:基于比较法的全景式观察》,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16页。)】当代法典编纂在这个问题上通常采取折中方案,不要求绝对的完备性,如环境法学界达成共识的“适度法典化”【吕忠梅:《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模式选择及其展开》,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6期,第76页。】模式就不要求未来的生态环境法典包含所有的环境单行法,允许生态环境法典和环境单行法并存。总之,体系性和完备性之间的张力对体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优化法典的结构才可能协调好这对矛盾,这也说明了体系性之标准没有上限。
权威性、体系性和完备性作为近代法典概念的构成要素,形成于19世纪以来的法典编纂实践。其中完备性是法典与一般立法的形式区别,但是不按一定的方法和技术编排,一味地追求完备性的法典必将冗长烦琐,不便于阅读、理解和适用,所以法典也要具备体系性。一部内容完备、体系融贯的法典通常要具有权威性才能取代其它法源发挥作用。这三个特征代表近代法典化的成就,对我国当下的法典编纂实践具有指引和借鉴意义。同时,当代的法典编纂实践也对这个形式取向的法典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法典概念的当代回应
(一)“民间式法典”对权威性的冲击
中西历史上不乏个人进行法律汇编、法律评注甚至法典编纂。相传,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就是魏国李悝参考诸国法令约于公元前406年编纂而成。李悝虽然在魏文侯时期任魏相,但搜罗各国法律编纂《法经》并非奉文侯之命,《法经》纯属个人作品,如果它是法典的话,我们称其为“民间式法典”。德国也有这样的民间式法典,其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法书的时代”(die Rechtsbuecherzeit),涌现了一大批私人编纂的法典。其中对德国影响比较大的有《萨克森明镜》(Sachsenspiegel)和《士瓦本明镜》(Schwabenspiegel),前者大约于1221—1224年由骑士艾克·冯·雷普高(Eike von Repgow)所编纂,后者大概形成于1275—1276年。雷普高曾经在教会里接受教育,在编写《萨克森明镜》时是一名伯爵的服役者,凭有限的文字记载无法得知他为什么要以个人之力撰写一部法书。但是这本记载萨克森地区的地方法(Landsrecht)和采邑法(Lehnrecht)的书对德国影响巨大,到14、15世纪,在当时的法律实务中,还引用《萨克森明镜》,在普鲁士地区,直到1794年《普鲁士通用邦法》出台前,《萨克森明镜》依然有效,甚至被后世当作法典。【参见[德]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270页。】近代早期也陆续有私人编纂的法典,1672年莱布尼茨编纂了《利奥波德法典》(Codex Leopoldus),他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之名命名法典是希望他将这部法典在整个奥匈帝国甚至欧洲实施,只可惜这部法典因利奥波德一世并未采纳而宣告破产。
但是发生在美国19世纪的民间式法典编纂运动却进行得比较顺利。早在1817年边沁就写信给远在大洋彼岸的麦迪逊劝说其编纂法典,虽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却影响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律师利文斯通(Edward Livingston),1826年他以个人名义起草了美国刑法典。后来,纽约律师菲尔德(David Dudley Field)也着手起草法典,包括民事诉讼法典草案、刑法典草案和民法典草案。刑法典草案于1865年提交纽约州立法机关,几经波折,在16年之后方获通过。民法典草案就没这么幸运,纽约州在1887年拒绝了他的民法典草案。但这个草案在其他地方开枝散叶,相继被达科他州、爱达荷州、俄克拉何马州、蒙大拿州等地方采纳。【高仰光:《美国19世纪法典化运动的兴衰》,载《中国人大》2017年第4期,第55页。】有了这些作为基础,当1940年卡尔·卢埃林受全国统一州法委员会的委托负责修订《统一买卖法》时,就决定制定出一部《统一商法典》,1952年编纂完成并正式公布。经过多次修订到1968年时,除路易斯安那州外,美国其他49个州均采纳了《统一商法典》。同时,美国法学会(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借鉴参考了菲尔德起草的纽约刑法典并于1962年公布了《模范刑法典》。【See Paul H.Robinson&Markus D.Dubber,The American Model Penal Code:A Brief Overview,10New Criminal Law Review: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322(2007).】美国法学会虽是一个由法官、律师和法学教授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但是《模范刑法典》相继被34个州的刑法典吸收或接纳,被几千份法院意见书引用【See Paul H.Robinson&Markus D.Dubber,The American Model Penal Code:A Brief Overview,10New Criminal Law Review: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326-327(2007).】,在司法实务中影响巨大。
在《萨克森明镜》中,条文编排缺乏理论线索,仅仅是相关事实的集中罗列,并且相邻“意思集群”之间缺乏必然联系。【参见高仰光:《〈萨克森明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67页。】总体而言,《萨克森明镜》并不具有体系性特征。与此不同,以美国《统一商法典》《模范刑法典》为代表的当代民间式法典呈现出了极强的体系性。《统一商法典》的起草人卢埃林早年留学德国,熟悉潘德克顿体系,模仿《德国民法典》起草了法典的总则编。同时美国《模范刑法典》也有综合性的总则、确定的术语、分析性的结构和完善的罪名体系,呈现出极强的体系性。【See Paul H.Robinson&Markus D.Dubber,The American Model Penal Code:A Brief Overview,10New Criminal Law Review: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330-333(2007);参见江溯:《美国〈模范刑法典〉对中国刑法再法典化的启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1期,第76页。】总之,美国《统一商法典》《模范刑法典》等民间式法典给法典概念中的权威性要素造成了冲击,因为这些法典都不是由有权机关编纂,不具有权威性,但却具有极强的体系性,且被美国大多数州采纳、被众多法院意见书引用,其发挥的作用不亚于权威机关制定的法典。
(二)体系性的应用与限度
体系性是近代法典的标志性特征,代表人类理性在立法上的极高成就,当某一法律部门的立法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体系化编纂能减少规范交叉,避免规范矛盾,让规范和规范之间形成一个结构有序的整体,这也是我国学者要推动生态环境法、教育法法典化的原因。关于这两部法典的体系结构,学界普遍认为应该采取“总则—分编”的模式。【吕忠梅:《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模式选择及其展开》,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6期,第78页;湛中乐:《推动教育法典编纂应当处理好八对关系》,载《中国高等教育》2023年第5期,第23页;任海涛:《教育法典分则:理念、体系、内容》,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67页;罗冠男:《论教育法典的功能定位、体例结构和编纂步骤》,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5期,第63页。】总则规定法典的共通事项,如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概念等,一般采取合并同类项和提取公因式的技术来提炼总则的内容。
教育法典的编纂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哪些教育行为属于同类项,哪些能作为提取公因式的素材?因为“教育”这个概念除了指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全日制学校教育外,还包括“宣传教育”“国防教育”“法治教育”等,它们和“学校教育”具有多大程度的同类性使得它们可以被总则中的“教育”所涵盖?这不是一个体系化的技术问题,这取决于立法者对“教育”理念的理解,是一个价值问题。另外,按教育类型可以把教育分为职业教育、民办教育、家庭教育、特殊教育、学校教育等;按教育阶段可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在分则编排的问题上到底是以“类型统筹阶段”还是以“阶段统领类型”?【参见段斌斌:《教育法典的体例结构:域外模式与中国方案》,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24页。】前一种主张认为应当以各种教育类型作为编排分则的主轴,后者认为应按时间阶段来编排分则。其实,这种争议产生的原因是没有理解体系化的核心方法——合并同类项。以阶段为主轴适合进行法律汇编,以类型为主轴宜进行法典编纂,因为体系性的提取公因式以类型化为前提。教育法学界普遍放弃了美国的汇编式立法模式,接纳了体系化的法典编纂模式,所以应该以“教育类型”作为分则编排的中心轴。
基于同样的理由,生态环境法典总则不能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的范畴,因为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能涵盖污染防治类的法律,但无法指导资源节约类的法律,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有大量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资源保护类的法律。总则应该最大限度地涵盖分则的所有内容,未来的生态环境法典总则应该基于《环境保护法》进行体系重构,均衡落实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的理念。【参见吴凯杰:《法典化背景下环境法基本制度的法理反思与体系建构》,载《法学研究》2024年第2期,第151页。】其实,体系性不是一味地追求大而全,它有内在的逻辑方法,这些方法也会限制体系性自身。所以,法典的体系化都是有限程度的体系化。体系化程度越高,提取公因式的抽象化程度就越高,法条中的概念术语就越专业甚至晦涩,法律规范中的禁止、命令或指引内容就越模糊。从而使得法典远离大众变成行内人的法典,并且,在适用过程中越抽象模糊的法典就越需要具体化解释,甚至需要制定单行法或颁布补充规定等,当这些规定和解释越来越多时,就会影响法典的法源地位。另外,体系性意味着结构的严谨性和秩序的稳定性,对法典的某一部分修改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社会变迁确需修改法典时,为了不破坏体系结构,替代方法就是在法典之外颁布修正案,但修正案不宜过多,否则会破坏体系结构的完整性。
任何法律的内部结构都有一定的排列顺序,但只有体现出科学性和哲理性的顺序才能叫体系。有的法律的科学性、哲理性强,有的较弱,这导致体系性有强弱程度之分。从《法国民法典》到《德国民法典》的发展就是体系性不断完善的过程。一种说法认为,正是因为体系性存在强弱之别,我国刑法在体系上还未实现尽善尽美,其体系性问题使得我国刑法学界认为1997年《刑法》需要再法典化。【尽管我国刑法学界存在要不要再法典化的争议(参见姜涛:《刑法再法典化的法理与蓝图》,载《中国法学》2023年第5期,第30-32页),但大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再法典化了(参见刘艳红:《我国刑法的再法典化:模式选择与方案改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3期,第60-79页;陈兴良:《从实质刑法典到形式刑法典:刑法的进阶之路》,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2期,第1-19页;刘仁文:《论“再法典化”背景下刑法量刑情节的体系优化》,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第106-116页;梁根林:《中国刑法再法典化:本土共识与国际视域》,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1期,第56页;江溯:《美国〈模范刑法典〉对中国刑法再法典化的启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1期,第70-79页)。】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理由有如下几点:第一,“再法典化”不是“进一步法典化”,也不是刑法的“进阶之路”,“再法典化”是“解法典化”之后的对策性措施。所谓的解法典化是指特别法从法典中夺取一些制度与一些类型的法律关系自己调整,使得法典成为剩余法,或给法典的统一性造成重大裂缝。【参见[意]那塔利诺·伊尔蒂:《解法典的时代》,薛军译,载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秘鲁]玛丽亚·路易莎·穆里约:《大陆法系法典编纂的演变:迈向解法典化与法典的重构》,许中缘、周林刚译,载《清华法学》(第8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体系性固然有其优势,但也会造成法典的封闭性和滞后性,为了解决法典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大量特别法应运而生,从而“架空”法典,它不仅给法典带来逻辑体系上的抵牾和漏洞,而且让法典变得多余,立法者不得不再次把法典和众多特别法熔为一炉进行体系化建构,可见,“再法典化”不是把之前的法典进一步法典化,而是重新法典化。很多学者误解了这点,也混淆了“法典修订”和“再法典化”。第二,“再法典化”以“解法典化”为前提,但我国刑法并没有被解法典化。解法典化是指法典被众多单行法、法官造法等分解,但是我国刑法体系中只有一部单行法,司法解释也并没有取代刑法。实际上存在的挑战是十多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影响,有学者据此认为存在“解体危机”【参见刘艳红:《我国刑法的再法典化:模式选择与方案改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3期,第61-65页。】,这有一点言过其实,刑法并没有解体。张明楷教授曾认为:“刑法从未像民法那样解法典化。”【张明楷:《刑法的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6期,第60页。】所以,我国刑法缺乏“再法典化”的前提。第三,我国刑法体系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如果能在体系性内部解决,体系就能维持,就可以在现有体系之下来修改和调整。有学者列举再法典化的理由是:“无论从克服现有刑法典的内容老化,还是从整合多次刑法修正案所造成的刑法制度和知识的碎片化,以及应对新的犯罪形势的需要方面看,都应尽快启动刑法典的全面修订工作,以实现刑法的再法典化。”【刘仁文:《论“再法典化”背景下刑法量刑情节的体系优化》,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第106页。】其实,“内容老化”“制度碎片化”及无法应对新形势等问题都只是修订法典的理由,基于这些理由把现行刑法“推倒重来”得不偿失。如前文所述,体系性有强弱程度之分,没有人能保证其所编纂的法典达到了最完美的体系性,我们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逐渐优化体系来解决“内容老化”“制度碎片化”等问题。第四,有学者主张刑法的再法典化宜采取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的三元模式。【参见李晓明:《再论我国刑法的“三元立法模式”》,载《政法论丛》2020年第3期,第32页;陈兴良:《从实质刑法典到形式刑法典:刑法的进阶之路》,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2期,第7页;姜涛:《刑法再法典化的法理与蓝图》,载《中国法学》2023年第5期,第38页。】其实这是自相矛盾的主张,因为再法典化源自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等对刑法典本体的解构,而这种三元模式的再法典化是搬石头砸自己脚,一边再法典化一边留下解法典化的隐患。
可见,体系性的限度给法典理想主义者带来了编纂上的难题,为了兼顾大众性只能采取有限程度的体系性。完美的体系仅仅只是一个“在路上”的理想,没有上限。正是因为体系性没有上限,也就使得法典不会轻易遭遇解法典化困境,很多问题还没等到累积到解构体系之时就可以通过完善体系、修改法典等方式消化掉了。
(三)完备性的要求与限度
由于完备性和大众性、体系性之间都有内在张力,这注定了“万全法”的编纂目标是不可行的,完备性是相对的,后来的《奥地利民法典》就不再尝试《普鲁士通用邦法》所追求的全面性。但是《奥地利民法典》却纠枉过正,规定过于简洁,仅有1502个条款,出现了大量的缺漏。所以,放弃涵盖领域上的完备性,不等于放弃对具体问题的规定上的完备性,因为完备性在宏观层面要求规范领域的完备性,同时在微观层面要求规范结构的完备性。完备性的限度更多地体现在宏观领域,其争议也在此。这种争议投射在刑法典编纂中就是“多元模式与一元模式”之争,在行政法典中是“统一的行政法典、行政程序法典及行政基本法典”之争,在教育法典中是“大教育法典与小教育法典”之争。
刑法一元模式主张编纂一部统一刑法典,把所有刑法都囊括其中。【参见刘艳红:《我国刑法的再法典化:模式选择与方案改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3期,第69页;周光权:《法典化时代的刑法典修订》,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5期,第48页。】多元模式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刑法典应该保持稳定,将法定犯规定在行政法、经济法中有利于随时修改法律,而不至于损害刑法典的稳定性。【张明楷:《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立法体例下的实质解释》,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第47页。】并且,如果将这些适用于特定领域、特定专业和特定主体的刑法规范纳入刑法典中,会使刑法典杂乱不堪。【陈兴良:《从实质刑法典到形式刑法典:刑法的进阶之路》,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2期,第7页。】所以,应该采取多元模式,把法定犯交给特别法或附属刑法来规定。其实,多元模式的理由并不成立,自然法和法定犯自然有很多相同点,可以合并同类项一体化立法而不至于杂乱不堪,我国现行刑法就成功做到了这点,把它们规定在了一个体系之中。人为区分自然犯和法定犯,把后者从刑法典中割裂出去,牺牲了完备性。并且,按照此逻辑,行政法就不能法典化了,因为绝大多数行政法规范和法定犯的基础一样,都属于国家出于社会管理发布的规章制度,经常变化。如果行政法还能法典化,那么多元模式的反驳就不成立。任何法典一经制定出来就面临体系的封闭性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开放性之间的张力,如果不坚持完美体系观,这种张力就很弱,通常可以在体系内部通过修改法典来化解张力。
而行政法典编纂中的“行政基本法典”主张和教育法典编纂中的“小教育法典”主张,都是因为存在“完备性的限度”。在行政法典编纂中,“统一行政法典”模式主张法典应包括一般行政法和部门行政法,也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参见杨伟东:《基本行政法典的确立、定位与架构》,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53页;刘太刚:《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障碍、模式及立法技术》,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25页。】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万全法式的理想,学者们的修正方案有两种:第一种主张把法典内容限缩为行政程序法,把行政组织、行政行为等实体法排斥在外,编纂行政程序法典;【参见王万华:《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的程序主义进路选择》,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第122页;姜明安:《关于编纂我国行政程序法典的构想》,载《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221页。】第二种主张把部门行政法排除,保留一般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法,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参见马怀德:《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内容与框架》,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46页;马怀德:《中国行政法典的时代需求与制度供给》,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4期,第861-862页。】第一种方案简单易行,但范围太窄、意义有限。比较而言,第二种更可取,因为一般行政法中有很多内容可以合并同类项进行体系化建构,不宜排斥在法典编纂之外。而部门行政法过于庞杂,且各领域之间差异较大,缺乏共性,难以进行体系化建构,不宜纳入法典。同样,“大教育法典与小教育法典”之争与行政法典编纂模式之争具有类似性,这取决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具有多大程度的相似性,如果相似程度较高,则能够合并同类项编纂大法典,反之如果相似程度低,就只能编纂小法典。可见,完备性以体系性为基础和前提,如果无法进行体系建构,就只能放弃完备性。
在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模式上,我国学者罕见地达成了共识,采取“适度法典化”模式。【吕忠梅:《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模式选择及其展开》,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6期,第70页;曹炜:《环境法“适度法典化”的理论反思与方案建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6期,第114页。】但是就何为“适度”存在不同看法,有调整范围与编纂程度上的适度;【参见吕忠梅:《环境法典编纂的基本问题》,载《荆楚法学》2022年第1期,第32页;何江:《为什么环境法需要法典化——基于法律复杂化理论的证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5期,第71页。】有体系化、开放性与阶段性层面上的适度;【参见张忠民、赵珂:《环境法典的制度体系逻辑与表达》,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30页。】有以法典体系效益为基础的三个维度上的适度;【参见李艳芳、田时雨:《比较法视野中的我国环境法法典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18页。】有动态进程上的适度。【参见张梓太、陶蕾、李传轩:《我国环境法典框架设计构想》,载《东方法学》2008年第2期,第33页。】我赞成第一种观点,“适度”应该从体系性和完备性的双重限度来理解,既包括适度体系化,也包括适度完备化。这是基于纷繁庞杂的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之现实的理性考虑。
完备性在不同法律中的限度有所不同,如刑法典对于完备性的要求就比其他部门法高,宪法对完备性的要求就较低。因为刑法要贯彻罪刑法定、禁止类推原则,相对于私法而言,刑法典编纂更加要追求完备,不留漏洞,所以可以提出编纂一部适度的生态环境法典,不能提出编纂一部适度的刑法典。而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等抽象内容,条文表述不宜过于具体,宪法的性质决定了其原则性规定和抽象性说明较多,其完备性要求可适度降低。
(四)法典的形式取向及其检讨
韦伯认为法律的发展变迁遵循“形式不理性→实质不理性→实质理性→形式理性”的模式。【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321页。】西方法律的发展尽管曲折多变,但大体上遵循了这套发展模式。罗马法在一千多年的复兴和成长中,一代一代的职业法律人通过技术理性祛除罗马法中的个案决疑式内容和地方性特色,逐渐建立起了抽象逻辑形式和法律的形式特质。这些形式特质使得法律规则在事实上拥有异常的明晰性与精确的了然性。【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页。】人们可以直接依据这些规则来行动,无须进行伦理、功利的考虑,这能防止主权者的恣意并最大限度地保护行动自由。形式理性只考虑以何种手段达成目的是最佳的,不考虑行动所要实现的价值,不会陷入到无休止的价值争议之中。韦伯因为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所以推崇形式理性的法律,而法律形式理性的发展巅峰正是体系化的法典。近代法典概念基本围绕法典的形式特质展开,权威性关注法典在形式上的合法性源头;体系性强调法典内部结构在逻辑形式上的无矛盾性;至于完备性,无论是宏观层面的规范领域的完备性,还是微观层面的规范结构的完备性,都是形式要求,不涉及任何实质价值判断。
其实,code之词本意也是形式取向的。Code源自拉丁文cōdex或者caudex,与cōdex对应的古希腊文有κώδιον、κύρβεις和ỏξυα。kώδιον的原意是“一块羊皮”,ỏξυα也指“板子”,κύρβεις特指用来书写法律的锥形三面板子,【参见[美]亨利·乔治·利德尔、罗伯特·斯科特编:《希英词典:中型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7-459、560页。】无论是“羊皮”“板子”还是“锥形板”都指记载文字的载体,所以,从词源上看,caudex的含义更侧重其载体形式。其含义经历了载体(羊皮纸)到泛指(册子书)到具体所指(法令集成)的变迁。法令集成就是法律汇编,在近代法典诞生之前,无法区分或者干脆不区分“法典”和“法律汇编”也就不足为奇了。古代的cōdex演变成近代的code还需要经历科学性的洗礼,19世纪的法典编纂运动完成了这场洗礼,给code添加了cōdex所没有的体系性,完成了“法令集成(法律汇编)”到“法典(体系性的有机整体)”的含义转变。近代法典不仅是所有生效法律的汇编,而且是它们的体系性表达。无论如何,cōdex的概念变迁都没有摆脱形式化的路线,完备性、体系性和权威性只是形式化路线精细发展的结果而已。
但是形式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如果形式理性只考虑以何种手段达成目的是最佳的,而不考虑行动所欲实现的价值的话,它可能无法确定何种手段是最佳的。例如,关于我国刑法典的分则编排顺序学界争论不休,刘艳红教授认为应该“将国家法益放在分则首位,社会法益次之,最后是个人法益,这样的体系排序在我国较为妥当”。【刘艳红:《我国刑法的再法典化:模式选择与方案改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3期,第76页。】陈兴良教授和张明楷教授则认为:“应当按照侵犯个人法益犯罪、侵犯社会法益犯罪和侵犯国家法益犯罪的顺序排列,前一类型的犯罪优位于后一类型的犯罪。”【陈兴良:《从实质刑法典到形式刑法典:刑法的进阶之路》,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2期,第14页;张明楷:《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法典化》,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第65页。】在形式理性看来,只要呈现出合逻辑的优位关系就可以了,是个人在前还是国家在前不影响法典结构的体系性。所以形式理性无法解决这场争议,这场争议涉及国家法益价值和个人法益价值的比较,以及我国刑法典应该采取何种价值立场,只有实质理性才能做出判断。
同样,在其他部门法领域的法典编纂争议中也有形式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法典编纂的逻辑主线问题。有人认为生态环境法的目的价值是可持续发展,所以可持续发展应该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逻辑主线;【参见吕忠梅:《环境法典编纂论纲》,载《中国法学》2023年第2期,第30页。】行政法典的编纂面临“客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与“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两种定位之间的选择,为了能更直接、更有力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学者们选择了后者。【王万华:《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与立法选择》,载《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5期,第82页。】关于教育法典的逻辑主线,任海涛教授认为应该是“教育法律关系”,【任海涛:《教育法典总则编的体系构造》,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6期,第131-132页。】特别是“受教育权”。【任海涛:《教育法典分则:理念、体系、内容》,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65页。】段斌斌教授认为应该是“教育主体”。【段斌斌:《教育法典的体例结构:域外模式与中国方案》,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25页。】其实,法典逻辑主线的确立依赖于法典的目的价值,形式理性对此无能为力,只有实质理性才能做出取舍和判断。
只强调形式理性的法典是空洞的技术性规范体系。不顾本国的文化特色或民族精神,制定一部形式完美的法典虽然符合完备性、体系性和权威性特征,但不能实现其目的价值也是枉然。波塔利斯曾告诫说:“要谨记,法律为人而立,人不是为法律而活。”【Andre Tunc,Grand Outlines of the Code Napoleon,29Tulane Law Review444(1954-1955);Andre Tunc,Methodology of the Civil Law in France,50Tulane Law Review468(1975-1976).】法典体系不是去织就一幅没有灵魂的网,还需要实质价值的指引。反过来,完美的体系也有利于法典从细节处贯彻和落实实质价值。在未来教育法典、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中,应该首先确立法典的实质理性和价值立场,这比确立编纂模式和体例安排等形式更重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中说民法典编纂的目标是:“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参见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2017年3月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7-03/09/content_2013899.htm,2024年7月26日访问。】“规范合理”是实质价值的要求,“体例科学、结构严谨、内容协调一致”是形式理性的体现,民法典的编纂目标很好地统一了形式和实质,这也应该成为我国未来其他法典编纂的目标。
五、结语
从古代的《汉穆拉比法典》到《优士丁尼法典》再到近当代的《德国民法典》和我国的《民法典》,法典名称没变,但名称背后的法典概念却几经变迁。按照近代法典概念,《汉穆拉比法典》和《优士丁尼法典》因不具备体系性,不配享法典之名。但那时的法典概念尚未经历科学性的洗礼,体系性未上升为法典的核心特征,汇编型法典也是法典,所以《汉穆拉比法典》和《优士丁尼法典》符合那个时代的法典概念。同样,当我们用近代法典概念来理解当下的法典编纂实践时,发现权威性要素排斥民间式法典,而体系性和完备性要素变得相对化,适度法典化甚至多元编纂模式被众多学者所拥趸,近代法典概念显得捉襟见肘。现代社会呼唤现代意义上的法典赋名。【参见董彦斌:《法典赋名及其恰当性述论》,载《政法论坛》2024年第3期,第172页。】特别是近代法典概念的形式取向只不过是对法典词源的形式意涵的进一步巩固。cōdex的概念内涵经历了载体(羊皮纸)到泛指(册子书)到具体所指(法令集成)最后又到泛指(体系性的有机整体)的过程,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脱形式取向的窠臼。而体系性、权威性和完备性要素都是从形式方面对法典的解释和描述,只不过更精细而已。
近代法典概念的形式取向使得它并没有完全颠覆优士丁尼时代的法典概念,哪怕他们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但是,近代法典概念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迫使它开始反思自身,特别是在面对法典编纂的核心分歧时,形式理性无能为力,需要引入实质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法典编纂实践正在催生新的法典概念。总之,法典之名千年未变,法典之概念却在变与不变之中发展、在挑战和应对之中更新自身。ML
Contemporary Respenses to the Concept of Modern Legal Codes
WANG Xio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The prevailing concept of codification consists of three elements:systematicity,authority,and completeness.This concept originated from the modern codification movement since the19th century.It is,however,facing various challenge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firstly,the folk codifications in the20th century have greatly impacted the authority;secondly,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diversified legal norm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not only make the codifications obscure and distant from the public if the traditional systematicity standard is stubbornly adhered to,but also sow the seeds of de-codification;likewise,the completeness has become relative,with scholars no longer demanding the completeness at the macro level of the scope of regulations,but more at the micro level of the regulatory structure;lastly,formal rationality cannot solve many controversies in contemporary codification,as codification is not purely formal.In summary,the concept of modern codification needs to abandon its own character,and develop in the change and invariance,and update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Key words:systematicity;authority;completeness;folk codification;formal rationality
本文责任编辑:董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