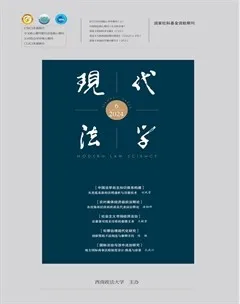兜底条款的法理透析与设置技术
2024-12-18刘风景
摘 要:兜底条款是以一个条文前面列举的各项规定为典型情形,对剩余的次要事项,以含有“其他”的命题式语句,体现为法律文本层次结构“项”的总括规定。基于良法标准对法律中兜底条款进行观察,可以发现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兜”“底”错配,外观标识不清,列举层次过少,主次地位混同。兜底条款是个复杂的法律现象,并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选择,需要在多元的法律价值目标面前,运用法律智慧,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兜底条款有着特定的规范结构、功能定位,也有着相应的技术规范。兜底条款的设置,应当编入立法技术规范,选择疏密适度的“过滤网”,经过充分细致的立法论证,采取与时俱进的动态调整。
关键词:兜底条款;例示规定;“其他”;立法技术
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4.06.01
兜底条款有着特定的规范结构、承担着专门职能,它在法律文本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且在司法适用中又很容易引发争议,是一种需要认真对待的法条形式。迄今,部门法学者对兜底条款做过多方面的分析,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法理学的研究尚不充分,还比较薄弱,有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空间。首先,法理学作为法的一般理论,可提炼出兜底条款的共同法理。兜底条款在制定法中分布很广,几乎每个法律文本都能找到它的踪迹,需要运用法的一般理论,能够从大量的立法例中抽象出超越部门法学的共同法理。其次,作为法的基础理论,可揭示兜底条款的深刻本质。兜底条款出现在许多法律文本之中,需要运用法的基础理论,透过复杂多样的法律条款形式,挖掘出深藏不露的内在本质,为相关的法律创制、法律实施,奠定坚实的法理基础。再次,作为法学方法论,可提供兜底条款的分析工具。目前,有关兜底条款的研究,多是立足部门法特别是刑法学,对一个个条文进行具体分析。除了少数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兜底条款外,这种对某个法条兜底条款的单项研究浪费学术资源,且容易造成学术成果的碎片化。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概括出所有兜底条款的一般法理,如逻辑结构、规范要件、功能定位、主要类型、实践样态、表述技术等,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作为法学价值观,可找准兜底条款的方向目标。法学价值观是一种系统化的法学认知观念,它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行为都产生重要影响。兜底条款的施行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需要法理学的拓展,进行适当的内容填充、价值协调,总结出兜底条款的一般性适用规则;兜底条款的规范结构特殊,需要法理学的支撑,编制出一套有效的立法技术规范。法理学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是法的一般理论、法的基础理论、法学方法论和法学价值观,是分析兜底条款不可替代的重要理论工具。还应当注意的是,在法典化时代,兜底条款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20年民法典的成功编纂,为其他领域立法法典化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提出:“积极研究推进环境(生态环境)法典和其他条件成熟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深化立法领域改革,“统筹立改废释纂”。作为一种重要的立法形式,法典编纂被赋予重要的历史使命。法典具有“统一、完备、系统化”的形式特征【参见董彦斌:《法典赋名及其恰当性述论》,载《政法论坛》2024年第3期,第177页。】,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与假定条件、法律后果比较模糊的兜底条款是排斥、不相容的,但有效地运用兜底条款,可以更好地协调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封闭性与开放性、现时性与长期性的关系,提高法律的实效性。
一、兜底条款的规范结构
兜底条款是以一个条文前面列举的主要事项为典型情形,对剩余的次要事项,以含有“其他”的命题式语句,体现为法律文本层次结构“项”的总括规定。兜底条款是由多个词语构成的独立句子,其自身有若干个组成部分,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分工明确,又相互联系、紧密配合,呈现出有序的规范结构。
第一,以“其他”为标识语。“其他”是兜底条款的外观标志,但不是全部含有“其他”的句子都是兜底条款,需要仔细的甄别。一般地,“其他”的含义主要有二:一是指列举事项以外的事物;二是指列举主要事项后的剩余次要事项。在法律中,“其他”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除外规定,即在排斥性关系中关于除外事项的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67条第2款【《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关于自首的规定。《刑法》第67条第2款所列举的典型事项与“其他”指涉的事物,是外延完全不重合的全异关系,非本文的研究对象。二是例示规定,即主要事项列举后,还有剩余的次要事项的规范样式,其标准的规范样式为:两个以上典型事项+和、以及、及等连词+其他+上位概念。【参见刘风景:《例示规定的法理与创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93-105页。】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10条第1款【《民法典》第110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的规定。在第二种用法中还可以具体区分为例示规定与兜底条款。
兜底条款是一种特殊的例示规定,它与例示规定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处。一般地,例示规定是立法者对于意欲调整且难以穷尽的事项,先对几个典型事项予以列举,再连缀助词“等”或代词“其他”,最后加上较为抽象的上位概念以全面涵盖调整事项的法条形式。兜底条款与例示规定之间是属概念与种概念的关系,前者为后者所包含。但是,在法学界,人们往往将兜底条款等同于一般的例示规定,两者不作区分。有学者认为,刑法中的兜底条款,是指刑法规定的,立法者无法穷尽法条描述之情形时所采用的概括条款,通常用“其他”或者“等”的表述方式。【参见马东丽:《我国刑法中兜底条款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页。】《刑法》第151条第3款“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规定中重复使用“等”与“其他”,有学者认为这属于“双兜底”条款。【参见刘涛:《走私犯罪中“双兜底”条款及其解释规则构建》,载《海关与经贸研究》2020年第5期,第65页。】这种将兜底条款与例示规定相混同的观点,有待商榷。兜底条款是例示规定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是“双层”例示规定,而非“双兜底”条款。该法条的第一层次是一般的例示规定,第二层次才是作为特殊例示规定的兜底条款。兜底条款是一种特殊的例示规定,它的设置除了遵循例示规定的一般性技术规范外,还有其特殊的要求。
“等”与“其他”都具有列举未尽的含义,并且都必须以列举事项为前提才能确定其所包括的事项范围,但是“等”与“其他”有着明显的差别,不能简单地置换替代。其一,在与列举事项的密切程度上,“其他”较为疏远,而“等”则更为接近。通过对比《刑法》第115条【《刑法》第115条第1款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和《刑法》第256条【《刑法》第256条规定:“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可以发现,由于《刑法》第115条“其他”一词前面有“以及”“和”等连词,使得这些连词前面和后面的词语表示的是相同类别的事物或对象。这些连词的运用,列举的典型事项与“其他”包含的事项之间的关系较为疏远,解释时相对自由灵活;同时,还由于不同连词含义存有差异,使得典型事项与“其他”包括的事项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刑法》第256条运用“等”字连接上位概念与典型事项,表明指代事项与典型事项更为类似,相对地,上位概念词义的射程范围更小。其二,在法条的结构中,“其他”可以构成兜底条款,而“等”则不可。兜底条款以前面的各项规定为典型情形,对剩余的次要事项,以命题形式做的总括规定。例如,《刑法》第7qL7ey6iS7Opq5TUHidZiWnq7riOtUyeQhSmQJexG1mw=8条第1款【《刑法》第78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关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减刑的规定。一般地,含有“等”字的句子,则不能构成独立的兜底条款。但在“等”与“其他”连用的情况下,“等”字也可能会出现在兜底条款中。其三,在法条的位置上,“其他”可以起头但不能结尾。“其他”之前可以无任何词语。例如,《刑法》第95条第3项规定:“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相对地,“等”不可以开头,但可以直接结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78条第6项规定:“人畜共患传染病:指人与脊椎动物共同罹患的传染病,如鼠疫、狂犬病、血吸虫病等。”
第二,兜底条款系分说句子。兜底条款是“将一连串应该同等对待的相似事项包含在一个简单句中”。【[美]安·赛德曼、罗伯特·鲍劼·赛德曼、那林·阿比斯卡:《立法学:理论与实践》,刘国福、曹培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句子是词或词组按照语法组织起来,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意思的语言单位,它比单词要复杂些。相对于以概念、词语形式表现的例示规定,兜底条款自身即为一个由多个词语构成的独立句子,其成分相对复杂。《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10条明确列举5项经济业务事项,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在此基础上,第6项“需要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的其他事项”的规定,即为兜底条款。之所以设置该条款,考虑到会计环境纷繁复杂,经济活动及会计业务的发展日新月异,会计核算中可能出现一些新的业务和内容,如企业的终止清算,破产清算等。【参见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相对地,《刑法》第256条“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只是一般的例示规定,被列举出来的都是概念、术语,它不属于兜底条款。
兜底条款体现为法律文本结构层级的“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规定,法律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编、章、节、条、款、项、目。兜底条款是命题式语句,在法律文本层级结构中表现为制定法的条或款之下的“项”。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6条第3项规定“其他因职务原因不适宜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人员”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兜底条款对应的都是法律文本层次结构的“项”,迄今尚未发现其他的结构层级成为兜底条款的情形。
兜底条款虽系分说句子,但它必须存在于总分结构之中。从逻辑角度看,“项”的结构是一个总分说复句,由总说句子和分说句子构成的。【参见郭继良:《如何引用法律》,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99页。】分说句子,也就是例示分项,先详细列举各要件,但为避免疏漏,以期立法周延完备,而在最后一项中作一概括性规定。大多数“项”是不能独立表达完整意思的并列分句,必须依赖于“项”之前的“项前主文”,即总说句子。分说句子,还可以细分为积极的择一法、消极的择一法、积极的完全法、消极的完全法等四种:其一,积极的择一法,是指符合例示分项的要件之一,即得为某行为或取得某资格。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第29条【《反家庭暴力法》第29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规定。其二,消极的择一法,是指符合例示分项的要件之一,即不得为某行为或任某职务。例如,《民法典》第106条【《民法典》第10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非法人组织解散:(一)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二)出资人或者设立人决定解散;(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规定。其三,积极的完全法,是指具备例示分项的全部要件,始得为某行为或取得某资格。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以下简称《企业国有资产法》)第23条【《企业国有资产法》第23条第1款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任命或者建议任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良好的品行;(二)有符合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三)有能够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规定。其四,消极的完全法,是指具备例示分项的全部要件,即不得为某行为或取得某资格。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14条【《反垄断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规定。
第三,“兜”与“底”相互依存。兜底条款的表述是隐喻式词语,是通过一物好像另一种事物的类比思维而构建的。在法学中,隐喻是一种重要的定义方式,人们运用熟悉的某一事物做中介来表达陌生、复杂的对象事物,以实现由此及彼的认知转换。“隐喻的使用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一个概念,特别是一个困难的概念。”【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客观地说,兜底条款是一个法律隐喻,虽不够精准,但能够描绘出一幅较为清晰的图像。在法学上,相似的容器类隐喻有很多,诸如“口袋”“包裹”“箱子”“兜子”等。例如,中国古代刑律的“不应得为”规定,就起到包括、容纳的作用,使所有不合法律的行为均落入圈套,难以脱罪。有国外学者将这一规定称为“catch-all”(“盛装杂物的箱子”)。【参见[新加坡]刘启扬:《洞悉法门:理解法律的复杂性》,张巍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127页。】还有,刑法中的“口袋罪”因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为许多人所诟病。兜底条款的“兜”,就是一种容器、包装物,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底”,与其他部分相合作,实现包装着前面列举的典型事项之外诸多类似事项的作用。
进一步观察可发现,兜底条款是指在列举规定之外,采用“其他”这样一种概括方式,以避免列举不全,涵括其他剩余事项。“兜底”一词,是由“兜”和“底”两个词素构成的。对于兜底条款中“兜”和“底”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理解:一是静态的偏正结构,即作为包装物的名词——兜之底部。前一个语素修饰限制后一个语素,前为偏,后为正。例如,汽车、黑板、法庭、法官、公审等。这里,如果把“兜”理解为裤兜、网兜、布兜等的容器、包装物,那么“兜底”就是兜的底部、下面的意思。二是动态的述宾结构。动词的“兜”,指向宾语的“底”。把“兜”理解为一种行为,即归拢、接收的意思,例如,兜风、兜捕、兜揽、兜售等。在我国,政府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需要运用社会法,发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制度兜底功能。【参见金昱茜:《论我国社会救助法中的制度兜底功能》,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3期,第144页。】2022年民政部会同中央农办、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ZG5NlvPfg2h0HS/FQ76slQ==等社会救助范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实现低保等社会救助扩围增效,切实兜住兜准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进一步做好低保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在此,“兜”和“底”之间的关系是,前一个语素表示某种动作行为,后一个语素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或趋向。其中前一个语素“兜”表示特定的行为,后一个语素“底”表示这一行为的目标和欲达到的结果。实际上,我们对兜底条款的理解,是将静态的偏正结构与动态的述宾结构结合起来,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
第四,“兜底”是疏密不等的“滤网”。密度是指物体的质量和其体积的比值;在植物群落的一定面积内,某个植物种群的单位面积个体数目或生物量。群落内全部植物物种的密度的和,同某个种的密度的比例,成为“相对密度”。作为引申义的立法密度,是指法规范数量与所调整社会关系面积的比例。“规制同一法律领域的条文数量越多,也就意味着其具体化程度越高。”【[美]弗朗西斯科·帕雷西、文西·冯主编:《立法的经济学》,赵一单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41页。】在不同的法律部门、法律领域中,规范密度差别很大。物权法、道路交通法的规范密度,要大于合同法、婚姻家庭法。进言之,针对不同的事项,兜底条款的规范密度也有所不同。兜底条款采用“其他”这样一种概括方式,以避免列举不全。兜底条款在“其他情形”之前,往往加上详略不同的限定语,用来控制法律规定的疏密度。这些限定语有的是抽象的规范性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5条第6项“法律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其他情形”之中的“法律规定”。根据该款规定,其他法律只有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才可以规定征地的其他情形,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无权对征地情形作出规定,这体现了严格限制征地范围,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的立法精神。【参见杨合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83页。】这类限定语主要包括“法律规定”(《民法典》第69条、第106条、第123条、第175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第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3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许可法》第80条),“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15条,《反垄断法》第12条],“法律、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证券法》第118条),“证券业协会章程规定”(《证券法》第166条),“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26条),等等。还有的是具体的行为,例如,“人民法院认定”(《民法典》第39条),“双方认为需要约定”(《著作权法》第24条、第25条),等等。再者,“其他”之前的限定语之中还可能嵌入“以及”“或者”“和”等连词。由于这些连词含义的微妙差异,也导致了“其他”所包含的事项与典型事项之间联系的复杂多样,也使兜底条款的规范密度,呈现出大小不等的情形。
二、兜底条款的实践审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立良法行善治。良法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内容方面,应立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现广大人民意志;在形式方面,要明确具体、和谐统一、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准确地表达权利义务。兜底条款是体现法律内容的法条形式,是形成良法的重要技术和外在形式。基于良法标准对现行法律中兜底条款进行观察,可以发现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第一,“兜”“底”错配。有刑法学者认为,兜底条款中的“兜”需要兜住列举事项的“底”,如果不存在列举事项,“兜底”之说自然不存在。兜底条款与列举事项相并列,共同指向同一法益,反映相同的罪质。所以,理解兜底条款需要结合前面的列举性规定,以该规定的内容为参照把握兜底条款的具体含义。法律适用者在对兜底条款进行使用时,应当根据该条款所处的位置和具体范围保护的法益,运用同类规则解释方法,了解立法者意图并把握兜底条款的内涵和外延,将性质相同的行为纳入兜底条款文义范围内,将性质不同的行为排除在构成要件外。【参见张建军:《论刑法中兜底条款的明确性》,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93页。】该观点准确地阐明了兜底条款的应然结构,“兜”与“底”应相互衔接、大小适配,既不能“兜”大于“底”,也不能“兜”小于“底”,而且“兜”“底”同质,指向同一性质的事物。但是,在立法实践中,“兜”“底”错配现象并不鲜见。
一方面,存在着“底”大“兜”小现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4条规定的是扰乱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行为及处罚,其第6项“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其他行为”的规定,取消了“文化、体育等”的限定语,扩大了行政处罚的行为范围。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兜”大“底”小现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款第12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在我国,倘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除人身权、财产权以外,宪法规定公民基本权利还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选举等政治权利,该兜底条款将这些权利置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似乎限缩了《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语义。
兜底条款的规定过于笼统模糊,其指代事项范围的伸缩度大,既可能导致“兜”大于“底”的囊括不足缺陷,也可能导致“兜”小于“底”的过度囊括弊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19条规定:“企业由于下列原因之一终止:(一)违反法律、法规被责令撤销……(四)其他原因。”第4项“其他原因”之前没有任何限定词,规定过于笼统、原则,有可能造成指涉对象外延的不当扩张或限缩。
再者,“兜”“底”错配还表现为“兜”“底”异质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一)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四)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前面总说句子中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属于法官能够自主裁量选择的“可为”;后面分说句子兜底条款中的“应当延期开庭审理”,则是不得不实施的“应为”。
第二,参照系不清楚。兜底条款是由“兜”和“底”两部分构成的,对兜底条款的理解以前面的列举性规定为参照系来把握。如果兜底条款列举的事项较少,那么不同事项间的共同特征也较少,对不同事项间的共同特征的概括规定也较为抽象。此时,为了明确抽象的概括规定,往往需要借助体系因素或将立法意旨具体化。列举的典型事例过少甚至是一个的,“兜”无法提供一个有用的类型的信息,兜底条款的理解就缺乏相对明晰的语境,“底”的模样也就含糊不清。可以说,兜底条款明确列举的同类项目越多,越能够清晰地呈现该条款的基本属性,越有助于理解把握规定内容。如果所列项目过少甚至是单独一项的,就难以理解兜底条款提供足够的参照对象,难以把握“其他”所指代的事项。例如,《著作权法》第9条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一)作者;(二)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该兜底条款之前的列举规定数量过少,参照系不清晰,法律适用难度大。
兜底条款与例示规定相叠加,也可能导致难以找到明确的参照系。兜底条款中“其他”所指代的事项,对它的理解,要以前面列举的典型情形为语境。如果语境模糊,就很难作出准确的阐释。例如,《行政许可法》第12条【《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一)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四)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五)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的规定,除了有兜底条款外,前面的5项规定中都有“等”字的出现,这样就存在着两个层次的例示规定,如果出现一种在明确列举规定之外的新情况,到底应归入前5项的“等”之中,还是第6项兜底条款的“其他”之中,就会产生困惑。进言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法律后果的归结,也可能产生分歧。
第三,外观标识不清。兜底条款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两者应同时具备。有的法律条款,实为兜底条款,但没有“其他”的字样,难以准确地认定、引用。例如,《行政诉讼法》第56条第1款第4项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其他法律、法规,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7条,也有一些诉讼期间停止执行方面的规定。【参见袁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该法条属于兜底条款,但外观标识不明显。这类标识不清的还有很多,比如,《行政许可法》第72条第8项规定:“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民事诉讼法》第21条第2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的案件”。这几个法条都属于是兜底条款,应当有“其他”字样,但不当省略的立法例。
第四,主次地位混同。哈特指出,所有规则的理解都需要将特定的情形归类于一般性语词所包含的事例中,在适用中,存在毫无疑问的核心事例,也存在尚有疑问的其他事例。当我们将特定的情形涵摄于抽象的规则项下时,总会存有确定性的核心和存有疑问的边缘,这使得规则具有“开放性结构”。【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86页。】这种核心事例与边缘事例的划分,在兜底条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称《广告法》)第68条【《广告法》第68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一)在广告中损害未成年人或者残疾人的身心健康的;(二)假冒他人专利的;(三)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服务的;(四)在广告中未经同意使用他人名义或者形象的;(五)其他侵犯他人合法民事权益的。”】的条文构成中,前面4项规定是核心的主要行为,“其他侵犯他人合法民事权益的”兜底规定则是边缘的次要行为。相反地,如果兜底条款没有区分出核心事例与边缘事例,就是失败的立法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17条规定:“红十字会财产的主要来源:(一)红十字会会员缴纳的会费;(二)境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三)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四)人民政府的拨款;(五)其他合法收入。”从兜底条款的结构上看,红十字会财产的主要来源是第1项到第4项明确列举的四个方面,第5项作为兜底条款,不是“主要来源”,而是次要来源。在该法条的具体表述上,总说句子将全部5项的内容都规定为“红十字会财产的主要来源”,但是,第5项的“其他合法收入”与明确列举的前4项相比,不是平列关系,而其地位作用相对次要。
在逻辑上,意欲完善兜底条款,就需要发现兜底条款存在的问题。正是因为发现了兜底条款存在着“兜”“底”错配、语境不清晰、外观标识不清、主次地位混同等问题与瑕疵,并揭示其可能的弊害,才能为提升兜底条款的立法水平,探寻可行路径。
三、兜底条款的功能定位
对兜底条款的审视,不能仅停留于条款表述的技术层面,还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其应当承担的功能上予以评价。当采取行动时,我们意欲实现的目标往往不是唯一的,但我们不能为了实现其中一个直接的目标而牺牲我们意欲实现的所有目标。当意欲实现的目标间出现冲突时,需要立法者理性地设定相互冲突之目标间的优先性。【参见[美]昂格尔:《知识与政治》,支振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立法是价值冲突的解决机制,并非简单的择一选择。而兜底条款也是个复杂的法律现象,并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选择,需要在多元乃至矛盾的法律价值目标面前,运用法律智慧,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第一,价值目标:赋权与限权之兼顾。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原则的核心要义。兜底条款是赋权与限权的统一体,是一种同时关注限制权力和促进权力正当行使的机制设计。任何智慧高超的立法者,都不可能制定出天衣无缝、完美无缺的法律,必然会给执法者留有一定的裁量空间。还必须看到,公权力包括立法权的行使,一招不慎就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复杂的系统经常显示出混乱的行为,一个小的变化或者系统某一部分的不安会带来其他部分指数级提升的反应。”【[英]杰弗里·韦斯特:《规模》,张培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一个小的立法瑕疵就会产生倍增的负面作用,就可能成为扩张国家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巨坑”。不完善的兜底条款,就属于令人担忧的“微小的漏洞”。【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9页。】如果不审慎处理,就会使公民的自由遭受严重的损害。兜底条款的表述必须完整、清晰、逻辑严密,防止出现不可预测的“蝴蝶效应”。
有关私人权利的法律规定,可以通过兜底条款予以扩展;有关国家权力的规定,依循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不能滥用兜底条款随意扩张。兜底条款是一种概括性的立法技术,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扩张性,在刑法领域一些兜底条款罪名被扩大,极有可能蜕变为“口袋罪”。【参见马东丽:《我国刑法中兜底条款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1页。】口袋罪是刑法学界对因极度概括的罪状表述或者司法适用的惰性,法律适用者将难以判断有罪与否的行为纳入某一罪名予以规制的形象称谓。比如,《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第1—3项规定了三种典型的非法经营行为,由于存有第4项这一兜底规定,使得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非法经营行为可以扩张为二十多种行为。【参见陈小炜:《口袋罪的限制适用和消减进路研究》,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页。】兜底条款是个中性词,有好的兜底条款,有坏的兜底条款。法治原则要求公权机关的活动都受到事先生效的规则的严格约束。如果公权机关利用兜底条款的模糊性,随意扩张或限缩其适用范围,将自己的任性行为合法化,那么,兜底条款即可能成为损毁法治堤坝的“蚁穴”。陈兴良教授指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虽然不存在绝对的兜底性罪名,但仍然存在着兜底条款。由于刑法的规定是概然性的,因而明确性程度较低,在某些情形下,相对的兜底罪名甚至完全没有明确性可言。这些兜底条款在司法适用中往往存有争议,也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需要应对的问题。【参见陈兴良:《刑法的明确性问题:以〈刑法〉第225条第4项为例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第114-124页。】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第9条【《行政强制法》第9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三)扣押财物;(四)冻结存款、汇款;(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第5项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不得随意扩张,必须以前面4项列举的典型情形为参照系,依据法律规定的权限与程序予以设定。
第二,条款表述:明确与模糊之调适。观察兜底条款的表述特征,列举性规定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对象。列举性规定的内容较为封闭,将会压缩法律适用者的自由裁量空间,而兜底条款与之不同,它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它的外延具有动态扩展性,法律适用者意欲适用兜底条款,就必须通过明确该条款的内涵和外延对该条款进行解释,再将犯罪构成要件与解释该条款的结果进行对接,作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裁判结论。【参见张建军:《论刑法中兜底条款的明确性》,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91页。】列举性规定通过对行为模式的具体规定,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明确的规则,而兜底条款则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司法裁判能更好地顾及个案的复杂性,保证法官能在充分考虑案件特殊性的情况下实现司法公正。
列举性规定,就是通过一一列举具体的事物,用来说明列举事项的总效果或上位概念意义的法条。在列举性规定中,对一些事项进行列举,意味着排除了其他事项,对一些事项进行省略,应当认为立法者有意对这些事项进行省略。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如果仅仅只列举了一些事物,那么就应当排斥没有被列举出的事物。省略规定的事项(就是未被列举出来的),并不是漏掉了,而是有意省略,因而该被省略的事项应当不在适用本条之列。相对地,兜底条款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是应对复杂万变社会生活的有效工具。
第三,案型归属:常规与疑难之寻绎。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在法律实施时,兜底条款往往适用于疑难案件。我们发现,获得清晰性的最佳方法是在法律中注入在普通生活中生长出的常识性判断标准,一种仅在名义上具有的清晰性可能比开放性的模糊更有害。【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6页。】常规案件与疑难案件是根据审理案件难易程度,对案件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分类。兜底条款所涵摄的案件不属于运用形式逻辑直接归类的常规案件,对案件性质、拟适用法律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都存在诸多难题。列举性规定具有较为清晰的内容,可以保障刑法的安定性,但过于清晰的列举内容可能会使得立法存有遗漏,破坏概念的完整性,并且列举的事项具有封闭性,难以涵摄复杂的犯罪事实,特别难以规制一些刑法没有作出规定,但就社会危害性程度而言值得进行处罚的反社会行为。由于兜底条款具有开放性,使得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立法的漏洞。【参见张建军:《论刑法中兜底条款的明确性》,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90页。】兜底条款在列举各项中的尾部,形象地说处于“兜”之“底”部。在规范样式上,兜底条款与列举事项共处于特定的条或款之下,相互结合。兜底条款对于列举事项存在依附关系。如果除掉兜底条款,就成为列举规定。
当把兜底条款作为裁判依据时,待决案件是否可被大前提所涵摄,其结论往往是存有争议的。例如,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参见蒋涛、刁永超:《从明确性原则的视角论刑法中兜底条款适用的法教义学建构》,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69-82页。】汪建中抢帽子交易案【参见何荣功:《刑法“兜底条款”的适用与“抢帽子交易”的定性》,载《法学》2011年第6期,第154-159页。】、成都的孙伟铭案【参见郏红雯:《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的立法思考》,载《公安研究》2010年第3期,第75-79页。】等,争议的焦点就是兜底条款是否可作为大前提,用来解决手头案件。适用兜底条款裁判的案件与典型案件相比,既高度相似,又存有差异。
第四,未来面向:稳定与发展之衔接。各种法律现象层出不穷,法律作为生活世界的行为准则,为人们的行为选择划定边界。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需要充分地实现刚性与弹性的有机结合,以使得该制度即便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长期存在并具有避免灾难和祸患的能力。当然,要实现刚性与弹性的创造性结合,是非常困难的,这要求立法者要有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洞见,拥有对传统的充分了解和政治家的敏锐。【参见[美]H.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24-425页。】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多么智慧的立法者都不能全面、准确地预见社会未来发展的复杂局面,无法有效地建立起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都明确具体的行为规则,只能构画出相对开放、弹性的规范空间,为将来法律的发展留有余地。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值得推荐一般条款与列举的例子相结合的做法,因为该做法不仅可以实现法治国家对确定性的追求,还可以便于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参见[奥]恩斯特·A.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兜底条款可将稳定性与灵活性、现时性与未来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为《高等教育法》)第28条【《高等教育法》第28条规定:“高等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以下事项:(一)学校名称、校址;(二)办学宗旨;(三)办学规模;(四)学科门类的设置;(五)教育形式;(六)内部管理体制;(七)经费来源、财产和财务制度;(八)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九)章程修改程序;(十)其他必须由章程规定的事项。”】是由9项列举规定和1项兜底规定组成的。一方面,前面的9项列举性规定是高等学校章程应当规定的事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第10项“其他必须由章程规定的事项”的兜底条款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出具有一定灵活性的解释。
四、兜底条款的设置优化
兜底条款是常见的法条类型,它有着特定的规范结构、功能定位,也有着相应的形式特征、技术规范。理性地看,兜底条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也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由于取消或替代它的操作方案,实际效果更糟糕,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之。对于兜底条款,最理性的做法是,用其长处、避其短板。
第一,编入立法技术规范。由于兜底条款是一种特殊的例示规定,它的设置应符合例示规定的一般性技术规范,同时还有更具体的要求。兜底条款是法律文本的重要内容,它的设置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立法法》第65条第4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编制立法技术规范。”立法技术规范的编制,应高度重视兜底条款的设置技术,在把握兜底条款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针对现行立法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要求“兜”“底”搭配对应,不与例示规定重叠使用,使用“其他”的标识语,明确区分主次关系,等等。
第二,设置疏密适度的“网眼”。法谚云:“法律不计琐事。”法律只规范立法者认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不重要的琐事法律不予调整。其一般原则是,某些违反义务、程序、契约的错误由于无关紧要,以致不需要给以法律上的补救或驳回请求,可以不被作为案件来审理。但当涉及公民的自由权时,按照最小限度的原则,很小的错误也不可被忽视。【[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因而,“兜底”不是包揽,它有着疏密不等的网眼。兜底条款在“其他情形”之前加上的“法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之类的限定语,是控制法网的“网眼”大小的重要装置,需要认真推敲、仔细设置。
第三,严控立法各环节。法案起草环节,仔细推敲。在漫长的立法过程中,法案起草是一个重要环节,需要先确定标题,再拟订提纲,然后编制条文,最后形成法律文本草稿。法案起草阶段,对兜底条款的表述,要高度重视,以形成高质量的法律草案。法案审议,是由有权机关决定法案形成、如何加以修改的专门活动,需要从立法技术规范方面,对兜底条款的设置进行仔细推敲。表决是对法案作出赞成与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决策机制。法案只有获得法定多数赞同的,才能获得通过而成为正式法律。可以考虑将争议较大的兜底条款纳入《立法法》第44条第2款、第3款规定的重要条款单独表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作为重要议题并进行单独表决,根据单独表决情况,决定是否将整个法律文本草案交付表决,或者决定暂不付表决。
第四,展开充分的立法论证。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对人们的行为有一定的限制,立法时必须进行充分的论证。惩罚需要特别的论证,因为它们涉及对自由的双重限制。首先,作为外在限制,它们排除、约束人的自由行动。其次,如果它们伴有一种惩罚,规则的意图、目标或目的就只能以所规定的方式实现。如果行为模式没有以规定的方式实现,就需要施加惩罚。如果要使用一种惩罚,那么其论证就是不可缺省的。【参见[比利时]卢卡·温特根特:《一种新的立法理论:立法法理学》,王保民译,载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331页。】在规范结构上,兜底条款之中的列举性规定是法律的主要调整对象,而兜底性规定则起到次要的辅助性作用。比如,《民法典》第1063条【《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第1—4项规定的情形,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的典型情形,是该条法律规定的主要调整对象,而第5项规定的情形则为非典型情形,起辅助作用。由于兜底条款包含着扩张国家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可能,立法者应就其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做出认真细致的说理。
第五,及时总结立法试验。法律具有稳定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法律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试验性,乃是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一个法律框架开始时可能过于自由,因此需要缩小范围;反之,一个框架开始时可能比较谨慎保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自由。”【[新加坡]刘启扬:《洞悉法门:理解法律的复杂性》,张巍、翁磊、李嘉宝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147页。】兜底条款也是一种立法试验,它的稳定性要弱于一般的法律条款,应当根据法律运行状况及时进行修改完善。例如,《刑法》第225条规定了非法经营罪,第4项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后续的相关立法不断地通过重新阐释兜底条款,扩大了非法经营罪的调整范围【比如:(1)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4条将扰乱国家秩序,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外非法买卖外汇,情节严重的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调整范围;(2)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8条规定,在《刑法》第225条中增加第3项“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刑法》第225条兜底条款的演进过程,反映出此类法律规范经由立法试验、不断调整完善的通常做法,也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安排。
还有,兜底条款自身的称名,也需要仔细斟酌。兜底条款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在法律文本结构单元中,它既不是条也不属于款,多出现于“项”的结构层次。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法律文本结构的层次有编、章、节、条、款、项、目。项,设在条或款之下,表示条或款的内容分为不同层次。设项时应当注意款的性质和层次,同一性质和层次用项表示,也可以用多项表示款的几层意思。【参见武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兜底条款是习惯的称谓,如果从约定俗成的角度看,保留现在的称谓也未尝不可;如果从名副其实的角度看,既然兜底条款不是“条”也不是“款”,而是“项”,称之为“兜底条款”,名不副实;换个角度看,兜底条款是“项”,与其搭配的是“条”或“款”,它可细分为“兜底条项”或者“兜底款项”,无论采用哪一种称谓,都可能有所遗漏。如果考虑名称的适当性、概括性,称“兜底规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五、结语
兜底条款是以前面的各项规定为典型情形,对剩余的次要事项,以含有“其他”的命题式语句,体现为法律文本层次结构“项”的总括规定,是一种特殊的例示规定。兜底条款既具有技术性也具有价值性,它给适用者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可以说,从源头上提高兜底条款的设置质量,能够防止适用者滥用公权力,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兜底条款的立法质量,对接下来的法律适用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立法质量不高,执法者就可能成为扩张滥用公权力、不当限缩私权利的“魔术师”。兜底条款有着特殊的规范结构、功能定位,在立法技术、法律适用等方面都存有诸多的难点,是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深入研究的法学议题。法理学需要在充分吸收部门法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挥作为法的一般理论、法的基础理论、法学方法论、法学价值观的理论优势,为提升兜底条款的设置质量、规范兜底条款的司法适用,提供有用的理论方案。ML
An Analysis of the Legal Rationality and Drafting
Techniques of Catch-All Provisions
LIU Fengj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Catch-all provisions typically address the residual,minor matters not covered by the main provisions of alegal text,using propositional statements containing the word“other”to form an overarching clause at the hierarchical“item”level of the legal document.Observing existing catch-all provisions in current laws based on the standard of good legislation reveals several shortcomings:mismatch between scope and depth,unclear external markers,insufficient levels of enumeration,and confusion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atus.Catch-all provisions represent acomplex legal phenomenon;they are not binary choices but rather require legal wisdom to strike abalance among diverse and even contradictory legal values.They have specific normative structures,functional positions,and corresponding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The design of catch-all provision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legislative technical standards,using an appropriately dense“filter”chosen.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proceed thorough legislative reasoning and adopt dynamic adjustments in line with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Key words:catch-all provisions;enumerative provisions;“other”;legislative technique
本文责任编辑:董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