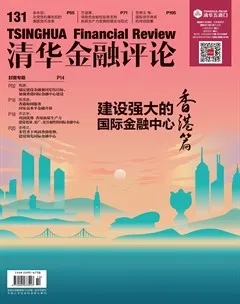最高限价、市场结构与股利政策
2024-12-10李雄师

在公司金融领域,米勒和迪格利安尼(1961)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股利政策不相关理论:在一个完全无摩擦的金融市场中,理性的投资者不会因为股利政策的形式以及分配的比例而改变对公司的价值判断,因此股利政策不影响公司的价值。而当考虑税收因素时,如果分红的税率高于股票回购的资本利得税率,公司理论上就不应该选择分红这一股利政策。然而,现实情况是,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尽管当时美国的分红税率高于股票回购税率,分红仍然是这一时期金融市场上主要的股利政策,这被称为“分红之谜”(Black,1976;Feldstein和Green,1983)。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美国股票回购的税率优势相对分红的逐渐消失(并在2003年完全消失),股票回购却迎来了比分红更为迅猛的发展,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超越分红,成为美国金融市场上最主流的股利政策(见图1),这也被称为“回购之谜”(Farre-Mensa,Michaely和Schmalz,2014)。“分红之谜”和“回购之谜”是股利政策研究领域一直困扰着学者的非常著名的谜题,要寻找能够解释这两个谜题的经济学因素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该经济学因素如何解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分红更为主流?二是为什么该经济学因素在长期趋势上朝同一方向发展,使得股票回购越来越主流?三是为什么该经济学因素使股票回购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而不是对市场造成一次性的影响和冲击?

广西财经学院金融与保险学院金融学副教授李雄师、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叶茂、美国得州克里斯丁大学助理教授郑永键共同撰写的2024年5月发表在《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的论文《最高限价、市场结构与股利政策》(Price Ceilings, Market Structure, and Payout Policies)(以下简称“论文”),发现最高限价和金融市场结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摩擦为解释“分红之谜”和“回购之谜”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论文首先对最高限价的产生机制以及现代美国金融市场的股票回购交易渠道进行介绍。
最高限价的产生机制。公司回购股票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最大的担忧就是公司通过抬高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股价操纵。于是在1982年,SEC颁布10b-18规则,规定公司在回购自身股票时,只有满足包括购买方式、时间、价格和交易量四个方面的要求,才能减轻遭操纵股价指控的法律责任。其中价格要求规定股票回购价格不能超过最高买单(Best Bid)或者之前的交易价格,以防公司推高自身股价。由于美国市场上的股票交易一般采用“价格—速度优先”的交易规则,对于普通的股票购买而言,价格竞争是主要的,速度竞争是次要的。但是10b-18规则的最高价格要求使得进行股票回购的公司无法通过增加竞价获得优先交易的权利,因此价格竞争不再成为股票回购的最重要竞争因素。此时,金融市场结构在股票回购时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决定了市场上交易者在同一价格上的竞争,包括:(1)谁的订单先被执行;(2)股票回购的公司要和多少个交易者进行排队竞争;(3)股票回购的公司进行盯盘和确保合规的成本和难度有多大。
现代美国金融市场的股票回购渠道。几十年前,当股票回购只能通过手工来完成时,公司在10b-18规则下面临非常大的盯盘和确保合规的成本和难度。随着金融市场结构的创新和改革,这些成本和难度不断下降。一方面,程序化交易的出现使得公司或其经纪商(Brokers)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使用特定的回购算法或向通用的算法添加10b-18规则合规指令来回购股票;另一方面,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暗池交易可以帮助公司降低回购股票的成本和难度。暗池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一项市场结构创新。虽然暗池并非为股票回购所设计,但由于其交易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交易者交易的挂单价格往往需要参考证券交易所的公开市场价格,从而自动满足10b-18规则的价格要求,可以有效确保公司股票回购的合规性。同时,很多暗池交易不采用时间优先的规则,能够降低公司在股票回购时面临的排队竞争。
论文接下来通过两个部分的实证检验就最高限价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摩擦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展开分析。其中,第一部分的随机控制实验——最小价格变动单位试点计划(Tick Size Pilot)——为论文的结论提供了坚实的因果关系分析推断,第二部分的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准实验的事件研究进一步估计美国历史上五大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对股票回购长期趋势的解释能力。
第一部分,基于随机控制实验Tick Size Pilot的因果关系论证。论文运用美国一个为期2年(2016年10月至2018年10月)的随机控制实验Tick Size Pilot作为识别策略,通过双重差分法估计建立起最高限价与金融市场结构所形成的摩擦对股票回购影响的因果关系。该计划的优势在于,SEC在近2400只股票中随机选择了1200只股票进入3个处理组,剩余的股票进入1个控制组。SEC将3个处理组的股票的最小报价单位从1美分提高至5美分,其中,第3个处理组的400只股票还被施加了Trade-at Rule规则(为增加整个市场的价格透明度,这一规则规定暗池交易中的股票交易价格要高于公开交易市场最高买单2.5美分)。而控制组股票的最小报价单位保持不变,且没有被施加Tradeat Rule规则。这个随机试验为论文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因果关系识别策略。
论文发现,3个处理组的股票回购相比控制组平均减少了21%,且这一减少是由于公司的平均股票回购减少而非回购股票公司的数量减少所致。为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论文根据股票在Tick Size Pilot启动前一季度的平均美元买卖价差将处理组分为报价约束组和报价未约束组两个子组。报价约束组包括Tick Size Pilot启动前买卖价差低于5美分的股票。显然,Tick Size Pilot将最小报价单位从1美分提高至5美分扩大了其报价价差;而报价未约束组的买卖价差没有或几乎很少受到Tick Size Pilot的影响。论文发现,报价约束组的股票回购下降了45%,而报价未约束组的股票回购几乎没有变化。
论文接下来对买卖价差、股票交易量和市场深度三个标准的流动性衡量指标的变动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市场深度的增加是导致报价约束组股票回购减少的原因。论文发现Tick Size Pilot导致处理组股票的市场深度增加了214%,因为更多的交易者愿意在更宽的买卖差价下报价。这使得在新的最高买单(Best Bid)处与股票回购公司进行排队竞争的交易者数量大幅增加。而这些竞争交易者中有很多高频交易者(HFTs),股票回购公司很难赢得与高频交易者的速度竞争,进而导致其股票回购减少。即使公司聘请高频交易者来进行股票回购,但由于检查是否符合10b-18规则条款而产生的额外时间延迟,这些被聘请的高频交易者的交易速度也将落后于其他高频交易者。与这一排队机制相符,论文将报价约束处理组的股票根据其买方市场深度的增加值的大小分为两个子组,并重新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发现买方市场深度增加较大的公司相对买方市场深度增加较小的公司多减少了24%的股票回购。
除了证券交易所之外,公司还可以通过暗池来进行股票回购交易。由于暗池交易不采用时间优先的规则,因此报价约束组的公司可以通过暗池来规避股票回购时的排队竞争。如前文所介绍的,Tick Size Pilot对第3个处理组施加了Trade-at Rule规则。Trade-at Rule规则规定暗池交易中的股票回购交易价格要高于公开交易市场最高买单2.5美分。但令SEC没有意料到的是,如果公司在股票回购时满足Trade-at Rule的规则要求,那么必然导致其违反10b-18规则的价格要求,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规则实际上出乎意外地使得第3个处理组中的报价约束处理组公司在股票回购时无法利用暗池来规避排队竞争。论文发现第3个处理组中的报价约束子处理组比其他两个组处理组中的报价约束子处理组多减少了19%的股票回购,在实证上表明了暗池是股票回购的重要渠道,也进一步佐证了排队竞争的作用机制。
总之,利用随机控制实验Tick Size Pilot,论文创新性地论证了最高限价和金融市场结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摩擦对股票回购的影响,其机制是公司在最高限价下与其他买家的排队竞争。论文接下来基于金融市场结构改革进一步论证了这一机制的普遍适用性,并估计近几十年来美国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对股票回购长期趋势的解释能力。这些历史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对部分公司影响更大,而对部分公司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包含了准处理组和准对照组。
第二部分,基于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准实验的事件研究证据。在1994年之前,公司在最高限价下进行股票回购时所面临排队竞争摩擦问题非常严重。在高频交易者成为美国公开金融市场事实上的做市商之前,做市商的职责主要由交易商(Dealer)担任。而交易商作为做市商享有购买和出售股票的特权,即在同一价格上享有相对于其他交易主体的执行优先权,从而可以在排队竞争时进行“插队”,更快达成交易。这使得公司在最高限价处进行股票回购时面临极为严重的市场摩擦。过去几十年,美国金融市场结构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投资者提供“无须交易商干预的执行机会”,这些改革通过多轮逐步实施,减轻了股票回购公司在最高价格下与交易商的排队竞争所导致的市场摩擦。这些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可以归纳为三步:第一步改革提高了公司在最高限价上的执行优先级。例如1994年的《曼宁规则》(Manning Rule)废除了交易商的优先权;1997年的《订单处理规则》(Order Handling Rules)进一步强化了客户的执行优先级。第二步改革降低了公司在最高价格上的排队竞争强度。例如最小价格变动单位在1997年从1/8美元降至1/16美元,在2001年进一步降至1美分,这些更连续的价格单位减少了同一价格上购买股票的交易者数量,也降低了排队竞争的强度。第三步改革降低了公司在最高价格处排队竞争的盯盘和确保合规的成本与难度。例如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在2003年引入了自动报价系统,允许公司使用计算机算法来回购股票。论文利用这五个美国金融市场结构改革作为准实验,对“准处理组”和“准对照组”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发现这五个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均显著增加了公司的股票回购。
根据论文的估计,1995年至2021年期间,受到五个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影响而增长的股份回购约为1.63万亿美元,而同期股份回购的总计累积增长约为9.11万亿美元,因此,五个金融市场结构改革所导致的股份回购对整体股份回购累积长期增长的贡献约为18%。从单个改革的贡献来看,2003年的NYSE自动报价系统的引入对股份回购的长期增长贡献最大(8.47%),而1994年的《曼宁规则》(Manning Rule)贡献最小(1.61%)。1997年的《订单处理规则》(Order Handling Rules)、1997年最小价格变动单位的降低和2001年的最小价格变动单位的降低,分别贡献了股份回购长期增长的1.96%、2.86%和3.04%。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对比,论文无论是在随机控制实验Tick Size Pilot,还是在五大金融市场结构改革事件中,均没有观测到处理组和控制组公司显著的分红差异。
综上所述,论文结果表明最高限价和金融市场结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摩擦为解释“分红之谜”和“回购之谜”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对于“分红之谜”,论文表明,由于在1994年之前,公司在最高限价下进行股票回购时所面临的排队竞争摩擦问题非常严重,即使股票回购拥有税收优势,但公司仍然更倾向于使用分红而非股票回购。而对于“回购之谜”,论文表明,近几十年来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大幅降低了公司进行股票回购时在最高价格处的排队竞争摩擦,即使这一时期股票回购的税收优势逐渐消失,但股票回购仍然迎来了比分红更加迅猛的发展。由于金融市场改革是在不断的优化中渐进式发展,因此股票回购的发展也呈现出逐渐增长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由于最高限价和金融市场结构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摩擦始终存在,股票回购也没有彻底代替分红。
论文也为我国金融市场监管的政策制定与研究带来了重要启示。论文反映出美国金融市场政策制定存在各部门各自为政、论证不充分等问题,例如Tick Size Pilot这项试点原本旨在为研究最小报价单位变化对美国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的影响所设计,却意想不到地对公司的股票回购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在制定Tradeat Rule规则时,其原本旨在探索提高金融市场交易透明度的路径方法,但由于SEC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协同度不足及论证不充分,却出乎意料地使得Trade-at Rule规则与10b-18规则相冲突,意外地限制了公司股票回购交易。这些例子给我国的金融市场监管带来重要启示:一是任何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必要做好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否则可能会出台相互矛盾的政策。二是在对金融市场的政策制定进行研究时,除了对宏观层面经济和市场形势进行研判外,还要对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及微观市场主体的博弈关系进行充分研究。三是要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市场“监管沙盒”机制,特别是在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金融市场的结构和环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错综复杂,即便微小的金融市场政策规则的变动也有可能引起剧烈且迅速的市场反应。“监管沙盒”作为一个受监督的安全测试区,有利于在最小化市场风险的条件下对新政策进行充分的实验及研判。
(李雄师为广西财经学院金融与保险学院金融学副教授。论文《最高限价、市场结构与股利政策》(Price Ceilings, Market Structure, and Payout Policies)由李雄师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叶茂以及美国得州克里斯丁大学助理教授郑永键共同撰写,于2024年5月刊发于《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特约编辑/孙世选,责任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