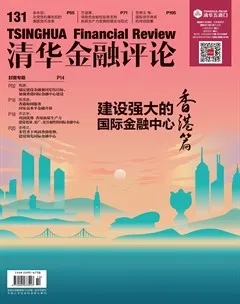金融市场稳定性与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险管理
2024-12-10郑联盛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着重强调金融强国要具有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是总书记在2022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对金融强国的内涵进行了再强调,对金融强调的建设进行了再部署。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市场的核心依托,是金融功能发挥的基础支撑,而健全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是强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内涵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回顾现代金融发展历史,金融强国无一不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是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其强大的信用体系支撑了现代金融的储蓄投资转换功能。在最辉煌时刻,阿姆斯特丹支撑了约一半的全球贸易,几乎垄断海洋贸易,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应运而生,其主要服务对象主要有两家:一是阿姆斯特丹政府,主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东印度公司,主要支持贸易融资。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等的支持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广泛进行海外贸易与投资。其后,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和期货交易市场发展壮大,逐步成为全球最发达的投融资中心。有意思的是,1648年由列克戴克上水坝水务公司发行的人类史上第一只永续债至今仍在支付利息。阿姆斯特丹的辉煌成就激励荷兰殖民者在北美大地上建设一座充满期待的新城——新阿姆斯特丹。1630年左右,荷兰殖民者设立“赞助人”制度,即在特定时间内能将一定数量的奴隶带到庄园的“赞助人”将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附属狩猎权和民事与刑事管辖权,这也被认为是最早的合伙人制度。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被英国夺取,思念故土的英国士兵将其改名为New York,就是当前全球最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
虽然,阿姆斯特丹作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时间不长,但是荷兰的历史经验充分显示了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特质。第一,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要集聚全球重要金融机构;第二,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要拥有重要的国际金融市场及其定价权;第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要具备全球储蓄投资转换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权;第四,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要有扎实的契约精神和鼓励创新的制度保障。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就是从联结度、多元性和专业性三个维度对金融中心进行分类的,按高低顺序划分为全球性(Global)、国际性(International)和区域性(Local)金融中心。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以及金融创新的深化,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整体呈现出三种类型:一是区域性或专业性金融中心。比如,旧金山是美国西海岸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创新资本集聚中心,而芝加哥是全球著名的期货和期权交易中心。二是国际性金融中心。主要以离岸型为主,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就是典型代表,当然香港地区离岸属性更加凸显。三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当前全球就只有纽约和伦敦,但二者存在显著的差别。纽约既服务于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美国经济,又同时服务于全球金融市场,是一种内外交互的国际金融发展模式。伦敦虽然发端于英镑“霸权”,但以其当前功能来论,伦敦是基于离岸欧洲美元市场发展起来的金融中心。对照各类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看,上述强大金融中心的四个特征基本都适用于三类金融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市场稳定性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最核心的表征是金融市场能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能有序促进储蓄投资转换,特别是全球的储蓄投资转换,而其前提条件是金融市场要具备必要的稳定性。这是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和国际社会强调金融监管重要性的内在根源。通过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确保各类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机构稳健和金融市场稳定,保障区域或全球储蓄投资转换顺畅,同时要能够有效防范化解潜在的重大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微观基础是金融机构稳健。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机构高度集聚的地方。不管是何种评价机制,金融机构集中度以及金融产业集群效应都是金融中心评价的核心指标。无论是区域性金融中心、国际性金融中心还是全球性金融中心,针对各类型金融机构运营及业务开展都设置了较为严格的金融监管要求和指标,以合规来限制金融机构风险头寸或约束其冒险行为,着力促进机构稳健和市场稳定。
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宏观要求是确保金融系统稳定。金融系统稳定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和监管机构提出的重大政策目标。这个要求最直接的政策任务就是着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此,金融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管理大多设置了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比如针对银行基本都设置了逆周期缓冲资本以缓释顺周期效应,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则附加新资本要求及流动性指标来限制关联性或复杂性。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样重要的是,当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时,金融管理部门如何有效应对处置风险并将金融系统恢复至正常状态。2023年3—5月,美欧发生了重大的银行业危机,美国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以及瑞士信贷银行等破产,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威胁。美联储联合英格兰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加拿大央行、瑞士央行(六家央行合称为C6)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启动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出台“兜底式”救助,迅速缓释了金融风险,确保纽约、伦敦、法兰克福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稳定性。
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基本特征是储蓄投资转换的顺畅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就是能链接内外的金融要素甚至其他要素,促进区域、国际甚至全球的储蓄投资转换,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这要求国际金融中心要具备多种要素资源的链接能力,特别是资金供求匹配功能。一方面要为资金需求方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融资可得性,另一方面要为资金供给方提供风险收益相平衡的资产。伦敦之所以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最核心的因素不在于英国的经济体量,而在于伦敦是离岸美元中心,承担美国境外美元供求匹配的功能。2023年,伦敦外汇交易占全球的比例超过45%。与这个功能直接相关的是,国际金融中心要具备资金、资产或市场的定价权。定价权的背后就是资源配置权或金融控制权,储蓄投资转换及其定价权的稳定性本质是国际金融中心及其背后经济体的全球核心竞争力。
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基本保障是制度与法治。不同类型金融中心的发展呈现差异化的路径,但是,对金融市场功能的基本保障是相似的。一是国际金融中心及其所在经济体的政治稳定性是首要的。政治稳定风险是国际资本风险评估中的首要风险。二是国际金融中心法律、法规和标准完备性。法律、法规和标准是包括政府在内所有国际金融中心主体的基本约束,是形成市场自我纠偏的有力武器,也是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支撑。以标准为例,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68工作组(TC68)就是专门制定国际金融标准的重要机构,其制定并实施的59项国际标准是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金融体系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础。三是公平有效的监管环境。虽然不同经济制度下,资本社会属性有差异,但难以改变资本逐利的自然属性和金融系统的风险内生性,有效的金融监管就极其关键。基于契约理念、法治精神和合规要求的现代金融监管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基本要求。当然,国际金融中心的办公条件、信息通信、交通设施、生活配套等硬件基础设施也非常重要。
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同时强调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金融强国的一系列核心关键金融要素,其中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六个强大”之一。作为我国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和香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市场稳定性是其功能发挥的基本保障,两大国际金融中心都需要构建起完备的内在稳定机制和有效的风险管理框架。
多措并举,构建金融风险管理长效机制。金融系统是“经营”风险的部门,金融风险无处不在,有效管理金融风险是金融市场稳定的基础。对于金融机构,要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和内部控制框架建设,适度限制金融机构的风险头寸和冒险行为,有效管理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对于金融监管部门,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框架,优化金融监管标准,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到监管范围之内,着力保障金融市场交易促进、信用转换、风险管理、政策传导和国内外资源交互等基础功能平稳发挥,有效处置危及金融市场稳定的风险及隐患。对于国际金融中心重要市场,要重点警惕流动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威胁,着重防范市场重大扭曲和市场失灵风险。
尊重市场规律,健全金融市场内生稳定机制。金融市场体系建设要尊重市场规律。一是充分发挥市场供求的内在平衡机制。供求关系是价格最基础的决定因素,也是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基础关系。现代金融市场特别是数字金融具有一定的双边或多边市场的秉性,即供求相互决定。刻意限制金融需求之时,可能会直接约束金融供给,为此要统筹政府与市场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强化基础金融要素定价改革。着重优化利率、汇率和国债收益率定价机制的改革,着力提高银行间市场短期利率和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定价锚功能,不断提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韧性。三是要有效发挥金融市场风险定价功能。各类市场主体或金融产品的风险定价,基本符合无风险收益率加信用利差的逻辑,要着力发挥市场机制,以信用利差对不同主体的风险进行科学甄别与合理定价。四是要鼓励创新以激发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活力。在风险底线要求下,要健全包容创新的市场氛围和生态体系。
加强金融法治,夯实金融市场稳定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金融系统关键的理念支撑是契约精神。坚决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以制定金融法为抓手,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的营商环境、产权保护和法治体系建设,实质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等的国民待遇地位,完善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法制体系,不断优化金融立法、执法和司法,提升金融发展法治化水平。在防范系统性金融安全威胁和保留资本管制“最后防火墙”的基础上,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外资管理和金融投资管理体制机制,完善国际投资的争端解决机制、投资权益保护机制,多渠道吸引国内外中长期资本。国际金融中心尤其要以法治建设为支撑,加强政策稳定性水平,增强外商、外资和长期资本对国际金融中心的长期信心,更好稳定市场预期。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强国建设的基础,是有效应对金融风险、提升资本市场内生稳定性和确保金融稳定的根本之策。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须顺应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强监管、防风险、促发展为主线,持续完善金融市场基础制度为重点,以金融法治和金融监管为支撑,增强金融市场内在稳定性,着力提升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服务金融强国建设,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郑联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研究室主任。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健全金融监管体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2018JRSA0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22MGCZD011)、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计划重点学科(金融监管学DF2023ZD23)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年度重点项目“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若干问题研究”(2023JB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责任编辑/王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