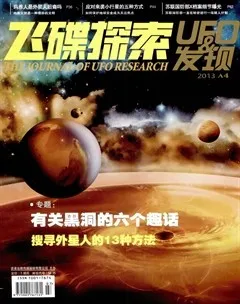扎根科研,守护“植物王国”
2024-12-07倪思洁
中国的西南角——云南,这片只占国土面积4.2%的地方,却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物种。其中,滇西北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中的核心区之一。
由于物种丰富,云南还享有“植物王国”的美誉。每年夏季一到,云南的大街小巷、咖啡馆、饭店、小商铺的门前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当山上的积雪融化时,虫草、滇重楼等高山药用植物就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宝贝。
2024年5月24日,戴着黑框眼镜的大高个儿许琨,收拾好行囊,准备第二天一早出发去爬哈巴雪山。这个花开遍地、药材满山的季节,他不是去旅行或挖药材,而是去调查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分布情况。
许琨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所”)正高级工程师。他和同事常在云南不同地方忙着不同的任务。让他们聚到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梦想——守护“植物王国”。
坐标:丽江
任务:守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许琨的工作地点以丽江为主。因为他还是云南丽江森林生物多样性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丽江站”)常务副站长。
和丽江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相似,许琨的工作也“四季分明”:春天,在实验室里播种育苗;夏天,外出调查植物分布情况;秋天,在野外收集植物的种子;冬天,则窝在实验室整理资料写报告。一年又一年,经过十四载的辛勤耕耘,许琨成了高山植物领域的专家。
他从事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工作,是昆明植物所的代表性研究方向之一。昆明植物所是全国最早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体系研究的机构之一。该所研究员孙卫邦及相关研究人员曾调查并积累了200个植物物种种群现状的基础数据,还对125个物种进行了迁地保护、9个物种开展了近地保护示范、20个物种做了回归试验示范。
许琨所在的丽江站是昆明植物所5个野外台站中唯一一个国家级野外台站,也是该所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重点实验室12个物种繁育和保护基地之一。
过去十多年,许琨亲眼见证了丽江站的发展。他们在玉龙雪山景区开辟出25公顷森林大样地,并在其他地方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监测样地。在云杉坪监测样地里,科研人员可以通过森林塔吊将自己吊到树冠上采集样本,避免了爬五六十米高大树的危险;实验室里,用以开展生态系统功能控制实验的平台越来越丰富,极大地降低了科研人员做实验的时间成本;“演西北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也从无到有,现已拥有2600余种滇西北地区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其中种子1600余种、活体1000余种。
在谈到丽江站时,许琨常常说“这里很阳光”。这种“阳光”体现在他们与当地居民的联系上。当地牧民的马就在站上吃草。除了实验室、观测站、试验样地等被围起来之外,其他地方都对相邻村社开放。更重要的是,站上的不少研究成果走出了实验室,让当地居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很多科研人员都向附近农户推广过站上的科研成果,昆明植物所工程师范中玉就是其中之一。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推广滇重楼的过程。
演重楼是云南白药的重要原材料,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等功效。最初,滇重楼无法实现人工种植,过度采摘导致其成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近危植物。
后来,科研人员经过不断的探索,终于掌握了滇重楼的人工种植技术。范中玉成为这—技术的推广者,滇重楼也因此成为他每次都要给农户讲的内容。过去十多年里,他培训过的农户不下5000户,而最终成功习得该项技术的却不超过50户。
这种小范围的成功,推动了滇重楼种植技术的应用与成熟。范中玉说,如今,不少农户种植滇重楼的技术已经超过科研人员,许多人已经不记得这项技术最初是从昆明植物所传授的。
尽管如此,无论是许琨还是范中玉,他们都不觉得委屈。“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不是农户的感激,而是把陷入危机的物种从红色名袒‘剔’出去,确保物种的安全。”
坐标:迪庆
任务:探秘冰缘植物
与许琨不同,昆明植物所研究员杨扬的工作地点主要在迪庆藏族自治州。他还有另一个身份——迪庆白马雪山高山冰缘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白马站”)副站长。
杨扬的工作节奏大概分为两季:下雪季和雪融季。每年4月到10月,冰雪融化,他会在海拔4300米的高海拔站点开展科研和监测工作;11月到次年4月,大雪封山,他主要进行冬季实验样品的采集和野外台站的定期巡护。
他从事的是高山冰缘带植物生态适应机制的相关研究。“高山冰缘带”是指永久雪线以下、高山草甸以上的狭窄区域,通常在海拔4500米以上。极端环境下,物种面临极限生存,造就了许多抗寒、抗旱、抗紫外线能力极强的特化植物,也因此成为耐逆基因和生物资源的宝库,被誉为“隐秘植物王国”。
白马站正是为研究高山冰缘特殊生境内植物物种适应性、群落形成及生态系统功能而设立的。野外台站位于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建于2019年,是云南省目前海拔最高的科研观测站。台站占地30亩,站区海拔3800至4300米,并在海拔近5000米和4300米处设有标准气象观测场和永久样地样方。
或许是因为长期在极端环境里工作,杨扬最喜欢两句话:一句是“缺氧不缺精神”,另一句是“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他常用“高黎贡山女神”李恒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经历激励自己和学生。“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应该把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传承下去。”杨扬如是说。
这样的理念感染着他的学生扎西尼玛。扎西尼玛是个藏族小伙儿,今年24岁,目前是西南林业大学和昆明植物所联合培养的本科三年级学生。扎西尼玛的父亲是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曲宗贡生态定位监测站的前任站长,今年刚退休。扎西尼玛小时候常在保护区里玩,还曾跟父亲—起繁育白马鸡。
幼年时的经历激发了扎西尼玛对动植物保护的热情。在杨扬的指导下,扎西尼玛积极参与高山冰缘带植物的物候节律和适应性状等科研和观测工作,几乎形影不离地跟随杨扬学习。
白马站的设立,不仅让科研人员得以在本地研究高山冰缘带植物,也提升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曲宗贡生态定位监测站现任站长江次农布感慨道:“白马站成立之后,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更加科学化。比方说,以前去野外巡护时,我们只是简单登记一下;而现在我们对动植物的识别能力提高了,也有了规范化的表格,对动植物的记录更加细致了。”
他们期待白马站能帮助培养更多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年轻人。“现在我们的监测站里有很多年轻人,我们希望白马站的科学家们能够带他们去外面学习,帮助我们更好地培养年轻—代。”江次农布这样说。
坐标:昆明
任务:让野生种子休眠
与许琨、杨扬等常在野外考察的科研人员不同,昆明植物所高级工程师蔡杰更像是守护“大本营”的人。他的主要工作地点在昆明,另一个身份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以下简称“种质库”)种质保藏中心主任。
种质库于1999年由吴征镒院士提议,2005年开工建设,2007年建成并投入试运行,2009年通过国家验收后运行至今。目前,它是全球第二、亚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与英国“千年种子库”、挪威“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等一起,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异地保护的主要设施。
科研人员在野外采集到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大多会被保存在这里。截至2023年12月,种质库已保存我国野生植物种子1.1万多种、9.4万多份;植物离体培养材料2000多种、2.7万多份;植物总DNA(脱氧核糖核酸)9000多种、7.1万多份;微生物菌株2000多种、2.3万多份;动物种质资源2000多种、9万多份。
尽管身处春城昆明,蔡杰仍常要进入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里工作。为了让种子更好地休眠,他们在地下建了5个巨大的“冰窖”。干燥后的种子被装入密闭瓶或铝箔袋中,最后放于“冰窖”内长期保存。5个“冰窖”的总面积有190平方米,可以存放约17万份种子。
在种质库里,种子的寿命被最大限度地延长:小麦种子预计可以保存786年,水稻种子预计可以保存1139年,棉花种子预计可以保存17076年……
蔡杰说:“我们现在收集和保藏这些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一方面是为了保护野生物种,另一方面是为了给未来的作物改良提供原材料。目前很多野生植物的潜在用途我们还不清楚,如果这些资源消失了、灭绝了,那将会非常可惜。”
种质库里的种子各有各的故事。对此,蔡杰如数家珍:“你看,这是川东灯台报春,2004年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把它列为‘野外灭绝’物种。2006年,科研人员在重庆大巴山再次发现多个野生植株,采集了种子进行保存繁育。这是沧江海棠,它是一种野生小苹果,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河谷区域,味道很好,只是果肉没那么多,如果不能改良为水果,或许可以用来做苹果的砧木。”
和昆明植物所里从事物种多样性保护的科研人员一样,蔡杰也在危机感中生出了一种科幻感:“如果有—天,地球不再适合生存,种质库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展望未来,这些在中国西南角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科研人员有着明确的方向。昆明植物所副所长李宏伟说:“我们要继续把野生种质资源的‘家底’摸清,对种质资源进行就地、迁地、近地、离体等各方面的保护,同时我们要提升科研技术能力,保证休眠的野生种子在人类真正需要的时候重归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