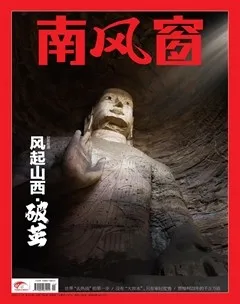没有一颗大枣,会孤独地离开吕梁
2024-12-05肖瑶

午后,崖坡边上的土灶升起炊烟,似着白衣的山间舞女,袅袅渗进背靠的黄土高坡视野里。秋日的阳光寂静。院子里晾晒的枣—不论是生枣、刚经清洗的枣,还是煮过的、烤过的大枣,一同散发出热腾腾的甘香,与暖色调的秋意相得益彰。
煮枣,是六郎食品收来的每一颗枣必经的工艺。
10月底,晋西已迎来晚秋的凛冽,自山谷岭刃劈下来的凉风,拂过位于黄河中游的柳林县三交镇,枣林掩映的黄土高原进入了萧条的时节。
不过,即便已过了丰收时期,在沿黄公路上驻足,置身开始褪叶的枣林,仍能闻到一股醉人的甘甜。
在晋西近黄河的吕梁一带,“红枣之乡”的名号,从柳林一直喊到临县,沿着黄河一路北溯。从黄河之畔独有的团枣、灰枣、骏枣等,到民间为贮藏或是留传而发明的酒枣,没有一颗大枣会孤独地离开吕梁。甚至连结枣的树木,也能物尽其用地培养当地特色的“枣木香菇”。
枣是这片黄土大地上长出来的温润之花,傍母亲河而生的柳林县和临县,历来也扮演着护花者的角色。用传承悠久的工艺与文化,温沉、缓慢而持续有力地,将母亲枣原本的色泽拭亮。
红色高原
中秋过后,在黄河东岸与陕西隔河相望的三交镇,枣林就几乎无果可采了。秋风刮了两个月,10月底,寥寥几簇绿叶仍挂在细枝梢头,缀着星星点点的熟透的红。
浅林中,一张碎花床单铺开,一家人坐在上面择果子,一大姐双手抱树轻轻摇晃,几颗硕大的红枣随着黄绿交接的树叶从头顶簌簌落下。
距离这片枣林不到两公里的六郎枣庄,也进入了商品待销的季节。
柳林六郎大枣加工基地,位处吕梁山和黄河之间,距离黄河仅两公里,隔河连接着陕西。院子不大,每一块区域都极尽其用。阳光直射的空地用来晒枣,金黄下的褚色盛宴,个头大的几乎近半个手掌大小。荫凉处堆放着经过两道烘烤技术的干枣,还需要等待另外两道工序,它们才能正式进入加工流程。
厂长薛兵成已年过六旬,他穿着浑身浸有红枣味的衣裳,引着我走进一道道红枣需要经过的工序。操作间没有亮堂的灯,一颗颗按个头与成熟度区分的大枣,安静地躺在层层钢架上,经过前后四道40度至70度温度不等的烘烤,分发至它们应去的不同加工产品处。
我们抵达这间大枣加工厂的时候,第一批酒枣还未发酵完全,薛兵成将黑黢黢的仓库拉开一条缝,携着微尘的午后阳光泄进去,拭亮黑暗中一箱箱泡在白酒里的半成品枣。
它们是这个秋天最后一批完成的枣成品,其余的干枣、紫晶枣、酸枣等加工品都已贮备就绪,只待在寒冬来临前,从黄河之畔发往全国各地。
在晋西的秋天,几乎每一颗枣都有注定的归宿。
作为产出名列全国八大名枣之一、山西最重要的红枣生产基地,柳林已有1300多年的红枣种植史。 据《永宁州志》载,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青龙枣交易甚广,以其个大、核小、肉厚、色鲜、味美、汁甜而闻名遐迩”。
柳林的红枣,密集生长于距黄河沿岸20米至1500米范围内的沙滩上,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带来雨热同步、光照充足的天然条件。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柳林的大枣呈现出颗粒硕大、色如墨玉的外形特征。传说中的“人参果”,在山西本来指枣。
枣区有民谚云:“七月十五枣红腚,八月十五枣上屋。”从农历七月十五开始,青枣渐渐变红,到八月十五,红枣已晒到房檐屋顶或者房前屋后了。早秋柔和而干燥的阳光催熟果肉,空气里也弥漫着一股温暖的甘甜。
枣在黄河流域的种植和食用历史,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诗经·豳风》有篇《七月》写道:“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柳林的大枣呈现出颗粒硕大、色如墨玉的外形特征。传说中的“人参果”,在山西本来指枣。
在柳林,枣是地里长出来的金,代表着一种当地人民对生活不断蓄起的本能希冀与热望。作为食材,它并不算稀贵,历来低调的饮食文化地位,反而赋予母枣一份包容和豁达的可塑性。在行情相对走低的近几年,大枣总能一次又一次,为这座黄河边上的小城洒下生的微光。
沉默的“铁杆庄稼”
自柳林出发沿黄河北行约80 公里,到达临县,那里是吕梁红枣的另一大盛产地。
地处北纬37度的临县,处于晋陕黄河大峡谷之间,全年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千千万万棵红枣树长于黄河沿岸,在气候整体干燥的山西,黄河流域属于相对湿润的地区。得益于充足的阳光、优质的沙质土壤以及昼夜温差大的环境,这里结出的枣,拥有核小、皮薄、肉厚、味甜等特征。
如今,临县全县保有82 万亩红枣林,遍布23 个乡镇454 个行政村,涉及37.26 万枣农,年均产量为3.6 亿斤,枣产业收入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近一半。当地有说法叫“沿黄枣区”,沿黄枣区的农民,足有70% 的收入都来自红枣产业。
根据临县县志记录,最早至2000多年前,当地就有过红枣树的栽植。如今已成著名旅游点的碛口古镇,就曾发现保存完好的枣树化石,而三碛公路穿村而过的林家坪镇薛家圪台,目前还存活着有1400 多年历史的枣树。树干主体已风化枯萎,但仍然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古时候,晋地交通不发达,为了运输物资,人们翻越险峻巍峨的吕梁山。黄河自然成为百姓的水路首选,河岸边的村落因此成为第一批忙碌的渡口。隋唐时期,柳林县黄河从北到南就有孟门渡、军辅渡、三交渡三处渡口。
而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枣不仅作为蔬果,更作为一种粮食来维持生活。
《战国策》有载:“北有枣栗之利,民不作田;枣栗之实,足食于民。”此处的“枣”就是被当作作物的,甚至可救灾应急,《韩非子》也曾描述枣作为备战食粮来养民:“ 秦饥,应侯(范雎)谓王(秦昭王)曰:‘五苑之枣栗,请发与之。’”
喜光且耐旱、耐涝的红枣,素有“铁杆庄稼”之称。顽强的生命力,一如这片土地上世代相承的人民,擅长适应环境,更擅长在环境里冶炼出独一份的脾性和文化。
仅按个头看,枣有基本的大枣和小枣,前者肉质丰厚,入口甘甜,后者则大多比较干,入口酸涩。山西人民当然不会放弃味觉不佳的酸枣,除了酸枣面,枣的大部分用途是作药。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早已研究发现,山西、山东产的枣肉质较厚、口感甘甜,适合入药。而临县红枣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军军告诉南风窗,如今,黄河母枣的大部分产出渠道,足有80%都是药用。
不过,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石凤鸣则表露一丝担忧:枣虽然是临县引以为傲的产业,但在市场的多元冲击和文化的相对封闭下,如何走出吕梁,跨越到秦淮以南的南方,迄今为止仍然是个难题。
王军军透露,如今,临县每年产枣量达3.6亿斤,其中大部分都销往位于我国北方的沈阳、内蒙古、河北唐山三地。
在南方,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群体里,红枣的存在感尚不高。
如今,市场与大众文化里熟知的枣有山东枣、新疆枣,尤其是以光照充足、甜分高闻名的新疆大枣。相较之下,本就在全国省份里存在感较低的山西,其大枣更是鲜为外人所知。
不仅在临县和柳林,整个吕梁地区的人都认为,要想守住大枣的精髓与分量,首要之义,得重建本土对于黄河枣的定位与认同。
为“母枣”正名
在我告别临县政府之前,临县红枣产业服务中心的“红枣文化学者”李孟谐留住我,坚持要给我看他为了给“母枣”正名准备了数年的文件。一沓沓A4纸,摞起来足有一掌高,令人惊赞。
“母枣”,顾名思义,即红枣的原始品种。对于临县与柳林的大枣,市面上历来有“木枣”的说法,但李孟谐认为,这是一种历史传播过程中的误听。
不仅在临县和柳林,整个吕梁地区的人都认为,要想守住大枣的精髓与分量,首要之义,得重建本土对于黄河枣的定位与认同。
早在1963年,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太谷果树研究编著的《山西省主要果实品种图谱》一书就已有说明:“木枣是我省分布较为普遍的一个品种,以晋西临县、中阳、离石等地最多,约占当地栽培株数的80%以上。”因此,晋西也许是华夏大地母亲枣的主要产地。

李孟谐的热情,在那些偏大号的黑字上腾跃而出。他在给当地政府的提议里阐述道:“从华夏文明进步的角度看,黄河母枣的培育进化史几乎与华夏先民步入农耕文明的历史一致。”
对枣的爱护与正视,代表着山西人民对“济世救民的‘铁杆庄稼’的敬畏”。
在中国人的饮食谱系里,大枣就像一个淳朴寡言的农妇,亲手缔造了餐桌上占比重要的一味,却历来鲜被注意,至少抬不上价。
但实际上,在黄河一带的山西人家,许多主食是离不开枣的。
比如一种名为“枣围围”的年馍。寻常人家爱挑好枣,嵌进面团底座里,按顺时针依次九颗,取“长长久久”之意。红白相间的枣围一起被放进蒸笼,出笼后,最后一道工序是用竹筷子头蘸点食色红,在面团上“画龙点睛”。
在蔬果物产相对贫瘠的黄土高原地区,人们更懂得因地制宜,最大化利用当地物产,使之食、色、味兼备。这是晋地百姓历来在“吃”上面延绵留传的一种生活美学。
民歌有道:“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里的“太行山以西”,就是柳林—临县一带傍黄河而生的居民聚居地,作为陕、晋与黄河衔接的重要咽喉,其素有“华北门户”“秦晋通衢”之称,曾是扼守三晋、力通中原的“西大门”枢纽。
对于天赐的“红色宝物”,吕梁人民绝不会轻视甚至挥霍。
近十年来,随着产业升级与城市化带动市场,黄河对沿线城市的滋养与带动作用,在一颗颗红枣上落地了。
又一年冬已至,黄河进入静息时期。黄河之畔的人们开始期待来年秋天,彼时,再一次枣林葱郁,漫漫红映,夕阳西下之时,整片河滩都将如沐金光,褚色照拂,壮阔而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