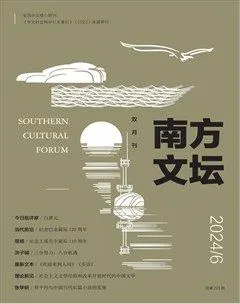人间万象,灵魂逃逸
2024-12-04耿艳娇
一个真正的作家,要把自己生出来两次。第一次,他要在形形色色的闪亮的事物中,找寻到写作这扇窄门,侧身而入,雕刻一个即使是再粗疏仍足以辨识的作家的形象;第二次,他要告别曾经开垦出来的大道,不管那路上有怎样美妙的流云与悦耳的鸟鸣,一个人踏上人迹罕至的荒野,再造一个新我。自2008年《推拿》发表以后,在长篇小说这一体裁上,毕飞宇陷入了漫长的停滞。这期间,他写短篇小说,写随笔。当然,更多的是写文论,他灵巧地向读者示范小说各种各样的读法——他仿佛重新成为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读者。直到《欢迎来到人间》,我们才恍然,这是转身前的必要停留和准备。现在,毕飞宇离开了他自己,他已经在寻求另外的出路,而这出路有可能造就一个完全不同的作家。
这也正是我们面对《欢迎来到人间》的第一反应。它不同于《推拿》,不同于《平原》,甚至不同于毕飞宇此前的任何一部小说。如果说,此前,毕飞宇的小说是如此清晰,就像结构分明的导航图,遵循着它的指示,你能毫无意外地到达终点,完整地领会作者的意图。而在《欢迎来到人间》中,尽管标识还在,但就像被废弃的城市,你仿佛被抛入混沌之中,在日常生活的面貌之下,你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小说潜行着混沌的力量,但很难找到明澈的语言指认它。这意味着,《欢迎来到人间》需要新的阅读法。虽然有现实生活作为外壳,《欢迎来到人间》并不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们必须卸载关于人物、情节、叙事主线、矛盾冲突等常规性路径依赖,在小说语言与结构的链接中打开小说的阐释空间。就像毕飞宇独自踏上荒原,你需要独自面对一开始就被提出的问题,《欢迎来到人间》是关于什么的?
“户部大街正南正北,米歇尔大道正东正西,它们的交汇点在千里马广场。”①这是小说的第一句话。小说的开头,是作者与读者签下的契约,直接决定了读者怎么读。毕飞宇素来起笔宏阔,越是要在一个个针尖似的人物上雕刻清明上河图,越是要给人物一个辽远的具有纵深感的背景和环境。这是小说发生的世界,是人物活起来的土壤。不妨回顾下毕飞宇另外两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平原》的开头是这样的:“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②麦子作为这一平原上的典型物候,兼具物质性与抒情性,在毕飞宇眼里,它甚至具有了某种生命能量。当它把这一能量灌注到田野里,田野就活了过来。毕飞宇不说田野,他用的是“大地”这样更浪漫化也更哲学化的词汇。这是他给《平原》定下的基调。相比之下,《推拿》要平实一些。“散客也要做,和常客以及拥有贵宾卡的贵宾比较起来,散客大体上要占到三分之一,生意好的时候甚至能占到一半。”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一般而言”。寥寥几笔,从顾客的构成上开局,推拿师的日常生活状态就有了个大致的画像。《欢迎来到人间》似乎仍然位于平实的延长线上,但细读却颇有端倪。户部大街、米歇尔大道的命名显然并不共享同一套法则,暗示出现实之上的象征性。在长镜头叠加寓言式的对于城市的探照中,我们大约可以建立对于时代的感知:这是一个中西方交融、碰撞的时代。现代性之花浇灌出对于“速度”的狂热。城市正在大张旗鼓地改造、建设中。旧事物一层层剥落,新事物覆盖上去,转眼间又变成了旧的。商业意识笼罩了几乎全部的心灵世界,成为唯一通行的法则。事实上,这也是《欢迎来到人间》的构成方法,即不以反映现实为旨归,而是在摹仿日常生活的同时,以富含张力的语言暗示出一个象征性的世界,从而在更高的维度上呈现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某些隐藏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视线的交集处,被命名为千里马广场的马的雕塑上看得更清楚。
是一匹马,坐北朝南。绛红色,差不多像人一样立了起来,像跑,也像跳,更像飞。马的左前腿是弯曲的,右前腿则绷得笔直——在向自身的肌肉提取速度。马的表情异样地苦楚,它很愤怒,它在嘶鸣。五十年前,有人亲眼见过这匹马的诞生,他们说,天底下最神奇、最可怕的东西就是石头,每一块石头的内部都有灵魂,一块石头一条命,不是狮子就是马,不是老虎就是人。那些性命一直被囚禁在石头的体内,石头一个激灵、抖去了多余的部分之后,性命就会原形毕露。因为被压抑得太久,性命在轰然而出的同时势必会带上极端的情绪,通常都是一边狂奔一边怒吼。
看似是“他们说”,看似说的是马,是石头,然而,这腔调毫无疑问是属于小说叙事者的。如果石头有灵魂,那么人有没有?人的性命原形毕露之后是什么模样?极端的情绪又是什么?叙述者大大方方将小说的要义陈列在我们面前,指望我们透过他的眼睛来观察这一切,进而得出自己的回答。好了,开场前的锣鼓敲遍,好戏就要开场了。
时间是2003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仿佛要借精准的时间定位来指向明确的现实。这一时间点唤起了我们的集体记忆,这是“非典”接近尾声的时刻。人们有着劫后余生的庆幸与放松。而在小说发表时刻,“新冠”将将过去,余威犹存,惊惧尚在。小说内外的时间形成有意味的对位。不过,这都是我们脑补的,叙述者无意在此盘旋。他只是轻巧地撬动着我们的记忆与情感。地点是第一医院的外科楼。在城市社会空间中,医院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科学的、理性的,代表了现代性对身体的疗愈与处置;同时,它又是心灵化的,对于当代城市人来说,医院类似于宗教社会的祷告所,医生就像牧师,有安抚心灵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医院是承载了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空间。那么,如果医院出了问题呢?现在,泌尿外科“圣手”傅睿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凶险的情境。继第一医院出现6例肾移植死亡以后,傅睿亲历了第七例死亡。而傅睿也遭遇了病患家属的质疑与殴打,只是这当头痛击被护士小蔡替了。在现实主义小说里,这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故事的核。叙述者既可以化身侦探,一路追踪死亡原因,也可以沿着医患关系的路子把脉社会问题。不管往哪个方向去,这粒故事的种子足以长成草木葳蕤的森林。然而,看起来,毕飞宇并不打算追索医治死亡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是将其投入叙事的水面,看它激起层层涟漪。
涟漪的第一层,毫无疑问是当事医生傅睿。此时,傅睿的情态却颇有些诡异。很难具体形容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不是被人误会了的愤懑、不是对花季生命逝去了的痛心,他的情绪仿佛被抽空了,叙事者用的词是“恍惚”。恍惚是失去了对外在世界的感知,也失去了对自我的感知。他再次回到了手术室,是要复盘手术情景吗?他淋浴,他张大了嘴巴喝沐浴用水,是饥渴难耐吗?他进入了空寂无人的手术室。对傅睿而言,过往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了,时间、空间、他自己的身体,仿佛都陷入了迷雾。毕飞宇娴熟地运用第三人称“意识中心”,过滤掉叙述者的声音。但恰恰因为傅睿的“恍惚”,我们反而意识到叙事者的存在。这个冷酷的叙事者,看似给了我们许多指示,却对发生在傅睿精神世界的事情缄口不言。我们只能从“此时此刻,他的体内全是烟”以及睡眠中的傅睿陷入了剧烈的搏斗之中这一两个细节中猜测一二。联想到从石头里挣脱而出的那匹马,或许,傅睿的灵魂正在与他的身体争夺主导权?
傅睿陷入迷雾之中,叙事的镜头转而摇向了傅睿的妻子敏鹿,就像水波渐次向往溢出。显然,作为傅睿最亲密的人,敏鹿并没有将此次事件当作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医院里死人,这简直是必然的。唯一让敏鹿不满的是,她的丈夫把患者的丧事带到他们家的床上。他人的死亡,就是一个个孤岛,与她隔着永不相连的潮水。因为共情力的匮乏,她也完全不能理解傅睿站在手术台前无时无刻不在的恐惧,不能理解对于死亡的焦虑像异种入侵,在傅睿的身体内部安营扎寨,渐渐改变了他。敏鹿只拥有一种叙事,那就是爱情叙事。就像新时代的包法利夫人,敏鹿将她和傅睿的故事,套用到王子和灰姑娘的模型中。在她看来,傅睿就是童话里不食人间烟火的王子,她和傅睿的故事就是王子来到人间,和灰姑娘花好月圆的故事。王子是去内心化的,他只有洁净剔透的外壳,那波涛汹涌泥沙俱下的内景,是不被看见的。
傅睿的父亲老傅也有自己的叙事。他的叙事主题是医生的专业技术问题。所以,他正视这起死亡事件的办法是,反复追问死亡发生的原因。看起来,老傅是工具理性的崇拜者,他认为事出必有因,病人的死亡必然有一个技术方面的解释。他穷根究底要找出这一个“因”。殊不知,貌似客观的认知其实来自于他个人的缺憾。这位前医生、现领导在医学的道路上半途而废,于是,儿子傅睿成为他完成个人心愿的补偿性替代。老傅看似是在与傅睿讨论问题,但他既没有切入问题域也并不关心具体的人,他要的是在讨论医学问题这件事本身。假装是个医生在讨论医学问题让他得以想象性弥补人生的缺憾,他也不可能理解,问题表面的反复纠缠会将傅睿推向痛苦的深渊。“说起环节,傅睿的记忆力惊人了,他能轻易地回忆起手术台上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又可以分成若干个细节。就细节而言嘛,傅睿的手术无懈可击。傅睿的痛苦正来源于此。当无微不至的记忆和不可避免的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记忆就残忍了。它会盘旋,永不言弃。”傅睿的母亲闻兰也不愿意他们讨论“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过,她的不愿意是从她的职业惯性出发,着眼于管控新闻舆论,避免事态扩大。如果说,老傅是权力掌控欲上身,那么,闻兰则是市侩,他们都对傅睿内心的风暴视而不见。
家人都如此,那么,旁人呢?有没有人能够察觉心灵深处的火焰明明灭灭,有没有人能够洞悉灵魂的战栗?于是,见义勇为的小蔡上场了。小蔡给自己安排的剧本是与偶像的一段不能不说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小蔡跟敏鹿都是爱情故事的爱好者,不同的是,敏鹿钟情的是老式的淑女的故事,小蔡更跳脱,也更野性,规矩伦理什么的框不住她。在她的经验里,爱情总是跟金钱纠缠在一起的。小蔡自始至终都是以看“偶实”的目光看待傅睿的。傅睿呢?他是以看病人的眼光看小蔡的。这是他们之间的错位。在小说不动声色地推进中,我们突然意识到,每个人携带着自己的经历、情感、趣味,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眼睛体认他人、处理生活,所谓的理解其实是不可能的。
田菲的离世让傅睿精神陷入泥潭。他必须有所行动,行动才能破局。深夜2点,傅睿来到了昔日病人老赵的家里,给老赵做了一番检查。因为背负着田菲的死,对于傅睿而言,他对所有病人都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叙事者没有明说,但是我们都知道,检查,是为了确认老赵这样的病人仍然好好活着。但是,请注意这个时间,深夜2点。显然,没有哪个精神健全的大夫会这么做。如果我们还记得,此前,傅睿在手术室里就丧失了对于时间的感知,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傅睿的精神世界已经一片混乱了。有意味的是,他的混乱并没有被识别。这是因为,在医生—患者的权力关系结构中,所有的异常都会被合理化甚至被美化。在讲述这一点之前,叙述者为我们构造了老赵的生活。生病以前的老赵,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在权力关系格局中,他获得了某个位置,自然也获得了高于舒适的经济收入。用叙述者的话说,“时代是宽阔与湍急的洪流,他没有被抛弃”。这么一个时代弄潮儿,可想而知,在家庭生活中一定处于权力关系的上游。但是生病将这一切都改变了。昔日安静、软弱和无为的爱秋在照顾老赵的过程中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她要按照她的意愿塑造老赵的生活。于是,一场争夺权力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家庭内部发生了。结果当然是老赵败北。他更加心悦诚服地臣服于妻子的权威。看看,权力关系就是这样扎入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中。作为权力关系的下位者,老赵不可能质疑傅睿是否正常,他只能归结为做医生太忙了,甚至,他要用他的方式“把这样的医生送到岗位上去”。一念之间,叙事的车轮越转越快。
在荒诞的故事愈演愈烈之前,不妨先停下来看一看,傅睿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小说写到了敏鹿、傅睿一家与东君、郭栋一家的一次城郊出游。这一章写得极为舒展、明媚、热闹、盛大,仿佛急促的鼓点暂停,悠扬的长笛响起。这是小说自千军万马的狂奔以来傅睿的第一次亮相,也是傅睿为数不多的从封闭空间来到自然环境下。叙述者似乎有意通过重建傅睿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休闲生活的方式来让我们认识一个医生以外的傅睿。显然,傅睿的参照系是郭栋。郭栋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构造物。他有着和这个时代同等膨胀的欲望、野心和能量。他风卷残云地吃,附庸风雅地喝,无所顾忌地闹。他是这个时代喧腾的高音。傅睿呢?我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对于食物没有爱好,对于茶酒没有兴趣,他沉默寡言,郁郁寡欢。在同行人看来,他“永远地斯文,永远地优雅,永远地高贵”,如皎皎明月,不似在人间。可是,谁又知道他背负着巨大的沉重呢?“傅睿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自己的累”。累,是因为万事万物都能牵动他的情绪,他觉得他对所有人都负有责任。摇曳的柳枝让他想起了去世的病患田菲,待宰杀的小山羊让他共情至深。他呀,他哪里是来到人间,他承担着整个人间,他认为他有责任疗愈这个世界。
然而人间却并不按照傅睿的逻辑运行。在老赵几分玩闹、几分对于权力的顺从的操作下,傅睿以他自己想象不到的方式被推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对于傅睿的心灵世界而言,田菲的意外病逝是第一个震撼性冲击,他被阴差阳错地推到了好人好事的话语系统里则是第二个冲击。他完全没有想到,一次医疗事件,居然滑向了它的反面——没有责任的追究,没有过错的讨论,只有讴歌和赞美。这讴歌和赞美事实上是不及物的,是某种情势的推进,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权力合谋的结果。傅睿只是充当了权力的表意符号。在傅睿看来,这讴歌近于残暴、近于蹂躏了。于是,他反抗了,他将烟灰砸向了喋喋不休的脑袋,烟灰四溅。请注意,这只是傅睿的幻觉。作为恪守规矩的人,他只可能在幻觉中完成这一切。某种意义上,我们也知道,他的精神彻底崩塌了。紧接着,他感到了“痒”,难以忍耐的“痒”。这是另外一种幻觉,或者说,是一个人对于荒诞的感受方式。庞大的无可逃避的荒诞倾盖下来,“痒”是身体的本能反应。就这样,我们眼见傅睿一步步滑入了精神的深渊。
而培训班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傅睿有他自己认知世界的一套法则,他不能消弭自我的边界,无间地融入整齐划一的集体。他永远是一个异类。而庞大的“我们”是不会顾忌他的情状的。为了获胜,哪怕这胜利毫无意义可言,他也必须被修剪——砍掉旁逸斜出的枝杈,将身体蜷缩进框架结构里。话说回来,哪个“我们”不是如此啊,只是大部分人麻木了,他们感觉不到自己是被修剪过的,他们以为历来如此,只有敏感如傅睿,才会感到痛,锥心刺骨的痛。
发生在傅睿身上的第三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是由盗窃事件引发的意外。为了抓小偷,傅睿的恍惚梦游状态被无所不在的摄像头拍了下来。关于这一事件,人们有着不同的解读。中心主任依照这个社会的功利主义法则,径直将他解读为为了追求名利的哗众之举。他以为他洞悉了真相,当然,不管内心怎么想,也不妨碍他再次将傅睿树立为典型。与之前相比,权力的运用方法倒是大同小异的。小有权力的人,老傅、老赵、雷书记和中心主任,都娴熟地运用这一套规则。他们无法想象,对于傅睿这简直是暴力碾碎。傅睿再一次感受到讴歌的残暴。“傅睿亲眼看着父亲手里的刀片把自己的额头切开了,中心主任和雷书记一人拽住了一只角,用力一拽,傅睿面部的皮肤就被撕开了,是一个整张。傅睿的面目模糊了,鲜红的,像一只溃烂的樱桃。却一点都不疼,只是痒。”用“痒”来形容精神世界遭遇的重大创伤,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痛,意味着与这个世界还在同一个维度,而痒,则是另外的觉知,或者就像小说题目所示,不在人间了吧。
对于傅睿而言,这荒诞的世界不可理喻,可是,他身边的人却觉得再正常不过了。比如护士小蔡,将恋爱当作自己的事业,轻巧地展开了同病人家属胡海的婚外情。在她看来,这遵循了商品社会物质交换的法则,是天经地义、各取所需的。再比如,对傅睿而言无法承担的重负,对郭鼎荣却意味着向上攀爬的捷径。他也期望从傅睿身上换取什么。问题是,生活在这样嘈杂的人间,傅睿真的就能一直格格不入吗?显然,叙述者没有这样的乐观。当行进到了三分之二处,小说开始逆转了。这逆转,不是情节的跌宕,不是悬疑的解开,而是人物的深层逻辑发生了转换。那么,这个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呢?
傅睿从未面对过这样的场景,它在傅睿的认知之外、能力之外、想象之外。这是他生命里的全新内容和全新感受。他的内里滋生出了非同寻常的感动,具体说,一种异乎寻常的激情,一种具备了优越感的情绪,与他内心深处的渴望出现了叠合与相融的迹象。傅睿舒服。有了光感。他的生命到底被拓展了,他内心最为深处的东西出现了。傅睿并不能命名他自己的新感受,但是,他高兴,接近于幸福,他确凿。
这是小说极为关键的一幕。人间的法则是权力关系,是利益关系,傅睿超脱其外。但是傅睿不是超人,他也有他的软肋。他执迷于拯救,这是他的职业伦理,也是他的生存伦理。没有拯救的人生简直不值得一过。现在,老赵跪在他面前,朝他磕头,将傅睿作为拯救者的身份具象化、形象化了。像上帝一样拯救众生,决定生与死,这是傅睿“新感受”的来源与指向。然而,这种所谓的“新感受”倘若没有理智作为堤坝,将会泛滥肆虐,成为新的迷障。正因为傅睿有所执,他的形象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不再“高贵”“清冷”,不食人间烟火,相反,他失去了从容。或者说,他失去了他自己。
在越来越深的黑暗中,死亡的意象开始盘旋在他周围。地铁窗外那一张张孤立、悬浮、凝固的死亡的脸,路灯下成群结队的昆虫的死,包括被水泥窒息的哥白尼的塑像,都是傅睿精神世界的外化,都是他无法宣之于口的呼救。只有拯救他人,才能把傅睿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过来。他尝试拯救哥白尼,结果失败了。现在,他发现了更好的对象,那就是堕落而不自知的小蔡。这是多么好的对象,他要拯救小蔡的灵魂,“把原先的小蔡还给小蔡”。汽车的突然拐弯让他体验到了失重的感觉,他视之为灵魂出窍。伴随着灵魂出窍的,是呕吐,以此清洗身体内人间的一切肮脏。经由如此荒诞的治疗方法,小蔡的灵魂能因此得到疗愈吗?答案可想而知。傅睿的拯救失败了,他自己成为一个亟需得到拯救的人。于是,一个光头出现了。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个形似和尚的男人此前曾经出现过。僧和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独特的象征意味。《红楼梦》中僧道登场,坐谈红尘,说起红尘虽有乐事,却美中不足,好事多磨;瞬息间乐极生悲、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脂砚斋点评说,“四句乃一部总纲”。一僧一道的出现,是叙述主旨,亦是点化世人。《欢迎来到人间》继承了明清小说的这一象征性人物的叙事方法。不过,这个光头男人并不是作为价值信仰的形象符号而存在。他更像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投射。小蔡遇到的“大师”,更像是一个江湖术士或者江湖骗子,看破了她对金钱的贪念,以此引她入彀。对于傅睿呢,光头要把身体内部的那些无法命名的“东西”给拔出来。那“东西”是什么呢?恐怕就是阻止他与“人间”融为一体的东西,他对于拯救生命的执着,以及被这执着异化了的自我。那么,傅睿成功了吗?小说到此是晦涩的,似乎作者有意给出一个开放式的解读。“他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为原材料,自己给自己吐一个茧,然后,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傅睿睡着了,像悬挂在外宇宙,那里有宽宏大量的黑。”“傅睿醒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空的。”这意味着,傅睿终于从身体内部诞生出一个新的自我了吗?还是他放弃执念,成为了他人的信徒?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予以想象与填充。但无论如何,叙事者还是给这个小说留下了光明的、充满希望的尾巴。在敏鹿的梦里,面对无限的远方,敏鹿和傅睿束手无策的时候,面团张开双臂、身轻如燕地滑向了北岸。困住我们这一代人的,将在下一代人面前化为坦途。
如果说,此前,毕飞宇是物质主义者,他擅长处理的是可触可感的生活,那么,现在他更偏重于精神了。他想写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叫“灵魂”的东西。然而,他又深知,没有什么悬在真空里的灵魂,灵魂的问题永远是在具体的人类处境中才能被捕捉的。换言之,他要写的是虚,但是没有密密匝匝的实,虚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浮现。这无疑是难度极大的工作,毕飞宇需要发明一套新的叙事语法,不妨总结一二:其一,以生活史构筑心灵史。心灵总是植根于日常生活不可化约的物质肌理之中。倘若没有对一个人的生活全局性的俯视与细节性的凝视,我们将对他的心灵一无所知。于是,小说创造性地运用了伞状结构。傅睿的生活是主轴部分。老傅、敏鹿、老赵、小蔡、郭鼎荣的生活是支撑起这把伞的幅面与纹路。小说不仅细致描绘其他人与傅睿交接的部分,还铺展出更为广阔的前史与远景,构筑丰饶的人间万象。生活有内在的整体性。傅睿的生活只有在与他人的生活交往中才能看得更清楚;傅睿的心灵也只有透过他人心灵的棱镜才更为清晰。其二,以常写异。在读完整部小说以后,我们才会恍然,傅睿有着严重的精神疾患。他常年的失眠,他的情感障碍,他的幻听、幻视,他异于常人的感觉和行为,无不在说明这一点。然而,叙述者似乎无意明示这一点。相反,傅睿始终是在我们可以理解的情理逻辑之中,其合情合理甚至可以让人忽视他的特异之处。更重要的是,我们理解了傅睿的情与理,其他“正常人”的情势的不合理、不正常反而凸显了出来。通过常与异的来回转换,我们的当下生活保有了某种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傅睿的心灵成为我们见证这个时代及其内在矛盾的倒影。其三,以诗化实。小说描摹精神世界的幻影与倒影,必然有着轻盈的质地,主要体现在意象、象征、重复、寓言等综合运用上。诗的品格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比如,蓝,象征了灵魂的安宁与平静。当傅睿完成了第一台手术之后,他渴望找一个游泳池平躺在水面上,一心一意望着高不可攀的蓝。老赵在静坐时也达到了这一境地。“老赵也蓝了,抽象。渡尽劫波的蓝。吉祥和如意的蓝。不寂不灭的蓝。老赵终于和蓝融为了一体,圆融啊。”再比如,傅睿有两次出现了幻视,一次是在培训班的课堂上,他仿佛看到了田菲向虚空中攀爬而去;一次是在目睹了小蔡的堕落之后,傅睿仿佛看到了小蔡向虚空中攀爬而去。重复使得这一带着诡异美感的意象令人更加难忘。类似于这样的修辞让小说在具备了阐释的多义性的同时,也有了呼吸的节律。读《欢迎来到人间》,犹如一场冒险,在整饬的叙事中,我们却总有迷宫之感,担心误入歧途。这也是毕飞宇向读者发起的邀约:他相信他的读者像他一样聪明狡黠,可以从不同的道路抵达小说的不同终点。
【注释】
①本文涉及的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引文,均出自《收获》2023年第3期,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②毕飞宇:《平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第1页。
(耿艳娇,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