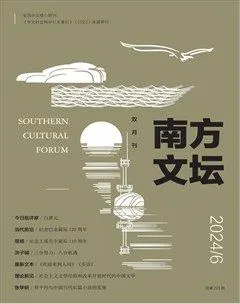从“不响”到“巨响”
2024-12-04刘明真
近年来,对文学作品尤其是严肃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掀起了热潮。从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梁晓声《人世间》,再到最近金宇澄的《繁花》,都成为现象级的作品,可以看到,影视改编的风向正逐渐地转向现实主义。其中,《繁花》以其独特的文化张力,在描绘上海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喧嚣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人性的复杂和时代的变迁,这些元素都为后续的改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多样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影视改编也让《繁花》跨越了文学与影视的界限,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尤其是在文化产业层面,《繁花》也以超长的制作周期、惊人的商业收益,以及对内地与香港优势影视资源的成功整合,成为业界重点研究的对象,也使得更多元化的观众群体能够接触到这部优秀的作品,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其影响力和传播范围,进一步推动了其经典化进程。
一、上海“不响”——《繁花》中的文化张力
自白话文运动和普通话推行以来,用方言来写作本就十分少见,成功者更是寥寥无几,偶尔有几部突出的,也是北方的作品,他们的方言实际与普通话已经十分接近了。如贾平凹、莫言、王朔等人的作品,尽管有很多方言掺杂其中,读起来却并无隔阂。但南方方言,却逐渐进入文学的边缘,哪怕是张爱玲极其推崇的《海上花列传》,也因其苏白对话而将大部分读者拒之门外。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粤语,因为香港的独特地位而独立于外。文学创作语言的同质化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繁花》的横空出世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种方言写作的可能性,也让人们重新看到了沪语的魅力。毋庸置疑,方言是这部作品的重心。
《繁花》最开始在一个面向上海话读者的平台“弄堂网”上连载,最开始的初稿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成书版的内容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动。“弄堂网”的宗旨就是“上海人讲自家身边故事”,他们谈上海的马路弄堂,谈上海曾经的旧事人物,谈消逝的戏院电影院。在《繁花》最开始的初稿中,是更为地道的上海方言,极具生活气息,也更加的口语化。就如引子中第一段,陶陶邀请沪生来自己店里坐坐。在“弄堂网”的初稿中,沪生还是“腻老师”,故事还被称为《上海阿宝》。
律师朋友腻先生回忆,80年代有次到菜场,一个摊头里有人叫他名字,原来是长远不见的小赤佬,前女友的邻居陶陶,在卖清水大闸蟹。当时菜场里,大闸蟹摊头很少,相当弹眼,因为蟹大,吃价畑,摆得也漂亮。赛过现在跑梅恒久,一进去就看到爬爬丽、苦气、爱而肥。陶陶招手,要腻先生到摊位里厢入坐,陶陶说:腻老师,侬进来好来,进来坐歇嘛。腻先生说,做啥啦,有啥事体伐。陶陶说,没事体,进来白相呀。腻先生说,有啥白相头啦。陶陶说,进来看呀,里厢跟外头不一样的,谈谈讲讲,风景好看,侬进来呀。(内容摘自“弄堂网”微信号)
可以看到,相比起正式修订后的出书版,在连载之初,小说中充斥着各种诸如“侬、伐、赤佬、坐歇、价畑、白相、里厢”等极具上海口语特色与生活气息的词汇,小说的叙述也显得随意且自由,完全就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个真实截面,我们每天走在马路上都可能碰到这样的情景。这段内容也奠定了小说的基调,这种自由随意的叙述以及所代表的上海腔调一直贯穿整部作品。同时,原作的话本气息更为浓厚,口语铺陈,不加断句,连载的标题也极具话本气息,“腻先生梅瑞会阿宝,扬州饭店抢生意”“阿宝伟民门口调邮票,思南路花园种花”“绍兴阿婆自觉命将尽,要回老家寻寻亲”等,都带有近代话本的韵味,偏偏讲的又是现代的故事,更具故事张力,但后期在出书版中却被简单地改为壹贰叁,不得不说也是一种遗憾。
在初连载的时候,金宇澄所面对的受众都为讲上海话的读者,“等于我对邻居讲上海话交流”,也因此,最开始连载的内容就像是他在跟朋友讲一些家长里短,口语气息浓重,也因此带有极其亲切的意味。他并没有什么野心,也从未预料到他的作品可以获得如此的成功,直到写到四分之一的部分,他才突然意识到这是一部小说,“我开始做提纲、结构、做人物表,心里想的是,不能仅让上海人读……凡属方言文字,不能有阅读障碍”①。正是出于这样的写作心态,金宇澄开始修订书中的内容,在尽可能保留上海韵味的同时,努力去除上海话的文字屏障,对一些极为形象的上海方言,也会贴心地通过角色的叙述为非上海话读者做好解释,如小毛让沪生有了“户头”也可以带来理发店,“沪生说,我不禁要问,啥叫‘户头’。小毛说,就是女朋友”②,又比如说第五章阿宝和贝蒂在讨论花草图案做成邮票时谈到,“姚女”是水仙花,“帝女”是菊花,“女郎”是木兰花等。在这些独特的语汇中,上海的文化被事无巨细地呈现出来,并非是作者要卖弄他的学识,而是想要让外地读者更多地了解上海的细节,了解上海的文化,不再是提到上海就只有纸醉金迷、小资情调、消费主义,而是一个更加生活化的、带有文化气韵的上海。
方言的使用,不仅展现了上海的地域特征,更是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文化和心理,尤其是对“不响”的解读,深刻揭示了上海地域的文化性格。“不响”便是沉默不语,有人总结过,《繁花》全文共有1500多处“不响”:陶陶给沪生讲完捉奸的故事,沪生不响;谈到变成金鱼的贝蒂,阿宝不响;小毛娘催促小毛结婚,小毛不响;讲到悲喜交加的高乃依戏剧,姝华不响;阿宝讲菩萨与荷花,李李不响……众人皆有过“不响”,“不响”展现了上海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性格特质,更代表了上海人深沉内敛的地域文化个性,而在更深层面,在面对诸多苦难之时,上海的芸芸众生们,也“不响”。
在整部作品的构思上,被说得最多的当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的新旧交替与穿插对比,但这之中更为重要的则是时代洪流中的人物命运如何飘荡。小说的叙述方式是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一个人带出另一个人,最后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展现了无限延长的人物线头,这是标准的话本叙事。饮食男女,鸡零狗碎,大量的饭局与闲谈,一件事还没讲完就仓皇地跳过了,要等到后面的章节才能找到蛛丝马迹,有时甚至没有结局,朋友聚散离合,再见已是暮年,人生也就这样结束了。按照作者的说法,自“文革”前后开始,每个人都在走下坡路,哪怕后面沪生做了律师,阿宝成为宝总,一步一步都是不如意的事情,在采访中金宇澄坦言:“《繁花》里那些人都不大说话,仿佛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③他们或者无语,或者无助,或者对命运无可奈何,但“不响”就是他们面对命运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得以尽可能地保持个体尊严而绽放出生活的诗意。其中最具诗意的当属黎老师,与丈夫一同被指认为特务的欧阳先生被放出来了,丈夫却已去世多年,只留下黎老师一个人面对满目疮痍回忆当时的美好时光,苦涩、无奈,在满书的世俗日常之外,黎老师像是满树繁花中的一支清冷树枝悄悄斜出,只留满地伤残。
阿宝觉得,只有电影蒙太奇,可以恢复眼前的荒凉,破烂帐闱,墙壁,回到几十年前窗明几净的样子,当时这对夫妻,相貌光生,并肩坐到窗前,看月的样子,娴静,荒寒,是黑白好电影,棱角分明,台面上摆了月饼,桂花糕,一壶清茶,黎老师年轻,有了醉态,银烛三更,然后光晕暗转,龙凤帐钩放落,月明良宵。④
金宇澄讲了大量的故事,但他并未做任何道德或者价值上的评判,这极符合他对自己“位置极低的说书人”的定位,而这是作者的“不响”,就如小说中出现了三次的那句话:“上帝不响,像一切皆有我定。”这恐怕就是金宇澄的意图,他不响,一切都由他笔下的人物自行决定人生走向。他让各种人说话,让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说话,让各种层次的人说话,他怀着对每个人命运的关切来书写他们,以细致的观察来描写他们,从而展示时代洪流之下的世俗景象,只期望能给人消遣和感动。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让小说《繁花》缺乏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导演王家卫曾直言,《繁花》根本没有任何影视倾向,而这种缺乏了戏剧性的“不响”背后,如何改编就成了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
二、“不响”到“巨响”——舞台剧与
电视剧的改编策略与异同
稠密的细节、繁多纷纭的人物线索、极具地域特色的方言、景观描写,再加上缺乏戏剧性的“不响”,让《繁花》的改编难度远远超过其他文学作品。但同样的,这些也是改编者的巨大宝库,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张力为改编提供了多重可能性,正如舞台剧导演马俊丰所说,“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原著里有各色各异的男女青年,有那么多套嵌的故事。年轻人看完,会被文学少女的命运感动。老人看完,无法从政治大潮、经济浪潮中摆脱出来,《繁花》背后呈现的是中国剧变的时代,那些漩涡和浪潮,会让人有无力感”⑤。《繁花》舞台剧和电视剧的改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舞台剧荣获第二届华语戏剧盛典“最佳创新剧目”,并于2019年“壹戏剧大赏”中荣获“年度大戏”及“年度最佳编剧”;电视剧的成绩则更为出色,在央视国剧盛典中,《繁花》获得年度大剧,而在第29届上海电视节中一举赢得“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改编)”“最佳摄影”“最佳美术”5个奖项,可谓是全场最大赢家,也让《繁花》电视剧成为中国电视剧的标杆作品。
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其实质为改编者对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与呈现。改编后的作品,自然而然地会融入改编者对作品的独特理解和阐释,包括自身的独特个性、文化审美、生活经历以及所处时代的独特印记等。舞台剧导演马俊丰迁居上海多年,却始终无法完全融入而心存隔膜,小说《繁花》的出现给了他理解上海的钥匙,因此他将《繁花》奉为圣经,舞台剧《繁花》则是他献给上海的一封情书,所以在改编的过程中他是尽量遵循原著,并展现了一种外地人的上海视角。上海出生的王家卫则对《繁花》的印象是一见如故。他幼年时期就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哥哥和姐姐却留在了上海,王家卫认为《繁花》写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因此在改编《繁花》的过程中,融入了他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想象,借《繁花》拍出了他心目中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魅力与腔调。不同的生活经历与美学理想让两位导演在改编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尊重原著与追求艺术表现之间采取了不同的取舍与平衡,但他们的重点都是对上海文化记忆的展现,以及时代洪流中人物的命运是如何的跌宕起伏。接下来本文将从美学理想与精神主题、情节构建与人物塑造、方言与怀旧三个方面对舞台剧和电视剧的改变策略进行分类对比阐述。
首先是美学理想与精神主题。在文学的影视改编上,这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也影响着改编者们对剧情及人物的塑造与改编。小说中,作者“不响”,不做道德评判,只给读者看故事,其中俗与雅、亵与诗并存,并不期待能起到“警世”的作用,写到最后结尾处的《新鸳鸯蝴蝶梦》更是展现了一种“篇终皆茫然”的美学态度,其中的是非功过自然是交由读者来自行思考。但作为一个面向公众敞开的电视剧,王家卫却不能含糊其词。《繁花》描写了许多道德线外的男女关系,如银凤与小毛、汪小姐与徐总、梅瑞与沪生等,“金宇澄以他独特的笔法,消解了这些关系的不道德感,让读者将注意力放在人物情感和命运上”⑥。但如果将这些原封不动地搬到电视剧中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厌恶,因此,电视剧消解了原作中的不道德感与虚无感,反而呈现出一种积极入世的美学追求。电视剧所展现出的上海,是一座在经济大潮中挣扎与奋进的城市,而这其中的人物,则是被赋予了更高的戏剧性与道德感,竭力彰显20世纪90年代中国飞速发展、人民奋力向前的时代精神。
相比较而言,舞台剧则面向更为特定与小众的观众群体,欣赏它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理解能力,因此舞台剧更为贴近原著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表现了一种日常生活之下的悲剧性与诗意。舞台剧中文艺青年姝华写的那封信是舞台剧美学核心的体现,姝华下放到东北,给初恋男友沪生写了最后一封信,信原封不动地从原作中摘录。“年纪越长,越觉孤独,是正常的,独立出生,独立去死。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恶情态,已经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⑦演员在台上一字不落地将这封信念了出来,真挚、纯粹,毫无保留地展示了舞台剧的悲剧美学。但同样的,舞台剧也并非完全追求呈现出绝望虚无的状态,正如编剧温方伊所说:“在结尾中,有获救(阿宝、李李),有陷溺(大妹妹、小毛),有挣扎(沪生、汪小姐)。世相纷繁,才是繁花。”⑧
其次是情节构建与人物塑造。电视剧面对的观众文化程度不一,如果想要取得商业价值上的成功,就必须照顾大多数,因此就要将繁杂的情节变得相对简洁。尤其是小说《繁花》将两个时代来回穿插,故事线索极多,对电视剧的观众可能有一定的门槛。因此,电视剧通过大刀阔斧的删减和增加情节,构建了一个以商战和股战为主线的故事,强化了戏剧性张力。王家卫删去了沪生和小毛这两个原作中极为重要的角色,而是以阿宝作为故事的主角。电视剧最大的改编或者说改编的核心,就在于“阿宝”如何完成“宝总”的身份转变。关于阿宝,小说中最多的“不响”就是来自于他,却并没有详细描述少年时期那个通透、寂然的阿宝是如何变成20世纪90年代的宝总,但电视剧却以此为切入口,填补了阿宝的“不响”,补白了小说的空缺,恰如该剧中一句台词所言,“不响最大”。可以说,在电视剧《繁花》中,王家卫将原作中“不响”的故事“响”了出来。电视剧《繁花》因此从普通的“故事性”而转向了“传奇性”,阿宝也从时代的旁观者变为时代的弄潮儿。他在电视剧中字字铿锵:“时代正在快速发展,我不想只是一个旁观者。”电视剧中的阿宝从一个消极接受命运的人,变成了充满欲望和行动力的英雄式人物。此外,电视剧还颠覆性地改写一些女性人物的命运,最为明显的就是汪小姐,在原作中一心只想养个孩子甚至不惜婚外情、假结婚,在电视剧中却自强自立、有勇有谋,最后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舞台剧则遵循了原作中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的交替场景,只做减法,不做加法,保留了小说中的并列存在和偶然事件,不追求戏剧性的高潮,而是倾向于叙述与抒情,这与其自身的美学追求相关。在人物塑造上舞台剧也是力求忠实于小说原型,人物性格和行为更贴近原著的描述。其中最难创作的人物便是阿宝,这一人物的戏份中混杂了太多的“不响”,他的每一处语言留白也具有不同的深意。编剧温方伊认为他除帮汪小姐和徐总谈判外,其他实事很少涉及。他“不响”,也不做,只做旁观者。因此在改编的过程中,舞台剧运用了大量的“静场”以及“舞台沉默”来进行演绎,主要是通过演员临场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来展示自己的“不响”,因此每场舞台剧的“不响”都是独特的,每位演员的“不响”也是独特的,却并未因此产生割裂感,而是让观众跟随他们的“不响”来一起思考,以此产生巨大的戏剧张力。
最后则是方言与怀旧。王家卫大刀阔斧的改编让人怀疑他到底是想展现《繁花》的什么内容,事实上,吸引和打动王家卫的,是《繁花》小说言语描写中的上海“腔调”,是吴侬软语的上海方言。王家卫的电影中对上海的怀旧叙事屡见不鲜,其作品《阿飞正传》《花样年华》《2046》都在不断追忆上海的城市图景。《阿飞正传》中最后梁朝伟的一分钟结尾被金宇澄写在了《繁花》的开头,《花样年华》中的沪语、旗袍、收音机里播放着的周璇老歌,更是满载王家卫对上海的追忆。这些在《繁花》电视剧中变成了极具上海味道的影像细节——从夜东京里阿宝细嚼慢咽的茶泡饭,到和平饭店英国套房里爷叔说得头头是道的西装,再到灯红酒绿的黄河路上让魏总出尽风头又黯然失色的“霸王别姬”,这些都为观众建构了一个个沉浸式的城市空间,让怀旧场域变得具象化,让观众得以感受上海的城市精神,更能体会到蓬勃的人间烟火。
而舞台剧相比起单纯的怀旧,更多地是想在舞台上展现上海的质感。包括导演马俊丰在内的舞台剧主创大多并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他们都在上海生活多年,有着自己的上海体验,而他们最后所呈现出来的舞台剧《繁花》,正是这种带着外地眼光和当代视角的上海怀旧感。在《繁花》的戏剧舞台上,精心雕琢的每一个场景都细腻地铺陈出一幅幅上海风情画。那些密密匝匝并且绕着圈的电线杆、老弄堂里支出的衣架、法国梧桐树叶细密的纹路,这些和上海密不可分的意象,都成为舞台上的细节。理发店内复古的陈设,搪瓷缸里残留的温情,弄堂口随意摆放的小板凳与轻轻摇曳的蒲扇,这些物件不仅仅是道具,更是上海人记忆的触媒,是对上海旧时光的深情回望。
在这些种种的怀旧场域之下,沪语对白构成了电视剧《繁花》不可或缺的听觉盛宴,精准捕捉并再现了上海人独特的日常交流韵味,深刻传递了上海的语言艺术与文化底蕴。《繁花》电视剧精心打造了沪语版与普通话版双版本,很多文本,只有通过沪语说出来才极具韵味。舞台剧《繁花》同样保留了小说中的方言特色,但在表现形式上可能更为内敛和注重文学性。沪语的巧妙融入,不仅为剧中角色赋予了更加鲜明立体的个性标签,如玲子的灵动、汪小姐的温婉、宝总的豪迈、爷叔的沉稳、陶陶的质朴等,这些语言形象均精准勾勒出角色的性格轮廓,更在无形中构建起一种强烈的地域认同与归属感,让观众在欣赏之余,也能深刻感受到那份独属于上海的韵味与风情。
在电视剧播出后,《人民日报》发文称,“《繁花》以现实主义精神反映时代的伟大变革”。相比起小说中的人世无常,最后小毛去世、李李出家、汪小姐不知是否能顺利诞下双头怪胎的结局,电视剧的积极向上带给了观众无限的生机与期待。原作的思想精神在于“花无百日红”,但电视剧却把落脚点放在“花开花落自有时”,虽然阿宝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变成黄河路上无人不知的“宝总”,最后又悄然离场,但他终究是抓住了机遇改写了命运,更何况是汪小姐、玲子等独立女性,完成了自我成长。时代洪流滚滚而过,不变的是一代代人不屈于命运的奋进之力,不论结果如何,这种力量本身就令人感动。小说《繁花》第一章,阿宝和贝蒂坐在屋顶,“东南风一劲,听见黄浦江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⑨。也许这正暗含了电视剧的结局,阿宝退出股市,但并未颓废惆怅,而是面对朝阳,大喊:“赤子之心常在,人不响,天晓得。”
三、《繁花》影视改编的经典化及其文化价值
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其内在蕴含的民间性不可或缺,但因其所带有的文学性质往往会提高民众的阅读门槛,而影视改编,作为一种旨在促进文学通俗化、普及化的手段,自然而然地搭建起文学经典通往民间世界的桥梁,这一过程中,它与文学经典及其经典化进程紧密相连,相互作用。因此,改编不仅是文学作品适应时代变迁、寻求更广泛接受的重要途径,更是其经典化历程中一个不可回避且至关重要的议题,持续影响着文学作品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影视对文学的改编由来已久,自1956年第一部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祝福》登上银幕,就开启了文学改编的热潮。影视改编最难的就是文学与影视剧相互成就、相得益彰,这也是改编者们不断的追求。小说《繁花》自发表以来便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经典之作,而电视剧的爆红,以及舞台剧的座无虚席,都引发了观众对两部作品以及那个时代的热烈讨论,长周期、高质量的制作模式也给电视剧行业带来新的思考和借鉴。
不可否认的是,舞台剧和电视剧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涉及叙事媒介转换的巨大挑战。文学作品的叙事媒介主要是语言文字,其表现手段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不确定性。读者通过文字阅读,依靠想象力在脑海中构建艺术形象和故事场景,这种阅读体验自由而充满个性。舞台剧和电视剧则主要通过表演和画面来叙事,电视剧还有较长的篇幅可供改编者进行铺陈,但舞台剧一般来说不会超过3个小时,表演与画面呈现更是仅限于舞台之上,因此表现手段相对局限、固定甚至不可改变。观众在剧场或电视屏幕前观看演员的表演,接受的是直观、立体的艺术呈现。这种叙事媒介的差异,要求改编者在将文学作品转化为舞台剧或电视剧时,必须进行精心的构思和再创造,以确保作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尤其是像《繁花》这样的长篇巨作,情节繁复,人物众多,舞台剧和电视剧受到演出时长或播放集数的限制,需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原作的核心内容。这就要求改编者要吃透原作,深入理解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然后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取舍和再创造,确保作品在保持原作风貌的同时,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也符合舞台剧或电视剧的篇幅要求。这种创造过程既是对原作的致敬和理解,也是对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尝试。当然,创新也需要适度,不能脱离原作的精神内核和艺术特色,否则将失去改编的意义和价值。
《繁花》改编最为成功之处在于其深入挖掘和呈现了上海的地域文化特色。无论是舞台剧还是电视剧,都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上海空间”与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交相辉映。舞台剧《繁花》带来了文艺演出的“沪语热”,电视剧则让“上海文化”以顶流IP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繁花》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精良的制作水准和深入人心的故事,更在于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反映,尤其是对本土文化风俗的完美呈现。作家和艺术家共同将这部作品打造成一部经典,不仅为人民提供了精神食粮,也展现了作为知识分子创造文化精品、传承文化的责任。”⑩无论是上海传统小吃茶泡饭、排骨年糕,还是上海人20世纪90年代的时尚穿着,抑或是吴侬软语的“沪语”方言,都展现了上海所独有的文化记忆,不仅还原了那个时代的风貌,更传递了上海文化的独特魅力。可以看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文化传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更是文化价值观的塑造者,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重大使命。《繁花》通过讲述上海的故事,实际上是在讲好中国故事。它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以及中国人民在这一过程中的坚韧和智慧。这样的故事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四、余论
随着电视剧《繁花》的播出,人们对上海的城市地理及人文历史的关注度不断攀升。“跟着《繁花》在上海city walk”一度成为外地游客的不二选择,在此之前人们来上海旅游可能都仅限于外滩、南京路等,但自《繁花》播出以来,众多市民与游客都开始了沉浸式“打卡”,黄河路、进贤路、苏州河、和平饭店的总统套房……掀起了上海文旅的新热潮,可谓是“为一部剧赴一座城”,这也深刻映射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间深度融合的新态势。这种融合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曝光度与知名度,更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塑造了城市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广泛的美誉。未来,期待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借鉴《繁花》的成功经验,探索出更加多样化、创新性的小说影视改编方式,为观众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注释】
① 金宇澄:《〈繁花〉创作谈》,《小说评论》2017年第3期。
②④⑦⑨金宇澄:《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第260、364、208、13页。
③钱文亮:《“向伟大的城市致敬”——金宇澄访谈录(上)》,《当代文坛》2017年第3期。
⑤吴丹:《修改一百次的舞台剧〈繁花〉,代表了南方戏剧的质感》,《第一财经日报》2024年7月10日。
⑥⑧温方伊:《繁华梦里说书人——舞台剧剧本〈繁花〉创作谈》,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6。
⑩张后安、姜楚娟:《时代风云、叙事结构与文化传承的兼容并蓄——谈电视剧〈繁花〉的艺术价值》,《文艺争鸣》2024年第5期。
(刘明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