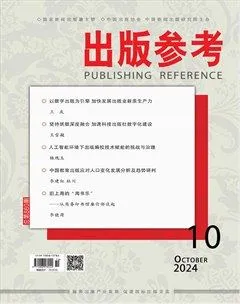历史的落差是心灵的秘径
2024-11-22谢明刘杨兵
《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以严肃史学方法来写文学人物和文学史,重新建置已经高度概念化的杜甫,在“千家注杜”之外,找到了一条通往更科学更精确的杜甫的秘径,带给读者新鲜的冲击:作为“诗史”的杜甫在参与历史和书写历史之前,首先必须是历史场域的一个普通节点。
“诗史”与“诗圣”,这已经决定了想要在高度概念化的杜甫身上作史学创新,绝对是一条非凡之路。历代蔚然大观的“千家注杜”文史兼具,以文辨史,以史载文,事无巨细,名家名著不可胜数,这给后来研究者以巨大的挑战,想要做出卓然不群又不哗众取宠的研究,新工具或可一试。王炳文的《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便是范例,他以现代的普遍史学方法介入杜甫研究,搁置文学方法与美学方法,将杜甫前后的历史场域作为诗人之路的先决条件进行研究,从而为杜甫的精神崇拜和人格崇拜增添了新的科学性历史观念。
“场域”就是历史环境的普遍性,历史场域则是新史学所倡导“整体史”的集中体现,尤其强调空间与时间属性,用以容纳文本、符码、实物等构成的事件。尽管概念非常笼统,用于历史写作首先是建置场域,再进行解域,用以重塑杜史与唐史能获得一种明澈的奇效,以往重史的方法,容易将杜甫还原为政治图景和社会工具,而重文的那一派,则容易陷入对杜甫诗人图腾的简单崇拜。
本书撷取公元683年至755年这样一个中时段进行研究,对应唐史则为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至安史之乱爆发这一时段,远比杜甫诞生之年(公元712年)早29年,正逢传统史学中盛唐。这一场域的核心为杜甫的家族场域,影响要素为唐代的权力场域、文学场域、经济场域和社会心理场域,涉及官制、家族制、财赋制等多种制度。场域的初建无关文学,书写杜甫诞生之前就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篇幅,八万字。大量引用罕见史料,将“杜鱼石-杜依艺-杜审言-杜闲-杜甫”这一世系传承作为士族场域的核心构建。家族场域既是所有历史人物的普遍境况,也是先决境况,必须置于其他场域之前,杜甫成长在一个日渐没落的传统士大夫家族:“以往掩盖在郡望大族之下的士族家庭,逐渐显露出真容,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可以说,士家大族的情况总体类似,具体的家庭却各自不同。”
如果说家族是个人起始点的话,权力场和经济场对个体的境况和走势则起到了主导作用。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和父亲杜闲建立了不少传承到杜甫的人脉资源,少年杜甫对张说张九龄这样的文学派领袖产生人格崇拜。动画巨制《长安三万里》中的少年杜甫形象是完全真实的,他因为士族出身能够心安理得置身于精英圈中,以不带雕饰的天然高贵来去自如。
而武周时代结束后,开元初年文学派步入衰落,杜甫已然感觉到文学派人脉存在的不足,曾经倜傥少年终于忧心忡忡地眺望未来。在家族场域“请托”权贵成为了维持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当务之急,以至于晚年杜甫写下“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的名句,心理的落差直指文学派的“盛世”。
从祖辈传承下来的旧交李邕,他的遭遇是文学派的权力场域影响杜甫的核心事件。李邕为人刚烈忠直。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却遭宰相李林甫勾陷,杖杀于狱中。他的死对杜甫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这一独立事件背后是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化,吏治派不但掌握了决定性力量,而且将这一场域实行了酷吏化,这使得杜甫内心存在的归隐与仕进矛盾越发剧烈。天宝六年杜甫已经36岁,此前他经历了科举失败,父亲去世,杜族分家,与高适、李白壮游等人生大事,祖上的余荫所剩无几,自己又勉为族长,门荫入仕已经不大可能。就在李邕遇难的同年,唐玄宗开特科取士,招天下有一技之长的士人,文学派由此看见了复苏的希望。杜甫于天宝九年(750年)以诗才得进待选之列,他趁热打铁,“献赋廷恩”,为三大国家祭典献上《三大礼赋》。
对于杜甫的这一行为,加上之前的各种“请托”,为临晋公主写神道碑,做汝阳王李琎门客等卑微举动,冯至在《杜甫传》里的评价颇为尖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方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寻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分不开的。”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无论是在权力场还是家族场,求“援引”都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既谈不上庸俗,也谈不上高尚,用后世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前世,未免有刻舟求剑之嫌。倒是历史学家王汎森提示的方法更为谨慎:“历史不再满足于政治外交史或以重要人物或历史事件为主的叙述方式……历史应有社会面貌,历史的理解应奠基于社会经济的基础上。”
由此可见杜甫所做的仅仅是用以改善自身和家族处境的社会性行为,研究这类行为的本质和社会基础远远比道德评价更为重要。
就在杜甫献“三大礼赋”的同时,盛唐的地理场域与权力场域同时在累积着巨变,最终爆发为一场惊天危机。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杜甫选授实职“太子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从八品下,掌管太子禁军的器械。同月,安禄山反,兵出范阳。“盛世”的历史场域一夜崩坍。造化便是如此的弄人,他没有在太平盛世如愿以偿地当上小公务员,而是在大厦将倾之时。他一度以为这是个讽刺,没想到却是一场真正的噩梦——也正是因为这场噩梦,才开启了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诗篇。
对于这个“不甚满意”的职位,杜甫上任之前需要回乡省亲,告慰先祖。等走上240里路,一路冰霜回到家中,猝然发现自己刚出生不久的第三子已经饿死,触发他写下了名垂千秋的不朽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诗篇再现了骄奢淫逸的宫廷生活与百姓苦难的鲜明对比,以历史的眼光则是“盛世”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这是他心中那座巍峨的大明宫骤然崩塌的时刻,而前方展开了苍凉无垠的地平线。他不再是跪拜在重楼叠檐下渴望着献赋、应诏的小公务员,他心中那点“士族”仅存的尊严与矜持荡然无存——他就在这一瞬间成为了苍生,成为了哭号流离的百姓,从而摆脱了自己自身悲剧的局限。所不同的是他具有一颗与生俱来的诗心。丢弃了富贵梦的包袱,开始任由这颗诗心自由地碰撞世界,不是伤怀,不是愤怒,而是彻底置身于历史和大众中的悲悯。
对于王炳文这一以“盛世”社会结构为主干、场域为底色的历史写作,普通读者需要有相当的适应过程。如果不了解场域观念,执念于事件与情节,阅读会陷入找不到事件头绪的缓慢进度之中。但真正的历史很多层面是没有情节可言的,是充满了事件碎片和力量碰撞的混沌漩涡,只是书写范式需要提炼出里面的连贯性。无情节似乎脱离了人类对历史演进线性结构的本能渴望,但负责任的历史叙述,就是需要发掘时间线与事件线之下的深层结构和场域,因为所有的事件都必定发生在场域中的某个点上,继而对场域施加影响,方能构成历史进程。至于诗歌,伟大的诗人面对这样惊人的历史落差,必然能积累出巨大的创作势能。
以“新史学”的工具介入文学史,无疑是本书一个创举,这意味着需要解决文学的精神性与历史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具体到杜甫身上,就是要从他“诗圣”“诗史”的特殊性之下寻找历史的共性。流行的“某某和他的时代”这类文学写法,只是简单地将历史与人物进行交互,很难说这些纯文学研究者经历过历史研究的苛刻训练,更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实际上是刻意避开需要验证真伪的世界。《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不将杜甫的特殊性置于普遍性之上,反而朝向历史的普遍性做更深的下潜,为盛衰两极所制造出巨大历史裂变和个体心理裂变,寻找尽可能可靠与广泛的历史图景。这种场域上的表达,刚好高悬了晚年杜甫创作的必要心理势能:权力的崩塌和重构,新旧时代的交替和斗争,会给天才提供精神生活的丰富养分和用武之地,从而完成从历史性通往文学性这一关键使命。正如T.S.艾略特所说,一个伟大的诗人不仅仅是他个人才情的表达,他还必须和历史以及文明的长河具有共时性。
在“千家注杜”之外寻求历史科学性的进步,这是王炳文为当代杜甫研究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系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产业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