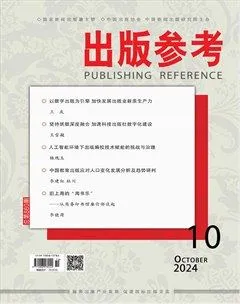旧上海的“淘书乐”
2024-11-22李晓荷
摘 要:商务印书馆自1917年首先设立廉价部,以低折扣销售残次书刊。廉价部清理了库存,吸引了大量读者、学者前来选购,形成了独特的“淘书乐”现象。廉价部的成功彰显了商务印书馆的市场洞察力,其创新的经营模式逐步打造出了上海出版业独特的旧书交易氛围。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 廉价部 图书折扣 “淘书乐”
近年来,“旧书市集”频频出圈,在各地上演“快闪”,吸引了周边地区的读者前来淘书卖书,这不仅是对市民文化需求的回应,更加强了出版社、书店和读者间的交流和互动。凡有读书人皆有贩书处,古旧书业在文化昌盛的江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上海自开埠以来,出版机构聚集发展,四马路(今上海黄浦区福州路)上书店林立,到民国时期,形成了中国现代出版的中心,那么,当年出版界的前辈们是如何处理积压的库存和残次书呢?笔者翻阅历史文献和学者随笔,以商务印书馆为例,摘录了几段民国年间发生的贩书、淘书、藏书的历史,以为镜鉴。
一、商务印书馆的廉价部和读便宜书活动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1897年创立于上海,至今跨越了三个世纪。“廉价部”一词最早是由商务印书馆首次提出并付诸实践的。1916年冬,由于仓库积压了过多滞销的旧书,由高梦旦[1]牵头,趁着学校放寒假,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设一专柜,专门销售这一批图书杂志,以一个月为期限,并商定为这个专柜叫“廉价部”,以利宣传。经筹措布置,廉价部于“一九一七年春节前十天开办。当时举办这个专柜,目的是专为廓清仓库里历年堆积不动的存货,所以定价的确非常便宜,例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刊物从创刊号起直到最近一年为止,几乎整套可以买到,而在外边,曾有人出高于定价几倍来征求而尚苦于难觅,可是在这里只须照定价一折到二折便可买到。消息一经传开,购买者蜂拥而至,每天挤满了人,后至者无法插足。有几种绝版书,外间有人出重价搜购,毫无着落,在这里有时竟能买到,因此人们争以光顾为快,从而‘廉价部’的声名大著”。讲这件事的谢菊曾[2]做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学徒,协助高梦旦参与了拟订廉价部简章的工作,他所述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对照《商务印书馆简史》一书所载,在民国六年(1917)8月20日商务印书馆的会议简报上,也特别介绍了廉价部的运作情况:“三、报告本馆各项陈旧及滞销书籍历年存积甚多,故设廉价部专售此种书籍。每年于暑假、年假时开办,每次收入约在五千元左右,将来拟令各分馆仿照办理。”[3]
1917年,郑孝胥在日记中两次提到廉价部,不仅提到贩卖廉价书聚拢人气,甚是热闹,又录有“陈列所新设廉价购书场,每日可售出百余元,此等书尝运至城隍庙设地摊,经月仅售四元余而已”[4]。郑孝胥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他显然对设立廉价部此举甚是满意和支持。
在商务印书馆经营者的努力下,廉价部加大宣传力度,周期性地在各大报纸杂志上连续刊登数日广告,不时承办如“庆祝儿童节——儿童图书特价加送赠品”“消暑读小说”等专题活动,一开门便顾客盈门,摩肩接踵,学者也以在廉价部淘书为美谈。廉价部的火热迅速被其他商人争相效仿,邻近的书店也不甘示弱,竞相设置廉价部,让利促销。时间一久,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大的出版机构,几乎每年都要设立廉价部,销售本社出版的书刊和教育文化用品。民国时期,在沪出版社多在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四马路(今福州路)设有发行所,于是一到假期廉价部开张,几条路上都是来淘廉价书的读者,此等热闹之情景,与今日“上海书展”、旧书市集之火热不相上下。廉价部的风行是市场规律的自然体现,同时也展示了商务印书馆领导者在经营中的独到眼光和智慧。
生意贵在“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据商务老员工方桂生在《回忆发行所点滴》[5]一文中写道:“通常办廉价部,以推销一部分残损书或滞销书为目的,由于残损书和滞销书的销售额总是有限的,不能解决经济上的特殊要求。因此,主办廉价部的当事者,就将一部分热门书,如《辞源》《英汉模范字典》《石头记》《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封神榜演义》等畅销书,以原价三折至四折,充实到廉价书籍中去,增加廉价书的花色品种,以招徕读者,扩大营业额。在廉价部开设期间,读者一早就等候在发行所的门口,一到营业时间,大门一开,读者即蜂拥而入,盛况空前。当时,充实到廉价部去的热门书,是机动掌握的,以经常保持廉价部的吸引力为原则。由于读者来得多了,当然也带动了残损书和滞销书的销售量,甚至一部分残损、滞销的文具、仪器及原版西书,也在廉价部中销售出去了。同时,发行所的正常营业,也被带动起来。廉价部视需要,一年举办一、二次,一般每次办一个月,有必要还可延长十天或半个月。”
商务印书馆还特意设计了廉价部的专用标志以示区别,内圈为廉价部三个艺术字,外圈等距嵌三个商务印书馆小标。
一般来讲,廉价部的活动仅限上海发行所及各地分馆内指定区域的图书,但为了照顾低龄读者群体,商务印书馆对童书的廉价销售采用了独特的策略。一是童书折扣最低六折,但写明儿童用书全都可享此优惠,除了单行本还涵括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儿童世界》《儿童画报》等期刊,即现在常说的童书全场六折。二是打折童书支持门市、函购、批发多渠道销售,同时买书还赠送童书类书目,包括幼童文库和小学生文库目录(附单行本价目),起到宣传品牌的作用;凡订阅全年儿童杂志的,包邮到家。在1935年,能够在保本的基础上为家长提供周到的购物体验,体现了商务印书馆对用户需求的洞察力。
但后来有商家借廉价部的名义,做一些以次充好、虚标价格的生意,甚至推出了一种“一折八扣书”,即在定价的基础上先打一折,又打八折。这种书,码洋一元,实洋八分,从纸张到内容都是糊弄。逐渐地,廉价部给人不良、劣质的印象。商务印书馆察觉后,1948年借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全运会的契机,广告语上引入了“紧接全运后的又一活动——读便宜书运动”这样一个概念,在推广上开始混用“廉价部”和“读便宜书运动”两个名称,以减轻廉价部一词的污名化。
二、学者笔下的淘书
事实上,学者对残次书、次新书的销售是欢迎的。汪曾祺先生诙谐地写了篇《读廉价书》,说自己在江阴读书时代就喜欢买廉价书,读便宜书。他认为“读廉价书有几样好处。一是买得起,掏出钱时不肉痛;二是无须珍惜,可以随便在上面圈点批注;三是丢了就丢了,不心疼。读廉价书亦有可记之事,爰记之”。
复旦大学杨焄教授在《〈庋榢偶识〉中的书人书事》提到一件王伯祥先生[6]的往事:他有一部《韩诗外传》在淞沪抗战期间付诸劫火,幸亏没过几年,“商务印书馆设廉价部,将旧存底货贬值斥卖,往往有绝版旧籍错列其间。一日清晨偶过之(时稍晏即顾客盈门,徘徊拥塞,无从插足),瞥见此本,标价仅六分,予喜旧帙之重遇,因购以归”,非但有故友失散再度重逢的惊喜,而且有眼皮底下廉值捡漏的意外,在颠沛流离的处境中更是让人悲辛交集。
作为旧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符璋[7]在日记里事无巨细地记录了自己的购书清单:
民国九年(1920年)二月二十日:在文明书局廉价部买来《史记》、《汉书精华》各八册,选择、评点皆好,坊本新出教科之佳编也,可代手钞。
五月廿七日:清晨诣商务馆廉价部,以太早,未开厅,仅照常买《吴挚甫尺牍》十二册八角而回。《文集》偶缺,《曾家书》字太小,不能看。未到商务馆,十馀家,有两家旧书廉价,未及观。
六月廿三日:二马路四海升平楼下廉价部书颇多。
读之,爱书人的形象跃然纸上,符璋于民国八年应邀来沪做总办哈同爱俪园文牍,短短一年间,已成为上海各大书店廉价部的铁粉了。
图书作为一种商品,在印制、运输、保存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遭虫咬鼠噬,或受雨淋水浸,全新完美品相的图书固然受到追捧,残次书(又称次新书)也无碍开卷有益。
谭正璧先生[8]在《煮字集》里讲了一件皆大欢喜的雅事,他“到商务印书馆去买吴梅编的《奢摩他室曲丛》第一第二集,可是这次却是难得的例外,第一集倒还有存书,而第二集反已售缺。但我知道这种书卖完了是不大会再版的,便决定把第一集买来了再说。以后又去问了几次有没有第二集,总是回说没有”。后来谭先生托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门市部的顾主任找书,隔了不到一个月,商务印书馆就派专人送上门了谭正璧求之多时而不得的《奢摩他室曲丛》第二集,但书上已经有了一些水渍。顾主任后来说明此书是他“写信到杭州分店里去访觅得来的”。其实有了污渍便是残次书,然而谭先生时隔多年依然写道当时的心情是“说不出的快乐”。
廉价书不仅自用,还可赠人。1932年8月12日,鲁迅先生致信许寿裳谈及自己在大马路(今上海南京路附近)上的文明书局的廉价部翻到“太炎先生手写影印之《文始》四本,黯淡垢污,在无聊之群书中,定价每本三角,为之慨然,得二本而出。兄不知有此书否?否则当以一部奉呈,亦一纪念也”。几日后再寄许寿裳信写道:“《文始》当于明日同此信一并寄出,价止三角,殊足黯然。近郭沫若有手写《金文丛考》,由文求堂出版,计四本,价乃至八元也。”[9]字里行间难掩激动之情,迫不及待要同友人分享这次淘书经历。
当然,再低的折扣在连温饱都成问题的学生面前,都是囊中羞涩。但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先生笔下也记录了出版人“有温度”的一面:“店堂中间放有两张大方桌;左边的方桌上陈列最新出版的图书,右边则是从七八折到三四折不等的廉价书。下午四点之后营业厅挤满了顾客,有如当年先施公司大减价一样热闹。我看见少数学子,因无力买书而每天来,选上一本新书,坐在靠墙的长椅上阅读,一连几天就看完一本。那只陈列新书的大方桌成了小型图书馆。店员们从不干涉。黄警顽先生(雅号为交际博士)是营业厅的总指挥,常与这些学子交谈,指出某书的精髓所在。这些常客在黄的指导下,一定得益匪浅,后来或许学有所长。”[10]
图书顶顶要紧的是内容,然而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这种不分贵贱对读者一视同仁的服务态度,也是让这些学者时过境迁仍然念念不忘的原因。
三、保存文脉,苦中作乐
张元济[11]曾在致傅增湘的信中写道:“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这段话不仅是张元济整理出版古籍的写照,也是商务印书馆致力于编印古籍、保护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宣言。
1948年5月21日,《申报》上照例刊登了一条商务印书馆关于廉价部的广告,这次的内容经过深思熟虑,言语直击人心,可谓出版广告的典范:
敝馆辑印“四部丛刊”,先后三编,士林珍视,日寇侵陵,藏家多半散佚,复员后纷来购补。敝馆亦残存无几。因向各地分馆搜罗。集中沪栈。并按时代撰人,分别门类,共成书七十组,兼应读者需要,特订廉价,加入本届廉价部。在上海发行所楼下特别陈列,存书有限,售罄即止,重印无期,选购请速。
外埠读者注意:一般廉价部书以上海门市现购为限,但“四部丛刊分组书”得尽存货供应外埠读者,另定廉售办法及书目,函索请附足回件邮费。
这次廉价部的重新回归,是为了解决经济困难,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同仁倡议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被炸焚毁,损失巨大,被迫停业,解雇全部职工;1937年“八一三”战役,(商务印书馆)上海各厂,因在战区以内,间接损失实甚严重(摘自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连遭两难,商务印书馆一度连日常开支都无法维持。
这一幕惨剧在中国土地上无数次重演,为了保护家中藏书,据黄侃先生的儿媳陈允贞女士回忆:他们一家辗转逃往重庆,一路上条件极为艰苦,仅将黄侃先生的珍贵藏书和手稿数箱贴身保存。每次空袭警报响起,全家人先抢运书箱,置家什衣物等等于不顾,一次大轰炸后,安顿好书箱,家中所有财物皆被烧光,“虽然如此,我们面对如此情景,见到先君遗著安然无恙,心中亦感安慰,于心安矣。”
广告中提到的《四部丛刊》是由张元济主持编辑大型影印古籍丛书,收录了历代最重要和常用的古籍,丛刊所选底本优良,至今仍是学者案头的工具书。战火纷飞,不少《四部丛刊》所选的底本和张元济先生从海外翻拍来的古籍胶片,毁于一旦,此处一句“重印无期”,充满了无奈和遗憾。且不说这段文字勾起了彼时多少读者的唏嘘,当下读到,也是感慨良多。1948年又逢金圆券改革失败,市场全面崩溃,上海民众的惶恐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商务印书馆还能拿出压箱底的《四部丛刊》继续降价销售,就不能只看成是收回成本的商业行为,更可视作是保存中华文脉的出版家担当了。
在当今出版业高度繁荣的背景下,上海旧书店等一批实体书店和新兴的“多抓鱼”“孔夫子旧书网”等交易平台线上线下共同发力,让残次书、二手书再次受到广泛关注,一些出版社也在自营的直播间里开起了“残次书专场”。这一系列措施,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物美价廉的阅读选择。时下的旧书市集和上海书展虽然和一百多年前的廉价部在形式、规模上都有不少创新,但它们本质上都是对图书价值的深度探索,是中华民族敬惜字纸重视文化的体现,值得我们传承和研究。
(作者单位系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