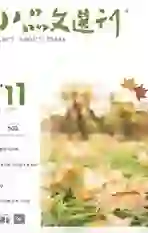一碗威风凛凛的面条
2024-11-07庞余亮
爱上面条,是在1983年,那时我已去扬州读师范了。
恰巧陆文夫的《美食家》在《收获》上发出来,实在太让人流口水了。
苏州美食,苏州面,还有那个爱吃“头汤面”的朱自冶。
“……最重要的是要吃‘头汤面’。千碗面,一锅汤。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话,那面汤就糊了,下出来的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汤气。朱自冶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汤气的面,他会整天精神不振,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所以他不能像奥勃洛摩夫那样躺着不起床,必须擦黑起身,匆匆盥洗,赶上朱鸿兴的头汤面。吃的艺术和其他的艺术相同,必须牢牢地把握住时空关系。”
真是腐朽得不得了的朱自冶啊。
虽然口头在批评,但内心深处是喜欢他的“腐朽”的啊。
朱自冶是苏州的,而我在扬州,几乎是差不多的江南。但是扬州面条和苏州面条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用竹筹取回来的面条,一半生一半烂,天知道下面条的师傅是怎么做出来的。
在扬州两年,我没吃过一碗好面条。
其实那时的扬州肯定有好面条的,只是我没吃到而已。一来我在扬州待的时间太短了,二来我是没有见过世面的穷小子,再者学校周围的面馆基本上都是小集体企业,没有老字号,下面条的师傅是吃大锅饭的,没有下好面条的积极性。
第三个原因是有点儿站不住脚的,那时扬州的每家小面馆里,与面条搭配的油炸糍粑绝对是超一流地好吃。
后来我回扬州就想吃油炸糍粑,用朱自冶的理论说,好吃的油炸糍粑仅仅存在于1983年到1985年之间的那个时空中。
1985年7月初,我乘着公共汽车离开了扬州,当然也离开了我的油炸糍粑。马上去教书的乡下肯定不会有油炸糍粑的,但肯定是会有面条的。
后来到了乡村学校,我对面条的欲望不见了,因为学校安排的课太多。上课需要力气,我更需要的是米饼油条。两块米饼包上一根油条,这样可以延续一个上午的气力。
后来就听老教师说了大老郑的面条。他们说起大老郑的面条,用词简单而粗暴:“打嘴巴子也不丢。”
越是简单,越是了不起。
这样的评语很让我口水无限,比陆文夫《美食家》里的朱自冶说起朱鸿兴的头汤面还要厉害呢。
老教师们其实没说到大老郑。
他们说来说去的,都是“人民饭店的面条”。
这样的说法不错,但没有特色,没有重点。
似乎所有的地方都有人民饭店,但我仅记住了沙沟人民饭店,我需要去尝一尝这个人民饭店的“朱鸿兴的头汤面”。
那时还没有双休日,要吃上一碗“人民饭店的面条”必须要等到星期天早上才行。
老教师说星期天早上太拥挤了,需要等。
我想,其实等也是制造口水的过程。
我实在低估了这“等”的时长。
我是星期天早上七点半去的,等面条到我的嘴里时已是快十点钟了。也就是说,我等待了两个多小时。
虽然我饥肠辘辘,口水咽了一口又一口,但我还是觉得特别值得。等于是看戏,一场由一碗面条引起的大戏。主角是那个叫大老郑的师傅,不是文戏,而是武戏。因为相比扬州面条的文下法,人民饭店或者大老郑的面条是武下法。
大家在排队。
有桌子的早坐下了,没有等到桌子位的就站着看大老郑下面条。
他个子不高,两只耳朵上各夹着一支老食客们敬上的烟,脚下垫有一块青石板,穿着一件印有红色“人民饭店”字样的白褂子,褂子前面有个口袋,口袋里装的是老食客们敬的烟。
灶是大灶。
大灶前的两口锅,一口锅里是永远沸腾的水,旁边是口清水锅。
大老郑两只手里各有一件“武器”,一件是特别长的竹筷子,一件是长柄的漏勺。漏勺是竹编的漏勺,一勺正好一碗三两面。
面条煮熟后浮起被大老郑用竹筷子捞到漏勺里,接下来“武术”表演开始。
嘴角叼着烟的大老郑首先把漏勺连同面条迅速“按”到冷水锅里,再迅速甩干冷却好的面条里的水。
那甩干要好几下的,的确是需要力气的。甩干的水会一直飞到大老郑头顶的屋梁上,灰黑色的屋梁边已有明显冲刷出来的“瀑布抽象画”。
大老郑除了照顾锅和面,还得和大灶后面的烧火者沟通。他的沟通完全是用粗话骂人,当然也相当于骂他手中漏勺里的面条。
被骂得完全没了脾气的,也就是完全被沥干的面条,接着被大老郑安放在排在一边的碗中。
碗中没有汤,仅有猪油、蒜头、生抽和味精。
面条到手必须赶紧拌,吮吸了佐料的面条一边被拌一边在“长”。
新鲜的生抽原来是酱红色的,被面条一“激”,酱红色完全消失,面条和佐料合而为一。
一碗威风凛凛的面条就这样诞生了。
筋道,有味儿,真的是“打嘴巴子也不丢”的好面条啊。
我彻底被大老郑的干汤面征服了。
老教师打趣说:“真正是有味儿呢,那是他嘴巴上掉下的烟灰加了‘料’。”
似乎是对的,又似乎不对。
还有屋梁上冲刷下来的灰呢。反正看不见,吃下去也没事儿。
反正我是爱上这碗面条了,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排队,看大老郑的“武侠戏”,吃他的干汤面。
大老郑每天开始下面的时间是早上五点多钟,天不亮的时候,早有赶轮船的、做生意的去了。等到我去人民饭店吃面条时,已经是第四五拨“朱自冶”了。
每每忙到十点多钟,大老郑才能歇手。
歇手后的大老郑会扔两支烟给灶后面烧火的老洪。
这个耳朵不好的老洪总是被骂,但大老郑不允许经理开除老洪。
经理讨厌这个老洪喝酒,更不喜欢老洪偷吃客人剩下的面。大老郑就让老洪躲到灶后面吃。
当然,还是要骂的,也是不能开除的——开除之后,这个老洪会饿死的。
我在那个地方待了15年,吃人民饭店的面条也有15年了。算起来,是人民饭店版的小“朱自冶”。
后来,我离开了那所乡村学校。
再后来,大集体性质的人民饭店关门了。
下了岗的大老郑盘下了桥口的粮贸酒家,老洪也跟他去了,但不用烧火了,改为值夜班。
不用柴草了,都用煤炭和鼓风机了。
粮贸酒家依旧是“朱鸿兴”,因为有许多追随干汤面的“朱自冶”,他家的春卷、小麻饼、鱼圆还有藕夹,都卖得不错。
当然他家的干汤面最好。
大老郑甩干汤面的力气一点儿也没小呢。
又过了很多年。
那年正月十五,我应邀回去看灯会,灯会的全称叫作沙沟彩妆游走灯会。我顺便去了粮贸酒家,我没有吃到干汤面,其他客人也没有吃到干汤面。
为什么呢?
这个总是不老的大老郑怎么可以理直气壮地怠慢客人呢?
没办法,再了不起的干汤面也没他的孙子重要。因为大老郑的孙子被选中做灯会的“金童”了。所以大老郑在正月十五之前就说过了,正月十五那天,他会对不住大家一天,他要向大家请假,他要去做宝贝孙子的勤务兵。
我没吃到期待中的那碗威风凛凛的面条,就在离开的那个时刻,我似乎理解了那个腐朽得不得了的朱自冶。
选自《胶东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