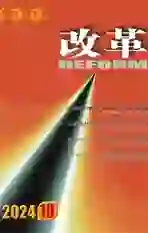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三重逻辑
2024-11-07孙博文

摘 要: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既有狭义上实现生态文明数字化、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的实践创新诉求,又有广义上以新质生产力催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理论创新空间。随着文明数字化与文明生态化双重转型时代的到来,从文明形态演进视角探讨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生态文明生成逻辑,对于深入理解后工业文明时代生态文明和数字文明两种新文明形态融合的内涵,以及廓清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构成和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价值。基于技术变革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演变下的文明转型历史逻辑,探讨生产力进步下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特征、内在关联以及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生态文明内涵意蕴。立足生产要素理论创新和四次工业革命演进下“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理论,从要素、技术、经济、社会、文化、治理以及全球文明互鉴等维度廓清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逻辑。加快数字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深入阐明培育数字生态要素、创新数字生态技术、发展数字生态经济、构建数字生态社会、弘扬数字生态文化、强化数字生态治理、建设全球数字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生态文明;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4)10-0062-16
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下,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途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数字生态文明”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脉络清晰,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到2021年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中首次提出“数字文明”、再到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数字生态文明”,加快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成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数字中国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的现实要求。从学术层面看,既有学者主要基于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狭义视角,将数字生态文明理解为生态文明的数字化形态,提出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渗透至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为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提供支撑[1-3],以及通过数字技术应用,推动绿色产业转型、促进全球气候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球数字可持续目标[4]。也有学者指出,完整理解数字生态文明内涵,需要将其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及全过程进行考量[5]。从政策层面看,2019年以来,围绕促进数字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融合发展目标,国家相关部门就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化、能源数字化智能化、生产方式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循环经济数字化、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绿色智慧城市与乡村建设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实践深入推进并取得重要进展。
不过,随着文明数字化与文明生态化双重转型时代的到来[3],从更宏大的文明演进视角审视数字生态文明,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后工业文明时代生态文明和数字文明两种新文明形态融合的内涵,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构成和推进路径具有重要价值。纵览人类文明史,每一次文明形态演进都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技术革命性突破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成为考察人类文明演进趋势的关键视角[6-7]。由历次技术革命引发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智能革命,为文明的物质形态变革创造了根本性的条件[8],在此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贯穿人类文明演变的重要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既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人类文明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不竭动力[9]。进入新时代,我国迈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征程[10-11],新一轮新技术革命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深入推进下,数字文明和生态文明作为继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两类文明形态[12-13],或在深度交织与有机融合中催生数字生态文明的新文明形态表达。鉴于此,对于数字生态文明的研究,有必要超越狭义上以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实现“生态文明数字化”的实践创新诉求,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视角深入理解数字生态文明的重大意义和生成逻辑。
一、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逻辑
汉语中的“文明”一词以词组的形式最早出现在《易经》之中,如“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意指人类社会的开化、文治[10]。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及其文明形态,归根到底源自物质资料生产,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取决于客观存在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转型升级是创新人类文明的关键所在。技术进步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观察文明转型的关键视角。从原始文明到后工业文明,人类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迁,而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并行交织、深度融合形成数字生态文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特征。
(一)原始文明时代:朴素性技术变迁以及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关系
原始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展现出了朴素的技术变迁与人与自然关系特征。
就技术进步视角而言,原始文明时期人类主要依赖简单石器、木器和火等工具,石器和木器的制作及使用标志着人类开始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并对其进行初级改造,火的利用则帮助人类取暖、驱赶野兽以及烹饪食物,大大提高了人类生存能力。在这一阶段,信息的传递和记录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手势、符号标记等方式进行,数字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也并不存在。受限于人类的语言交流以及知识的积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技术进步也非常缓慢。
就人与自然关系视角而言,原始文明时期人类依赖、顺应、敬畏自然,主要通过观察与模仿动物生活习性捕获猎物,使用初级工具提升生存适应能力,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保持相对平衡状态。
(二)农耕文明时代:农业技术改善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趋于紧张
从原始文明到农耕文明阶段,人类从采食捕猎向栽种畜养转变,生产力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总体不高,土地及附着在其上的作物是主要劳动对象,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就技术进步视角而言,农耕文明时期人类发明了农耕、灌溉和畜牧等农业生产技术,提升了人类主动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通过发展农耕技术帮助人类改造土地、种植作物而获取稳定食物来源,利用灌溉技术不断提升农作物产量和质量,利用畜牧技术进一步拓展了食物的来源渠道,相关农业技术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使得农业成为支撑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尤其在工业革命兴起之前的1000—1820年,虽然农业技术进步较为缓慢,但依然是农业生产率以及全球人口缓慢增长的主要动力[14]。在农耕文明阶段,人类仍然依靠传统方法(文字、计数、邮驿、日晷等)来进行信息的记录和传播,也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数字技术或信息通信技术。
就人与自然关系视角而言,农耕文明时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对和谐但又存在矛盾的关系。人类在顺应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农业生产和生活活动,同时也开始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与原始文明时期人类顺应依赖自然相比,农耕文明时期人类开始更加深入地利用和改造自然,通过开垦土地、修建水利设施等方式发展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总体上,人类主要通过精耕细作和轮作轮休发展可持续农业,保持着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但与此同时,对自然过度开发也带来了水土流失、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等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三)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技术群涌现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加剧
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由技术革命催生的工业革命,极大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并伴随着工业技术群的涌现,为人与自然关系和解提供了技术支撑。
就技术进步视角而言,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以及工业技术群涌现成为工业文明的显著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大约从1760年延续至1840年,以蒸汽技术发明为标志,为通信和贸易网络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性,引领人类进入机械生产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约在1850—1920年发生在英国、德国、美国,以电力技术和内燃机技术发明和使用为标志,其通用技术是电力、电信、运输与工厂生产线,以及支持石油工业与一系列化学产品的技术开发,极大促进了制造业和整个供应链实现创新整合,规模化生产应运而生,引领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50—2005年的美国,也称计算机革命和数字革命,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通用技术是计算机、智能手机、移动通信、移动计算设备,催生这一革命的是大型计算机(20世纪60年代)、个人计算机(20世纪70—80年代)和互联网(20世纪90年代)。21世纪以来,第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逐步渗透至经济社会各领域。
就人与自然关系视角而言,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开始以更加主动和强势的姿态改造和利用自然,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消耗,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和污染物,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工业革命同时也是一场能源革命[14],能源利用类别与形态的变化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同的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用煤作为动力,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第二次工业革命也伴随着新一轮能源革命,通过电力极大拓展了人类使用能源的范围和形式,但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创新引发信息技术革命,但依然沿用了化石能源使用模式,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人类第一大能源,气候危机日益严重。人类逐渐意识到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开始寻求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第四次工业革命也被称为绿色工业革命,更加注重可再生能源应用以及绿色低碳技术突破创新下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及碳减排,在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同时,以碳中和目标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也有学者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依然解决不了人与自然关系矛盾问题,并将碳中和时代的工业革命界定为以新能源设备为载体、以碳中和能源替代为要素、以可再生能源技术为支撑的生态革命或第五次工业革命[15]。
(四)后工业文明时代: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生态文明内涵意蕴
在后工业文明时代,生态文明与数字文明并行交织、深度融合,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和可持续发展诉求为标志,分别从不同维度实现对工业文明的继承与超越。
就技术进步视角而言,2005年以来发生于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基于数字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快速发展并全面渗透至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各领域和全过程为突出标志,为解决工业文明时代带来的冲突和矛盾提供数据要素驱动、数字技术赋能、数字经济引领、数字治理升级以及文明成果共享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催生了数字文明新形态,并呈现全球参与、全民共享和技术向善的突出特征[16]。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不仅包括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还包括绿色技术(新能源技术、智能电网技术、零碳负碳技术)、物理技术(无人驾驶交通、3D打印、高级机器人、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生物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应用。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应用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数字技术应用更加深入、渗透更为广泛、智能化程度更高,除自动化功能大幅提升外,还能更加智慧地辅助决策制定和执行,且更加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
就人与自然关系视角而言,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继承与超越,以把握自然规律、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为内涵,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的文明发展形态。生态文明时代,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全面绿色变革,生态劳动成为劳动的普遍形式,人类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17-18]。
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深度融合形成数字生态文明新形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构成与突出标志。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证,精神文明是灵魂,社会文明是条件,生态文明是前提,“五个文明”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中国式现代化以“五个文明”进步与协调发展,开创了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技术进步、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历史视角,数字生态文明与“五个文明”逻辑关联体现在:数字生态文明是一种“新文明形态”而非一种“独立文明形态”,基底是生态文明和数字文明两类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新文明形态,特征是两类文明形态与其他“五个文明”的融合质态,实践上体现了数字技术与生态约束全面渗透至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各领域的创新,落脚于“五个文明”的全面数字化和生态化。基于此,数字生态文明(广义)可理解为两类文明形态的有机融合,表现为生态文明数字化与数字文明生态化的共生特征,以及与之匹配的社会—制度结构。它既强调数字技术革命对生态文明各领域的赋能作用,又突出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实现绿色化融合的要求。
(五)文明形态演进动力与内在关联:新质生产力视角
生产力进步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每一次技术革命性突破下的巨大生产力进步,都会催生与时代对应的生产力新质态。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影响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的演进。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并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质变为基本内涵。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技术革命性突破(技术进步)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改善(如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关系优化)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19]。这是因为,科学技术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结合,促使科技成为物质生产力,加之大数据对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新质生产力的三要素全面超越了传统生产力[20-21]。另外,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是不同时代生产力发展要解决的一以贯之的问题。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历史相对概念。生产力水准(即质)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产生新质生产力[22]。这意味着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与之对应的新质生产力。文明转型背景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周期、需要有历史耐心,从原始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推动原始文明以及农耕文明转型的农业、工业技术革命性突破及生产力要素优化组合,分别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生产力新质态,表现为新质生产力I促进原始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变、新质生产力II促进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生产力发展从量的积累实现到质的跃迁,并逐步形成催生数字生态文明的新质生产力III(见图1,下页)。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文明形态的演进并非线性割裂的,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技术进步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成为驱动力量和约束要求,并分别表现出“指数型”与“倒U”型变化特征。这使得前一种文明形态的技术突破为后一种文明形态的发展提供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技术作用逐渐降低、淡化直至被新的技术替代,与此同时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要求越发被强调。第一,从原始文明到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继承了原始文明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在继承原始文明狩猎、采集等生存技能的同时,发展出了农耕、畜牧等新的生产方式,农业技术不断进步(图1中新质生产力I酝酿的N1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精心耕作的生产方式,显著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新质生产力I逐步形成、扩散催生农耕文明新形态。第二,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继承了农耕文明对物质生产的重视,发展出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的生产方式,工业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图1中新质生产力II形成的N2阶段),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但也加剧了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危机。第三,从工业文明到数字生态文明。在数字生态文明阶段,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图1中新质生产力III形成的N3阶段),数字技术进步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并寻求破解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和资源短缺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总体上,新文明形态实现了对旧文明形态的包容性超越,旧文明形态为新文明形态的形成提供物质、技术、知识、文化、社会组织的准备,为推动文明形态转型过程中从新质生产力酝酿(图1中文明转型交叉阶段N1—N3)到全面实现(新文明形态阶段)奠定基础。最终,数字生态文明(广义)作为数字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融合质态,兼具数字文明生态化与生态文明数字化的双重特征,作为一种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五大文明”相互渗透的“新文明形态”而非“独立文明形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构成与突出标志。
二、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逻辑
科学把握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关键在于立足技术进步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双重视角和逻辑起点,创新数据要素与生态要素理论,廓清“数字技术—经济”范式与“绿色技术—经济”范式协同变革逻辑,进而构建包含要素、技术、经济、社会、文化、治理与全球等七个维度的理论框架。
(一)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
新质生产力下要素理论创新与“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奠定了数字生态文明的重要理论基石。
一是数据与生态要素理论创新。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及其组合构成,新质生产力则以生产力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特征。数据要素已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呈现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双重属性:作为劳动对象,通过劳动者的加工和转化形成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作为劳动工具,能够提升生产效能。数据要素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渗透性,即大量数据提炼出的有效信息可以缩短其他要素相互衔接的成本和时间[23],通过原始数据资源化、数据资源要素化、数据要素产品化三次重大形态转变和价值增值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仅包括人的劳动和创造力,还包括作为人类生存依托和劳动对象的自然界。生态环境要素(生态要素)是生产力要素的重要构成,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将生态要素作为独立生产要素,是促进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产品资产证券化,进而实现生态要素价值转化的重要理论创新。
二是“数字技术—经济”范式与“绿色技术—经济”范式协同变革。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初级阶段的“数字技术—经济”范式和“绿色技术—经济”范式。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标志,极大地推动了信息处理与传播的速度和效率,但有关技术主要集中在信息处理领域,对于制造业、能源行业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在应对第二次工业革命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环境危机、人与自然共生矛盾中,“绿色技术—经济”范式应运而生[24]。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兼容,灵活的生产模式将实现能源和材料的节约,甚至创造新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了更加成熟的“数字技术—经济”范式与智能绿色增长背景下的“绿色技术—经济”范式。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渗透至经济社会各领域,形成新生产技术、新工艺流程、新分工模式、新市场结构、新消费市场、新治理模式,表现为更加成熟的“数字技术—经济”范式[25]。这一阶段“绿色技术—经济”范式也更加成熟,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及清洁能源技术进步取得突破,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下智能绿色增长成为可能[26],形成更为绿色智能的“绿色技术—经济”范式。
鉴于以上分析,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和生态要素)产生和优化组合理论创新,以及基于技术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约束而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变革,代表了特定时期的主导“技术—经济”结构和适应性“社会—制度”框架,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整体水平[26-27],不仅从技术层面推动了数字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而且通过推动“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引致生产关系的匹配性变化,在经济、社会及治理(制度)等多个维度形成有效支撑,共同构筑了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基石。
(二)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框架
基于要素、技术、经济、社会、文化、治理与全球的视角,将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分解为七个维度的形成机制:数字生态要素、数字生态技术、数字生态经济、数字生态社会、数字生态文化、数字生态治理、全球数字生态文明,本质上体现了数字技术与生态理念全面融合并协同渗透至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领域的过程。这一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微观上嵌入数字生态要素(技术)、宏观上遵从文明形态演进规律,拓展了相关研究关于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基准分析思路[5]。这七个维度的逻辑关系是:数据要素和技术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动力支撑,并协同推动“技术—经济”范式变革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经济社会发展反过来为生产要素配置与技术应用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反映了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导向。数字生态文化不仅为其他要素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数字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路径。数字生态化治理重构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元共治格局,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保障者、推动者和协调者的关键角色。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中国方案。
一是数字生态要素维度,包括生态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要素生态化。生态要素数据化是对生态要素数字化的升级,是利用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数字化的生态要素信息进一步加工和整合,形成结构化、标准化的数据集,实现各类生态要素的数据化科学管理、形成大数据资源,为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就数据要素生态化而言,实现数据信息计算、存储、传递、加速、展示等功能的数据中心通常具有突出的高耗能问题[28-29],采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或者优化管理等方式有助于促进数据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化,进而实现数据要素生态化。生态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要素生态化是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要素理论基础,体现了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等要素的优化组合,是加快形成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二是数字生态技术维度,包括数字技术生态化与生态技术数字化。数字技术生态化通常指的是将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与生态保护原则相结合的过程。这意味着在研发和运用数字技术时应考虑到环境影响,努力减少负面影响并促进可持续发展。根据技术偏向性理论[30],数字技术进步能够影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能源、生态、管理)的边际产出,这种偏向性包括提高某一要素使用效率,或者创造新的需求或市场。数字技术生态化体现了数字技术的生态偏向性特征,数字技术应用提高了生态效率、增加了生态产品的市场需求。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通用数字技术而言,其既可以被用来推动环境治理与绿色低碳发展,也会因为数字技术应用而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并不具有典型的生态环境偏向性。实现数字技术的生态化则充分依赖于数字技术与其他要素(管理、能源、生态)的优化组合,通过政策引导、标准制定、监管和评估等科学管理手段实现数字技术的低碳化场景应用,这涉及技术创新、结构转型、绿色生活等多领域;或者针对直接相关的能源环境领域开发专用数字技术(如智慧能源技术、智能电网技术、实时监测和评估生态系统状况的专用传感器及数据分析系统),促进实现节能、降碳和减污,这一生态环境偏向的专用数字技术能够更好体现数字技术生态化的理论逻辑。生态技术数字化则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增强和优化传统生态技术(如清洁能源技术、废物管理技术等)的过程,使这些技术更高效、更智能。生态技术数字化是将生态技术相关数据和知识转化为计算机可处理的数字形式,便于进行数据分析、模型构建和仿真优化,进而促进绿色发展。实现生态技术数字化,在更高效地处理、存储、传输和共享绿色技术信息的同时,通过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对绿色技术研发进行模拟、优化和预测,通过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整合效应以及风险规避效应,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实现生态技术“双重外部性”的“双重内部化”,提高研发成功率和应用转化率。此外,以“数绿融合”为突出特征的数字生态技术专利识别和测度方法不断涌现,如引文法、文本法和专利共类法等,为测度数字生态技术的绿色发展效应提供了科学方法支撑。
三是数字生态经济维度,包括数字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数字化。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数字经济生态化则包括实现数字产业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以及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过程中注重生态化导向、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就生态经济数字化而言,生态经济的本质是实现生态正外部性以及环境负外部性的“双重外部性”的“双重内部化”,要求以生态要素理论创新为基础,通过促进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产品资产证券化,对生态要素进行确权与交易,并利用市场化机制打通生态要素价值实现渠道,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基于此,生态经济数字化的过程,就是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供给、核算、抵押、交易与变现的全过程。
四是数字生态社会维度,体现了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动下的生活方式变革。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驱动力,推动与数字生态文明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为数字生态社会建设创造生产关系条件。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而言,数据要素和生态要素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从而引致数据和生态要素所有权、使用权和权益的市场交易等问题,进而影响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就人的生产地位及相互关系而言,数字化和生态化融合发展促进实现生产关系网络化、数智化、绿色化、公平化,使得生产过程中的信息传递更加高效、生产合作更加紧密、劳动关系更加和谐、生态导向更加突出。就产品分配形式而言,数据要素和生态要素直接参与收入分配,数据要素产生、采集、处理和分析等环节市场价值将得到充分体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将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极大提高产品分配的智能化、精准化、透明化、公平化水平[31]。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转型,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作用下的生活方式变革趋势。生活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关系的具体体现,涵盖人们衣食住行、消费娱乐、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活状态及文化特征,也是人们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和社会习俗的集中表现。在数字生态文明时代,人们生活方式呈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态势,是数字生态社会的显著特征。
五是数字生态文化维度,包括数字文化生态化与生态文化数字化。数字文化生态化是指以生态文化理念引领数字技术、数字文化发展,破解生态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网络违法与监管失效、数字自由主义以及西方反生态思潮泛滥等问题[5]。生态文化数字化则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供给,促进生态文化传播,如开展数字化生态教育、在线生态文化展览、数字文化产品营销、数字生态文旅等活动。数字文化生态化与生态文化数字化的关系体现在,前者强调问题导向、聚焦数字文化与数字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无序问题,后者强调技术赋能、聚焦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效能问题,都以实现数字文化和生态文化融合发展为目标,促进数字生态文明理念与行动融入文化建设及其全过程。
六是数字生态治理维度,体现了生态环境全过程数字化治理过程。全过程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个环节和方面,包括搭建数据监测平台、开展数据搜集、打通数据壁垒、深度挖掘分析数据促进智慧化精准化治理决策、提升生态监管水平等。搭建数据监测平台是数字化治理的物理基础,为生态环境及碳排放数据的搜集提供硬件和软件支持;开展数据搜集是后续分析和决策的重要依据,这一环节对决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产生直接影响;打通数据壁垒是实现数据共享和互通的关键环节,通过打通不同部门和系统之间的数据孤岛,促进生态环境与碳排放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利用,有助于显著提升治理效率;对生态环境及碳排放数据的深度挖掘和科学分析,有助于发现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为智慧化精准化治理决策提供支撑;提升生态监管水平是全过程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的最终目标,通过深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应用,可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实时监测和预警,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降碳已成为我国未来生态环境治理的战略重点,推动全过程数字化碳治理以及实现数字碳中和成为数字生态治理的关键任务。
七是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逻辑。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是物质和精神不断丰富和拓展的过程,妥善应对文明差异、处理文明冲突,是促进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内核。当今世界,数字文明和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在全球已形成共识。人类继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具有世界意义的数字文明和生态文明并行交织的数字生态文明新阶段。文明之间互相尊重、交流互鉴是解决文明冲突、实现全球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基石。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新文明形态,数字生态文明以数字新技术应用为支撑、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主张用包容、合作、对话等方式解决分歧,将为引领世界、造福世界各国民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驱动力量。
三、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逻辑
加快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是阐明培育数字生态要素、创新数字生态技术、发展数字生态经济、构建数字生态社会、弘扬数字生态文化、强化数字生态治理、推动全球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实践逻辑。
(一)培育数字生态要素,推进生态要素数据化与数据要素生态化
第一,加快实现生态要素数据化,推动自然资源、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数据融合创新。一是加快构建自然资源三维立体“一张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三维数据库建设,构建针对全国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域海岛等在内的三维时空数据库。二是推动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精准搜集。加强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应用以及实施传感器、图像解析等现代感知技术应用试点,提升对传统污染(如PM2.5、工业废水、固废、扬尘、水体COD)及新型污染(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微塑料)数据种类、频率、范围的精准监测,汇聚污染物收集、转移、利用、处置等各环节数据要素。三是强化生态环境数据融合创新。制定和完善生态环境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处理和分析等各个环节标准,实行“一数一源一标准”,实现数据资源清单化管理,促进公共数据与经济社会数据、城市规划数据、交通数据以及企业生产经营数据的融合。
第二,积极推动数据要素生态化,加快打造绿色智慧的新型数据中心。一是优化数据中心空间布局。优先在高纬度、温度低、湿度适中、新能源富集地区布局数据中心,提升对西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水平,促进算力运行过程中的节能、减排、降耗。二是提升新能源和绿电应用水平。引导新型数据中心向新能源发电侧建设,支持数据中心企业探索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燃气分布式供能等配套系统,实现新能源就地消纳。鼓励数据中心购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三是加强新型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应用。部署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管理软件和温度传感器,加强能耗监测平台、预制模块化手段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利用人工智能建模分析预测数据中心资源利用率,探索浸没式液冷技术、机械风冷式制冷、冷冻水制冷等绿色制冷技术应用。四是提升绿色运维管理水平。强化数据中心IT设备、供配电系统、清洁能源利用系统以及制冷和散热系统绿色设计。优化机房冷热气流布局,采用精确送风、热源快速冷却等措施降低能耗水平。建立能源资源信息化管控系统,加强能源资源消耗智能化调控,力争实现机械制冷与自然冷源高效协同。
(二)创新数字生态技术,推动数字技术生态化与生态技术数字化
第一,加快实现数字技术生态化,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能源领域专用数字技术创新。在生态修复领域,积极开发基于数字技术的土壤污染精准修复技术、水体生态修复技术、植被恢复技术和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技术等。在能源利用领域,强化能源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创新,加快形成面向新型电力系统的智能电网与数字技术群,促进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以及源网荷储一体化。创新功率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及先进监测控制技术,实现风、光、储协同优化、智能高效运行和智慧能源多能互补。推动共性技术突破,加快实现能源装备智能感知与智能终端技术、能源系统智能调控技术和能源系统网络安全技术等实现新突破。在污染物及碳监测领域,加强污染物及碳排放监测技术创新,创新光谱分析技术、激光雷达技术、碳同位素分析技术、光学传感技术、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技术等,实现对污染物及碳排放的科学精准监测。
第二,积极促进生态技术数字化,实现传统绿色低碳技术数字化升级,以数字技术应用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一方面,实现传统生态技术的数字化升级。梳理现有绿色低碳技术清单目录,对其应用领域及节能减排效果进行全面分析,识别企业在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和分析等方面的短板,引入先进的传感器、控制系统、数据分析工具等数字化设备和技术,实现生态技术相关数据和知识的计算机采样、量化和编码,推动数据分析、模型构建和仿真优化。另一方面,搭建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创新平台。利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内部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流程,通过大数据试错、重复实验等途径,促进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加快构建“产—学—研—金—介—用—政”一体化数字合作新机制,推动不同产业链供应链的企业、产学研主体之间、企业与金融机构、绿色技术交易供需主体以及不同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和知识整合,形成数字化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合作网络。搭建数字化绿色技术交易平台,高效智能匹配技术供需双方,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
(三)发展数字生态经济,实现数字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数字化
第一,加快推进数字经济生态化,强化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的生态化改造。一方面,推动数字产业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推动数字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将绿色生产理念贯穿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数字产业全过程。在设计阶段,优先采用可再生材料、低能耗芯片和高效能源管理系统。在生产过程中,选用节能环保的生产设备和工艺,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在循环利用阶段,科学把握产品收集、分类、检测、拆解、零部件再利用和废物处理等各个环节技术要求,确保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等硬件产品的回收过程安全、规范、高效。另一方面,加强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一是推动煤电升级,构建绿色智慧新型能源体系。发展和应用智能分散控制系统,促进燃煤机组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提升电网、油气、煤炭基础设施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整合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与智能技术,构建智能电网,实现能源高效利用与供需智能匹配,推进储能技术发展,加强能源互联网建设,实现多能互补,提高系统灵活性和可靠性,建设绿色智慧的新型能源体系。二是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针对钢铁、石化、建材等“两高”行业,发挥数智化在生产流程再造、能源资源效率提升、智能化控制与决策、降低设备故障及产品残损率等方面的作用,促进企业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降碳减排。三是构建绿色智慧供应链系统。加强数字技术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物流、包装、循环利用等供应链各环节的应用,实现生产全生命周期绿色管控[32]。四是构建数字化循环经济体系。搭建数字化循环经济平台,助力商品交换、共享和回收,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应用可嵌入射频识别标签(RFID)和传感器,实现组件再利用、回收和再制造,构筑“能源—产品—再生能源”的循环生产路径。五是利用数智技术推动绿色建筑全过程优化升级。提升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建筑信息模型(BIM)等技术手段在建筑设计、施工、运营和管理中的全过程应用,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优化建筑资源利用并及时调整施工计划,实时监测建筑能耗和环境质量等,优化建筑智能化管理,提高建筑能源利用效率。六是推动交通运输行业绿色智慧升级。加大智慧交通信号、智慧停车场、智能充电桩以及新能源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提升港口、机场、铁路货场、公路集散中心、物流园区等不同枢纽衔接水平,构建绿色智慧的多式联运体系。七是发展绿色智慧农业。搭建智慧农业云平台,推动农业生产资料高效利用、农业管理精准高效、农业信息资源共享、农业与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农产品安全可追溯,促进农业数字化生态化协同转型。
第二,深入推动生态经济数字化,以数字技术破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五难”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经济数字化的过程,就是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促进生态修复与环境综合整治、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私人产品交易和生态产业化、生态资源资本化与生态权益交易等[33],破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五难”问题[34]。一是破解供给难的问题。加强数字技术在生态修复、环境治理、扩大森林覆盖率、改善森林质量等领域的应用,保障生态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二是破解度量难的问题。利用数字技术全面掌握生态产品空间分布、数量特征、质量等级、权益归属、功能特点、保护与开发、市场价格情况等信息,改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价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开展多类别先进核算模型的数据核验、参数校准及科学方法遴选,实现对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数字化及精准量化。三是破解抵押难的问题。利用数字技术对各类海量生态产品数据进行精准搜集及价值科学核算,通过提高生态产品的透明度、可追溯性以及可预测性等方式,消除金融机构与生态产品供给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生态产品抵押风险,提高抵押效率,并基于此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生态金融与绿色信贷产品。四是破解交易难的问题。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包含各类生态产品类别、产地、质量、价格等信息的生态产品数据库,对生态产品信息开展智能化处理和分析,提高交易平台运营效率。搭建多层次生态产品数字化交易平台,提升全国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以及用能权市场交易效率,开展生态碳汇、森林覆盖率等生态权益指标交易,激活生态产品市场活力。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生态产品交易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增强平台的信任度。五是破解变现难的问题。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生态产品的信息可查询、质量可追溯、责任可追查,促进生态产品溢价和增值。利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方式拓展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渠道,满足消费者多层次需要。搭建生态交易数字交易平台,推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用能权、碳汇等的供需精准对接。利用数字技术摸清生态产品家底、科学核算生态价值,帮助确定合理的生态保护补偿标准,为纵向转移支付、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政府购买服务等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提供科学支撑。
(四)构建数字生态社会,促进生产关系适应性变革及培育数字低碳生活方式
第一,发展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下的新型生产关系,促进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与人生产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形式的适应性变革。一是积极解决数据要素与生态要素的产权问题,发展生态导向的共享经济。明确数据要素和生态要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对数据要素和生态要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登记和确认。二是发展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减少社会资源浪费,提高生产资料利用效率和环境绩效。引导劳动者合理竞争,实现生产关系网络化、数智化、绿色化、公平化。三是推动数据要素和生态要素直接参与市场化交易,促进数据及生态要素价值转化,提高市场激励性。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利用社交媒体、直播等新兴技术手段拓展绿色产品分配渠道,通过精确预测需求和优化库存管理减少产品积压损耗,基于消费者购买历史、偏好和行为大数据分析定制个性化促销策略,实现绿色产品精准分配。
第二,营造数字低碳生活方式新风尚,打造数字零碳社区与智慧低碳城市。一是培育数字低碳生活方式。利用数字平台传播绿色低碳知识和理念,提升全民数字环保素养。推广智能化家居系统和智能照明系统,减少能源消耗。推进远程办公、在线会议、公共出行、绿色消费的广泛应用,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建立数字碳账户平台,完善积分奖励制度。二是打造数字零碳社区。建设社区智能微电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社区内各类设备的互联互通,提高能源管理和使用效率。建立社区碳排放监测系统,利用数字化工具开展社区碳足迹评估,实时跟踪社区的碳排放情况。运用数字技术推动社区提升水资源、垃圾分类回收等智能化管理水平。三是构建智慧低碳城市。构建城市运行低碳转型监测体系,强化城市重点行业、产业、园区等碳排放监测与治理。建立城市智能电网和数字化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对电网及能源生产、传输、消费的智能分析和决策优化,提高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建立智能交通系统,优化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网约车等数字化出行服务。建立城市废弃物数字管理平台,推动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建立城市管理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推动城市的智能化、高效化和绿色化发展。
(五)弘扬数字生态文化,提升数字文化生态化与生态文化数字化水平
一方面,以生态化引领数字文化,促进数字文化健康有序发展。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渗透,出现了一系列非生态化的数字伦理问题,比如数字技术引发的生态失业问题、生态违法行为以及反生态文化传播等,还存在西方非生态主义不良思潮通过网络文化进行渗透的问题。从狭义生态视角着手,可通过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转型支持等措施缓解数字技术引发的生态失业问题,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加大执法力度抑制生态违法行为,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数字生态素养;从广义生态视角着手,可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网络监管机制、健全治理机制,推动构建有利于数字文化健康发展的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以数字化赋能生态文化,提升生态文化传播效能。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的有机构成,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对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起到了文化塑魂的作用。以数字技术提升生态文化传播效能,需加强宣传手段、方式方法创新应用,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生态文化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开发数字化生态教育资源,如在线课程、互动体验项目等,提高公众生态文化意识和参与度;通过数字平台促进国内外生态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增进国际理解和支持。
(六)强化数字生态治理,推动生态环境全过程数字化治理和数字碳中和
第一,推动生态环境全过程数字化治理,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一是搭建生态环境信息平台。搭建生态环境信息智慧管理平台,开展全地域、全方位、全要素动态感知及监测,集成空气质量、水质、土壤质量、生物多样性等各类生态环境数据,提升环境风险预测的及时性和精准性。加强各类数据创新融合,健全生态环境数据采集、融合、分类、共享、应用的标准规范体系,提升生态环境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水平。二是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加强部门数据合作,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和互通,促进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转移等跨区域联防联治、流域上下游协同治理以及赋能跨区域、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提升跨区域、跨流域、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解决数据“烟囱”和数据“孤岛”问题。三是促进生态环境治理决策智慧化、精准化、高效化。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模拟仿真等数字技术,提升生态环境监测感知能力、预警预报能力、形势研判能力、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监管执法能力,高效、精准解决生态环境治理的突出痛点与难点问题。四是提高生态环境社会监督效能。建立可视化环境监测平台,营造开放透明的信息传播环境,促进民众有效监督政府和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治理,提高治理成效。
第二,加强数字碳治理,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促进实现数字碳中和。一是构建碳排放动态核算和智能监测体系。强化碳排放主体碳排放量智能化、自动化核算,尽快摸清各类碳排放主体碳足迹家底。建立碳排放管理大数据平台,高效获取碳排放主体全品类、全过程能源利用数据。动态监测各区域、各城市、各行业、各园区、各微观主体的碳排放量,为“双碳”目标落实主体提供可监测、可管理、可展示的大数据可视化解决方案。二是提升数字化碳治理效能。加强碳排放数据深度挖掘和科学分析,揭示碳排放规律,为考核碳减排工作绩效、预测减排趋势、挖掘减排潜力以及科学制定减排规划提供支持。利用智能计算技术,选取碳减排关键环节,系统模拟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碳减排、电能替代碳减排、煤改电碳减排、新能源汽车碳减排等多种碳减排潜力场景,为制定针对性碳减排方案提供支持。三是促进碳配额公平分配,提升碳市场交易效率。通过引入先进的算法和模型,精确计算不同企业和地区碳排放量和应获得的配额数量,公平合理落实分解碳排放责任。利用数字技术和智能合约技术,实现碳配额买卖和转让实时进行,确保交易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四是构建数字化碳治理社会监督体系。发挥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网络宣传等渠道作用,普及碳治理知识,提高公众碳减排意识。完善数字化监督机制,支持公众对碳治理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提高碳治理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七)推动全球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加强全球数字生态要素国际合作。加强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合作,共同制定数据安全标准。建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环境数据的实时共享,协同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二是建立全球数字与绿色技术合作机制。建立全球性的数字技术合作机制,共同研发和推广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加快建立跨国界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转移体系,推动先进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转移。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加强在气候监测、预测预警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的合作和经验共享。三是以数字化赋能全球气候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全球统一的数字化气候治理平台,整合全球各地的气候数据、碳排放信息以及生物多样性数据,实现实时动态监测,通过高级算法和模型分析,促进数据的互通共享和协同治理。深化数字技术和绿色金融的融合,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准确的环境风险评估工具,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吸引更多资本投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加强跨国数字合作,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技术创新和经验共享。四是利用数字技术促进跨国企业构建全球绿色低碳供应链,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加强跨越多地域,甚至覆盖全球范围且结构高度分散的大型供应链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全面梳理、精确掌握各节点公司的碳排放情况,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精准识别并控制物流网络中的关键排放源,促进价值链可持续绿色转型。五是用数字思维做好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故事。利用社交媒体、在线论坛等平台,扩大宣传覆盖面,展示中国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和贡献,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利用数字平台向世界展示中国在“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方面的积极努力和卓越贡献,通过传播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蕴含的一系列观念、故事、情感模式和价值观,传递中国精神,展现大国担当。 [Reform]
参考文献
[1]张波,王媛祺,吴班,等.数字生态文明的内涵、总体框架和推进路径[J].环境保护,2023(21):34-38.
[2]刘国菊.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18):87-91.
[3]施志源,景池.以数字生态文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EB/OL].(2024-01-22)[2024-06-20]. https://theory.gmw.cn/2024-01/22/content_3710
2554.htm.
[4]BINDER J, WADE M. Digital sustainability for a better future[J].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2023, 22(1): 52-60.
[5]黄爱宝.数字生态文明的理论蕴涵、实践机理与建设价值[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2-22.
[6]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简史: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7]卢风.生态文明:文明的超越[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8]项久雨.世界变局中的文明形态变革及其未来图景[J].中国社会科学,2023(4):26-47.
[9]孙熙国,陈绍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世界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22(12):26-42.
[10]王立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23.
[11]韩庆祥.5Yzq8VzMq9SuHAH/BjlNEPKmIbdUyWm8goFJKQ7hIT8=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
[12]杨奎,刘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价值和世界性贡献[N].光明日报,2021-12-13(006).
[13]洪燕妮.中国式数字文明建构的演化逻辑、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22-29.
[14]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M].张体伟,孙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5]王元丰.能源革命促进新质生产力爆发[J].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4(S1):38-40.
[16]刘卓红,刘艺.数字文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J].学术研究,2023(10):8-15.
[17]庄贵阳.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范式变革[J].人民论坛,2023(14):98-103.
[18]潘家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19]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改革,2024(2):15-24.
[20]周文,许凌云.再论新质生产力:认识误区、形成条件与实现路径[J].改革,2024(3):26-37.
[21]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22]洪银兴.新质生产力及其培育和发展[J].经济学动态,2024(1):3-11.
[23]蔡跃洲,牛新星.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测算及结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21(11):4-30.
[24]FREEMAN C. A green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for the world economy(Chapter 10). The economics of hope: essays on technical chang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M].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1992.
[25]杨虎涛.数字经济:底层逻辑与现实变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26]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M].田方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7]PEREZ C. Structural change and assimil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J]. Futures, 1983, 15(5): 357-375.
[28]杨刚强,王海森,范恒山,等.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3(5):80-98.
[29]ANDRAE A S, EDLER T. On global electricity usag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rends to 2030[J]. Challenges, 2015, 6(1):117-157.
[30]ACEMOGLU 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2, 69(4): 781-809.
[31]李海舰,李真真.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机理与策略选择[J].改革,2023(12):12-27.
[32]CHEN J D, GAO M, MA K, et al. Different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n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0, 29(2): 481-492.
[33]孙博文.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瓶颈制约与策略选择[J].改革,2022(5):34-51.
[34]孙博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五难”问题及优化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23(4):87-97.
Triple Logic of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riented towa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un Bo-we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ncompasses both the narrow aim of achiev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uilding a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for a beautiful China, as well as the broade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pace for the emergence of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catalyz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dual transformations towards digitalization and ecologization of civilization, exploring the logic of generating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riented towa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his exploration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converST+/nm7IqxNy4CK+Wjw4xO9pm6jmo+FmgLlgjujxHiI=gen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digital civilization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as well as clarifies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creating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ivil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we can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connections of human civilizational form evolution under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ve forces, as well as the implications of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riented towa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Grounded in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factor innovation and the paradigm shifts in technology-economy through four industrial revolutions, we can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factors, technology,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governance, and global civilizational exchange.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quires actively elucidating the practice logic of cultivating digital ecological factors, innovating digital ecological technologies, developing digital ecological economies, constructing digital ecological societies, promoting digital ecological cultures, strengthening digit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building global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责任编辑:罗重谱)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课题“抢抓时代机遇与增强我国发展主动权研究”(特重立000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机制与路径研究”(7230323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项目(2024SYZH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研究”(22VRC082)。
作者简介:孙博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