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斯基的反叛实践与现代主义绘画的观看机制变革
2024-11-04张清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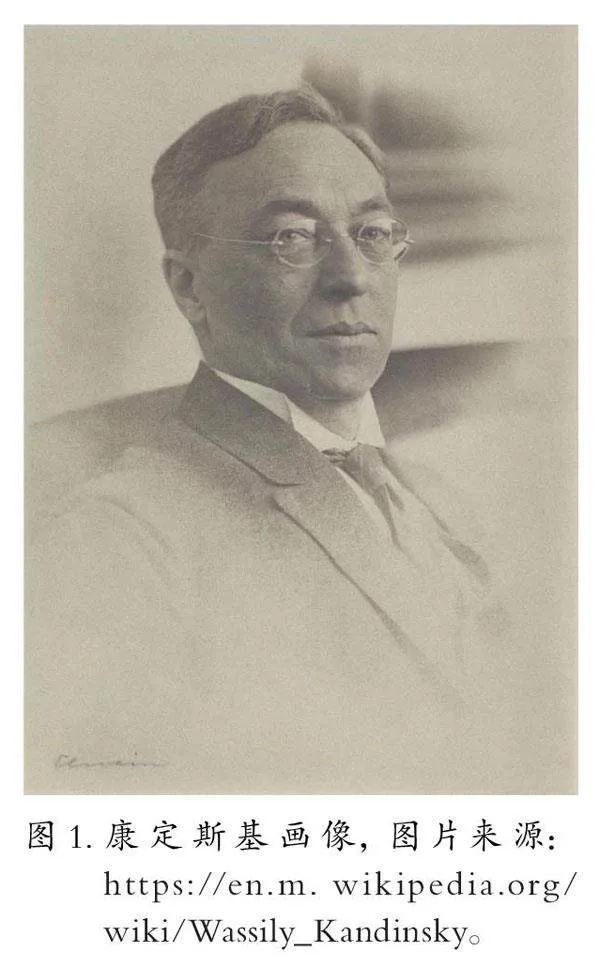




摘 要 本文以康定斯基及其艺术实践为例,试图探讨以反叛姿态出现的现代主义绘画在何种意义上代表了视觉政体的变革——在康定斯基这里,其文字与绘画所呈现的实证主义科学与神秘主义的杂糅,正是笛卡尔透视主义被科学实证主义所取代的过程中主体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想要真正理解现代主义绘画的产生,就需要回到观看机制的问题上来。
关键词 康定斯基;反叛;笛卡尔透视主义;视觉机制;现代主义
Abstract: Taking Kandinsky and his abstract ar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sm painting, which shows an intense rebellious attitude, and scopic regime of modernism. In Kandinsky’s case, the hybridization of positivist science and mysticism in Kandinsky’s texts and paintings was precisely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risis of the subje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placement of Cartesian perspective by scientific positivism. In this sense, it is required to investigate the concept of scopic regime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st painting.
Keywords: Kandinsky;rebel;Cartesian perspectivalism;Scopic Regime;Modernism
一、现代主义作为反叛者:批判对象的明晰性和自身立场的复杂性
(一)反叛者的复杂性
彼得·盖伊(Peter Gay)在《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From Baudelaire to Beckett and Beyond)中将现代主义指认为一种广泛涉及各个艺术门类的反叛思潮,并强调“现代主义者对敌人不亦乐乎地进行攻击恰恰让人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阵营很难说比他们所攻击的体制更为坚固”[1]。加埃坦·皮康也曾经指出,“沙龙落选者”(也即现代主义艺术家)“赢了战争却没有统一意见”[2]。关于现代主义艺术内部复杂性的描述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50年代,艺术史家阿诺尔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就已经指出了现代艺术的对立现象:“一边是代表形式严格主义的立体主义和构成主义,一边是代表打破形式的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3]而毕加索(Pablo Picasso)则表现为两种风格的杂糅。在众多璀璨的大师当中,康定斯基是艺术史家与理论家们反复提及的对象——彼得·盖伊甚至将康定斯基、蒙德里安与马列维奇并称为三位最伟大的现代主义画家,认为“他们成功地卸下了内心的伪装(这里借用波德莱尔的措辞),服从神秘的现实意识”。[4]
尽管1863年落选者沙龙以及沙龙上马奈(Édouard Manet)惊世骇俗的《草地上的野餐》(Le déjeuner sur l'herbe)常常被视为现代绘画的起点,但正如马克·吉梅内斯(Mark Gimenez)所指出的那样,为现代主义划分出精确的历史时间是困难的,尽管“现代艺术”在广泛的意义上指的是“从1860年到1960年这一百年中出现的艺术”[5],但“想在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之间划一道清晰的界限近乎是幻想”[6]。比起历史时期,现代主义画家的批判对象——以几何透视法为准则的架上绘画——显得更加清晰,在这个时期,艺术家纷纷想要摆脱稳定的、符合几何学法则的绘画创作法则。
(二)现代绘画与观看机制
艺术家对于几何透视法的自觉突破是对于学院及沙龙体制的反抗,但同时,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这种“叛逆尝试”也是对于透视技法本身的偏离。透视法不仅仅是一种绘画工具,更是一种观看的方式,对于技法的反抗本身同时意味着观看机制的动摇。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现代性的视觉政体》(The Scopic Regime of Modernity)一文中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视觉政体称为笛卡尔透视主义(Cartesian perspectivalism),并与欧洲北方“描绘的艺术”(the Art of Describing)和巴洛克艺术相区分[7]。在《低垂之眼》(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中,马丁·杰伊详细考察了笛卡尔在《屈光学》(La dioptrique)中的视觉观念,并指出这样一种基于几何透视法以及笛卡尔哲学的视觉机制可以追溯自古希腊以来的对于视觉的重视——自建基于视觉隐喻的古希腊形而上学起,西方哲学已经形成了“观看主体—观看对象”的“主体—客体”二分结构,笛卡尔透视主义只是这样一种古老脉络的内部演变。同时,在“观看主体”的概念下,存在着经验的(因此是不可靠的)“肉体之眼”和先验的(同时也是稳定的、永恒的)“心灵之眼”的区分。到了20世纪,对于笛卡尔透视主义之视觉政体的反叛则集中体现在(以法国思想家为代表的)理论家对于视觉的贬损之上。
有趣的是,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也对几何透视法以及笛卡尔《屈光学》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指出(在克拉里看来以暗箱为代表的)笛卡尔透视主义在19世纪发生了巨大转变(并被以立体视镜为代表的观看方式所取代),这种观看方式的断裂影响至今。
“面对19世纪前卫艺术家与作家的创新,以及同时存在的‘写实主义’与当时科学和流行文化界的实证主义……这两大类现象乃是同一社会表层里的交互重迭的组成元素,而视觉的现代化过程早在此前几十年, 就已经在这个社会表层上开始发展。……关键的系统转换早在1820年之前即已成形,而19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现代主义绘画,乃至于1839年以后的摄影发展,都可以看成此系统转换之后的后续征候或结果。”[8]
尽管克拉里与马丁·杰伊并没有在精确的历史分期上达成一致,但两人都将现代主义艺术所表现出的反叛姿态与视觉政体(或者说观看机制)的概念结合在了一起——也就是说,现代主义绘画是视觉政体变革下的一种征候,如果想要真正理解现代主义绘画的产生,就需要回到观看机制的问题上来。这也正是我们探寻康定斯基其艺术实践的切入点——康定斯基通过文字与绘画传达出的实证主义科学与神秘主义的杂糅,正是笛卡尔透视主义被科学实证主义所取代的过程中主体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康定斯基与作为“新科学”的实证主义艺术实践
(一)艺术作为科学
康定斯基(图1、图2)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写作者。在《艺术中的精神》(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与《点·线·面》(Point and Line to Plane)等著作中,他跳出了画家的身份,试图用语言建构抽象艺术的创作理念并讨论艺术的本质问题。尽管贡布里希(Ernst H. Gombrich)等批评家曾认为康定斯基更重视情感的表现[他曾经在《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借用康定斯基作品《静止》(At Rest)的例子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把康定斯基的构图放回原来的历史背景中”,就可以感受到画家通过“运用无结构的色彩和几何图形” 向我们传达的情感力量[9]],但事实上,康定斯基对于科学理性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如何与艺术之间的关联构成了其艺术创作的核心理念。
在上面提到的这两本书中,康定斯基将艺术学称为“新科学”,认为这种新科学可以被分为无目的的、出于科学探索需要的“纯科学”与出于艺术创造需要的“实用的科学”两种类型。为了获得关于新科学的一系列(脱离主体存在的客观)知识,我们有必要使用“‘实证’科学所运用的方法”[10]进行一系列关于新科学的实验。在他看来,艺术学的奠基者是反叛学院派的印象主义画家——后者尽管过分强调自然对于艺术创作的作用,但仍然为艺术学的科学探索铺平了道路。康定斯基指出,这门新科学在时间线索上应当分为“实证科学”与“哲学”两个阶段,艺术学在前期更接近于科学而在后期更接近于哲学——当下,关于这门新科学的知识建构才真正地开始起步,因此艺术学此时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完成“实证的”(或者说“分析的”)科学任务。
康定斯基对于科学的接受几乎是毫无保留的。在关于“精神金字塔”的系列描述中,他将科学家描述为没有疑虑的“不被任何问题所打倒”的“勇敢的守护者”,“他们跨过障碍,联手攻克新的难题,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理论。在他们眼里科学无所不能”[11]。尽管如此,艺术学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仍然存在着差别,康定斯基将之称为“内在驱动力”,也即“对客观原则的不可抑制的表达欲望”,这种表达欲望使得不同时代的艺术“以历史的、主观的方式,去表达永恒的、客观的元素” [12]。在他的“物质—精神”二分法体系中,现代科学不断揭示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艺术则负责扬起主体自由的风帆。因此,在康定斯基看来,塞尚和马蒂斯等诸多现代主义大师都是新科学的探索者,他们既是科学的,又是充满了精神性的内在趋力的——塞尚“以近乎数学般精确的抽象方法来调和颜色,却又让色彩充满表现力”,而马蒂斯则“试图通过数值比例的方式来构成画面”[13]。
(二)艺术方法论:拆分与综合
在康定斯基的实验中,“新科学”要求艺术家的心灵可以从视觉之所见中提取一种通过“遮蔽”和“截取”手段实现的“隐性结构”,这个“隐性结构”剥离了“对象非本质的部分,将对象简化为单纯的基本形,或截取最有特征的部分形体”[14]。也就是说,康定斯基的艺术实践基于对“就像世界可以被还原为物理法则那样,艺术也可以被还原为永恒稳定的艺术法则”这样一种观念的信奉。康定斯基借用了实证主义科学的自然实在论,即认为世界具有某种秩序因而可以被“还原”,也认为世界的秩序脱离于人的先验感知结构而存在——这也直接为其“艺术中的精神”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这种意义上,对于画面的“拆分”和被拆分各要素的“综合”是至关重要的。康定斯基试图使用构图来取代透视法,用点线面来取代具体的自然形状,这是一种想要使得“观看画面”变得和“聆听音乐”类似的尝试。康定斯基用画面类比语言,像语言学拆分最小单位那样,他将视觉画面“拆分”为组成画面的艺术元素,“点”“线”“面”由此产生。其中,点是“最简洁的形”;线是点移动的结果,是“第二元素”;面则是由线组成的第三元素。康定斯基对这三种元素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指出对这三种元素的系统研究将“产生一部元素的词典,再进一步将出现‘语法’,最终将达到作品构图的理论”[15]。(图3、图4)
“构图”是各艺术要素之间的综合,是把要素组织成为“层次分明的有机体”[16]的尝试。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在《艺术与视知觉》(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中同样尝试以类似实证主义的方式对视觉元素进行拆分,但他仅仅强调视觉之理性而没有给出计算关系——在阿恩海姆那里,“元素”可以被主体探知,但是不能够用来计算。与之相对的是,康定斯基进行了试图探索被他称为类似化学公式的“准确法则”,其中包含了点线面的内部组合,也包含了点线面与颜色的组合。在他看来,画面是可以被计算的也是必须被计算的,因为对于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是“通向作品内在律动的桥梁”。当然,这些公式作为视觉语言体系和艺术元素构成体系显然是不够好的,康定斯基也认为他是在“最初必然是什么都不精确的领域”[17]进行初步的实验工作,但这也正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科学知识积累的必然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康定斯基的理论体系回应了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在这种“结构主义艺术学”中,图像是可以被分割的,各个元素之间的可交换性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一幅艺术作品中,没有哪个元素是不可化约的和不可替换的,“点”与“点”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被康定斯基认为是新科学奠基者的印象主义者们由于提出“颜色之冷暖”而为“还原论”提供了可行性基础——尤其是在修拉的绘画中。这与克拉里对于实证主义观看机制代替笛卡尔透视主义观看机制的描述相一致。在克拉里那里,实证主义观看机制的形成正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结果,在其中,观看者在实证主义的自然态度下被拆解,被理解为两只眼睛,进而被理解为“光线穿过眼球的眼角膜、玻璃状液和晶状体传到后方视网膜的折射规律”[18]。康定斯基的艺术实践,也正是实证主义观看机制不断确立自身的结果。
三、绘画作为主体危机的表现形式
(一)自然态度下康定斯基的“活的艺术”
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在《视阈与绘画》(Vision and Painting: The Logic of the Gaze)中指出,随着实证主义在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中所占据的比例与日俱增,绘画实践被实证主义所隐含的、胡塞尔意义上的“自然态度”所主宰,这种自然态度意味着不假思索地认为我们所感受、所遭遇的世界脱离人的先验框架而独立存在。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绘画中,自然态度不仅体现在具象绘画中,体现为“没有人会质疑绘画记录的真实属于自然的范畴”[19],同样也体现为以康定斯基为代表的抽象绘画之中存在着的自然主义实在论(Realism)倾向。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中世纪的衰落》(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中曾经指出,中世纪具有某种“把具体事物归为抽象概念”的实在论倾向,这种倾向也往往使得抽象概念变得具体,比如当时的人们“把‘最后审判日’比作一次结账,就如同以前设在里尔的审计室大门上方写着的诗行里的一句:‘接着,和着鼓声,上帝会敞开他宏伟的总账房’”[20],却不会有人因此感到不妥。相似的是,康定斯基将精神比作“金字塔”(并在书中多次对其进行描述),同时认为张力有“内在的声音”,不同状态的声音甚至能组成三和弦。
如果说阿尔贝蒂(Leone Battista Alberti)建立的是“视觉之窗”,那么康定斯基则试图建立某种意义上的“心灵之窗”,透过画框,我们可以看到精神的可视化表达。康定斯基认为这些“声音”“张力”乃至和谐之规则存在于绘画内部,就像自然实在论认为规则只存在于事物内部而与主体感知无关那样。但同时,康定斯基却像现象学家们那样同样感受到了对象之中由于受到主体感知方式而产生的“精神性”特征。“艺术中的精神”概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得以被理解——具体地说,康定斯基将视觉对象拟人化,认为尽管“每一种力都能用数学术语给以表达”,但张力使得点线面成为“一种活的要素”,要素所构成的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生命”,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则是“两种活的生命之间的真正对应”,这种思路已经几乎奠定了康定斯基的神秘主义倾向:
“艺术家‘培育’这一生命,并知道如何合理地和‘喜悦地’使画面按正常的规律容纳正常的元素。这一得到认可的、最初的,但是活的机体如果处理得当,就会转变成一种新的、活的机体,这个机体不再是最初的,而是明显带有新生机体全部特点的机体。”[21]
(二)神秘主义作为科学实证主义体系中的“0”
当科学实证主义应允了一种完全外在于主体的有秩序的“自然”,主体危机就会随之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以理解康定斯基所面临的时代危机:在实证主义的统治下,包含艺术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变得可计算,艺术是否会在这个“被解剖”的过程中死亡?人的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康定斯基一方面对实证主义科学表现出几乎毫无反思的推崇,另一方面却对科学世界中的主体生存和创造自由感到焦虑。弗兰科尔(Viktor Frankl)将康定斯基的这种状态称为“存在的神经症”(existential neurosis)和“意义意志的挫折感”(frustration of the will-to-meaning)[22]。
而康定斯基的解决方案是通神学。在他看来,通神学作为“与实证主义理论相悖的方法”拥有前现代的起源和至今“较为翔实的阐述”,其象征着“一股强大的原动力,预示着压抑、沮丧的心灵将得到释放”[23],是解决精神问题(或者说主体危机)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康定斯基通过引入神秘主义来解决主体危机,在他的体系中,物理学和化学需要加上通神学才能组成整合的主体,点线面组成的艺术新科学也需要加上通神学才能够组成整合的艺术。和超现实主义不同,神秘主义在康定斯基这里不是孤立存在的“灵感来源”,而是用来解决实证主义之主体危机的手段和方法。
康定斯基并没有在科学实证主义与通神学两者之间的关系之间多做纠缠,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宗教与科学之间内在关联的讨论由来已久。卡斯滕·哈里斯(Karsten Harries)在《无限与视角》中指出,笛卡尔透视主义式的、稳定的先验主体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和系统的纽带,而现代科学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们对实在和真理的理解与这一理想之间存在着联系。取消先验主体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是取消现代科学根基的合法性”。[24]就像彼得·盖伊所指出的那样,生活在20世纪这样一个后宗教的时代的人们,无法在经历巨大时代动荡时寻求足够的、合法的宗教安慰而只能借助于各式前现代宗教,“在这种混乱的氛围中,一批以先锋派画家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将他们对传统思维习惯的不屑——如亵渎神灵的实证主义——表现为宗教形式。康定斯基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25]
柄谷行人在《作为隐喻的建筑》中提到,任何人造结构的都会产生类似的主体危机,而结构主义者“发现了如何将‘人类制造’物之上的‘剩余’导入结构之中的装置,那就是零”[26]。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音韵体系中的零音素是如此,数学中随处可见的零符号也是如此。康定斯基对于这两者的共同追求,让人们认识到神学问题在现代思想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科学不是宗教的反面,相反,宗教是科学实证主义结构的剩余物,科学实证主义通过引入宗教科学结构中的“0”完成了结构的闭合。因此,康定斯基通过宗教主义来解决主体危机的路径恰恰是传统的而非前卫的,是守旧的而非创新的,也并不会给出某种真正可能的解决途径。相反,康定斯基对于实证主义的推崇正意味着物理世界与艺术的合体,这正是一条走向主体消失的道路。实证主义的主体危机在这里仍然悬而未决。
四、不彻底的反叛
(一)两种视觉机制的内在一致性
当我们从表现方式上——也就是从再现到表现,从自然主义到风格主义,从具象到非具象的脉络上去探讨现代艺术时,我们看到的是现代艺术对于传统艺术的背离,艺术不再试图表现人眼所见,更放弃了再现技巧的不断提升,艺术摆脱了摄像机所带来的致命威胁从而获得了新生。这在与康定斯基相识的批评家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那里进一步表现为移情冲动和抽象冲动的对立——沃林格认为,艺术开始于抽象而不是模仿自然,抽象的冲动来自理性,是理性留下的痕迹,因此抽象绘画作为心灵的表达优于对于自然的模仿[27]。讨论抽象与移情,就是讨论风格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审美机制问题。但从观看机制的角度上看,康定斯基的艺术实践却展现出一种近乎正统的传承,这种传统是自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透视法实验以来的科学对于艺术实践的统治。也就是说,尽管在视觉上看,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图5、图6)与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的《大宫女》(La Grande Odalisque)等学院派艺术相比简直天差地别,但从视觉机制上看,康定斯基的反叛并不是彻底的,笛卡尔透视主义与实证主义观看方式两种观看机制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一致性——康定斯基的绘画理念延续了笛卡尔透视主义以来的对于资本主义理性的追求。文艺复兴时期正是“在理性主义方向深化了中世纪走向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发展趋势”[28],而与其说现代主义绘画作为反叛先锋对资产阶级理性发起攻击,倒不如“说它是其共谋者更能让人满意”[29]。
此外,康定斯基也延续了笛卡尔透视主义的去叙事化目标。尽管阿尔贝蒂在《论绘画》(On Painting)中描述了一种将绘画视作透过“窗户”的观看——在这种观看方式中,绘画不作为符号指向他物而是作为视觉的再现——但到了现代主义时期,学院派绘画的绘画主题变窄,图像“总是暗示着另一个图像,而另一个图像本身也是一种暗示”[30],观众也总是急于判定“画面各元素的对外关联”[31]。在这种意义上,康定斯基试图恢复绘画的可视性传统,绘画不再是插图,也不需要有文字对其进行说明,观众只需要站在画面前就可以感受到作品的所有意蕴。
(二)稳定的主体
在观看机制上,康定斯基将笛卡尔透视主义关于主客二分的观念与关于“身体之眼”与“心灵之眼”的区分也完整继承了下来。正如罗世平在《艺术中的精神》序言中所说,康定斯基在这本书中“采取身心二元论的态度,沿用通神学者的说法,认为精神(灵魂)是世界的本源,物质只是蒙在真实世界之上的一层面纱、人只能透过面纱才能看到闪光的精神,而现实中具备这种洞察力的人不多,只有通神学先知和真正的艺术家才具备这种能力”[32]。而康定斯基对于“物质主义”的鄙夷,将“精神”与“理智”对立[33]等观念也正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展开。
笛卡尔对于主体与客体的二分依赖于稳定的、永恒的,同时是去身体化的主体概念,而实证主义观看机制则基于身体在场的前提,这种对于身体的引入必然会带来感受的模糊与不确定性,这给康定斯基的理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出于这样的前提,康定斯基的颜色理论直接绕过了后天习得结构(如语言)对于色彩辨认的作用,并认为画面上的每一种颜色能够激起不同的个体以相同的感受:黄色和蓝色分别具有向前和向后的张力[34]、白色“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比黑色暖”[35],由于联想血液的缘故暖红让人兴奋而暗红令人恶心,白色让人感到静止而红色具有向心力,褐色则不蕴含情感力也不蕴含运动[36]。
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但康定斯基对于语言的忽视向世人展示了实证主义下稳定主体概念的非理性特征与意识形态底色,就像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将现代艺术指认为“有意味的形式”那样,这种观念预设了一种稳定的主体,其可以在没有受到训练的情况下阅读现代主义艺术。通过宣称“每一个人都能看得懂”,现代艺术区别于需要图像学知识才能够解读的传统绘画,完成了精英和大众趣味之间落差的填平,在20世纪初这样一种危机时代成为启蒙主义神话的一块补丁。
作者简介:张清莹,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与艺术本体论问题。
[1][美]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骆守怡、杜冬译,译林出版社,2017,第17页。
[2][法]加埃坦·皮康:《1863,现代绘画的诞生》,周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序言第16页。
[3][匈]阿诺尔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史》,黄燎宇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549页。
[4][美]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骆守怡、杜冬译,译林出版社,2017,第81页。
[5]王瑞芸:《西方当代艺术审美性十六讲》,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第22页。
[6][法]马克·吉梅内斯:《当代艺术之争》,王名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37页。
[7][法]布鲁诺·拉图尔等,唐宏峰主编《现代性的视觉政体:视觉现代性读本》,汪瑞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第79页。
[8] [美]乔纳森·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蔡佩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9页。
[9] [英]恩斯特·汉斯·约瑟夫·贡布里希著:《木马沉思录:艺术理论文集》,曾四凯、徐一维、杨思梁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第87页。
[10][俄]瓦西里·康定斯基:《点·线·面》,罗世平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第8、49页。
[11][俄]瓦西里·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余敏玲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第49—50页。
[12]同上书,第89页、22—23页。
[13]同上书,第56页。
[14][俄]瓦西里·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李政文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8页。
[15][俄]瓦西里·康定斯基:《点·线·面》,罗世平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第18页、39页、63页。
[16]同上书,第9页。
[17]同上书,第6页、9—10页。
[18][美] 马丁·杰伊:《低垂之眼》,孔锐才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第xxiii页。
[19][英]诺曼·布列逊:《视域与绘画:凝视的逻辑》,谷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第8页。
[20][美] 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刘军、舒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87—188页、134页。
[21][俄]瓦西里·康定斯基:《点·线·面》,罗世平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第70页、93页、96页。
[22][俄]瓦西里·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余敏玲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第25页。
[23]同上书,第51页。
[24][美]卡斯滕·哈里斯:《无限与视角》,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20,第20页。
[25][美]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骆守怡、杜冬译,译林出版社,2017,第83页。
[26][日]柄谷行人:《作为隐喻的建筑》,应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第35页。
[27][德]威廉·沃林格:《抽象与移情》,王才勇译,金城出版社,2019。
[28][匈]阿诺尔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史》,黄燎宇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159页。
[29][法]加埃坦·皮康:《1863,现代绘画的诞生》,周皓译,新知三联书店,2021,第54页。
[30]同上书,第47页。
[31][俄]瓦西里·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余敏玲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第112页。
[32][俄]瓦西里·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李政文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2—3页。
[33]在《艺术中的精神》中康定斯基提到,“我们的精神不久前刚从漫长的物质主义时期苏醒过来,这精神中深藏着绝望的萌芽——这是缺乏信心、非理智性和无目的性的后果。”(第8页)
[34][俄]瓦西里·康定斯基:《点·线·面》,罗世平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第44—45页。
[35]尽管康定斯基也探讨了民族、时代等因素的影响,但终究还是语焉不详地归结到个体的敏感程度之上。他说:“这一论断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高度敏感的人与其心灵是如此接近,其心灵自身是如此敏锐,以致任何味觉印象都能立刻传递到心灵再由心灵传递给其他感官,比如眼睛。”(《艺术中的精神》第70页)
[36][俄]瓦西里·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李政文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70页、96—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