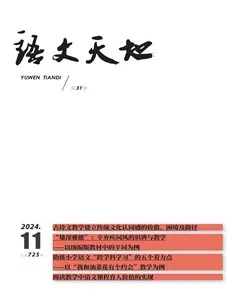多重蓄势下《猫》的“忏悔”意识之建构
2024-11-04朱文静
[摘要]《猫》中猫的命运与人的情感态度、人性的不同层次有关,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包括功利性、偏见、冷漠等。文中的猫置身于人组成的家庭之中,猫性是人性的一面镜子。《猫》在对三只猫的不同命运的呈现中进行了猫性、人性和审判的蓄势,最终导向作者在自我审判下的“忏悔”。通过分析猫运和人性,探讨了人类对猫的审判,揭示了人的偏见、弱肉强食和易怒等缺点,引导作者和读者进行自我审判和反思,彰显了人道主义精神。
[关键词]知识分子;猫运;人性;审判;忏悔;《猫》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A
《猫》是统编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第一篇文章,以“我家养了好几次猫,结局总是失踪或死亡”开篇,含蓄地将无数哀愁伤感寄予其中。文章所记叙的“我家”的三只猫的命运虽各有其不幸,但其不幸程度显然在逐渐加深,这是作者在行文时的有意蓄势。三只猫的不同命运跟人的不同情感态度有关,也因此折射出人性的不同层次,这也是作者在暴露人性时的有意蓄势。三只猫的死亡充斥着对人的批判乃至审判,文本最后,作者在“自此,我家永不养猫”的“忏悔”中将审判推向最高潮。这是蕴藏在文本内部的审判蓄势。
蓄势,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手法。“蓄势,究其实质,是文章意绪和读者心理势能的积聚,作者竭尽所能,百般腾挪,务使情志郁积成不可遏止之势,而全部能量指向文章结局,并在此集中释放出来,从而造成惊心骇目的效果。”[1]作为一种兴波技巧,它在《猫》一文中被充分运用到对第三只猫的命运的建构上,由此引发对人性愈发深入的揭露和最终作者的自我审判。
一、猫运的蓄势:越来越深地受制于人
文章的开篇就潜藏着矛盾的张力:“我家养了好几次猫,结局总是失踪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欢猫的,她常在课后回家时,逗着猫玩。”猫的不幸结局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三妹对猫的“最喜欢”显得失真,但既然三妹“常”“逗着猫玩”,证明这份“最喜欢”是确实的,也为第一只猫为我们带来“生命的新鲜与快乐”做了铺垫。
第一只猫是从隔壁要来的一只新生的猫,“花白的毛,很活泼,常如带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阳光里滚来滚去。”[2]显然,这只猫是漂亮的,讨人喜欢的,富有生命力的,这只猫一开始以“宠儿”的身份出现,跟主人一家形成了非常亲密愉快的互动,但不明原因的,猫不再漂亮,不再与人逗乐,不再富有生意。从三妹对它想方设法地逗乐都不奏效来看,这只猫应该是主动选择了“枯萎”,直到“有一天中午”它在自暴自弃中最终走向死亡。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只猫实则是一种摒弃了动物性的贪生怕死和取悦主人,而实践了一种为自己而死的具有高度自觉和灵性的动物。似乎可以这样说,第一只猫相较于后面两只猫命运更少不幸。
第二只猫是三妹怂恿着二妹从舅舅家里拿回来的,它“浑身黄色”“较第一只更有趣、更活泼。它在园中乱跑,又会爬树”,“有一次,居然捉到一只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间便不再听见讨厌的吱吱的声了”。显然,这第二只猫兼具审美功能、情感功能和实用功能。因为它的不怕生,结果三妹一语成谶,第二只猫果真在门外被人捉走,而且还是在邻居亲眼看到却不加制止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只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本身也具有很强生命力的猫。但是人性是有正反两面的,有人爱猫的活泼强大,就有人利用它的活泼强大来伤害它,而且还被冷漠的人漠视不管。活泼强大是它的天性,可以说,它成于此也毁于此,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性的贪婪与冷酷。这是一只死于天性和残酷人性的猫。
第三只猫是在“我家好久不养猫”后,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为了避免它在“我”家门口冻饿而死才“取来留养”的。这第三只猫与第二只猫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是招人嫌弃的,是多余的。于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成为它被攻击的导火索。妻子买回来一只很受宠的芙蓉鸟死了,大家都去找这只讨厌的猫,想给它以一顿惩戒。从一开始的不被人喜爱,到最后的被冤打,这第三只猫的命运似乎是那么顺理成章,它死于无法给人类提供价值,死于人类的自私与功利、盲目与偏见。
三只猫的命运都是不幸的,但不幸的程度因为人类的介入而愈发深重,第一只猫受限于主观的命运,第二只猫同时被主观和客观原因操纵的命运,都为第三只猫近乎完全为外力支配的命运进行了有力的蓄势。
二、人性的蓄势:愈发深重的人性弱点
在对这三只猫,尤其是后两只猫的命运的分析中,人的因素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三只猫都是置身于人类家庭中的,都扮演着“宠物”的角色,它们在家中的地位不同源于它们所能提供的价值不同。它们是被凝视被标价的客体,人才是它们服务的主体,能提供越多价值的“宠物”越被人喜爱,反之亦然。所以,猫的际遇跟它所能取悦人的程度密切相关。更进一步的,在猫运的蓄势中也潜藏着人性的蓄势,随着猫运不幸程度的加深,在文本中暴露出来的人性问题也愈发深重。
第一只猫最开始凭借自己的活泼漂亮、富有生气,给主人带来了“生命的新鲜和快乐”,人们对它的喜爱是出于审美和情感上的必然。当它突然变得“毫无生意”“懒惰”和“郁闷”时,“我们都很替它忧郁”是一种喜爱的惯性使然,三妹把一个铜铃系在它颈下,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其自身的关爱欲和玩乐欲。敏感的主人肯定会意识到,这种突然的变化应该是源于猫自身的,是人力无法左右的,更人道一点的主人肯定会对此选择尊重。总之,这份爱并不是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的爱,而带有人的俯视和取舍。小猫死后,隔了几天后从舅舅家里要回一只更让人喜爱的小猫。显然,第一只猫于“我”们是可以被替代的,只是一个玩伴而已。从这只猫生前死后的际遇来看,它始终是这个家庭的局外者,它甚至在用某种猫性来对抗着人性。人在这只猫面前显得旁观和虚伪。
第二只猫可以说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优越的出身(来自舅舅家)、外形漂亮且稀罕、有趣活泼能干。这些优势使它成为这三只猫中最受宠的猫。这只猫对这家人的用处很大。于是,人们都为它的亡失感到“不高兴”“怅然”“愤恨”或是“诅咒”,并决定“好久不养猫”。这个家庭对第二只猫的喜爱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对猫的保护的欠缺也是很明显的,而且,在猫被捉走后,“我们”仅仅只是产生了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并没有继续寻找,证明了这第二只猫只是“我们所爱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所爱的家庭成员。看到猫被路人捉走却不加以阻止的隔壁周家更能够代表一般人对猫的态度:它只是一个动物,没有人会真正在乎它。对自私自大冷酷的人性的批判在此更进一步。
第三只猫有着看似截然相反实则殊途同归的命运,它是不受待见且“不被看见”的,因为它不具备任何出身、外形、性情和能力上的优势,自然的,“大家都不喜欢它”。按照常情,对于真正爱猫的人家来说,第三只猫的出现应该能够极大地抚慰前两次丧猫之痛,可事实是,因为这只猫不够好,爱猫的人也不够爱。站在这样被嫌弃的位置上,受宠的芙蓉鸟的出现自然就能把它推向“替罪羊”的命运。这个命运是由人一步步推进的,它对鸟的凝望被视为蓄谋吃鸟,鸟死后它不容分说地被锁定为“犯罪凶手”,看到它“嘴里好像还在吃着什么”就直接把它定罪并“惩戒”它。这好像就应该是它“应得”的命运,像极了每一个在强权里无法出头的弱者。人在做判断时武断盲目,傲慢地化身“道德使者”惩戒“不道德”之事,人性的劣根性于前面的层层蓄势后在此暴露无遗zPGXLMMfvwXioqbW07zsIkoVjrR6415xrdF84dNlfHI=。
直到第四只“嘴里衔着一只黄鸟”的猫的出现,“我开始觉得我是错了!”“我心里十分的难过,真的,我的良心受伤了。”“我”为自己无法补救伤害这只“不能说话”的动物的过失而痛心疾首。“我”对于它两个月后的“忽然”死亡,“比以前的两只猫的亡失,更难过得多。”“自此,我家永不养猫。”在这里,人性得以反转,前面层层蓄势的人性弱点在这份“忏悔”中升华成了知识分子出于良知的强烈自省。这份自省是可贵的。
三、审判的蓄势:最终导向“忏悔”的自省
综上所述,猫运折射出人性,猫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猫的不幸跟人有直接关系。在思考猫的命运时,人类自然无法免责。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中,可以发现,伴随着猫运的蓄势和人性的蓄势,对人的审判也在层层蓄势。
第一只小猫的死更多地源于自身,并不涉及对人的审判。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对人的审判是面向偷猫人的,在得知小猫“被一个过路的人捉走了”时,审判的是偷猫人的自私冷酷贪婪。第二次审判出自三妹之口:“他们看见了,为什么不出来阻止?他们明晓得它是我家的!”审判的是隔壁周家人的冷漠。来自熟人的冷漠比来自恶人的恶意往往更加令人难以接受,审判的程度确实在蓄势。第三次审判是对张妈:“不是这猫咬死的还有谁?它常常对鸟笼望着,我早就叫张妈要小心了。张妈!你为什么不小心?”而“张妈默默无言,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3],这场当事人无法进行辩白的审判与第四场对猫的审判如出一辙,且为后者蓄了势。和张妈的默默无言一样,猫也是“不能说话辩诉的”,不过,它迎来的并不仅仅是指责而是冤打。综合全文来看,第三场审判表面是面向张妈,实则是在审判妻子作为雇主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武断。而第四场审判表面是面向第三只猫,实则是在审判人性中的主观偏见、欺凌弱小和由愤怒体现的无能。
第五场审判的是第四只猫,也就是那只“嘴里衔着一只黄鸟”的黑猫,李妈的那句“猫,猫!又来吃鸟了”代表所有人为第三只猫洗刷了冤屈。引用李欢欢的论断:“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只猫是一只黑猫。黑,有什么样的价值呢?如果注意比较,就知道第三只猫是一只花白的猫,人们常说‘黑白分明’。正是因为黑白颜色上的差异,使得作者以及读者内心变得分明了。于是作者一瞬间就认定自己错了。”[4]对第四只猫的审判既有充分的证据也有惯常逻辑的加持。这一审判直接推翻了第三场和第四场审判的定罪,使这两场审判有了更真实的面向。更重要的是这一场审判将矛头最终对准了“我”,是“我”基于偏见主观臆断将第三只猫冤打,而且这只猫突然死去使“我永无改正我的过失的机会了”,这是一种沉痛的忏悔,是在多次审判后最终导向自我审判的知识分子的忏悔。这一“忏悔”意识在三只猫的命运蓄势和围绕着猫的一群人的人性蓄势下最终得以成形,“我”忏悔的是自己的倚强凌弱、不经调查就胡乱定罪的愚蠢盲目。从这一“忏悔”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可贵的自省意识浮出水面,文章的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的内核愈发凸显。
[参 考 文 献]
[1]杨春锦.联类对比蓄势摭议[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11).
[2]王清.温情中的哀愁:人性的“亡失”——郑振铎《猫》的“非构思”解读[J].中学语文,2020(04).
[3]杨枫.《猫》:自以为良善的人为何作恶[J].读写月报,2021(02).
[4]李欢欢.第四只猫的隐喻——对郑振铎《猫》一文的重新解读[J].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2022(11).
[作者简介]朱文静(1985),女,安徽省灵璧县第一初级中学,一级教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