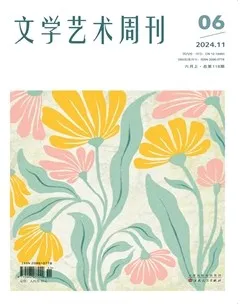彼真此假俱迷人:虚拟主播的情感传播
2024-10-27徐天悦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如 5G 网络的普 及、AI(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等,虚拟主播 行业正繁荣发展。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全球虚拟主播用户数量已超过 500 万人, 市场规模超过 500 亿美元。
虚拟主播其实是一种虚拟偶像,它借助 先进的动作和表情捕捉技术,使得屏幕背后的 真人能够实时操控一个虚拟形象。这种技术使 得虚拟主播能够以直播或其他互动形式,与粉 丝们进行实时交流和互动。虚拟主播外在的虚 拟形象被称为“皮套”,“皮下”负责操纵的 真人被称为“中之人”。中之人用自己的声 音、表情和动作与粉丝互动,粉丝可以购买 SC (superchat,醒目留言)与主播进行一对一式 互动,实现情感交流。
越过皮套去了解中之人本人的行为被称作 “开盒”,是虚拟主播粉丝圈中公认的禁忌, 但粉丝们仍乐此不疲。在这里,公认的禁忌和 广泛存在的“打破禁忌”形成了矛盾,虚拟主 播的粉丝们追求的究竟是虚假还是真实?介于 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虚拟主播又如何实现情感传播,引得众多粉丝为其付费?本文将着重解决 这些问题。
一、虚拟主播:虚拟与真实的交织
世界上第一位虚拟主播“绊爱”诞生于日 本,制作人松田受到视频网站(YouTube)主播 使用动漫形象出镜的启发,创造出了能够通过 中之人与粉丝实时沟通的虚拟主播。在最初的 计划里,中之人只是虚拟主播声音和动作的提 供者,AI 才是虚拟主播的中心。但在实践中, “绊爱”的形象在中之人的出色演绎下日渐丰 满,最终粉丝的关注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了虚拟 主播皮套背后的中之人身上。
因为事与愿违,“绊爱”的负责人提出由 四位中之人共同出演“绊爱”,以削弱中之人 的存在感,提高虚拟主播的主体性,但这一提 议遭到粉丝的强烈抗议。在此冲击下, “绊爱” 最终选择了隐退。可以说,虚拟主播自诞生起 就充满了虚拟与真实交织的矛盾。
如今,虚拟主播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粉丝
来到直播间,他们在同一空间中进行互动仪 式,增强集体情感。正如凯尔纳所言:“随着 现代化步伐的迅猛加速,人类对情感的感知似 乎逐渐淡化;如今,我们似乎被一座由现代化 构建的城墙所围困,在这座围城内,人类情感 的迷失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当 下社会,随着人们交往空间不断被压缩,公众 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于是他们越来越依赖 于市场上的“商品”来满足内心的情感需求。
二、虚拟主播的三层次情感传播
虚拟主播与其粉丝之间形成了一种虚拟社 会关系:虚拟主播并不认识粉丝个体,但粉丝 将虚拟主播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人并投射情感。 本文主要研究虚拟主播如何在直播中进行情感 传播,满足粉丝的情感需求,为其提供情感价 值。
美 国 学 者 唐 纳 德 ·A. 诺 曼(Donald A.Norman)在其著作《情感化设计》中阐述了 情感和情绪的重要性,他认为日常的产品设计 和传播应当根植于人类的情感,强调情感要素 在产品创新中的不可或缺性。诺曼还提出了情 感三层次理论,进一步揭示了情感的多层次和 复杂性。
( 一 )形象设计:表层的情感体验
情感三层次理论中的本能层次聚焦于产品 外观给用户带来的感官冲击,特别是通过视觉 和听觉的强烈刺激来触动用户的情感。这种情 感体验直接源于用户的即时感知,用户能够直 观地感受到产品所传递的情感价值。
虚拟主播利用风格化的外观达成对粉丝视 觉上的吸引,并且通过穿戴设备,中之人的肢 体语言和神态表情也都得以呈现,虚拟主播此 时更贴近于拥有完美外表的真人;同时,虚拟 主播凭借声音优势,直播内容常常与 ASMR(自
发性知觉经络反应)、模拟约会等相关,给粉 丝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
(二)直播互动:深层的情感共振
情感三层次理论中的行为层次着重于产品 的功能性表现,即产品如何有效地满足用户的 具体需求,进而为用户带来特定的情感体验。 就虚拟主播而言,本文认为其为粉丝提供的情 感体验可以划分为两类:模拟约会和聊天。
模拟约会是虚拟主播直播中的常见环节, 在模拟约会中,主播是你忠诚的恋人,拥有完 美的外表和性格。对于从小接触互联网的千禧 一代,一年见一面的亲戚朋友未必比互联网上 朝夕相伴的虚拟主播更加“真实”。粉丝对虚 拟主播投射的爱恋可以说与现实中的情感无异, 甚至更为强大。
除此之外,虚拟主播提供的聊天功能也不 容忽视。当粉丝将诸如亲人去世、父母离异、 找不到工作这样现实中的困扰,以 SC 的形式分 享给虚拟主播,主播会给予情绪上的支持,并 提出有效的建议以帮助对方走出困境。在这个 过程中,虚拟主播的身份虽然是虚拟的,但提 供的情感价值却是真实的。
(三)粉丝参与:用虚拟构筑现实
反思层是情感三层次理论中的最顶层,它 源于本能层和行为层的触动,融合了用户的文 化背景、个人意识、理解力等多重因素,形成 了一种深邃且复杂的情感体验。在互联网时代, 虚拟主播与粉丝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传教式的 输出,粉丝也能参与虚拟主播形象的网络传播。
参与式文化刻画了新媒体环境下的一种互 动图景,其中,广大网民作为核心参与者,基 于共享的身份认知,自发且积极地投身于媒介 内容的共创、信息的广泛传播以及网络互动的 深度构建之中,共同塑造着丰富多样的媒介生 态。
粉丝上传自己翻译的外国主播的直播片段 被称为“切片”,更多的粉丝通过同人文、同 人图、二创视频等形式对虚拟主播创造的内容 进行再生产。他们利用不同的平台,对原始内 容进行编辑、二次创作,并赋予其个人化的意 义和解读。粉丝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也收 获了粉丝社群的接纳与认可。
三、虚拟还是真实:年青一代的情感需求
在虚拟主播的“圈子”之中有这样一条不 成文的规定:探寻那些尚未公开中之人身份的 虚拟主播的真实身份信息,被普遍视为一种极 其不礼貌的行为。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中之人 的隐私和安全,避免被极端粉丝跟踪求爱,另 一方面也是粉丝为了维护自己内心的幻想主动 为之。
中国红极一时的虚拟偶像女团 A-Soul 曾宣 布要在线下举办握手会,安排中之人与粉丝一 对一互动,这一安排遭到粉丝的强烈反对,甚 至发表声明联合抵制本次活动。当官方希望带 给粉丝更多“真实”的体验,粉丝们却甘愿置 身于“虚拟”的世界之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 喜欢的只是幻象。
那么,虚拟主播的卖点究竟是皮套还是中 之人?粉丝所追求的究竟是虚拟还是真实?实 际上,这两者都同样重要。象征虚拟的皮套却 由真实的像素点组成,象征真实的中之人反而 令人难以揣摩。虚拟主播的粉丝游走在虚拟和 真实之间,以虚拟主播为蓝本,附加自己所喜 爱的元素,最终拼搭出属于自己的、高度理想 化的虚拟偶像。
对虚拟的对象投射感情也许会被“圈外
人”视为异端,质疑为什么要为了幻象付出爱 与金钱。但在这层虚构的面纱之下,粉丝们得 以寄托对理想伴侣的憧憬,并通过二次创作将 其打磨至最为理想化的完美状态。他们与想象 中的客体搭建亲密关系,由此激发的情感与现 实中的情感无异。粉丝在运用他们的拼搭权利, 依照个人喜好“重塑”虚拟主播的过程中,能 够更深刻地感受到自身的渴望与忧虑,从而更 加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这恰恰印证了王玉玊 提出的“二次元存在主义”: “我做出抉择, 我深信不疑,我付诸实践,我亲手塑造自己的 价值与信仰体系,同时,我勇于担当这一过程 中可能带来的所有结果,无怨无悔。”
作为第一代“数字居民”,00 后们成长在 一个难以分辨真实与虚拟的时代。网络时代的 媒介不再致力于创造虚拟或者模仿现实,它们 生成了某种“超现实”,并对现实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年青一代不再试图辨析真假,因为没 有什么绝对可信,也没有什么绝对虚假。
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存在主义,并在 虚拟的世界中践行存在主义。他们并非沉溺于 电子的乌托邦,而是对这个世界的宏大叙事感 到无能为力,所以选择超越虚拟和现实的二分 论,去寻找再造现实的可能性。虚拟主播的粉 丝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值得去爱的形象,这个形 象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但“我”选择相 信是真的,因为“我”从对这个形象的爱中感 受到了自己的存在。
[ 作者简介 ] 徐天悦,女,汉族,江苏南京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媒介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