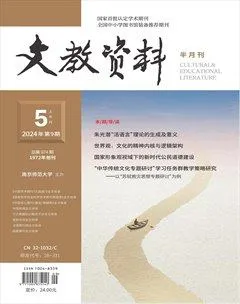李达的法理学思想研究
2024-10-23单芳
摘 要:始源于救亡图存的历史感召,因应我国政法制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情势,李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依据、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研究方法、坚持以实践性和本土性为研究导向,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思想。李达的法理学思想研究,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基本要义,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及此前的各法学流派,深入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实践,从而率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研究进路,丰富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李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李达并非法科专业出身,机缘巧合之下进入大学法科任教并撰写相关专著,尽管如此,与其同时代及此前国内的相关研究相比,李达的法理学思想研究可谓是独树一帜,开时代之先河。我们通过一一剖析李达法理学思想研究的缘起、内容、特色与价值,既能够从理性层面深化对李达法理学思想史研究的认识,又可以从中窥见李达法理学思想与后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法学之间的因循关系。
一、李达法理学思想研究的缘起
李达身处内忧外患频仍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早年受“教育救国”思想的感召,从湖南家乡北上求学,力图通过发展教育救国,然而面对政治制度腐朽、封建礼教观念仍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现实,新兴教育的发展步履维艰,冀望教育救国的计划难以避免失败结局。李达于1918年弃理从文,不仅阅读和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在国内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1920年回国后,李达积极投身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工作。此后,尽管面临动荡不安的时局与漂泊不定的际遇,李达始终未曾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采取一切可能的形式和途径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思想研究正是此背景下的重要成果之一。
李达在主编《共产党》月刊时,就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我国的现实问题,关注劳动者立法、妇女权益保障等社会热点难点议题。《劳动立法运动》等文章的编撰标志着李达已经有意识触及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法律问题。1928年,李达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法理学家穗积陈重的《法理学大纲》一书。穗积陈重在该书中依次阐述了法理学的意义,西方法理学的各主要流派,法律的本质、形式、内容与本位等法理学基本内容。翻译该书为李达认识与思考法理学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为李达此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构法理学体系积累了一定的知识论基础。同一时期李达还撰写了《社会学大纲》和《现代社会学》等相关著作,初步阐述了法律是受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法律的阶级立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律的不同特征等若干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基本论题。
1947年,李达几经辗转赴湖南大学任教,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检查和监视并禁止其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此背景下李达转而投身法理学思想研究,冀望于通过溯源法理学背后的哲理理据和寻求马克思主义对法理学的指导意义与价值,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大学任教期间,李达克服资料匮乏、身体多病、生活窘困等诸多困难,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创作完成了《法理学大纲》,这标志着李达法理学思想研究已初具体系,对在我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李达法理学思想研究的内容
(一)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基本要义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思想的阐释集中体现在《法理学大纲》一书中。该书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基本要义的阐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理论根据是“科学的世界观”。李达认为法理学本身是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因而必然依赖某种特定哲学立场作为立论根据,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与其他各派法理学的本质区别在于以“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根据;法理学接受“科学的世界观”的总指导,最终形成了科学的法律观;科学的法律观“把法律制度当作建立于经济构造之上的上层建筑去理解;阐明法制这东西,是随着经济构造之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而取得历史上所规定的特殊形态,阐明其特殊的发展法则,使法律的理论从神秘的玄学的见解中解放出来”[1]。
其二,李达在《法理学大纲》中阐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与范围。李达认为“法律的发展法则才是新法理学真正的研究对象”[2];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任务首先应当是系统阐述法律发展的普遍原则,并以这种普遍真理去认识和指导世界各国的法律发展,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而言,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以法理学普遍真理来指引中国的法律发展实践;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判例法等正式法源和法理学说、法律思想史等非正式法源的法学内部范围;主要考察法律与国家、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社会现象的复杂关联性的法学外部范围。
其三,李达在《法理学大纲》一书中阐述了法律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法律的属性等法理学的基本范畴。李达指出,法律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法律关系的表现形态;法律形式“即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在国家规范中所采取的形式。因而法律本身,即是摄取经济关系的内容而具有成文或不成文形式的国家规范”[3]。法律的属性在李达看来,是阶级关系决定的并由法律特有机能表达出来的、与其他社会现象有所区别的外在表现。
(二)尖锐批判资本主义及此前的各法学流派
李达以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范式为武器,对西方自古希腊到20世纪西方各法学流派思想一一进行阐述与批判。如对于西方近代自然法思想,李达将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法理论定性为“拥护君权”,并认为其带有“反动”本质;对于提倡民权的洛克(John Locke)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n)的思想,李达肯定了其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特质,不过与此同时也指出他们理论中民权主体的有限性,无财产的人民难以经此转化为国家主权保障的公民,进而无财产便意味着无自由。李达通过这种批判,不仅揭露出了非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共同缺陷,而且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李达以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科学法律观为依据,对各派法理学给予总批判,明确指出它们存在着如下四方面共同缺陷:其一,以观念论为哲学基础,秉持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将主观思维作为考察法律的依据”[4];其二,普遍缺失历史主义视角,以主观想象替代客观历史发展,无法展现国家与法律起源的真实过程;其三,将法律孤立于其他社会现象、隔绝于现实社会生活之外,故意掩盖法律的阶级立场,对法律与国家、经济的关系以简单化处理;其四,在公平正义的目标诉求背后隐藏着实质上的不公平与非正义,法律始终难以克服少数统治者与大多数人民之间的利益对立,无法达致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
(三)深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的宪法实践
李达法理学思想研究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其不局限于纯理论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来论证中国社会主义宪法实践的正当性和解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的难题。
其一,李达的法理学思想全面阐述了宪法的产生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宪法的特点。李达认为苏维埃的宪法实践,以无产阶级民主专政为基础,在吸取宪法制度独特价值功用的同时,克服了资产阶级宪法的固有缺陷,形成社会主义宪法的全新特征:确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稳固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与基本柱石,确认民族、种族等集体之间的平等和一切公民间的个人平等,规定公民自由和权利实现所需的物质条件。
其二,李达的法理学思想系统论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李达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概括总结了自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这段中国人民英勇斗争以争取独立解放和艰难探索国家宪法制度的历史经验,是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李达由此在《热烈参加宪法草案的讨论》中指出,“全国人民多年来的共同愿望是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这个共同愿望已经在宪法草案中反映出来了”[5]。
其三,李达的法理学思想深刻揭示了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人民民主本质。李达指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人民民主本质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表现。首先是公民权利的平等性、普遍性与真实性。平等性意指权利面前人人平等,不因主体的特殊身份而予以差别对待;普遍性包括权利主体和内容的广泛性;真实性意味着公民权利有着坚实的物质条件作为实现保证。其次是公民权利义务的统一性,既包括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履行是相互对应的,又包括权利义务背后的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高度统一。
三、李达法理学思想研究的特色与价值
(一)李达法理学思想研究的特色
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依据
李达法理学思想研究的突出特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的哲学依据。首先,作为我国最早一批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李达在不同学术研究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该学科内在发展规律相结合。以此而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依据,不仅是李达法理学思想研究,而且是李达整个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最大特色。其次,李达在法理学思想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哲学依据详细阐述了从科学的世界观、社会观到法律观的理论逻辑,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范围和基本范畴,并以此范式为据对西欧自古即今的各法学流派展开批判,从而“初步构筑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理论框架”[6]。
2. 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研究方法
李达法理学思想研究在方法进路方面的特色,主要体现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法理学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唯物辩证法坚持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反对孤立片面地看待事物。李达不仅正确认识到法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而且全面揭示了法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其次,唯物辩证法坚持辩证地看问题,认为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是优点与缺点的对立统一。李达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西方各法学流派的同时,也客观认识到各法学流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再次,李达应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法律的本质与现象、法律的内容与形式等之间的关系,认为应当在深入考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现象的基础上,揭示其阶级性的法律本质;法律的形式受法律内容的制约,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内容。
3. 坚持以实践性和本土性为研究导向
李达的法理学思想研究重视实践性和本土性原则,他也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先驱。其一,李达法理学思想研究以中国社会现实为立足点。在《法理学大纲》一书中,李达认为“民国”时期法学思想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律及对法律的注释都是舶来品,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高度脱节,法理学研究只有反映并指导中国社会现实才能获得生机,进而推动法律改造与社会进步。其二,法理学思想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法理学大纲》表面看来是一本纯理论的著作,但其实是通过探究马克思主义在法理学领域的指导价值以进一步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批判武器深入反思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以及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当局黑暗统治的社会现实本质。
(二)李达法理学思想研究的价值
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研究进路
李达之前的法理学思想研究,存在过分强调法律移植、盲目效仿西方法学理论思维范式等问题。李达认为,法理学是研究法律发展普遍法则的学问,担负着探求法律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的任务。在他看来,中国法律体系的革新不能照搬西方已有发展模式的“捷径”,而应立足当时我国社会发展实际,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与中国社会基础和前途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新型法律体系的形成离不开新法理学基础理论的支撑,李达通过旗帜鲜明地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研究法律现象的指导原则,超越了此前传统的法理学研究范式,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学理论。李龙认为,李达法理学思想研究“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改革开放以来推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起了极为重要的奠基作用”[7]。
2. 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
李达的法理学思想研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特别是宪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首先,李达紧密结合中国实际,阐明了宪法的阶级本质,无情地揭穿和批判了旧中国宪法的虚伪,加深了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民主专政”的认识,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其次,李达认为公民权利不是天赋的,权利和自由都是通过斗争得来的,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实现国家独立就是最好的例证。李达早年较为关注妇女、劳工等少数群体的权利保障,之后的相关研究中更为重视民族与国家的权利问题,提出应正视民族自决权,追求包括关税在内的国家法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
四、结语
李达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法理学研究的哲学理据,“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奠基人”[8]。李达的法理学思想研究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是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助推器,对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3]汪信砚.李达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3,264.
[2]程梦婧.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开创[J].法学研究,2020(5):55-71.
[4]朱晓璇,汪信砚.李达法哲学思想探析[J].法学评论,2019(5):1-6.
[5]本书编辑组.李达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25.
[6]方宁.作为法学家的李达——李达的法学思想及其价值[J].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10(10):241-251.
[7]李龙.中国法理学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261.
[8]蒋海松,张浪.李达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肇启——基于湖南大学讲义《法理学大纲》的考察[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2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