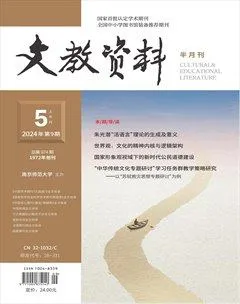贝特朗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
2024-10-23张云
摘 要: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马丁·盖尔归来》中用了不少笔墨对一名女性人物——贝特朗的境遇、性格、选择与行为以及其身处的社会环境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在戴维斯的叙述中,一个生活在16世纪法国乡村的女性逐渐觉醒女性权利意识,一个勇于挑战当时的父权制度和森严的性别秩序,努力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关键词:贝特朗;《马丁·盖尔归来》;女性权利意识
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所著的《马丁·盖尔归来》叙述了一个发生在16世纪法国乡村阿尔蒂加的冒名顶替的故事。在16世纪的法国乡村阿尔蒂加,一个富裕的农民马丁·盖尔离开了家乡,之后数年杳无音信。八年后,他却突然出现在村子里,并因为与叔父皮埃尔的财产纠纷而被控告。在假马丁,即阿诺·迪蒂尔即将凭借自己出众的记忆力与口才骗过法官时,真正的马丁出现了,最终假马丁被判处死刑。
虽然这部作品主要围绕男性角色真假马丁的故事展开,但也有不少女性角色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对一众女性角色的刻画与描写中,戴维斯花了相当多的笔墨来描写马丁的妻子贝特朗。作为一名生活在16世纪法国乡村的女性,贝特朗逐渐突破了当时社会实行的严苛的父权制度,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觉醒了她的女性权利意识。
一、贝特朗生活的社会环境
在展开对贝特朗这个人物的详细叙述前,戴维斯先对贝特朗身处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背景作了较为清晰的论述。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所接触的信息与观念,从而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与塑造,贝特朗也不例外。贝特朗虽然受到了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但她并未完全按照社会规定的道路前行。
贝特朗生活在16世纪的法国乡村,这是一个实行严苛父权制度的社会。女性很难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者说没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利。
何谓父权制度?美国女性史研究先驱格尔达·勒纳(Gerda Levda)认为:“父权制是男性在家庭中对女性和儿童的支配地位的表现和制度化,以及男性在整个社会中对女性的支配地位的延伸。”[1]促使父权成为一个体系并助长竞争、侵略和压迫的是控制与恐惧之间的动态关系。父权体制鼓励男性追求安全感、地位和其他通过控制所得来的奖赏。掌控权被特别强调,因为父权制度坚信拥有掌控权便可以避免损失与羞辱,亦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与欲望。在这样的背景下,控制者将自己视为主体,而将其他人视为客体。被控制者便是客体,他们被拥有掌控权的人视作不具有完整性与复杂性的人。[2]
在贝特朗所生活的乡村中,女性处于被支配地位,是被控制的客体。从女性的婚姻便可以想见其被支配地位的具体表现。她们的婚姻自由并不掌握在她们自己手中,结婚与离婚的选择权皆由她们的长辈掌握。女性的婚姻更像是一桩交易——一桩父亲与其丈夫之间的交易[3],女性自身的意愿并不被考虑,女性的主体性被忽视。贝特朗的婚姻亦是如此,她被父亲安排结婚时的年龄相当小,只有十几岁,甚至还不符合当时教会的规定。[4]后来因为马丁的身体原因,无法绵延子嗣,贝特朗的家人便想要解除这段没有结果的婚姻,可见贝特朗的离婚自由也不完全由她自己决定。贝特朗的再婚自由权同样受到了社会的干涉,当时的教会规定,若丈夫不在场或无法提供丈夫死亡的证据,妻子都没有再婚的自由。[5]女性的名字也体现了其被支配地位。在16世纪的阿尔蒂加及其周边地区,女性的名字中常常出现虚词“de”,这并非为了效仿贵族取名的方法,而是为了表达村落的分类系统,体现女性同父亲的附属关系。例如,贝特朗的父亲名叫罗尔斯(Rols),而贝特朗唤作“德罗尔斯”(de Rols)。[6]她的名字代表女儿是父亲的附属,受父权的管制与束缚。女性工作的自由权也被父权制度吞噬,女性从小便跟随母亲学习织布、女红,长大后或是被送去服侍其他人家,或是在自己家中帮忙做家务直至出嫁。[7]女性对财产的使用权在阿尔蒂加同样受到了父权制度的干预,女性对丈夫财产的享用权与丈夫的态度和决策息息相关。若是妻子不能与丈夫的继承人和平相处,那么丈夫会为她制订详细的供给计划。[8]
法国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对16世纪法国女性的处境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法典拒绝给予她接近‘男性’地位的权利,完全剥夺了她的公民资格,使她未婚时受父亲的监护。若后来没有结婚,父亲就会把她送进修女院;若结婚,她、她的财产和子女就会完全被置于丈夫的权威之下。丈夫被认为应当对她的债务和品行负责,她和政府当局及外人几乎没有直接关系。”[9]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任何有关妇女或女性的事情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10]
深受女性主义影响的美国学者亚伦·强森(Allan Johnson)也认可父权制体现在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上。除此之外,他还对父权体制的定义作出了补充:“一个社会是父权的,就是它有某种程度的男性支配(male-dominated)、认同男性(male-identified)和男性中心(male-centered)。”[11]对于男性支配这一点,强森不仅仅论述了男性对于女性选择与行为的支配,还对男性对于权力的支配与掌控作出了强调。他认为男性支配并决定了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这种权力差异在《马丁·盖尔归来》中体现在继承权的归属与参加议事会的权力上,二者在一般情况下都属于男性。莱兹河两岸的继承人总是男性,除非这户人家“不幸”到只有女儿。村中的执政官只召集男性村民参加议事,只有在发布命令时才会召集妻子与寡妇们。这就意味着女性没有发声的机会与权利,女性被排除在权利之外,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戴维斯认为,成年女性的世界几乎所有的组织结构都与男性有着密切的关系。[12]这样的社会文化逐渐被人们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人类学专家王明珂对此类现象也作出了重要论述:“社会透过‘文化’而制度化的将女性排除在这些表征体系中……强化女性的社会边缘性。”[13]女性成为“他者”,而男性是主体。
父权制度的核心是对女性的压迫。[14]在这样的制度下,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名字、婚姻、生育、工作都没有掌控的权利。在一些学者看来,产生这种压迫的父权制度源于劳动分工。男女在生物学上的差异是早期性别分工的基础[15],勒纳也认同这一观点,为了生存,男性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与压力,成为主要生产者。[16]除此之外,勒纳还认为女性的性取向与独特的生理构造使得她们容易被男性控制,女性的性能力与生殖能力被商品化,实际上处于不利地位。[17]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力量常被低估,但实则不然。女性在田间与家庭生活中承担了极其重要的责任。她们与丈夫一道承租、耕种、剪羊毛、照顾牲畜[18],在维系家庭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女性几乎一辈子都困在田间劳作与家庭生活中,于是家务劳动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女性的义务,女性像是农事与家务劳动的“奴隶”。[19]贝特朗面对的便是这样的境遇——作为一名女性,她一生都被农事与家务劳动所包围。
贝特朗便是在这样严苛的父权制度下长大成人的。年幼时的她无法选择自己的名字与婚姻,因此她选择了顺从。后来,尽管没有表现出明显地脱离这一社会的意图,但她逐渐走上了寻求自身主体意识的道路。
二、贝特朗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历程
随着年龄的增长,贝特朗不愿再继续顺从父权社会对她的限制与规范,她逐渐偏离了当时社会规定的女性发展道路,并努力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符合自身利益的道路。贝特朗的女性权利意识在慢慢觉醒。她逐渐意识到为自己争取更多自身权益的重要性,她对个人的独立性与尊严越发重视,不愿再依附于父亲与丈夫,不愿再继续当父权制度的奴隶。贝特朗尝试以自己的方式温和而坚定地突破父权制度的限制,同时争取个人利益,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贝特朗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对父权制度的反抗从掌握自己的婚姻开始。她拒绝了亲人让她离开马丁的要求,对自己身为女性的名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她知道贞洁的名声可以赢得旁人的尊重。当然,贝特朗反抗的原因不止于此,她对父权制度下普通女性的境遇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她知道若是她同意离婚,她的父母便会立即给她安排另一桩婚事,她便无法从妻子的某些职责中解脱出来。在16世纪的法国乡村,绵延子嗣、传宗接代被视为一件很重要的事,但贝特朗不愿意被这些社会规定的规范所束缚。因此,不与阳痿的马丁离婚对她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贝特朗是一位现实主义者。
在马丁出走后,贝特朗因为无法证明丈夫的死亡而不能再婚。但贝特朗并没有逃避法律再婚的打算,尽管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乡村并不罕见。理性的贝特朗通过权衡利益,选择了一条最切实可行的道路——与小儿子桑克西培养好关系,让儿子继承财产,并努力维持好自己恪守妇道的名声,体面地生活。[20]这是贝特朗自我意识觉醒并不断增强的体现。她的选择与做法都体现了其作为一个女性的独立人格。她在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找寻一块父权制度下的“自由空间”。[21]从某种程度上讲,戴维斯所著的《马丁·盖尔归来》讲述的是贝特朗的“回归”,即从男性的附属物到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的回归。[22]
贝特朗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进程中,假马丁的到来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对于贝特朗是否知晓马丁的真假这一点,戴维斯提出了一个与前人全然不同的观点,即认为贝特朗是知情的,且她是假马丁阿诺的同谋。在戴维斯看来,贝特朗之所以不揭穿假马丁的身份,是因为她逐渐爱上了这个男人。从表面上看,贝特朗的决定似乎只是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但其实这是贝特朗勇于突破父权制度带来的束缚,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表现。
这桩不为世俗所容的婚姻终究使贝特朗产生了罪恶感与愧疚感。为了减轻负罪感,
她将这桩婚姻想象成由他们自主缔结的事件,并援引当时教会法的规定作为佐证。从12世纪末到1564年,根据教会法的规定,婚姻的成立产生于配偶双方的同意,而且也仅仅需要缔结双方的同意,并不需要别人的见证等仪式。但教会并不提倡这种方式。[23]
此外,贝特朗还选择从新教中寻找慰藉与希望,因为新教允许信徒直接将心中的故事告诉上帝,而不必通过其他中介。1545年,加尔文宗教改革后的日内瓦制定了新的婚姻法,即妻子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被丈夫遗弃,在经过一年审查后,便可从宗教法庭得到离婚的许可,并允许再婚。[24]这就意味着贝特朗与假马丁的婚姻是可以得到认可的。
贝特朗挪用了这些有利于她消除心中罪恶感与愧疚感的观念,为她的选择与行为寻找依据。作为一个在父权制度中长大成人的女性,她从小被各种各样对女性的要求束缚。贝特朗能够这般“离经叛道”,已然是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结果。尽管她自小生活在父权社会中,受到种种规定的影响,从而产生些许负罪感,但她仍旧坚定地为自己想要的生活付出努力、寻找解决方法。
在控诉假马丁冒名顶替的场景中,知道真相的贝特朗并没有因为对假马丁的爱而盲目地拒绝控告那位骗子,因为她需要为自己的名声与子嗣考虑,但她同时也盘算着与假马丁商量好证词输掉这场官司。[25]这位理性聪明的女性在努力做到两全其美。她并没有因为爱而让自己再次陷入父权的牢笼中——牺牲自己的利益而维护丈夫的利益。贝特朗在女性权利意识觉醒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审判假马丁的过程中,贝特朗的理性与聪明才智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那时,贝特朗处境艰难,她一边面临着被假马丁怀疑的挑战,一边面临着可能受到通奸指控的困境,她必须小心谨慎行事。只有这样,假马丁的证词才不会露出破绽。
此外,贝特朗善于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因为女性意识的觉醒,贝特朗对公众所认同的、遵守的性别秩序十分熟悉,她选择利用这种“共识”——女性是容易上当受骗的,为自己开脱。[26]在审判中,法官科拉斯一直没有对贝特朗产生怀疑,坚信贝特朗是无辜的。
波伏娃认为,在所有的父权社会中,男人总是作为主要者和绝对的主体存在,而女人却总作为客体和他者存在。[27]因此,女性总是被当作男性的辅助品。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总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是被支配的、弱小的、愚笨的从属者。[28]在父权社会中,人们总是习惯认同男性。这种习惯的核心便是将所有美好的品质都附加在男性身上,女性被当作是对照物,因此女性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正像法官科拉斯在审判这个案件时对贝特朗的行为所解释的那样,“因‘她性别的弱点,轻易地被奸诈狡猾之徒欺骗’变得可以理解”[29]。贝特朗身为女性,被当作是愚笨的、容易上当受骗的、弱小的,这是生活在16世纪的科拉斯受父权社会环境影响的体现,他想要借此传递森严的性别秩序与父权观念,这并不奇怪。而贝特朗利用这种对女性的偏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脱罪空间,从而保护了自己,这不失为一种女权意识的体现。
如此,贝特朗成功让法官以为自己是被欺骗的。她一直以来为自己塑造的形象与表现的态度对法官的判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之前的日子里,贝特朗一边“循规蹈矩”,一边竭尽所能地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为她的成功脱罪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对图卢兹的审判中,法官科拉斯考虑到这个女子一直以来都恪守妇道,曾坚决反对她的继父与母亲控告假马丁的决定,并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免受伤害。即使她后来同意控告自己的丈夫,贝特朗也一直表现出不确定与紧张的神色,法官遂认为或许她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才提出了错误的诉讼。[30]于是,贝特朗成了一个被狡诈之徒欺骗的无辜女子,她成功洗清了包庇假马丁与通奸的嫌疑。
三、结语
从反对离婚到坚持等候马丁归来,从接受假马丁到经营与假马丁的婚姻,从反对控告假马丁到在法庭上想尽办法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贝特朗总能在父权社会的束缚与争取自身利益中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她用自己的方式与16世纪法国乡村严苛的父权制度进行持之以恒的斗争,其独立自主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强。在一次又一次的抉择中,贝特朗的女性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并增强。
参考文献
[1][16][17]Gerda Lerner.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239,40,214-215.
[2][11][14][美]亚伦·强森.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M].成令方,王秀云,游美惠,等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08:56,22-23,33.
[3][22]张强.性别表演视域下历史的重构——《马丁·盖尔归来》中女性身份的重塑[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90-94.
[4][5][6][7][8][12][18][20][23][24][25][26][29][30][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M].刘永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23:25-26,46,41,39,43,41,41,46,61-62,65,77,85,132,98.
[9][27][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18,11.
[10][美]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M].程志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7.
[13][19]王明珂.毒药猫理论——恐惧与暴力的社会根源[M].修订版.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85,77.
[15]Gail Omvedt.The Origin of Patriarchy[J].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87(44):70-72.
[21]王守梅.《马丁·盖尔归来》中贝特朗女权意识的透析[J].新西部(理论版),2016(12):96,94.
[28]梁艳春.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新文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10(3):27-37,158.